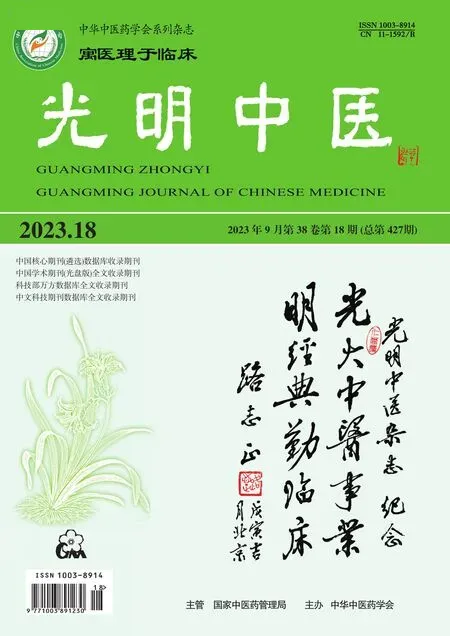扎跳類針法研究現狀
鄭倩茹 王鐵云
得氣是指針刺過程中毫針與經氣相得,又稱氣至,現代又稱針感或針刺感應。得氣是針灸取效的關鍵,因此判斷是否得氣至關重要。得氣的指征一是患者主觀的感覺和反應,一是醫者手下的感覺,患者的主觀感受包括酸、麻、脹、重、涼、熱、觸電感、跳躍感、蟻走感、氣流感、水波感和不自主的肢體活動等,醫者手下的感覺包括如魚吞鉤的手感,可感到肌肉由松弛變緊張,有的還會感到肌肉的跳躍或蠕動[1]。現代臨床有研究者將這種針刺后肢體不自主的活動或肌肉的跳躍蠕動作為得氣的客觀評價指標,認為相較于酸、麻、脹、重等主觀描述性針感,這一類跳動性針感更具客觀性,有利于臨床研究的量化與評價。筆者將引發跳動性針感的針法統稱為扎跳類針法,本文將從針法特點、機制及運用現狀等幾個方面對目前國內臨床常見的扎跳類針法進行概述。
1 扎跳類針法概述
1.1 王岱——跳動穴王岱教授是最早提出并在文獻記載“跳動穴”概念的針灸大師[2]。王氏“跳動穴”[3]是指針刺得氣后在一定手法的配合下,能使肢體跳動或肌肉抽動的穴位,對治療急性痛癥,以及神經、肌肉運動功能障礙類疾病具有較好的療效。“跳動穴”的針刺手法可概括為“按、找、中”三步,“按”用左手固定穴位,做下針準備;“找”由左右手配合,用提插手法,在穴位所在的經脈垂直面做扇形尋找,直至肌肉跳動或抽動為止;“中”是在運動反應之后將針固定在一定深度,保持針感不丟失。每一步都強調左手與右手的緊密配合。王岱教授認為提高“跳動穴”的刺中率,關鍵在于所刺穴位下有沒有軀體傳出神經纖維這個物質基礎。《靈樞·刺節真邪》[4]云:“用針之類,在于調氣”,王岱教授認為調氣的前提是得氣,針下運動引發的肌肉跳動或抽動也是一種得氣的表現,應該受到重視。王岱教授的“跳動穴”是從腧穴的角度總結了容易被扎跳的穴位,并認為此類腧穴扎跳的原因是針刺部位位于軀體傳出神經纖維附近,主要用于治療急性痛癥及神經、肌肉運動功能障礙類疾病。王曉紅[5]認為“跳動穴”是通過刺激或影響穴區特定的運動神經纖維,通過以“動”治“靜”而達到治療肢體運動功能障礙的目的。應有技[6]認為“跳動穴”位于肢體重要的神經干上,中風是因為上運動神經元受損,而支配肌肉的下運動神經元是正常的,所以針刺“跳動穴”產生強烈的肌肉跳動或肢體抽動,使癱瘓的肌肉產生自主性收縮,起到防止肌肉萎縮的作用,反復刺激,可將針刺信息輸入中樞神經,興奮腦細胞,幫助恢復和重建反射弧。鄭萍[7]發現電針“跳動穴”可顯著地提高中風患者患側肢體的肌力,從而改善患側肢體功能。
1.2 石學敏——醒腦開竅針法“醒腦開竅”針法是石學敏院士針對中風的基本病機“瘀血、肝風、痰濁”提出“以醒腦開竅、滋補肝腎為主,疏通經絡為輔”的治療大法,該針法具有特定腧穴的有序組合、特定的手法量學標準及處方的規范化加減3個基本操作規范,分為“主方I”“主方II”2種臨床方法,其中涉及到扎跳類針法的操作有:刺三陰交,沿脛骨內側緣與皮膚呈45°斜刺,進針1~1.5寸,用提插補法,使患側下肢抽動3次為度;刺極泉,原穴沿經下移1寸,避開腋毛,直刺1~1.5寸,用提插瀉法,以患側上肢抽動3次為度;尺澤,屈肘120°,針刺1寸,用提插瀉法,使患者前臂、手指抽動3次為度;委中,直腿抬高取穴,直刺0.5~1寸,提插瀉法,使患側下肢抽動3次為度;合谷,針向三間,進針1~1.5寸,采用提插瀉法,使患者抽動或五指自然伸展為度[8]。石學敏院士的“醒腦開竅”針法是具有完善的操作規范、量學標準及腧穴組合的針灸治療方案,而采用特定的針刺角度、進針深度、提插手法引發肢體抽動的操作只是“醒腦開竅”針法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改善中風患者肢體功能障礙。如張旭龍等[9]總結“醒腦開竅”針法對腦卒中后睡眠障礙、抑郁、血管性癡呆、吞咽障礙、便秘、呃逆等癥狀有確切療效。許軍峰等[10]總結“醒腦開竅”針法治療中風的機制,認為“醒腦開竅”針法對血流變學、血脂、微循環、腦電生理、心功能具有正向的改善作用。左曜瑋[11]通過臨床對照試驗發現“醒腦開竅”針法聯合新Bobath療法在改善腦卒中后下肢痙攣性癱瘓患者的痙攣程度、患肢運動功能的靈活性、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優于對照組。
1.3 陸飚——扎跳法陸飚教授的“扎跳法”是指在針刺過程中,從外部可以觀察到的針刺部位的肌肉跳動、產生局部收縮的現象。陸飚教授認為扎跳時,醫患雙方均可直接感受到肌肉的跳動變化,故將這種扎跳現象視為肉眼可見的針刺得氣的客觀評定標準,提出按照局部解剖位置的肌肉走向進行尋氣的手法和守氣手法,總結為“按、找、守”三步:“按”是指用左手固定穴位并向下按壓,起到定位、減少進針疼痛、激發經氣的作用;“找”需要左右手相互配合,通過快速提插,順著肌肉紋理尋著肌肉間隙做扇形尋找,直到出現相應肌肉的跳動或抽動,一旦扎跳立即停止進針;“守”即守氣,是指得氣后固定針的角度、深度及方向,左右手配合,行小幅度捻轉平補平瀉手法維持針感[12]。陸飚教授的“扎跳法”從操作手法上看與王岱教授的“跳動穴”類似,通過提插類手法誘發目標肌肉的跳動為目的。劉征等[13]對比了“扎跳”血海、足三里配合電針治療原發性不安腿綜合征與常規頭針、體針的臨床療效,發現“扎跳”加電針組總療效明顯優于常規針刺組;孫云霞等[14]對比肩井“扎跳”與傳統針刺法治療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發現“扎跳”組可進一步改善臨床療效,改善臨床癥狀及影像學結果,且有助于調節性激素水平,下調血清生長因子的表達;詹天宇等[15]治療頸椎病采用頭后大直肌及頭下斜肌、胸鎖乳突肌及頭夾肌2組肌肉以壓痛點為穴位采用“扎跳”的手法,“扎跳”后不留針,在縮短治療時間的同時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熊建平等[16]對比了對側三角肌“扎跳”與傳統針灸方案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發現“扎跳組”的療效顯著高于對照組,且具有取穴少、減輕患者痛苦、節省耗材的優勢,值得進一步推廣。
1.4 干針療法干針療法是不注射任何藥液,使用實心或空心針具,刺入身體的肌肉筋膜組織,達到緩解疼痛的物理療法,主要流行于西方國家。干針療法操作的關鍵是要引發肌肉的收縮反應,并在肌肉收縮或抽動后立即出針,一般不留針或僅停留短時間后拔除,如未起到緩解疼痛的作用,則重復2~3次操作。干針的治療靶點是激痛點,激痛點多位于肌腹中央、肌肉附著骨骼處或肌肉與肌腱交界處,所以干針主要治療肌肉骨骼和肌筋膜疾病,近年來逐漸擴展到神經系統疾病[17]。干針療法在理論依據、治療靶點、操作手法等方面與傳統針灸仍存在爭議,其誘發的肌肉抽動就與傳統針刺得氣中的跳躍感十分類似,如彭增福等[18]認為干針療法是傳統針灸現代發展的一種表現,屬于針灸學的一部分。干針與傳統針灸的關系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但是筆者認為爭議的存在推動了國內研究者聚焦中醫學的研究,激發了國人挖掘針灸經典內涵的使命感與決心,具有正面的價值和意義。近年來,干針療法在國內也被廣泛使用,羅登攀等[19]發現干針療法相較于常規電針療法對頸肩肌筋膜疼痛綜合征患者的療效較好,可有效減輕疼痛、腫脹程度,提高頸椎活動度;肖毅等[20]發現在常規藥物治療的基礎上予以干針療法,可增加患者血清睪酮水平及陰莖血流速度,提高總有效率,且安全可靠,有利于患者生活質量的提高。
1.5 其他扎跳類針法
1.5.1 筋膜瘢痕針刺松解療法該療法是劉寶庫老師個人經驗的總結。劉氏以中醫經筋為生理基礎,認為經筋勞傷虛損,氣滯血瘀,日久會形成瘢痕組織,可存在于全身各部,故以這些瘢痕組織作為腧穴,采用多針刺法,通過扎跳、松解手法,起到松解肌筋膜、緩解疼痛的目的。如臀中肌筋膜損傷運用“雙針平行針刺法”,梨狀肌損傷運用“三針平行針刺法”,斜方肌筋膜瘢痕組織采用“四針平行針刺法”,臀大肌肌痙攣或勞損采用“五針平行針刺法”[21]。
1.5.2 調橫針灸張文勇老師的調橫針灸,近年來受到國內針灸從業者的追捧,調橫針灸是通過望診了解人體形態結構的失衡,確定目標肌肉,要求將目標肌肉扎跳,從而緩解肌肉痙攣,調節肌肉張力,改善體態,達到治療目的。此外,還有一些針法不刻意追求跳動性針感,但是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常常會出現此類針感。如原山西中醫學院李濟春教授的“乾坤針法”[22],關玲老師在《結構針灸刺法經驗》[23]中提到李濟春教授施針,用2根針“對氣”,“氣對上”后中間的大肌肉開始像波浪一樣起伏,節律和緩,此處大肌肉的起伏就是跳動性針感;國醫大師程莘農教授的“三才針法”中的震顫催氣法[24],將高頻的提插與捻轉相結合,做小幅度快速的提插捻轉略加震顫,可使一次得氣率達到80%以上[25],筆者在臨床使用 “震顫催氣法”時就常常會引發針刺局部肌肉的跳動;鄭魁山教授的“溫通針法”,是通過一定的針刺手法使所刺穴位產生溫熱感并傳導至病處,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26],該針法重視左手,強調“氣至沖動”,在行針過程中要求左手隨時感應針下的經氣活動[27],在臨床研究中,有一些研究者認為鄭氏強調的 “氣至沖動”就是跳動類針感的一種描述[15,16]。
2 理論探討
2.1 古代文獻研究扎跳在古代文獻中并無明確記載,現代研究多從論述針刺得氣相關古籍入手。古代關于得氣的相關描述浩如煙海,《針灸大成》[28]中明言:“寧失其時,勿失其氣”,從古至今,針刺調氣是根本,而調氣的前提是氣至,關于“氣至”的論述,《靈樞·九針十二原》[4]記載:“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針……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標幽賦》云:“氣速至而速效,氣遲至而不治”,可見得氣是取得療效的關鍵。對“得氣”的記載,從醫者的角度,《靈樞·九針十二原》[4]有:“孔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指出醫者手下的感覺難以把握;《靈樞·終始》[4]云:“邪氣來也緊而疾,谷氣來也徐而和”,描述邪氣和正氣來時醫者手下針感的不同;《素問·寶命全形論》[29]中記載:“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徒見其飛,不知其誰”,形容得氣的感覺如空中飛鳥的來往,忽聚忽散,難以捉摸。《標幽賦》中記載:“輕滑慢而未來,沉澀緊而已至,氣之至也,如魚吞鉤餌之沉浮;氣未至也,如閑處幽堂之深邃”,此句《針灸大成》[28]注解:“氣既至,則針有緊澀,似魚吞鉤,或沉或浮而動;其氣不來,針自輕滑,如閑居靜室之中,寂然無所聞也”。明確指出得氣與未得氣的差異。從患者角度,如《素問·針解》[29]云:“刺虛則實之者,針下熱也……滿而瀉之者,針下寒也”。其實古人在判斷得氣與否時也注重客觀指標的變化,如《靈樞·終始》[4]中記載:“所謂氣至而有效,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大如故而益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大如其故而不堅者,是雖言快,病未去也”,古人在針刺前后通過脈的變化來判斷氣至與否,而不僅僅以患者的感受做為評判標準。在針刺手法上,重視左右手的配合,如《靈樞·刺節真邪》[4]云:“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后取而下之”。指出針刺之前應先揣穴;《難經·七十八難》[30]云:“知為針者,信其左,不知為針者,信其右”,強調左右手的配合在針刺得氣過程中的重要性。
2.2 機制研究針刺得氣研究至今,逐漸發展出顯性得氣和隱性得氣的概念。隱性得氣是指針刺后患者未產生主觀感受和客觀可見的變化,但是病痛能消除的反應[31]。相對的,針刺后患者產生了主觀上酸麻脹重等感受或出現客觀可見的變化如局部皮膚紅暈、皮疹、肌肉跳動顫抖等現象就叫顯性得氣。跳動性針感就是一種顯性得氣的表現。有研究者認為顯性得氣可刺激受試者小腦和邊緣系統的負激活、引發腦電圖特異性θ波和α波變化,增加微循環血流灌注[32]。針灸得氣的物質基礎在于穴位區域豐富的感受器,包括游離神經末梢、肌梭、腱梭、環層小體、克氏終球等,針感的性質與刺激到的組織結構密切相關,如刺激到神經多引起麻感,針刺到血管多引起痛感,刺激到肌腱、骨膜多引起酸感,刺激到肌肉多引起酸脹感。有研究發現一些體表部位用最弱的電流刺激就能引發肌肉最大程度的收縮,故將這種刺激點稱為肌肉運動點,這些部位是體表神經末梢密集區,又稱神經終板部位[33],這可能就是跳動性針感出現的結構基礎。魏鵬緒[34]認為跳動性針感是針刺觸及了單個肌肉的“觸發點”引起的單個肌肉的收縮,這個“觸發點”就與肌肉運動點極為相似;肖文迅等[35]認為針刺得氣在局部會引發肌張力升高、肌電信號增強、放電次數增多及肌肉收縮力增強等;張琦等[36]指出針刺引起局部產生抽搐反應,肌纖維得以伸展,進而緩解毛細血管的受壓狀態,增加局部肌肉的含氧量,進而加速局部微循環的恢復,從而使得僵硬的肌肉得到松弛,疼痛及炎癥反應終止。總的來說,跳動性針感的出現與針刺部位的解剖結構、神經、肌肉的走形分部密切相關。
3 總結
扎跳類針法是通過一定的針刺手法引發肌肉或肢體的跳動達到疏通局部氣血、通絡止痛功效的一類針法。作為一名針灸臨床工作者,筆者認為扎跳類針法引發的跳動性針感是臨床常見的一種針刺現象,具有較強的可量化性和臨床實操性,可以作為得氣的客觀指標進一步研究,但是扎跳是否能作為針刺得氣的普遍適用指標,與療效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相關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