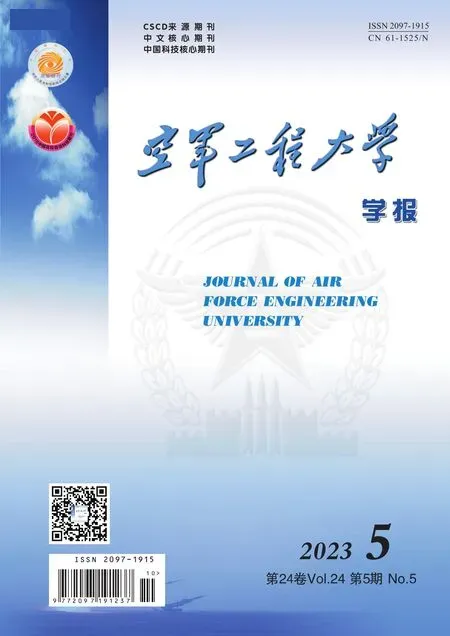空中進攻作戰安全返航通道容量評估
韓雪艷,沈 堤,余付平,霍 丹
(空軍工程大學空管領航學院,西安,710051)
軍民用航空中,無論是軍航作戰還是民航發展,在有限的空域資源內通過流量管理實現流量最大化,一直是國際學術研究的焦點[1-4]。由于軍航戰時與民航平時的運行方式、運行目的以及運行機型不同,盡管目前民航已有大量學者對航路容量展開研究[5-9],但針對軍航戰時特有返航方式下的返航通道容量研究目前較少。評估軍航戰時特有返航通道的容量,進而基于容量科學管理流量,是保障戰機安全、有序、高效完成作戰任務的重要基礎。
目前,國內外對容流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當前扇區運行方式,考慮扇區容量進行航路流量管理[5]。對扇區容量的研究是基于交通流運行特性展開的,研究分為兩類,第一類通過建立交通流模型進行研究,主要包括隊列模型、流體力學模型和微觀行為模型。第二類通過建立管制員模型進行研究,主要包括認知模型與計算模型[8]。在第一類交通流模型中,元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CA)作為微觀模型,是用來描述個體性格的模型,在交通流研究領域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10-12],文獻[13]最早將元胞自動機模型應用于空中交通流理論,以開發交通流性能和容量提升的新理念。隨后,文獻[14]基于歐拉方法建立二維元胞自動機模型,定義每個單元代表一個扇區,建立扇區進入規則進而對扇區容流進行分析。文獻[15] 在針對終端區運行效率的研究中,基于連續下降方法(CDA)提出元胞自動機模型,通過模型進行仿真,證明了在最小化目標交通流總延遲的情況下,能夠得到進近過程近似最優的流量。文獻[16]將安全間距引入元胞自動機模型,利用統計物理方法研究了空中交通系統平衡,以期為空中交通管制提供決策。文獻[17]以機場飛機起飛時間為變量建立模型,通過元胞自動機研究微小起飛時間變化對流量影響,提出優化航班時刻表。文獻[18]利用元胞自動機對地面滑行、起飛以及著陸飛機進行建模,進而對進場運行效率進行定量分析,以此預測空中交通。可以看到,隨著空中交通管理新技術的提出,研究者們開始聚焦于個體航空器,CA模型因其具有描述并記錄單個航空器運行特點的優勢,并且由于其固有的離散性,使得其具有高效仿真特點,近些年被廣泛應用于空中交通運行分析的各個階段。
綜上可以看出,基于CA模型對空中交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利用CA模型進行建模仿真,對運行結果進行評估以驗證所提模型的有效性。鮮有研究者從微觀角度,基于CA模型記錄個體航空器交通運行特性,針對航空器在不同管控措施下的交通運行特性展開流量管控研究;尤其是考慮戰時返航戰機在預設安全返航通道的運行特性,展開戰時戰機返航流量管控研究還處于空白階段。本文結合戰時,戰機通過安全返航通道返航的特點,針對安全返航的指定返航模式,從微觀角度進行安全返航通道的容量評估研究。通過建立返航通道節點合流動態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cellular automata model based on merge point regulation,MRCA)。對返航通道節點合流容量進行分析;并基于模型確定返航通道進入時間窗,將容流平衡調控的時間節點前移,強化網絡航跡管理能力,在戰略管理和預戰術管理中消解個體航空器在戰術運行中的潛在航跡沖突。
1 空中進攻作戰安全返航通道
空中進攻作戰安全返航通道用于戰時前出實施空中進攻作戰如空中遮斷、縱深打擊的航空器安全返航時使用。在戰機通過安全返航通道返航過程中,利用容流協同措施,并配合各類技術識別手段,可確保敵我識別的可靠性。安全返航通道包括最小風險通道(枚紅色通道)、低空穿越通道(藍色通道)和空中通道(黃色通道),設置如圖1所示。

圖1 返航通道劃設
如圖所示,返航戰機加入指定最小風險通道,在己方部隊前沿線進行敵我識別,利用最小風險通道飛行所獲取的傳感器位置信息與敵我識別器信息進行綜合識別,完成敵我識別后加入低空穿越通道,最后進入空中通道返回指定機場著陸。返航通道由最小風險通道、低空穿越通道和空中通道,根據戰場前沿打擊戰術以及返回我方空域敵我識別要求,返航戰機低高度加入返航通道,隨后高度依次增加,設置參數如表1所示。

表1 安全返航通道參數設置
戰時,通過開通指定高度層的指定通道,配合完成敵我識別,保證識別的可靠性。由圖1可知,返航通道是網絡結構,研究返航通道的容量需要考慮返航通道的構型以及運行具體方式。為便于開展研究,構建返航通道戰時的開通形式以及使用著陸機場如圖2所示。其中,最小風險通道開通4條;橫向低空穿越通道開通1條,縱向低空穿越通道開通3條,空中通道開通2條,供戰機由戰場前沿返回后方機場使用。具體飛行路線如圖2所示。

圖2 返航通道開通形式
根據圖2具體開通形式可以看出,研究返航通道容量,首先需研究空中通道1與空中通道2的容量,兩通道的容量決定了該開通形式下返航通道的總容量。其次由于戰機從最小風險通道1與最小風險通道2返航時,在橫向低空穿越通道的節點處存在合流情況如圖中黃色圈A;同時,從最小風險通道3與最小風險通道4返航時,在分別經過低空穿越通道2和低空穿越通道3后,向空中通道2返航時,在節點處亦存在合流情況如圖中黃色圈B。此時合流之后的通道容量制約合流前各通道的容量,合流前戰機在各通道的時空位置又決定了合流處是否存在碰撞風險,進而影響合流點處的合流行為。
因此,針對戰時特有返航通道布設,戰機在合流節點處的合流特性是制約節點前后通道流量的關鍵,研究返航通道容量主要應分析節點處的運行特性。下文通過建立模型,確保戰機在節點處滿足保持安全縱向間距以及橫向間距的同時,又能達到合流后實現通道的最大流量,進而分析節點交通運行特性,評估返航通道容量。
2 節點合流元胞自動機模型
為研究節點處的運行特性,考慮航空器性能,基于節點處縱向間隔以及橫向安全間隔要求,將安全間距量化到合流規則中,提出節點合流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cellular automata model based on merge point regulation,MRCA)。
2.1 節點合流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MRCA)理論
節點合流原則為進入最小風險通道入口的戰機盡量不減速,保證快速返航。對安全返航通道節點處合流理論進行分析,建立MRCA模型節點合流理論,如圖3所示。

(a) t時刻 (b) t+n時刻
圖中,戰機1號從最小風險通道2加入節點,以1號到達決策圓邊界作為開始速度調控的初始位置。當決策圓邊界出現1號,在目標合流航路搜索1號到達合流點處,前后相鄰兩戰機,如圖3(a)所示,即2號與3號,計算1號分別與前后戰機間距,當間距小于縱向間隔要求時,進行速度調整,使得1號在t+n時刻到達節點時,2號飛出安全圓,3號未到達安全圓,安全圓半徑為10 km,由此保證目標合流航道上前后機間距最小10 km,滿足前后機縱向間隔要求。同時1號機與2號機以及1號機與3號機斜距應滿足兩機橫向間隔要求。
2.1.1 縱向間隔約束
2.1.1.1 縱向間隔要求
目前根據飛行間隔規定,雷達管制條件下縱向間隔要求為:進近管制范圍內不得小于6 km,區域管制范圍內不得小于10 km。進攻作戰返航時距離著陸機場較遠,因此,返航通道內運行應依據區域管制要求,取前后機為10 km。
MRCA模型中決策圓半徑是理論的關鍵參數,即為1號是否能安全加入目標航路的初始判斷位置,為方便分析,以節點為原心建立坐標系,最小風險通道2為x軸,目標合流通道為y軸。為保證前后機有足夠的距離完成速度調整,順利在節點處完成合流,取決策圓半徑R=20 km。1號機坐標(R,0),2號機坐標(0,y2),3號機坐標(0,y3),則1號機能夠在合流點安全匯入需滿足的縱向間隔約束條件為:
t1=20 000/v1
(1)
L2=t1v2>y2+10 000
(2)
L3=t1v3>y3-10 000
(3)
式中:v1為1號機速度;v2為2號機速度;v3為3號機速度;t1為1號機到達節點時間;L2為t1時間內2號機的飛行距離;L3為t1時間內3號機的飛行距離。
2.1.1.2 基于縱向間隔約束的速度調控分析
根據1號機到達決策圓時,在y軸上與2號機與3號機的相對位置,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戰機1號距離戰機2號較近。
由表2得到速度調控具體為:當兩機間距為10 km時,1號、2號機均采用250 m/s的速度,可以在節點處完成合流;當兩機間距6~10 km時,1號速度為250 m/s,2號加速為300 m/s,可以保證在1號到達節點時,2號飛出安全圓;當兩機間距0~6 km時,1號減速為200 m/s,2號加速為300 m/s,可以保證在1號到達節點時,2號飛出安全圓。

表2 1號戰機與2號戰機間距分析表
2)戰機1號距離戰機3號較近。
由表3得到速度調控具體為:當兩機間距為10 km時,1號、3號機均采用250 m/s的速度,可以在節點處完成合流;當兩機間距7~10 km時,1號加速為300 m/s,3號速度為250 m/s,可以保證在1號到達節點時,3號到達安全圓邊界;當兩機間距4~7 km時,1號加速為300 m/s,3號減速為200 m/s,可以保證在1號到達節點時,3號到達安全圓邊界。當兩機間距≤4 km,如 3號戰機坐標為(0,23)時,1號到達節點時間為67 s,而3號到達安全圓時間為65 s,也就是說,3號機在1號機到達節點前到達安全圓,當1號機到達節點時,3號機與其間距小于10 km,因此在該情況下,無法通過調節兩機速度,保證安全合流,故此情況下1號機從其他通道加入。由于3號減速將對其與后機間距產生影響,同時為后文時間窗計算取整考慮,這里取最小間隔為5 km。

表3 1號戰機與3號戰機間距分析表
2.1.1.3 基于縱向間隔約束的最小風險通道進入間距分析
1)在1號機減速2號機加速的情況下,減速的1號機在到達節點時刻,3號機位置距離1號機間隔大于等于10 km,即:
得到:G>21 000
(5)
2)在1號機加速3號機減速的情況下,減速的3號機與其后方間隔大于10 km,即:
得到:G>23 000
(7)
3)在1號機加速的情況下,加速的1號機在到達節點時刻,2號機距離1號機間隔大于10 km,即:

(8)
得到:G>18 000
(9)
綜上所述,根據式(5)、式(7)與式(9),當從最小風險通道進入的兩機間距G介于20~23 km時,與前后機間距盡量保持等間距進入通道,避免出現速度調控;G大于23 km時,前后機間距在決策觸發時刻,1號機與3號機間距應大于等于5 km。
2.1.2 橫向間隔約束
2.1.2.1 橫向間隔要求
根據飛行間隔規定,返航通道內戰機依據區域管制要求,取橫向間隔為10 km。如圖4所示,即L≥10 km。

圖4 橫向間隔要求
由于1號機與3號機根據縱向間隔要求,在1號機到達節點時,3號機在安全圓之外,故兩機橫向間隔始終≥10 km。因此,僅需考慮1號機與2號機之間的橫向間隔約束。1號機能夠在合流點安全匯入的橫向間隔約束條件為:

(10)

(11)
2.1.2.2 基于橫向間隔約束的速度調控與進入間距分析
通過上文分析,橫向間隔僅需考慮1號機與2號機。基于表2速度調控,進一步分析橫向間隔對速度調控以及最小風險通道進入間距的要求。
由圖5可以看出,當兩機速度不發生調控時,兩機間距G大于15 km,可滿足橫向間隔要求,即L2>10 0002。

圖5 10 km≤G≤15 km,1號機與2號機速度均為250 km/h
由圖6可以看出,當兩機間距小于10 km時,盡管通過速度調控可以使兩機在節點滿足縱向間距10 km要求,但在2號機飛過節點后,與1號機橫向間距不能滿足橫向10 km要求,在圖6中即縱坐標滿足L2>10 0002。

圖6 G<10 km,1號機速度為250 km/h,2號機速度為300 km/h
2.1.3 節點合流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MRCA)速度與間隔要求
通過對縱向間距及橫向間距綜合分析,確定返航通道速度調控與間距要求如下:
1)同一最小風險通道戰機進入間距≥20 km;
2)在決策圓處,1號機與2號機在目標合流通道上間距應大于等于15 km,與后機間距大于等于5 km;
3)發生速度調控情況有以下兩種:
①1號機與3號機間距7~10 km,1號機加速;
②1號機與3號機間距5~7 km,1號機加速,3號機減速。
2.2 節點合流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MRCA)參數
對于合流節點模型參數具體如下:
1)模型更新采用開放邊界,在模型入口生成航空器,模型出口航空器加入下一航段,離開本模型;
2)元胞尺寸:長50 m;
3)模型長度:120 km;
4)模型寬度:3 cell;
5)時間步長:1 s;
6)不同機型速度:對不同機型巡航速度與最大速度統計分析,為實現可仿真性,規定返航戰斗機與轟炸機速度如下:在合流處,為避免前后機因不同機型速度不同,存在合流干擾,導致流量減小,綜合考慮戰斗機與轟炸機可達到的最大巡航速度,規定戰斗機與轟炸機巡航速度均為250 m/s(900 km/h),元胞速度為5 cell/s,加速速度達到300 m/s(1 080 km/h),元胞速度為6 cell/s,減速速度達到200 m/s(720 km/h),元胞速度為4 cell/s。
7)縱向間隔要求:10 km
8)橫向間隔要求:10 km
2.3 節點合流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MRCA)更新規則
基于理論分析,建立MRCA在節點處的調控技術,具體節點處更新規則如圖7所示。

圖7 MRCA模型更新流程圖
圖7中,當2號機、3號機在1號機到達節點處時,不能滿足位于安全圓之外時,觸發速度調控具體如圖8所示。

圖8 速度調控流程圖

圖9 時間窗模型
圖8中,基于上文對1號機到達決策圓時,在y軸上與2號機與3號機的兩種相對位置,速度調控為:①1號機與3號機間距7~10 km,1號機加速;②1號機與3號機間距5~7 km,1號機加速,3號機減速。
2.4 最小風險通道進入時間窗
1)最小風險通道1
記第一架戰機從最小風險通道1進入時刻為K,隨后戰機進入最小風險通道1時間T1為:

(12)
2)最小風險通道2
①最佳進入時間T2

(13)
ta1=K+
②允許進入時間窗T3
ta2=

(16)
③禁止進入時間窗T4
tf=
(18)
式中:G為進入最小風險通道前后機間距,v為巡航速度,L為向節點合流的兩相鄰最小風險通道之間,低空穿越通道長度;l1為最小風險通道長度;d為最小風險通道2長度減去最小風險通道1的長度;ta1為戰機最佳進入最小風險通道2的時間;ta2為戰機允許進入最小風險通道2的時間范圍;tf為戰機禁止進入最小風險通道2的時間范圍。
3 仿真結果與分析
節點容量與指揮員接受間隔以及各通道加入飛機時刻有關。根據2.4節中最小風險通道進入時間窗規定,在飛機允許進入時間窗范圍內,利用MRCA模型對不同進入間隔進行仿真,同時要求當由最小風險通道加入的戰機到達決策圓處時,間隔滿足2.1.3節中模型規定,進而分析節點合流后通道的容量。
3.1 節點容量仿真分析
3.1.1 節點容量
由上文分析可知,目標合流通道戰機的最小間距為:1號機與前機2號機在決策圓處最小間距為15 km,與后機3號機最小間距為5 km。在該情況下,通過MRCA模型調控,可使得1號機到達節點處時,與前機2號機縱向間隔為10 km,與后機3號機縱向間隔為10 km,即目標合流通道在合流點后間距最小為10 km。同時,考慮戰時高效返航,前后機間隔控制不應過大。本文設定指揮員接受間隔為10~100 km,則從最小返航通道加入的戰機前后間距應為20~200 km,此時,兩最小返航通道戰機在合流點處匯合后,間距可達到10~100 km。利用MRCA模型進行仿真,得到不同間隔下節點最大流量,如表4所示。

表4 節點合流后航段最大流量
由表4可以看出,隨著間距的減小,節點的流量增大,但對最小風險通道加入戰機在決策圓處的前后機間隔有要求,即需滿足2.1.3模型規定間距要求。表4中的最大流量則為節點容量。
3.1.2 MRCA模型下節點容量的不變性
節點流量除考慮間距,還需考慮戰機加入返航通道的時間,時間不同,戰機到達節點的時刻情況不同,產生沖突情況就不同,調節情況隨之發生變化。但只要進入最小風險通道的戰機在決策圓處滿足2.1.3節中模型規定,通過MRCA模型的速度調控,可使戰機在節點處順利合流,保證不降低節點的流量。
以前后機間隔30 km進入最小風險通道為例,說明通過MRCA模型的速度調控保證不降低節點流量。以30 km進入間距為例,是由于30 km進入間距在進入間距安排合理的情況下會出現MRCA模型的兩種調控方案。當進入間距過小或過大時,MRCA調控情況可能僅出現一種,無法通過對比說明MRCA模型的速度調控能夠保證不降低節點流量。如當間距為20 km時,根據2.1.3節間距規定,MRCA模型的速度調控,在圖8中僅為情況2;當間距過大時,進入間距安排合理情況下,則可能在圖8中僅為情況1,或者無需調控。故在此以30 km進入間距為例說明通過MRCA模型的速度調控保證不降低節點流量。
1)與后機間隔為7~10 km(圖8中情況1)
基于2.4節最小風險通道進入時間窗規定,制定飛行計劃如下:
最小風險通道1:于00:00:00開始,以120 s間隔,于入口處加入;
最小風險通道2:于00:00:08開始,以120 s間隔,于入口處加入;
在決策圓處,1號機與前2號機間隔22 km,與后3號機間隔8 km。
通過仿真得到1小時內低空穿越通道流量為56架/h。時空圖與速度圖如圖10所示。

(a)時空圖 (b) 速度圖
由圖10(a)中可以看到,1號機的時空軌跡在A點處,斜率變小,即速度變大,同樣由圖10(b)可以看出,1號機運行速度由5 cell/s(250 m/s)加速為6 cell/s(300 m/s),說明在該飛行計劃中,1號機到達決策圓(坐標(20 000,0)),處時,對應于圖8中情況1與后方3號機間隔為7~10 km的情況。通過MRCA速度調控,在t1時刻,1號機到達節點匯入低空穿越通道時,1號機與前方2號機相距20 km,與后方3號機相距10 km,滿足縱向間隔要求。
2)與后機間隔為5~7 km(圖8中情況2)
基于2.4節最小風險通道進入時間窗規定,制定飛行計劃如下:
最小風險通道1:于00:00:00開始,以120 s間隔,于入口處加入;
最小風險通道2:于00:00:20開始,以120 s間隔,于入口處加入;
在決策圓處,1號機與前2號機間隔24 km,與后3號機間隔6 km。
通過仿真得到1h內低空穿越通道流量為56架/h。時空圖與速度圖如圖10所示。
由圖11(a)中可以看到,1號機的時空軌跡在A點處,斜率變小,即速度變大,同樣由圖11(b)可以看出,1號機運行速度由5 cell/s(250 m/s)加速為6 cell/s(300 m/s);同一時刻,由3號機在低空穿越通道的時空軌跡可以看出,3號機在B點處時空軌跡斜率變大,說明3號減速,具體可由圖11(b)看出,在B點處,運行速度由5 cell/s(250 m/s)減速為最低速度4 cell/s(200 m/s)。

(a)時空圖 (b) 速度圖
說明在該飛行計劃中,1號機到達決策圓(坐標(20 000,0))處時,對應于圖8中情況2與后方3號機間隔5~7 km的情況。在t1時刻,1號機到達節點匯入低空穿越通道時,1號機與前方2號機相距18 km,與后方3號機相距12 km,滿足縱向間隔要求。
綜上,盡管低空穿越通道進入時刻不同,通過MRCA模型調控,使得在節點處以縱向間距滿足最小10 km要求順利合流,合流后低空穿越通道流量均為56架/h,說明了MRCA模型的速度調控保證不降低節點流量。
3.2 結果討論
基于最小風險通道進入時間窗規定,制定飛行計劃,通過MRCA模型對節點合流特性進行仿真分析。結果表明,在安全間隔范圍內,節點合流后通道容量隨間隔減小而增大,最大達到102架/h;節點合流后空中通道的容量具體如表4所示。由于本文設定返航方式在空中通道處無交叉(圖2),當存在交叉時,根據合流后通道容量表4 以及合流前各通道連接戰場前沿戰術計劃,合理分配返航戰機流量。
4 結語
本文針對戰時特有的空中進攻作戰安全返航通道設置構型,提出最小風險通道最佳進入時間、允許進入時間窗以及禁止進入時間窗。建立節點合流調控元胞自動機模型,并基于模型對不同可接受間隔條件下節點后通道容量進行評估,通過MRCA模型保證在可進入時間窗范圍內實現流量最大。
研究得到的通道容量可用于確定不同通道開通條件下,最小返航通道返航戰機數量;最小風險通道進入時間窗可用于返航計劃制定的合理性評價。未來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展開戰機編隊返航時,空中進攻作戰安全返航通道的容量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