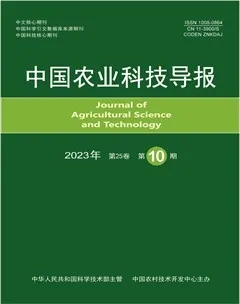滇西槽舌蘭內生真菌多樣性及其共生真菌對疊鞘石斛種子萌發的效應
李愛花, 王濤, 王苗苗, 鄧軍育, 劉佳, 亞吉東, 張毓
(1.國家植物園北園,植物遷地保護國家林業與草原局重點實驗室,北京市花卉園藝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北京100093; 2.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昆明 650201)
蘭科植物是被子植物的第二大科,由于生物多樣性喪失、人類過度采集等原因,許多蘭科植物生存狀況受到威脅,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旗艦”類群。植物內生真菌對植物的生長、適應性、進化及植物群落的結構和多樣性產生影響[1-3]。多數蘭科植物與真菌共生,其種子萌發和原球莖發育需要依賴共生真菌[4],且大多數蘭科植物在成年階段也會維持這種共生關系[5-6]。高度依賴于特異共生真菌的蘭花,往往會因為其潛在生境的可用性和分布限制,導致物種瀕危[7]。
滇西槽舌蘭[Holcoglossum rupestre(Hand.-Mazz.) Garay]是中國特有物種,僅發現2~3 個居群,位于金沙江干熱河谷地帶高山櫟樹上。由于工程建設、全球氣候變化、人為破壞等原因,滇西槽舌蘭所依存的高山櫟林正處在快速消失中,因此,目前滇西槽舌蘭被評為極度瀕危物種,并被列入國家極小種群植物名錄(2002 版)。如果沒有搶救性措施,滇西槽舌蘭有可能成為長江流域滅絕的蘭科植物[8]。因此,亟需對滇西槽舌蘭及其生態環境開展保護性研究。了解滇西槽舌蘭的內生真菌多樣性及其與蘭科植物的共生關系,可以為滇西槽舌蘭的物種瀕危原因提供理論參考,但相關研究較少。Tan等[9]對9個槽舌蘭屬物種進行了內生真菌的分離和鑒定,共鑒定得到46 株內生真菌,但是滇西槽舌蘭中僅鑒定得到5株,且均為非共生真菌。因此,有必要對已知分布地及栽培地滇西槽舌蘭的內生真菌進行分離和多樣性分析,并進行功能鑒定,為滇西槽舌蘭的保育及瀕危機制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材料
2021年5—6月,從云南香格里拉、楚雄、昆明盤龍、昆明呈貢4 個生長地收集健康、新鮮、粗壯滇西槽舌蘭植株的氣生根3~7段,用濕紙巾包裹,放到干凈的盒子內,快速運回實驗室。
1.2 試劑及儀器
采用PDA 培養基對內生真菌進行培養。配置方法如下:PDA 培養基粉末46.0 g,加入到1.0 L超純水中,于121 ℃高壓蒸汽滅菌20 min,制備固體PDA 培養基。18S rDNA 擴增所用試劑均購自TaKaRa 公司;PCR Purification Kit 購自Promega 公司;PCR 儀為Biometra 公司生產的Tgradient;凝膠成像分析儀為Bio-Rad公司的Gel-Doc2000。
1.3 試驗方法
1.3.1 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菌的分離 選用組織塊分離法分離內生真菌,流程如下:首先用自來水沖洗干凈根段,去除根表面泥土及附屬物,用吸水紙吸干水分;然后將根切成2~3 cm 的小段,用75%乙醇消毒30 s,無菌水沖洗1 次,5%(質量體積分數)NaClO 消毒5 min,無菌水沖洗3 次,吸干水分;最后用無菌雙面刀片將根段切成1~2 mm的薄片,放到PDA培養基中,每皿放置12小片,密封放置在25 ℃暗培養。及時觀察培養皿中菌絲生長狀態,待菌絲長出后用接種針挑取菌絲尖端轉接到新的PDA 培養基中進一步純化,待菌落無雜菌,生長均勻后,進行保藏和檢測。
1.3.2 內生真菌的鑒定 分離的共生真菌分別進行形態學鑒定[10]和分子鑒定。通過光學顯微鏡(Olimpus CX31)觀察內生真菌的菌絲形態,方法如下: 用透明膠帶粘取少量菌絲,置于涂有10%(質量體積分數)KOH 的載玻片上,觀察菌絲的直徑、分枝、念珠狀細胞、孢子、隔膜等特征。
采用通用菌類18S rDNA 鑒定方法[11]進行分子鑒定。樣品DNA 提取、PCR 擴增及測序均由北京博友順生物技術有限公司進行。引物為真菌通用引物組合ITS1/ITS4,由上海生工有限公司合成。PCR 體系包括:處理后的樣品(20 ng·μL-1)模板2 μL,dNTP Mixture (2.5 mmol·L-1) 2.5 μL,引物(20 μmol·L-1)各1.5 μL,10×ExTaqBuffer (Mg2+plus ) 5 μL,Ex Taq 酶(5U·μL-1)0.2 μL,ddH2O 補足到50 μL。PCR 程序:94 ℃ 3 min;94 ℃ 1 min,55 ℃ 1 min,72 ℃ 2 min,30 個循環;72 ℃ 5 min。PCR 產物經1.5%(質量體積分數)瓊脂糖檢測后,回收目的條帶,純化后,用擴增引物進行雙向測序。獲得的序列在GenBank 中進行BLAST 比對,查找相似性最高的序列信息,并結合菌株的形態學特征,以確定真菌種類。當所測菌株的ITS 序列與NCBI庫中片段相似性大于99%,則認為是同一物種;所測菌株ITS 序列與NCBI 庫中片段相似性大于95%,則認為是同一屬的物種;相似性小于95%,認為是未鑒定物種[12]。
1.3.3 膠膜菌對疊鞘石斛種子共生萌發的作用膠膜菌菌株P2、P24、P35、P47 用無菌打孔器打成直徑5 mm左右的圓片;將約八成成熟的疊鞘石斛果實滅菌后,接種到放有纖維網的固體燕麥培養基上,將菌株圓片放到播種的燕麥培養基上,每皿放4 塊;同時設置1 個陰性處理(僅燕麥培養基),1 個陽性對照(1/2MS 固體培養基)。每個處理重復5次。
1.4 數據統計與分析
通過Mega 11.0 軟件利用Kimura2-parameter模型進行系統分析。使用NJ(neighbour-joining)法[13-14]構建系統樹,Bootstrap 設置為500。用分離率(isolation frequency,IF)來衡量特定植物組織樣品中內生真菌的豐度以及植物組織樣品中多重侵染的頻率[14];內生真菌的多樣性通過香農多樣性指數(H)表示,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i=1……k,k指滇西槽舌蘭的第k個生長地,Pi指第i個生長地滇西槽舌蘭內生真菌個體數占總個體數比例。
2 結果與分析
2.1 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的分離
從滇西槽舌蘭根部分離得到94 個菌落,香格里拉、楚雄、呈貢、盤龍分別獲得22、12、8、52個(表1)。

表1 4個分布地/栽培地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分離結果Table 1 Isolation results of fungal isolates from roots of Holcoglossum rupestre in 4 localities
2.2 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的分子鑒定
分子鑒定結果(表2)顯示,從滇西槽舌蘭根部共鑒定內生真菌68 株,其中盤龍居群最多,為29 株;香格里拉和楚雄居群次之,分別為18 和12株;呈貢居群最少,為9株。68株內生真菌經初步分子生物學鑒定歸屬于18個屬。 其中27.94%屬于鐮刀菌屬(Fusarium);10.29%屬于間座殼屬(Diaporthe);8.82%屬于膠膜菌屬(Tulasnella);8.82%屬于角擔菌屬(Ceratobasidium);8.82%屬于交鏈孢屬(Alternaria)(表2)。鐮刀菌屬真菌在楚雄和呈貢居群的可培養內生真菌中均占50%以上,在香格里拉和盤龍居群中的占比也較高;膠膜菌屬真菌僅在盤龍居群分離得到,占比19.35%;角擔菌屬真菌僅在香格里拉居群分離得到,占比31.58%(圖1)。

圖1 不同地區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的相對豐度Fig. 1 Relative abundance of cultured endomycetes in root of Holcolglossum repestr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表2 不同地區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的種類及數量Table 2 Fungal taxon and amount in roots of Holcoglossum rupestr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香格里拉和盤龍居群可培養內生真菌的Shannon 多樣性指數較高,分別為2.93 和3.23,不同種群在不同屬間分布較均勻;楚雄和盤龍居群的Shannon 多樣性指數僅為1.38 和1.44,即分離的內生真菌種類少且分布不均勻,僅分布在3個屬。
系統聚類分析(圖2)表明,68 株內生真菌屬于2 門、3 綱、8 目、12 科(圖2)。其中有12 株內生真菌屬于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有56 株內生真菌屬于子囊菌門(Ascomycota)。在綱水平,分 別 屬 于 傘 菌 綱(Agaricomycetes)、座 囊 菌 綱(Dothideomycetes)和糞殼菌綱(Sordariomycetes)。屬于傘菌綱的12 個菌株中,菌株P2、P21 與美孢膠膜菌(Tulasnella calospora)序列的一致性較高,菌株P24、P35、P12、P49 與膠膜菌屬(Tulasnella)序列的一致性較高,因此將其鑒定為膠膜菌屬;菌株D4、D5、D6、D10、D13、D19 與 角 擔 菌 屬(Ceratobasidium)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因此將其鑒定為角擔菌屬真菌,這些菌株聚為1 支,屬于雞油菌目(Cantharellales)。

圖2 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的系統聚類樹Fig. 2 Phylogenetic tree of cultured endomycetes in root of Holcolglossum rupestre
在屬于糞殼菌綱的47 株內生菌中,除毛殼菌屬(Chaetomium)的菌株P17、P19 外,其他45 株內生菌被聚為4 個分支。其中,屬于鐮刀菌屬、木霉屬(Trichoderma)和生赤殼屬(Clonostachys)的23個菌株被聚為1 支(Ⅰ),屬于肉座菌目(Hypocreales);屬于炭角菌屬、Obolarina、炭墊菌屬(Nemania)、Biscogniauxia、擬 盤 多 毛 孢 屬(Pestalotiopsis) 和 新 擬 盤 多 毛 孢 屬(Neopestalotiopsis)的13 個菌株被聚為1 支(Ⅱ),屬于炭角菌目(Xylariales);菌株D2 單獨聚為1 支(Ⅲ),它屬于刺盤孢屬(Colletotrichum)、小叢殼目(Glomerellales);屬于間座殼屬和擬莖點霉屬(Phomopsis)的8 個菌株被聚為1 支(Ⅳ),屬于間座殼目(Diaporthales)。
屬于座囊菌綱的9 個菌株被聚為2 個分支。其中,菌株D12 和P29 被聚為1 支(Ⅰ),屬于新殼梭孢屬;屬于交鏈孢屬(Alternaria)和旋孢腔菌屬(Cochliobolus)的7 個菌株及屬于糞殼菌綱毛殼菌屬的P17、P19被聚在1支(Ⅱ)。
2.3 疊鞘石斛種子共生萌發的效應
膠膜菌P2 與疊鞘石斛種子的共生萌發試驗顯示, P2 對疊鞘石斛種子萌發有促進作用,即共生菌P2能夠促進疊鞘石斛種子萌發(圖3)。萌發60 d后,對照種子全部處于萌發第1階段(圖3C);與膠膜菌P2 共生的疊鞘石斛種子已長出生長點(圖3D),處于典型附生蘭種子萌發的第3階段[15];1/2MS 培養基上萌發的疊鞘石斛部分原球莖也長出生長點,但仍有少量種子僅吸水膨大,處于萌發的第1 階段(圖3E)。與P2 共生菌共生萌發處理的種子86.16%處于種子萌發第2 階段,13.84%處于種子萌發第3階段;對照大部分種子萌發至第2階段(84.09%),仍有15.01%種子胚處于第1 階段(圖3F)。綜上所述,膠膜菌菌株P2對疊鞘石斛種子萌發有顯著促進作用。

圖3 膠膜菌菌株P2與疊鞘石斛種子的共生萌發Fig. 3 Myco-germination of Dendrobium denneanum with mycorrhiza fungus P2
3 討論
本研究在4 個生長地的滇西槽舌蘭根內均分離得到多種內生真菌,且不同生長地分離得到的內生真菌存在差異,鐮刀菌屬、間座殼屬、膠膜菌屬、角擔菌屬、鏈格孢屬是占比較高的真菌類群;且不同分布地的內生真菌在屬水平也存在差異。其中,角擔菌屬、刺盤孢屬、生赤殼屬和旋孢腔菌屬為香格里拉居群的特有菌屬;膠膜菌屬、擬盤多毛孢屬、新擬盤多毛孢屬、炭角菌屬、炭墊菌屬、毛殼菌屬、擬莖點霉屬、Obolarina為盤龍居群的特有菌屬;而楚雄和呈貢居群未檢測到特有菌屬。這可能與居群所在地(栽培地)的環境有關,同時與采樣的廣度和強度也有關[16]。
對滇西槽舌蘭根部內生真菌進行ITS rDNA序列測定,鑒定其親緣關系發現,在門水平分離菌株分別屬于擔子菌門和子囊菌門2 大類;在目水平屬于雞油菌目、肉座菌目、炭角菌目、糞殼菌目、葡萄座腔菌目、格孢腔菌目、Glomerellales、間座殼目8 個目,這幾個目也是熱帶、亞熱帶附生蘭常見的內生真菌類群[11];在屬水平,間座殼屬、角擔菌屬、Biscogniauxia、擬盤多毛孢屬、木霉屬、新擬盤多毛孢屬、炭角菌屬、新殼梭孢屬、旋孢腔菌屬、炭墊菌屬、毛殼菌屬、Obolarina等內生菌屬,均為槽舌蘭屬植物首次報道的內生真菌類群。其中,蘭科典型的共生真菌膠膜菌屬、角擔菌屬為首次在滇西槽舌蘭中分離得到,且角擔菌屬還是首次在槽舌蘭屬植物中分離得到。膠膜菌屬中的無性態瘤菌根菌屬(Epulorhiza)曾 在 短 距 槽 舌 蘭(Holcoglossum flavescens)、舌唇槽舌蘭(Holcoglossum subulifolium)、維西槽舌蘭(Holcoglossum weixiense)、中華槽舌蘭(Holcoglossum sinicum)中分離得到[9]。
Tan 等[9]在9 個槽舌蘭屬物種中分離得到16個屬的內生真菌,其中赤殼屬(Cosmospora)、枝孢屬(Cladosporium)、擬隱孢殼屬(Cryptosporiopsis)、亞格孢殼屬(Didymella)、小球腔菌屬(Leptosphaeria)、蟻霉屬(Myrmecridium)、擬盾殼霉屬(Paraconiothyrium)、須殼孢屬(Pyrenochaeta)、Stephanonectria在本研究中未檢測到;而本研究分離得到的間座殼屬、角擔菌屬、擬盤多毛孢屬、木霉屬、新擬盤多毛孢屬、炭角菌屬、新殼梭孢屬、旋孢腔菌屬、炭墊菌屬、毛殼菌屬、Obolarina共12個屬的內生真菌在Tan 等[9]的研究中未檢測到。說明槽舌蘭屬植物的內生真菌具有較高的物種多樣性,且已分離得到的內生真菌與宿主間的專一性較低。
研究表明,植物組織狀態、水分、碳氮營養條件等均影響蘭科植物根際真菌多樣性[17-19]。本研究在香格里拉居群分離得到鐮孢菌屬、間座殼屬、角擔菌屬等共10個屬的菌株,而Tan等[9]于2011年在該地采集的滇西槽舌蘭中僅分離得到4 個菌屬。其中,僅鐮刀菌屬是2 個研究中都分離到的菌屬,且本研究中該居群分離得到較多前人未報道的菌株類群,包括蘭科典型的共生真菌角擔菌屬。這可能是因為蘭科植物內生真菌的多樣性會隨生長季節的變化而變化,從而滿足植株生長發育的營養需求[20]。
Jacquemyn 等[21]認為,親緣關系較近的蘭科物種中的共生真菌相似性較高,即蘭科植物與共生真菌間存在一定的專一性。附生蘭大多與膠膜菌科、角擔菌科、臘殼菌科等擔子菌門的真菌類群有較強的專一性[22-24]。在香格里拉的滇西槽舌蘭居群分離得到角擔菌屬、盤龍居群分離得到膠膜菌屬,這些是典型的蘭科共生真菌類群,而在Tan等[9]研究的滇西槽舌蘭中未分離到這類菌群。由此可見,滇西槽舌蘭內可培養共生真菌在屬水平上具有較低的物種專一性,這可能是由于蘭科根部共生真菌對生境具有較高敏感性,進一步表明光合自養型蘭科植物具有較低的內生真菌專一性[21]。
膠膜菌是典型的蘭科植物共生真菌,它們可顯著促進蘭科植物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25-26];分離自兜唇石斛(D. aphyllum)和硬葉蘭(Cymbidium mannii)的內生真菌能夠促進齒瓣石斛(D. devonianum)的種子萌發及圓球莖形成[27]。本研究發現,6 株膠膜菌中,有2 株(P2、P47)能夠顯著促進疊鞘石斛種子萌發,縮短疊鞘石斛種子的萌發時間,增加種子萌發的一致性,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是因為這2 株共生菌能夠提供疊鞘石斛種子萌發過程所需要的營養物質。滇西槽舌蘭中分離的共生菌能夠促進疊鞘石斛種子萌發,說明菌株P2 和P47 對宿主植物在種水平上不存在專一性,即宿主特異性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Hadley[28]關于蘭科植物與共生菌不存在專一性的觀點。關于蘭科植物與共生真菌之間的互作關系,一直以來是蘭科植物的研究熱點和爭論焦點。本研究發現,滇西槽舌蘭內生真菌的多樣性較高,且內生真菌的宿主植物具有廣泛性,由此表明,滇西槽舌蘭與內生真菌間的共生關系存在廣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