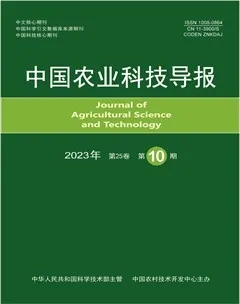土壤有效磷和磷形態對磷肥施用次數的響應
沈玉榮, 李然, 徐明崗, 周懷平, 劉平, 孫楠2
(1.山西農業大學生態環境產業技術研究院,土壤環境與養分資源山西省重點實驗室,太原 030031; 2.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農業農村部耕地質量監測與評價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1)
磷是作物生長必需的三大營養元素之一,施用磷肥是作物高產優質的主要措施。由于土壤對磷肥有強烈的固定作用,施用的磷肥75%~90%被土壤快速固定[1],從水溶性磷轉化為難溶性磷,導致磷肥利用率低。因此,研究磷肥施用方式對磷肥有效性的影響及其差異機制,對于降低磷肥固定率、提高磷肥利用率和磷肥合理施用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磷肥在土壤中的固定過程主要受施肥方式和土壤性質等的影響。土壤中磷素有效性與磷肥施用方式密切相關。耿玉輝等[2]研究表明,磷肥施用量150 kg·hm-2時,基肥施用 90%和種肥施用10%搭配最佳;磷肥若作追肥施用,在玉米抽雄期1 次重施效果最好。王靜[3]研究也發現,追施磷肥可顯著提高小麥盆栽土壤的有效磷(Olsen-P)含量。通過少量、多次、勤施的方式可以降低單位土地的磷含量,保持土壤始終處于較高的含水量,從而提高磷肥有效性。當土壤溶液中磷的含量較低時吸附固定是土壤對磷固定的主要方式,吸附固定的磷具有較高的活性,而當土壤溶液中磷的含量較高時吸附固定和化學固定同時作用,且以化學固定為主[4-5]。土壤性質主要影響土壤中磷素的有效性,如pH、Olsen-P、碳酸鈣含量等[4]。土壤Olsen-P 水平顯著影響水溶性磷肥的固定率。于淑芳等[6]研究發現,在土壤Olsen-P<70 mg·kg-1的石灰性土壤上,隨著土壤Olsen-P 水平的提高土壤固磷率顯著下降。土壤中各形態磷間的相互轉化也直接影響著土壤中磷素的有效性,液體磷肥以追施方式施入土壤后轉化為高活性磷形態的比例比基施方式提高了1 倍,液體磷肥以追施方式施入后轉化為穩定磷形態的比例比基施方式降低了32.6%[3]。
褐土是我國北方特別是山西的主要農田土壤類型,有機質含量低,碳酸鈣含量較高。目前關于磷肥1 次與分3 次施用對磷有效性和磷固定的影響研究,多集中于其他土壤類型上,在褐土上鮮見報道。雖然前人廣泛地研究了不同施肥方式和不同Olsen-P水平對磷肥有效性的影響,但對不同施肥措施下磷形態變化的研究較少。本文采集山西省3 種不同Olsen-P 水平的褐土進行培養試驗,分析磷肥1 次與分3 次施用的土壤Olsen-P 含量、固磷率和磷形態的變化特征,探討施肥次數對褐土磷有效性的影響及差異機制,為磷肥的高效利用和合理施用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供試土壤
供試土壤采集自山西省晉中市壽陽縣長期施肥試驗基地(37°58′23″N、113°06′38″E)。該基地海拔1 130 m,屬中緯度暖溫帶半濕潤偏旱區大陸性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季節溫差大,無霜期130 d 左右,年均氣溫7.4 ℃,年均降水量500 mm,年均蒸發量1 600~1 800 mm,成土母質為馬蘭黃土,土壤類型為典型褐土,常年種植作物為玉米,1年1 熟。2020 年4 月,多點采集長期不同施肥處理的耕層(0—20 cm)土壤樣品3個(P1、P2和P3分別代表3 個不同Olsen-P 水平的土壤),其土壤Olsen-P 含量差異顯著。土壤經風干、研碎、過篩備用。土壤基本理化性質見表1。

表1 供試土壤的基本性質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soils used
1.2 試驗設計
為模擬玉米生長,培養試驗設置90 d。稱取過2 mm篩的40 g土壤于培養瓶中,進行施肥和培養。每種土壤(P1、P2 和P3)設置3 種施肥處理:①不施磷肥(CK);②磷肥1 次施用(T1),施磷總量60 mg·kg-1,在第0 天全部基施;③磷肥分3次施用(T2),施磷總量與T1相同,分別在第0、30、60天施磷24 mg·kg-1(模擬基肥,占施肥總量40%)、18 mg·kg-1(模擬苗期追肥,占施肥總量30%)和18 mg·kg-1(模擬后期追肥,占施肥總量30%),每處理3 次重復。施肥后的培養瓶加水到田間持水量的70%左右,置于室內25 ℃恒溫培養90 d。培養過程中采用稱重法調節含水量,每隔3 d加1 次水至土壤含水量恒重。采用破壞性取樣方法,培養3 h、2 d、4 d、10 d、30 d、30 d+3 h、34 d、60 d、60 d+3 h、64 d、90 d 分別采集土壤測定其Olsen-P 含量。培養結束后,測定土壤磷形態。
1.3 測定項目與方法
1.3.1 供試土壤的基本性質測定 土壤有效磷采用鉬銻抗比色法測定,全磷(Total P)采用高氯酸-硫酸法測定,有機質采用外加熱-重鉻酸鉀容量法測定,土壤pH采用pH計測定,碳酸鈣采用氣量法測定[7]。
1.3.2 磷肥固定率的測定與固定動力學方程 磷肥在土壤中的固定指標及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y為不同培養時間下的固磷率(%);x為培養時間(d);Qmax(maximum phosphorus fixation rate)為最大固磷率;T為達到最大固磷率50%時的時間;α為初始固磷速率;β為固定速率常數。
1.3.3 各形態磷含量測定及轉化百分比計算 采用修正的Hedley 磷素分級方法測定各形態磷組分含量[8],該方法能通過連續浸提法得到9種不同形態的磷含量:①樹脂交換態磷(Resin-P),通過陰離子交換樹脂膜交換浸提出的磷,這部分磷是易被土壤吸附解析的無機磷;②0.5 mol·L-1NaHCO3(pH 8.5)提取出來的無機磷(NaHCO3-Pi)和有機磷(NaHCO3-Po),其對植物的有效性較高;③0.1 mol·L-1NaOH提取出來的無機磷(NaOH-Pi)和有機磷(NaOH-Po); ④1.0 mol·L-1HCl(稀HCl)提取出來的無機磷(Dil.HCl-Pi),比較穩定,主要與鈣結合;⑤12 mol·L-1HCl(濃HCl)提取出來的無機磷(Conc.HCl-Pi)和 有機磷(Conc.HCl-Po),穩定態磷,難以被植物利用;⑥濃H2SO4-H2O2消煮后得到的殘留磷(Residual-P),其很難被植物吸收利用。這9種形態根據其活性被劃分為3大類:活性磷(Resin-P、NaHCO3-Pi 和NaHCO3-Po)、中活性磷(NaOH-Pi、NaOH-Po、Dil.HCl-Pi)和穩定性磷(Conc.HCl-Pi、Conc.HCl-Po、Residual-P)[9]。該方法操作簡便、耗時短,適用于任何土壤類型,可以區分出有機磷和無機磷體系,便于驗證:測定出來的9 種磷形態含量相加原則上應該等于測定的全磷含量,但在實際過程中由于操作誤差,兩者數值相差在±10%范圍內表明數據可行。通過式(6)計算磷肥轉化為各形態磷的比例[3]。
式中,P表示肥料磷轉化為某一分級磷的比例;Px表示施磷肥處理某一分級磷在土壤中的含量,mg·kg-1;x 分別表示Resin-P、NaHCO3-P、NaOH-P、HCl-P 和Residue-P 這5 級磷;`Px表示不施肥處理某一分級磷在土壤中的含量,mg·kg-1;TPx表示施磷肥處理各級磷在土壤中的含量總和,mg·kg-1;`TPx表示不施肥處理各級磷在土壤中的含量總和,mg·kg-1。
1.4 數據處理分析方法
采 用Origin 2019、Microsoft Excel 2016 和SPSS 20.0 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及作圖,不同施肥處理之間的差異采用最小顯著差數法(LSD法)分析(P<0.05),試驗結果均為3 次重復的平均值和標準誤。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壤Olsen-P含量對施肥次數的響應
磷肥1 次施用下土壤Olsen-P 含量在培養前10 d 內隨著培養時間延長逐漸降低,之后趨于平緩(圖1)。在培養前30 d 內,分3 次施用下土壤Olsen-P 含量顯著低于1 次施用,之后顯著高于1 次施用。培養90 d 后,與CK 相比,各施肥處理的土壤Olsen-P 含量均顯著增加,分3 次施用下土壤Olsen-P 含量顯著高于1 次施用。培養90 d 后,在P1土壤上,與CK相比,1次施用和分3次施用的土壤Olsen-P 含量分別顯著增加了10.0%、33.0%,且二者間差異顯著;分3次施用相比于1次施用的土壤Olsen-P含量顯著增加21.0%。在P2土壤上,與CK 相比,1 次施用和分3 次施用的土壤Olsen-P含量分別顯著增加了15.1%和30.6%;分3 次施用相比于1 次施用的土壤Olsen-P 含量顯著增加了13.5%。在P3 土壤上,與CK 相比,1 次施用和分3 次施用的土壤Olsen-P 含量分別顯著增加了15.3%和26.1%;分3次施用相比于1次施用的土壤Olsen-P 含量顯著增加了9.4%。綜上所述,在3 種Olsen-P 水平土壤上,各施磷肥處理均顯著增加了土壤Olsen-P 含量,增加幅度在磷肥分3 次施用下最大。

圖1 不同培養時間下3種土壤的有效磷含量Fig. 1 Olsen-P content in soils under different incubation time
2.2 不同施肥次數下磷肥固定率分析
2.2.1 不同培養時間下的固磷率 在3 種Olsen-P 水平土壤上,磷肥在10 d 內被快速固定,之后進入緩慢固定階段(圖2)。培養90 d 后,在P1、P2和P3 土壤上,與1 次施用相比,分3 次施用的固磷率均顯著降低,分別降低了7.8%、6.4% 和9.2%;1 次施用的固磷率大小表現為:P1>P2>P3;分3 次施用下,與P1 和P2 土壤相比,P3 土壤的固磷率顯著降低了12.4%和10.8%。綜上所述,磷肥分3 次施用能顯著降低磷肥固定率;土壤Olsen-P水平越高,磷肥被土壤固定的數量越小。

圖2 不同培養時間下3種有效磷水平土壤上的固磷率Fig. 2 Phosphorus fixation rate in soils at three Olsen-P levels under different incubation time
2.2.2 土壤對磷的固定動態過程 米氏方程和Elovich 方程都能很好的擬合土壤對磷的固定過程,均達到極顯著水平(P<0.01),而且米氏方程的決定系數(R2)更高,擬合效果更好(表2)。由米氏方程的擬合參數可知,同一Olsen-P 水平土壤下,1 次施用的最大固磷率(Qmax)大于分3 次施用,而達到最大固磷率50%的時間(T)小于分3次施用;同一施肥次數下,低Olsen-P 水平土壤的Qmax大于高Olsen-P 水平土壤。由Elovich 方程的擬合參數可知,同一Olsen-P 水平土壤下,1 次施用的初始固磷速率(α)大于分3次施用,而磷的固定速率常數(β)小于分3 次施用;同一施磷次數下,低Olsen-P 水平土壤的α 大于高Olsen-P 水平土壤。可見,分3 次施用下高Olsen-P 水平土壤的最大固磷率低,達到最大固磷率50%時所用的時間長;土壤初始磷含量越低,土壤初始固磷速率越小。

表2 3種有效磷水平土壤上磷固定率的動力學方程參數Table 2 Kinetic equation parameter of phosphorus fixation rate in three types of Olsen-P soils
2.3 不同施肥次數下磷形態的變化分析
2.3.1 不同施肥次數下磷形態含量 由圖3 可知,3 種Olsen-P 水平土壤上,分3 次施用比1 次施用與不施肥均顯著增加了活性態磷含量,比1 次施用顯著降低了穩定態磷含量。在P1、P2 和P3土壤上,與CK 相比,1 次施用下活性態磷含量分別顯著增加了13.4%、12.9%和10.3%,分3次施用下活性態磷分別顯著增加了27.2%、21.3%和17.7%。在P1、P2和P3土壤上,與1次施用相比,分3次施用的活性態磷含量分別顯著增加了12.1%、7.4%和6.8%;分3 次施用的穩定態磷含量分別顯著降低了9.1%、8.4%和7.6%。在P2 土壤上,分3次施用比1次施用的中活性態磷含量顯著增加了0.9%。綜上所述,分3 次施用能顯著增加活性態磷含量并顯著降低穩定態磷含量。

圖3 90 d培養結束后不同施磷方式下土壤磷形態含量Fig. 3 Content of phosphorus forms under different phosphorus application methods after incubation for 90 d
2.3.2 不同施肥次數下磷肥轉化為各形態磷的比例 不同施肥方式和不同Olsen-P 水平下,磷肥施入土壤后轉化為各形態磷的比例存在差異(表3)。在P1、P2 和P3 土壤上,分3 次施用相比于1 次施用轉化為Resin-P 的比例均顯著增加,分別增加了209.1%、117.6% 和50.6%;轉化為濃HCl-P 的比例均顯著下降,分別下降了47.5%、39.3%和34.1%。同一施肥次數下,與P1 和P2 土壤相比,1次施用在P3土壤上轉化為Resin-P的比例均顯著升高,分別升高了16.5%和14.2%;轉化為濃HCl-P的比例均顯著降低,分別下降了64.5%和62.5%。分3次施用在P3土壤上轉化為Resin-P的比例均顯著升高,分別升高了55.9%和43.2%;轉化為濃HCl-P 的比例均顯著降低,分別下降了55.5%和59.3%。綜上所述,分3 次施用顯著提高了磷肥轉化為活性態磷的比例;土壤Olsen-P水平越高,磷肥施入土壤后轉化為活性態磷的比例越大。

表3 不同施磷方式培養結束后磷肥轉化為各形態磷的比例Table 3 Percentage of phosphorus fertilizer to various phosphorus forms in different P application methods after incubation (%)
3 討論
3.1 土壤Olsen-P含量對施肥次數的響應
本研究表明,施用磷肥均能提高土壤Olsen-P含量,這與前人[10-12]在公主嶺、鄭州和祁陽3 個長期定位試驗點的研究結果施磷肥處理下土壤Olsen-P 含量不斷上升基本一致。其原因是當磷肥施入土壤中,在初始階段土壤對磷的吸附和固定快,吸附很快達到飽和,后期進入緩慢固定階段[13-14]。本研究還表明,不同施肥處理間土壤Olsen-P 含量的變化不同,培養30 d 后,分3 次施用下土壤Olsen-P 含量顯著高于1 次施用。研究表明,液體磷肥分4 次追施比全部基施顯著增加了土壤Olsen-P 含量,底肥全部追施的施肥方式可顯著提高土壤的Olsen-P 含量[3,15],這與本研究結果一致。磷肥分次追施效果好可能是因為追施磷肥及時補充了土壤的水溶性磷;低量的磷肥施到土壤上,不易被土壤固定轉化,提高了土壤中的Olsen-P 含量;在輸入磷總量一致的情況下,通過在不同時期減少磷的輸入量,可以降低土壤溶液中H2PO-4的質量濃度,吸附態磷仍然會保持較高的有效性[16-17]。綜上所述,磷肥分3 次施用能顯著提高土壤Olsen-P 含量,且效果最佳。
3.2 固磷率對不同施肥次數的響應
當磷肥1 次施用到不同Olsen-P 水平土壤后,磷肥的固定率隨土壤Olsen-P水平的升高而降低,這與于淑芳等[6]的研究結果相似。這表明在同種施肥次數下不同的土壤Olsen-P 水平影響著磷肥的固定率,在一定范圍內,土壤Olsen-P水平越高,磷肥固定率越小。其主要是因為Olsen-P 水平高的土壤顆粒表面的吸附點位周圍聚集了大量的無機磷酸根離子,它們與土壤膠體表面吸附點位上的羥基(M-OH)或水合基(M-OH2)迅速地進行配位體交換反應,使吸附易于進行[18],因此,高Olsen-P 水平的土壤對磷的固定率較低。本研究還發現,米氏方程和Elovich 方程都較好地擬合了土壤對磷的固定動態過程,其中米氏方程擬合的效果更好。在米氏方程中,同一Olsen-P水平土壤上,分3 次施用下的最大固磷率低于1 次施用,而達到同樣固磷率所用的時間長。這與王光火等[19]報道的土壤中初始水溶磷濃度越大,其固磷速率越快和固磷量越大的結果相似。其主要原因是,相比于1次施用,分3次施用下初始水溶性磷含量較低,固磷速率較慢;分3 次施用下土壤中的水溶性磷含量一直處于較低狀態,土壤對磷的固定主要為吸附固定,這部分磷易解吸[20],故分3 次施用下土壤對磷的固定量低,分3 次施肥可以有效減少磷的固定。
3.3 磷形態對不同施肥次數的響應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3 種不同Olsen-P 水平土壤上,與1 次施用相比,分3 次施用均顯著提高了活性態磷含量,顯著降低了穩定態磷含量。這與褚貴新等[21]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可能原因是,一定時期內提高磷肥施用次數可能產生了“養分混合效應”,使該區域的穩定態磷分解[22],故磷肥分3 次施用能提高土壤中的活性態磷含量,且效果最好。本研究還發現,分3 次施用下,磷肥施入土壤后轉化為活性態磷和中活性態磷的比例增大,轉化為穩定態磷的比例減小,這與已有研究[3,15]結果一致。其主要是因為分3次施用減緩了土壤對磷肥的固定并延長了可溶性磷肥在土壤中的時間,磷肥轉為活性磷的比例較大。Aulakh等[23]研究發現,施入的磷肥有14%~18%轉化為高活性磷形態,28%~35%轉化成中活性磷形態,47%~57%轉化為土壤中難溶性磷。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似,本研究發現在低Olsen-P水平土壤(P1)上,1 次施用轉化為各形態磷的比例分別為15.0%、29.2%和55.8%。其可能原因是進入土壤中的磷肥,會很快轉化成溶解度高的鈣結合態磷,進而向難溶性的磷轉化,最后形成羥基磷灰石類難溶性的磷[24];被吸附固定或化學沉淀固定的磷在最初階段均具有較高的有效性,隨時間推移逐漸向難溶態磷轉化(磷的老化)[25]。說明水溶性磷肥進入土壤的時間越久,轉化為穩定態磷的含量越多,與本試驗中培養90 d 后分3 次施用轉化為穩定態磷含量顯著減少的結果一致。從劑量效應分析,1 次施入磷肥時,起始水溶性磷含量較高,土壤中固磷的主要方式為化學固定,土壤磷的活性大大降低;分3 次施用磷肥時,起始水溶性磷含量較低,以粘粒吸附固定為主[25],被吸附固定的這部分磷仍具有較高的活性,進而也驗證了本研究中分3 次施用后土壤活性態磷含量顯著增加的結果。分3 次施用通過增加土壤中活性磷和減緩活性磷的轉化進而提高了土壤Olsen-P含量,為磷肥高效利用和合理施用提供了科學依據,為實際生產中磷肥分次施用來提高磷肥有效性提供有效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