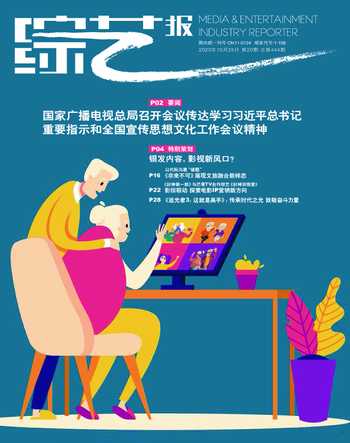《河邊的錯誤》演繹余華筆下荒誕故事
鐘茜

改編自余華同名先鋒代表作,由新銳導演魏書鈞執導、朱一龍領銜主演的電影《河邊的錯誤》10月21日全國上映。該片曾入圍、展映于戛納國際電影節、平遙國際電影展、倫敦國際電影節、釜山國際電影節、芝加哥國際電影節等22個國際電影節,并斬獲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藏龍”單元費穆榮譽·最佳影片、迷影選擇兩項榮譽,映前貓眼、淘票票雙平臺想看人數突破20萬人。
電影延續原著小說荒誕現實主義的風格和戲仿偵探小說的特色,講述一個被河溪環繞的小鎮上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殺人案,刑警隊隊長馬哲(朱一龍 飾)前往調查,不料案件陷入困境,整個小鎮都被恐慌的氣氛所籠罩……
“這是我第一次改編小說。”導演魏書鈞坦言,“每個讀過小說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馬哲,因此改編最重要的是把原小說更內在、更深層次的感受傳達出來。”影片采用16毫米膠片拍攝,運用大量長鏡頭,營造真實細膩的20世紀90年代氛圍,力求還原余華筆下的南方小鎮。
改編曾難倒張藝謀
《河邊的錯誤》是余華1988年發表的同名小說,講述一樁吊詭的兇案牽扯出多名嫌疑人,刑警隊隊長馬哲被無法言喻的真相不斷撥弄,逐漸陷入荒誕、不安和分不清是真是幻的記憶中。
“這部小說改編起來是一個陷阱。”余華曾透露,陸小雅導演、張藝謀導演先后買下版權,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當年)我跟張藝謀兩個人討論了四五天都理不出一點頭緒,他后來轉而去拍《活著》了。”《河邊的錯誤》原著改編難度大,主要在于其跳躍敘事、前衛結構,以及先鋒派藝術風格。這也讓觀眾對此次改編充滿好奇。
回憶拍攝初衷,魏書鈞介紹,“2018年,出品人、總制片人唐虓琿向我推薦了這本小說。他表示,小說故事精彩、氣質獨特,很值得影視化改編;雖然寫于三十年前,但今天看依然先鋒。”帶著高期待看完小說后,魏書鈞深感震撼,“疑云重重的氛圍、敘事的吸引力,以及隨時可能浮出水面的毛骨悚然。”2020年,魏書鈞終于得到了改編的機會,他帶著最初的閱讀體驗,開始了兩年多的劇本工作,“對我而言,這簡直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創作,又惶恐又幸運,這是一次向前輩藝術家學習、致敬的寶貴機會。”
魏書鈞告訴記者,改編的難點在于“無法把文字直接翻譯成影像”。劇本創作階段,他從自己執導的《永安鎮故事集》中找到了突破口,影片講述一個電影劇組入住永安鎮拍攝的故事,“片中的導演對編劇說,‘這部電影你不要理解,要感受。”這句臺詞讓魏書鈞放下對偵探類型的預期去理解小說,對《河邊的錯誤》劇本改編有很大幫助。魏書鈞也建議觀眾,“放下固有的經驗,去感受,會得到更多。”
“在和編劇康春雷討論劇本的過程中,主創發現原著既是一部戲仿小說,又有犯罪元素。電影一方面要把案件講清楚,另一方面要呈現小說戲仿的觀點、味道,這是難點。”電影新增了主人公馬哲生活的部分,使故事脈絡更為豐滿清晰,削弱了原著中對于幺四婆婆、王宏、許亮等角色的刻畫,結局也有所改動。作為原著作者,余華在電影首映禮上肯定了此次改編,認為該片拍出了90年代的生活質感,尤其是“最后的場景我覺得特別好,比我自己寫的結局要好,改編就是要這樣”。
貼近角色,
朱一龍快速增減重二三十斤
朱一龍表示,“怎么把文字對內心的描述呈現出來,讓觀眾感受到,是開拍前我面臨的挑戰。因為這部戲沒有高強度的戲劇沖突,也沒有太多強節奏的表現方式。所以馬哲這個角色,我不能通過‘演(設計一些表演方式)去完成。”
為了適配現實生活中有刑警隊隊長“過勞肥”的特點,增強角色在職業身份上的真實感,朱一龍快速增重30斤。隨著劇情推進,為了呈現人物狀態的轉變,朱一龍又在短短兩個月內減重20斤,“這部戲是順拍的,我用這個過程中生理產生的變化,來展現馬哲在破案期間承受的一切,用一種外化的方式,把他從內心掙扎到逐漸走向荒誕的感受表現出來。”
由于原著中有關馬哲外貌的描寫不多,如何讓馬哲的形象更具體,也是人物塑造的難點。朱一龍提到,某次翻看老照片時,看到一張多年前余華留著中分發型、站在雪地里的照片,“突然覺得馬哲在我腦海里出現了。”
在魏書鈞眼中,朱一龍是“敬業、認真、聰明的演員,他對劇本助益良多”。朱一龍的加入,讓馬哲多了幾分內在的能量,“這種能量,仿佛更能吸引我們穿透這張英俊的臉,抵達他的心里——角色更為復雜幽暗的內心世界。”魏書鈞和朱一龍經常在現場討論不同的表演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看回放和演練,力求表演既寫實又足夠有說服力。“我們常常在監視器前討論一場戲里肢體動作的順序,很懷念和他一起那段純粹、愉快的創作時光。”
影片故事發生在90年代,除了從服化道等方面還原年代氛圍,該片還采用16毫米膠片拍攝,哪怕只是一個簡單的鏡頭,開拍前都要反復排練。“90年代給我的印象是質樸的。一方面,膠片這種特殊的介質,有助于復原時代的影像氛圍;另一方面,膠片提供了‘看得見時間的可能性,它并非數字流程里后期調色可以達到的。”魏書鈞表示,對一段舊時光的塑造,膠片可以給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之前沒有完整地用膠片拍過電影,也想試一試。這是奢侈和冒險的!雖然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膠片電影已漸漸遠離公眾視野,但每當膠片攝影機的馬達聲響起,某種既衰落又神圣的儀式感就會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