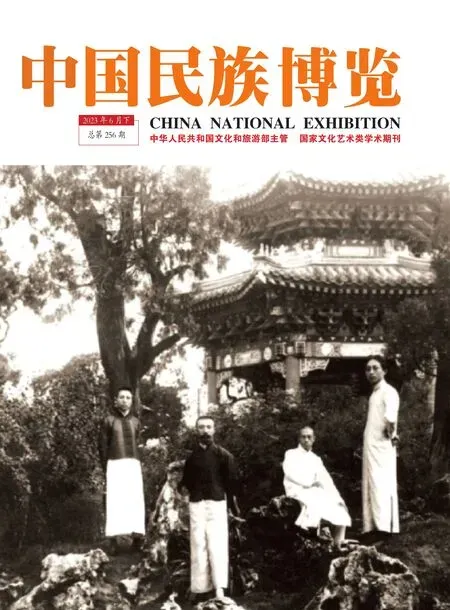老舍與“評講聊齋”淵源考論
王宇婷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引言
老舍,北京滿族旗人,作品主要著眼于尋常小事,將北京社會環境與北京旗人聯系起來,充分展現京旗文化特質,也就是常說的,老舍小說“京味兒”十足。老舍是地道的“老北京”,說北京話,住四九城,所見所聞無疑是老舍寫作素材的大部分來源,如《駱駝祥子》中的車夫祥子,《我這一輩子》中的巡警,《月牙兒》中的母女等,這是創作出“京味兒”小說的基礎。環境對于作家創作固然有著深刻影響,但作品是作家在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下產生的結果。那么除環境因素外,老舍的創作是否還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在老舍的小說中有怎樣體現?
老舍寫作小說用白話文,其語言風格、情節敘述中均可以窺見清末民初京旗作家的影子。清末民初是現代中國轉型期,雖然以尹箴明、莊耀亭、穆儒丐等為代表的早期京旗作家根據當時北京城的人和事進行創作,形成早期京旗白話小說,但由于外部因素影響,至今暫未受到特別大的關注。老舍以前是否關注到該群體,是否受到影響,孫玉石、張菊玲在《〈正紅旗下〉悲劇心理探尋》一文中寫道:“不大可能找到材料說明,老舍動筆寫小說之前曾經讀過這一類作品。老舍是否看過這些描寫北京和旗人生活的通俗小說,這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創作潮流的存在。”[1]抽絲剝繭,可以發現,老舍創作確實受到早期京旗作家創作的白話小說影響,特別是“評講聊齋”。
一、“評講聊齋”簡介
(一)發展過程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蒲松齡先生的《聊齋志異》極受八旗子弟喜愛,有人選取其中經典篇章,根據原有故事和人物進行再創作,當時流行的評書、子弟書等表演形式均以聊齋故事為素材,滿月川、張智蘭都曾演說過。但演說聊齋需要演說者具備基本功,讀懂聊齋故事、能講、會講,講的語言、方式、技巧都有講究,講得精彩才能有更多觀眾,而評書聊齋也為“評講聊齋”的發展奠定基礎。[2]
小說由評書發展而來,與評書一脈相承,“評講聊齋”與評書聊齋也是同理,都是用北京話,以說書人的口氣,將文言小說《聊齋志異》變為通俗易懂的白話小說,在保留原有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基礎上,加入了大量的逗哏打趣、戲詞俚語,并運用合理想象,對部分情節展開敘述,使原來的奇異故事增添了詼諧幽默的色彩。1908 年底,尹箴明、楊曼青、莊耀亭等早期京旗作家創辦《北京新報》,并開設“評講聊齋”欄目,刊載第一篇《白話聊齋》的作家正是說評書的張智蘭先生,這足以見得評講聊齋與評書聊齋的淵源。隨后,尹箴明、耀亭也對《聊齋志異》中流傳廣泛的篇章進行連載,將聊齋故事由口頭傳播變為以報紙為媒介的書面傳播。
(二)作者簡介
尹箴明,原名勛銳,字藎臣,北京旗人,筆名尹箴明、湛引銘,均是“隱去真名之意”。他曾說道:“在下八股改業,混進摔評一門。”在報界,從學做演說到任編輯員。“評講聊齋”欄目設立后,尹箴明與莊耀亭輪番創作,署名“尹箴明”。尹箴明自行接辦《群強報》,專門負責編輯白話《聊齋》,欄目同樣叫做“評講聊齋”,1915 年后,改為“演講聊齋”,署名“湛引銘”。[3]在此期間,尹箴明將《聊齋》四百多段故事說過一遍,被北京人所喜愛。直至1925 年去世前,該欄目所刊作品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后由另一位旗人作家時感生接替。
莊耀亭,原名莊萌堂,亦作蔭棠,字耀亭,旗人身份,久居北京,與早期京旗作家劍膽是好友。博學能文,愛好戲曲,是戲劇、曲藝的行家,對于戲曲內容有深刻獨到的見解。維新后,耀亭投身報界,先后在多家報紙發表文章,風格滑稽,符合當時社會大眾心理。直至1910 年7 月開始在《北京新報》上刊載“評講聊齋”。后期,他也在《白話國強報》《實事白話報》開辦“說聊齋”“白話聊齋”等欄目,均受到當時北京市民的喜愛。[4]
尹箴明、莊耀亭有相同的“底子”,即北京生活經歷和旗人身份,寫作時更能將北京人獨特的文化氣質代入其中,而在經歷、興趣方面又有所差別,因此使小說內容豐富有趣,受到讀者喜愛。“故白話報界,提起白話《聊齋》,人皆知莊耀亭與尹箴明。”[5]
從“評講聊齋”到后來二人各自負責的其他白話聊齋欄目,欄目數量多,持續時間長,可見作家水平之高,小說新穎有趣,符合當時北京市民需求,很受追捧。
二、“評講聊齋”與老舍小說
“我幼年讀過書,雖然不多,可是足夠讀《七俠五義》與《三國志演義》什么的,我記得好幾段《聊齋》,到如今還能說得很齊全動聽,不但聽的人都夸獎我的記性好,連我自己也覺得應該高興,可是,我并念不懂《聊齋》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記得的幾段,都是由小報上的‘評講聊齋’念來的——把原文變成白話,又添上些逗哏打趣,實在有個意思!”[7]這是老舍在1937 年創作的中篇小說《我這一輩子》中寫到的,可知,老舍也曾是“評講聊齋”的讀者,而且是忠實讀者。“評講聊齋”欄目止于1915 年,當時的老舍只有十多歲,距離這部小說創作約有20 年的時間間隔,卻可以完整動聽地講出來,對其特征進行概括,足以看出“評講聊齋”對老舍的影響之深。
(一)趣味性
老舍對比《聊齋志異》原文與“評講聊齋”,認為后者更加有意思,原因之一在于文言文變為白話文、加入逗哏打趣的成分,更具魅力。
在《群強報》尹箴明演說為:“想到其間,這氣不打一處來,七孔冒火(昆生成了火判兒咧),用手一指偶像,說:‘好你個老丈人,養活女兒,嫁了人不懂得三層大,兩層小,連公公婆婆不懂得尊敬,已經可惱,你還聽信你女兒一片嘴兩片舌的話護犢子。’”[9]在這段演說中,完全可以聽到評書的“音兒”,案頭能閱讀,上場能表演,使讀者有形象感、色彩感,在閱讀時,既能感受他的氣憤,但又多了一些詼諧成分,牢牢吸引讀者眼球,并且期待后面內容。
首先,根據《聊齋》原有故事情節,在文言變為北京白話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創造,如“七孔冒火”“護犢子”等土話俚語多處出現。其次,北京評書“說、演、評、噱、學”五大技巧也多有應用,充分體現老舍所說的“逗哏打趣”。“逗”本是指運用滑稽好笑的語言或動作引人發笑,如文中的“刀山油鍋雄搗磨研,盡管朝我來,”就是作家使的“包袱兒”;“學”體現為《寶蓮燈》唱詞,戲腔十足,最后寫到昆生的尊貴身世,是作者在進行打趣,也是作者埋下的“扣子”,給讀者留有懸念,以期來日。
“評講聊齋”彌補了《聊齋志異》艱深難懂的不足,將形式、內容與技巧充分結合,使平淡說詞變為言之有“物”、段段有梗,詼諧幽默,符合當時京旗子弟追求輕松娛樂的心理,受到讀者青睞。
(二)教化啟示
《云翠仙》開篇處,尹箴明先生說:“那位說,我們不愛瞧,話雖如此,這可不能由著一位一個主意,我們是以報的漲落為定,只要報數直漲,就算我蒙對啦”。[10]可見,當時人們對于小報上連載的“評講聊齋”欄目是極其追捧的,報紙的數量便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標準,只有人們喜歡上面的內容,才會購買報紙,報紙的銷量才會增加。老舍小說中也出現過相似片段,在《老張的哲學》中,老舍將王德設計成一個在報館工作的年輕人,小山在公園里賣報紙,央告王德幫忙寫“廣告”以增加報紙銷量,在小山看過王德寫的東西之后,十分滿意,而這個廣告恰好與聊齋故事有所呼應,原文說“尤其關于中央公園的一條,特別說好,他拿著筆一一地加以題目,那條關于中央公園的事”,[11]賣報數量的增加很能說明問題,王德有報社工作經驗,清楚地知道當時人們最愛看什么內容,抓住賣點,使報紙多賣五百多份。王德作為老舍筆下人物,相當于老舍的代言人,王德知道的事,老舍也必然是了解的。所以,認為老舍先生知道當時北京人追捧小報上刊載的志怪小說,以上都與“評講聊齋”的內容不謀而合。
王德聽到小山的要求時,說:“造謠生事,我不能作!”[12]在他看來,報紙應該符合事實,不編寫傳播不實言論,寫過廣告之后又接著說“人們買報原來是看謠言!”王德把婦女問題擱下,又想到新聞紙上來,“到底是報館的錯處呢,還是人們有愛看這種新聞的要求呢?”[13]他的話引人思考,當他在質疑人們買報紙為了看謠言這一現象時,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其中的不合理之處,認為報紙應該有更重要的作用。老舍寫作小說,關注底層小市民,以滑稽幽默的語言,揭示社會現象的同時,也帶有一種令人反省的意味,反對語言庸俗,內容空洞。因此,也許老舍對“評講聊齋”印象深刻,不單單是由于其有趣的語言特色,深層原因是它蘊含的價值和傳達的思想。
(三)標點符號
另外,“評講聊齋”中標點“()”的使用,不同于現在的“()”表示解釋說明、引用等作用,現代標點通常可念可不念,但在早期京旗白話小說中括號里的內容需要念出來,雖用括號區別于正文,但多數是起到逗哏效果,相當于“包袱”所在。[16]如上文引用的“評講聊齋”《俠女》篇片段中括號里的內容,“昆生成了火判兒咧、唱上《寶蓮燈》咧”等都是在給昆生的話起逗樂效果。老舍在小說創作中沿用括號的這一意義,例如在小說《老張的哲學》中寫到“老張拿著一套銀票,精精細細地擱在靠身的口袋內(可惜人們胸上不長兩個肉袋)”。[17]這里的括號并非現代括號,而是在調侃老張愛財如命,增加了的幽默效果。而老舍寫作該小說同樣是在英國講學期間,但在老舍出國之前國內便已經推行白話文,規范標點括號,曾由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人提出《方案》,[18]這發生在老舍出國4 年前,這段時間足夠老舍學習、接受新式標點,但老舍依舊沿用“評講聊齋”中“()”的用法,可見老舍對此早已習慣,影響之大。
三、結語
老舍小說是京旗小說的代表之作,但并不只是因為他北京人的身份,同時還受到了早期京旗小說的影響,尤其是“評講聊齋”,在老舍作品中足以見得老舍對其強烈的喜愛和追捧,并將其中一部分創作經驗吸收理解,運用在創作之中。因此,如今在強調老舍的小說京味十足、詼諧有趣,嘗試通過作品窺見當時的社會人生,還原北京風貌的同時,不妨轉換視角,細細研究“評講聊齋”以及其他早期京旗小說的特色與價值,也許會看見更加清晰完整的北京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