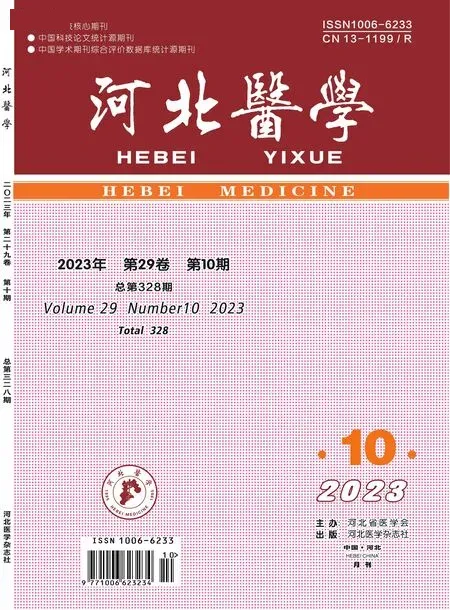免疫療法聯合靶向治療對轉移性結直腸癌的療效及安全性研究
王 巍, 曹 博, 王志武, 于鎵銳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醫院放化二科, 河北 唐山 063000)
結直腸癌的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居胃腸道腫瘤之首,每年有超過185萬新發病例和85萬例死亡,在新的結直腸癌診斷中,20%的新發患者患有轉移性疾病,另外25%的患者在出現局限性疾病后會發展為轉移[1]。在腫瘤切除和系統治療后,轉移性疾病患者的5年生存率為40%,而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僅為20%[2]。目前臨床上化療和靶向治療的益處已經達到平臺期,需要尋找新的有效治療方式來改善結直腸癌患者生存情況。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調節T細胞、抗原遞呈細胞和腫瘤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幫助釋放被抑制的免疫反應,對于錯配修復缺陷或微衛星高度不穩定的患者來說,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治療方法。卡瑞利珠單抗是程序性死亡分子-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為主要免疫抑制分子的抑制劑的一種,可阻止PD-1與其受體相結合,激活T淋巴細胞,啟動抗腫瘤免疫應答并抑制腫瘤發展[3]。既往研究表明,卡瑞利珠單抗聯合阿帕替尼對二線及以上方案失敗的晚期結直腸癌患者具有潛在療效且不良反應可控[4]。近年來,以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為靶點的抗血管生成治療已被證明能夠控制結腸癌的進展,抗血管生成藥物單獨或聯合靶向藥物治療結直腸癌越來越受到重視[5]。目前,尚無卡瑞利珠單抗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的相關報道。本研究探討了卡瑞利珠單抗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在晚期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中的療效和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研究為前瞻性觀察性隊列研究,收集2021年6月到2022年6月期間在唐山市人民醫院放化療二科接受卡瑞利珠單抗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或抗血管生成藥物單藥治療的晚期三線轉移性MSS結直腸患者40例。納入標準:①年齡:18~75歲,男女均可;②病理組織學證實的結直腸癌患者(均為MSS狀態),確診轉移且無法手術切除或接受局部治療;③既往二線化療失敗或不耐受,且未接受過抗血管系統治療或者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④至少有一個可測量病灶;⑤ECOG PS評分:0~2分;⑥預計生存期≥3個月;⑦主要器官功能正常;⑧血常規檢查:HB≥90g/L、ANC≥1.5×109L-1、PLT≥100×109L-1;⑨生化檢查: ALB ≥30g/L、ALT和AST≤2.5'ULN;存在肝轉移的患者,ALT和AST≤5'ULN、TBIL ≤1.5'ULN、肌酐 ≤1.5'ULN。排除標準:①活動性或未經治療的腦轉移;②存在軟腦膜轉移的;③存在有癥狀需要反復引流的心包積液、胸腔積液和腹腔積液;④用藥前14d之內使用過免疫抑制藥物,不包括噴鼻和吸入性皮質類固醇或生理劑量的系統性類固醇激素(即不超過10mg/d 強的松龍或同等藥物生理學劑量的其他皮質類固醇);⑤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⑥5年內患有其他惡性腫瘤的患者;⑦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或患有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活動性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或合并乙肝和丙肝;⑧用藥前6個月內出現心肌梗死、嚴重/不穩定型心絞痛、NYHA 2級以上心功能不全、控制不良的心律失常、癥狀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腦血管意外;⑨用藥前4周內并發重度感染,或在篩選期間/首次給藥前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熱>38.5℃;⑩患者既往做過異體器官移植手術或有精神障礙的患者。
1.2方法:治療方案,聯合組:卡瑞利珠單抗+抗血管生成藥物(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對照組:抗血管生成藥物(呋喹替尼/瑞戈非尼)。均為每3周一個周期,持續給藥至疾病進展或毒性不可耐受,各20例患者。卡瑞利珠單抗以30min時間靜脈滴注(滴注時間不少于20min,不長于60min),3周一次。抗血管生成藥物:瑞戈非尼,120mg/次,每天1次,吃2周停1周,每3周為一個給藥周期;呋喹替尼5mg/次,每天1次,吃2周停1周,每3周為一個給藥周期。治療期間每6周進行一次疾病評估,直至病情進展或毒性不耐受。
1.3療效評價:根據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將患者分為完全緩解、部分緩解、穩定和進展進行療效評價。完全緩解是指病灶消失并持續4周以上;部分緩解是指病灶最大徑之和減少30%并持續4周以上;病情穩定是指病灶介于PR和PR2之間;疾病進展是指病灶最大徑之和增加20%或有新病灶產生。評價兩組的總生存期(OS)、疾病控制率(DCR)和客觀緩解率(ORR)。
1.4不良反應:記錄患者治療期間出現的不良反應:手足綜合征、骨髓抑制、乏力、肝功能異常、高血壓、蛋白尿、甲狀腺功能減退、腹瀉和反應性毛細血管增生癥。
1.5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采用卡方檢驗分析兩組患者的臨床特征和兩組間近期療效。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log-rank檢驗進行生存分析對比,COX回歸分析計算HR值。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兩組患者臨床一般資料比較:比較兩組患者年齡、性別、PS評分、原發灶位置(左右半)、肝轉移、肺轉移、其他轉移、RAS、BRAF突變,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臨床一般資料比較n(%)
2.2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兩組患者治療疾病控制率、客觀緩解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2.3兩組患者總生存曲線比較:治療組中位總生存期11個月,對照組中位總生存期為7.5個月,HR 0.713(95%CI:0.357~1.422 ),兩組總生存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

圖1 總生存曲線
2.4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比較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n(%)
3 討 論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年中,結直腸癌免疫療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最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基于來自2個II期試驗的令人信服的數據,批準pembrolizumab和納武單抗用于微衛星高度不穩定型患者的二線治療,基于KEYNOTE-177的令人信服的數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在2020年將pembrolizumab作為該亞群的一線治療藥物[6]。PD-1信號通路參與介導腫瘤免疫,其中PD-1配體PD-L1的過表達被發現會損害T細胞的細胞溶解活性,并顯著增強腫瘤的形成和腫瘤的侵襲性,此外,通過應用抗PD-L1單克隆抗體進行抗PD-L1治療可以逆轉這種作用。進一步采用多種干擾PD-1信號通路的方法,包括抗體阻斷PD-L1,PD-1細胞外區DNA接種,腫瘤特異性T細胞克隆注射時,可以觀察到腫瘤的加速根除。我們對PD-1信號傳導的理解大部分來自急性活化T細胞的研究。PD-1細胞質結構域中含有兩個酪氨酸殘基,其中近膜端殘基形成免疫受體的基于酪氨酸的抑制基序,另一個形成免疫受體的基于酪氨酸的轉換基序。在與PD-1配體結合后,位于PD-1 ITSM內的酪氨酸殘基被磷酸化并招募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如SHP2。這些PTP可以使多種關鍵信號激酶去磷酸化,并對抗T細胞活化過程中TCR-CD28受體共同刺激引發的陽性信號事件,與CD28介導的途徑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tcr驅動途徑的偏好。例如,SHP2抑制ZAP70、PI3K-AKT和RAS-ERK,而不是PKCθ。最終,PD-1信號轉導導致激活蛋白1 、活化T細胞核因子和NF-κB等轉錄因子的激活降低,從而拮抗驅動T細胞活化、增殖、效應功能和存活的正向信號。此外,與CTLA-4在免疫反應早期主要在淋巴結中抑制T細胞活化不同,PD-1在免疫反應后期主要在外周組織中抑制T細胞,這使得PD-1通路阻斷對抗腫瘤T細胞具有更特異性的作用,同時與CTLA-4阻斷相比表現出更小的毒性。目前以抗PD-1抗體及其配體抗體PD-L1為代表的免疫檢查點阻斷已被批準用于結直腸癌的微衛星高度不穩定型和DNA錯配修復缺陷表型,作為二線或后續治療,或作為PD-L1陽性結直腸癌的三線治療,但單一治療效果有限。探索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作為微衛星高度不穩定型結直腸癌患者和早期微衛星高度不穩定型結直腸癌患者一線治療的潛在益處的多項試驗正在進行,并備受期待。卡瑞利珠單抗是一種高親和力、人源化免疫球蛋白和選擇性IgG4-anti-PD-1單克隆抗體,在中國已被批準用于治療霍奇金淋巴瘤、晚期肝癌、晚期食管癌和晚期非小細胞肺癌[7]。由于中國患者的藥物可及性和經濟壓力,卡瑞利珠單抗是實時實踐中用于各種實體腫瘤的最廣泛使用的抗PD-1抗體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檢測點阻斷免疫療法和放射療法的組合可以產生針對局部和遠處腫瘤的協同抗腫瘤效果,可降低腫瘤分期并減少局部復發,基于臨床試驗中的積極療效結果,它在幾種實體瘤中顯示出有希望的臨床療效,并且還顯示出對微衛星高度不穩定型實體瘤有效[8-9]。在16名患有微衛星穩定難治性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中,瑞戈非尼和卡瑞利珠單抗的組合實現了25%的客觀緩解率,表明在適當組合的治療策略下免疫治療的潛在益處[10]。
血管生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包括從已有的血管形成新的血管,它對于促進癌癥的存活、生長和擴散至關重要,抑制血管生成可防止腫瘤進展。在包括CRC在內的各種癌癥類型中已經觀察到對抗VEGF的耐藥性,這可以通過其他信號通路的代償性激活和血管生成相關蛋白的替代性分泌來解釋。相關研究顯示VEGF驅動的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腫瘤微環境之間的密切關系,提示使用抗VEGF治療結合ICIs來克服錯配修復缺陷結直腸癌的耐藥性。抑制血管生成可阻止腫瘤進展的假說已被實驗證實。在標準化療中加入貝伐單抗,以及使用抗VEGF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如瑞格非尼,已顯示出治療一些癌癥的療效,包括mCRC。然而,大量腫瘤被認為對靶向VEGFA信號的抗血管生成抑制劑不敏感,通過治療誘導的損傷、代謝改變、炎癥和骨髓源性抑制細胞的擴張。從而通過抑制免疫細胞募集和阻止腫瘤和血管內皮細胞釋放血管生成因子,降低了代償性血管生成因子上調的來源。瑞格非尼是一種多激酶抑制劑,用于治療結直腸癌通過VEGF受體2-3 /RAF/MEK/ERK途徑抑制酪氨酸激酶介導的信號轉導,并已被證明可延長總生存期。
隨著免疫療法的不斷發展,免疫檢查點阻斷和低劑量抗血管生成劑已顯示出有希望的抗腫瘤功效和相互作用。與化放療不同,免疫療法的發展旨在增強針對腫瘤抗原的系統免疫,消除微轉移,否則微轉移將是復發的來源。此外,當以較低劑量給藥時,抗血管生成劑的有利作用被認為在免疫調節中發揮作用,而不僅僅是減少腫瘤細胞的血液供應[1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和抗血管生成藥物單獨使用時各有局限性,但臨床前和臨床研究表明,抗血管生成藥物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治療腫瘤具有優勢,可以相互促進。已有研究表明卡瑞利珠單抗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安羅替尼對既往接受治療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具有可耐受的毒性和良好的抗腫瘤活性,且在聯合治療中沒有觀察到額外的毒性[12]。Rao J等[13]研究發現,通過卡瑞利珠單抗和阿帕替尼聯合治療,對于進展期膽囊癌根治術后多發性肝轉移患者,治療后外周血中(CD)16+CD56+自然殺傷細胞比例升高,表明抗血管生成藥物聯合免疫治療可能是復發性膽囊癌或晚期膽囊癌患者的潛在治療選擇。Cheng H等[14]研究發現復發性妊娠滋養細胞腫瘤患者通過卡瑞利珠單抗和阿帕替尼聯合治療,顯示出有希望的抗腫瘤活性和可接受的毒性,可以作為治療高危化療難治性或復發性妊娠滋養細胞腫瘤的挽救性治療選擇。
本研究通過對40例轉移性MSS結直腸癌患者使用卡瑞利珠單抗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治療或單用抗血管生成藥物治療,研究顯示,兩組患者基線資料大體一致,聯合治療組提高了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的總生存期。而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則表明聯合治療安全性整體可控,兩組無明顯差別。綜上所述,卡瑞利珠單抗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臨床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安全有效。但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樣本量小,單中心,為回顧性分析存在偏倚,隨訪時間較短,需要大量前瞻性臨床研究進一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