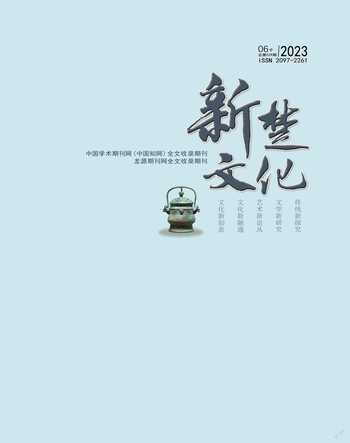儒家倫理學的互系性詮釋
【摘要】西方質相性思維對中國儒家思想的“詮釋”遮蔽其內在互系性,依靠個人修養以家庭為起點進而延伸至社會與宇宙的和諧,人皆是鑲嵌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的“綜合人”,自身的價值是由他人所決定,在自身的家庭或社會角色中各司其職,家庭與社會反饋自身價值,從而實現整體性和諧。
【關鍵詞】儒家角色倫理;中國式宇宙觀;互系性倫理
【中圖分類號】B82-0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17-0004-04
“研究的國際化趨勢也是不可阻擋的,一個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國外同行正在說什么、做什么的時候。”[1]47儒家角色倫理(Confucian role ethics)是安樂哲(Roger T. Ames)反思西方現有文化秩序,剖析東方儒學蘊含的以“互系性”“結構性”等中國倫理特有詞語為核心的倫理構想以此來重構人與自身、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宇宙關系的有機倫理法則。表1能夠更加直觀地對此書中提及的東西方倫理關鍵詞差異進行對照。在確保中國倫理植根于中國本土意識形態特有內涵與價值主張的前提下,從安哲樂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與中國倫理發展軌跡相契合的精華,有助于從新視角對儒學理論進行創造性轉換與詮釋。
一、儒學的詮釋域境
(一)“互系性思維”作為“常識”
“互系性思維”字面理解,互是相互,系是聯系,即相互聯系的思維。針對馬克斯·韋伯及黑格爾對傳統中國的誤解,安哲樂指出:“中國人講‘人本質,不是宣稱存在一個質相、‘個體性靈魂。而是互相關聯視域,把個人行為納入‘自然循環過程之中,把文化與社會視作與自然宇宙相統一的方面。”[2]51
“常識”是我們對事物進行思維的根本方法,是距離我們極遙遠祖先們的發現;這些發現得以在后來經驗中自始至終地保留下來。這些根本方法與發現,構成人類思想發展的巨大平衡階段,即一個“常識”階段。但“常識”其實并不常,在數百年中沉淀于每個人思維與生活方式,無疑是始終受到外部影響的,成為我們每個民族表面變化基礎的內在脈沖力,它是相對具有彈性的、堅毅的。書中提到,尼采認識到“文化特殊性的確造成深層基質的形成與其內容差別”,不同語系具有不同特質;英國修辭學家I.A.理查茲考慮到“從一種文化之‘常識向另一文化之‘常識(從當代西方傳統向古代中國傳統)轉換的困難性,也擔心‘分析作為研究方法論,很可能會引進與早期中國傳統十分‘格格不入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
《易經》成為西方學者解讀中國傳統世界觀的視角。吉德煒肯定地將“互系性思維”歸結為占卜的根源并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變化”觀念使用兩極相反符號語言表述,兩極互含,兩極為一。“它是一種主流思維模式;通過生態性的二元聯系、鼎新比喻、喻義意象、啟發性圖案的擴散與聚集,展示既復雜又具闡釋性的力量;生態性二元聯系的各種形式,都在平常經驗中獲得重視、考量與檢驗。”[2]59這樣的闡釋視域被稱之為“互系性宇宙觀”或“互系性‘氣的宇宙觀”。
其次是中華傳統醫學中所蘊含的中國式宇宙觀。具體“形式”與生命活力的“氣”,是對同一事物的兩個“非分析方面”——“轉變性”與“形式”,也同是對同一事物過程階段性理解的含蓄表達。自然科學中“場”的概念有利于我們對“氣”與“形式”進行了解。任何事物都不只是肉眼可見的“生命體”,而且還是看不見的“環境”。
“互系性宇宙觀對形式結構、對功能理解是根本‘域境性的,即將‘事物置于它總是處在變化狀態的‘環境中去,這樣形成一種內在與外在的‘場景;身體被內外兩方面看待,作為或多或少的主觀,亦作為或多或少的客觀。”[2]69這一宇宙觀是生命的、域境的、過程性的觀念意識。此外,在安哲樂的書中提到互系性宇宙觀也被稱作生態宇宙觀。有感知與無感知、有生氣與無生氣、有生命與無生命之間并無一種最終界限。生命與物質是同一事物從兩個方面的考慮。西方觀念預先設定一種本體論,追求物質與精神的絕對分割,也可將其稱為是具有絕對“一”的“一元本體論”;中國則無特定個體,而是將人與事物置于具體情境、具體過程中再加定奪。
(二)“關系”的相互性與相構性
儒家提倡的是從認識人類經驗的整體性和人類經驗的關系性相互構成性質出發,“牽一發而動全身”,反映的也是儒家互系性宇宙觀,追求整體性與相關性。印歐語系與漢語語系中的邏輯不同導致東西方相互翻譯時具有差別,西方注重抽象的概念、東方注重具體的概念。“‘禮這一觀念,表達一種充滿活力的社會形態;在這形態之中,人都是特殊的人,都是特殊狀態的角色和關系,同時也是協同的,如同許多‘公體人,每個具體角色與關系,是由‘公體性定義的,如‘兒子與母親‘祖父母與孫兒女,每個人都是特殊具體人,同時構成人的一般角色與關系。”人既是自己的也是社會規定下的角色,兩者是不可分的。社會關系特定的角色是必須的,只有被置于整個世界關系中才能夠得到社會的和諧。對這一中國自然宇宙觀而言,正是一切事物嚴格意義相系不分,要求人們從總是域境化又特別具體性方面思考,而不是去假設什么不變質相與自然種類的理念。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無特點無個體性,恰好相反,我們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國社會人的特殊性是伴隨成就而來的與眾不同,是人在適應同家庭與社會的聯系之中形成的。在儒家這種擔任由多種關系構成的不同角色的人身上,人不是‘在社群中實現聯合的個人,反而恰恰是由于我們在社群中有效聯系在一起,從而使我們變得特殊了,變成關系構成的個性人了。”[2]88
二、儒家人生觀:志于“仁”
(一)邏輯起點:“做人”
意義來自共生性,來自盤根錯節的關系。一個人致力于“為仁”——成就自己在家庭環境關系中的最適宜性,既是對人、社會乃至宇宙意義的起點,也是其根本的源泉。通過成就和開拓于家庭環境之內與之外的健康關系而對人格進行修養。儒家思想的本質“為仁”以家庭為起點,縱向發展至社會和諧,再到宇宙的和諧。
(二)《大學》奠定人生觀
《大學》講的是個人、家庭、社會乃至宇宙的修養與滋養,根本是連通一氣、相互蘊含的,務必以人的修身為起點。家庭在儒家倫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學》中所表明的正是這樣一種以血緣倫理為基礎的和諧:“家庭的意義蘊含在、依賴于每個家庭成員的有效修身;延伸開去,整個宇宙的意義也都蘊含在、依賴于每一家庭與社會成員的有效修身。特殊的人的價值是人的文化的來源,人的文化又反過來成為一種聚合性源泉,為每一個人的修身提供了一個域境。”[2]107即家庭靠個人的修身、宇宙靠家庭與社會成員的修身。西方依賴形而上學假設推定或者超自然遐想,而東方注重自然主義。儒家思想的一個最顯著特點,是其滲透與適應的能力,它尊重具體事物的特殊性。
家庭之所以具備如此高的地位,是因為我們鑲嵌于諸多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家庭關系是我們的出發點,家庭具有自身獨特話語。我們成長的是我們的生命,其意義只在于關系的延伸與放大,橫向延伸依靠“友”,縱向延伸依靠家庭社會宇宙線。“關系已經是由時間過程所承載、不同層次和不同范疇話語構成的了。我們通過延續話語和其他話語媒介,如肢體、接觸和舉止,互相進行語言塑造。當然‘禮,作為人身份和關系既成的一種適宜性呈現,本身就是語言,不僅是限于語言的相互對話,也是人去‘活自己身份與關系過程中的語言。”[2]111而這一切都是源于家庭,儒家所強調的所有關系,哪怕是天地萬物宇宙的關系,都是用家庭話語來表述的。
儒家觀念中人或物都是置于過程中“活”的人或事物,而不是故步自封、目光短淺的人。諸事皆宜,不逾矩,但隨著歷史的發展,產生的新事物必定會超出已規定的“禮”的范圍,這個時候儒家便要求人們能夠具有前瞻性,這尤其反映在儒家對統治者的要求,例如荀子要求的大儒。
(三)從“齊家”至“治國”
家庭是儒學宇宙觀的基礎,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單獨的個人,不是“獨人”,而是鑲嵌于運動著的、“活”的諸多關系、諸多事物的“綜合人”。我們是各種角色的總和,而非單獨存在的人。在我們與他人的關系及相互性中“扮演”的角色(play roles in)。且為了個人榮耀感,我們的特殊性與獨特性皆是由所處的關系決定的。家庭作為儒學的理論出發點,其意義與價值不僅是社會秩序性的根基,家庭關系還具有宇宙及宗教性的意義,即依靠家庭角色的家庭和諧穩固達到社會角色的社會和諧穩固再達到宇宙的和諧穩固,家庭被視為社會和宇宙所有秩序的核心。
(四)人倫角色,體認以禮
西方講求質性與屬性,東方講求人的行為,在人自己行為中做到協和性和一體性;以家為中心是區別于西方的東方特點。錢穆認為“正如‘家庭‘家族與‘民族都是以具體家庭成為行為的向外輻射形態擴大,是在對這些身份與關系體現之中的一貫性,構成著作為具體人的認同性。家庭是儒家的人取得身份的基礎”;內森·席文針對人體、天地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認為“自然、國與人體的觀念是相互依賴的,稱其為渾然而一體是最恰當的理解”。
國內眾多學者認為的“義”具備適宜的意思,諸事皆宜,做事都應處在恰當的范圍內,安哲樂支持接受儒家所認為的對“人”的理解堅持一種關系性而不是質相性的理解。“‘義必須是在那些與自己的具體家庭和社會的關系之中包容性的‘自己的恰當行為。也就是說,‘義是最符合具體情況的行為,而不是簡單地執行一些外在的原則或法規——什么絕對正確的行為。”[2]126
(五)“友”指開放性
縱向層面的強化家庭認同延續性、對祖先的關懷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橫向家庭互相依賴的關系層面,這個層面向外拓展與朋友建立聯系。
個人成長是社會關系的產物,朋友關系在個人建構中占據重要角色。在向外尋求和發展豐富含義的友誼方面,我們有空間、有自由度,這與我們的親屬血緣關系性質不一樣。作為儒家“家為中心”倫理的一個層面,“友”是一種確定的、具有補償性的意義與價值來源。朋友之意義的根本不是來源于外在,而是友誼本身發展過程的呈現。“‘友在家庭親屬關系的外圍開辟了一個輕松的環境,為更有意識、有意志地造就有個人特殊性的關系,也為形成個人人格提供了可能。‘友是自愿選擇關系,但仍是以家庭意識為基礎,而且有潛力為個人提供超出正式親屬紐帶的成長意義與復雜性。”[2]132
(六)“成人、成仁”之內在性
西方認為是本體論(human being)而儒家認為是成人(human becoming),多種角色內在聯系著的人,這些角色決定著我們是誰,承認我們在行為上具有的特殊性差別和道德能力。換句話說,我們是我們去“活”的、與我們同胞互相協同的角色的總和。
三、儒家“角色倫理”
(一)源于關系而產生的“價值”
我們日常所說詞匯:公平、正義、平等、博愛、勇氣,在西方視角來看都是具有超越性的概念,而在儒家視角下此類概念是人從家庭與社會關系中的勇敢或正義性行為歸納而來的。換句話說,儒家思想中的一切價值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從人與他人、家庭、社會甚至宇宙的關系中而來,這些價值指向的不是虛無概念,而是最實在地指向獨特、具體的關系。
當我們意識到,價值其實是從對行為方式的簡單特征概括中而來,而不是植根于或從先決原理起源而來,人價值的提高只能在人們的分享活動與共同經驗環境內發生。“原則”“德行”等詞語都是抽象的,而活著的角色本是第一位的。
(二)“子為父隱”而得“直”
孝道在儒家觀念中是一個較為重要的概念,羅哲海在其著作《軸心時期的儒家倫理》中就已經提到了孝道中包含著“勸諫之孝”:“‘諫,即當家長有錯誤行為之時,為人子有義務表示反對并加以糾正,成為儒家經典講‘孝中很突出、關鍵的內容。”[2]180“儒家的最終目標不是道德與角色倫理的對抗,而是兩者的調和。”[3]81“孝順的義務必須服從更高的標準。”“在‘義這個標準之下,道德勸誡必須凌駕于孝順義務。”[3]82
家庭關系是雙向的,“雖然‘孝這個基本美德含有奉養和順從之意,但是并不表示可將更高的道德準則排除于家庭的領域之外。不僅要求長對少要仁慈和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孝道本身也要求子女以道德為依據,而對父母進行勸諫,或是拒絕服從。”[3]83羅哲海與安哲樂在闡述中國儒家倫理的“孝”時皆提出了“諫”,服從于“義”即高于“孝”的道德觀念。孝順本身是為了扮演和諧的家庭角色,構建和諧的家庭氛圍,但若與更高層次的道德準則產生沖突,則需要讓步。
(三)“仁”“忠”“恕”“義”等概念范疇的詮釋
首先“仁”不是一種道德。西方思維總傾向于將概念“質相化”與“形而上學化”,而東方傾向于非具體與“過程化”,即仁不是一種具體的道德,是一個統稱,決定因素是情景環境,由它決定什么是最適宜的德行,即是否符合“義”。對于儒家角色倫理學,起點是考慮發生了什么,而結束是讓正在發生的更好地發生,即儒家角色倫理是非預設的。
其次“恕”所表達的,既是道德困惑,也是對找到最適宜回答所做的開創性探索,是相對于他人行為,自己做出的相應行為,然而賦予“恕”如此核心的意義,是根據人做出的有效相應性行為以及確定人的道德判斷時,想象力之無可比擬的重要性。恕與想象關聯,也是儒家所期望的在后世中超越“禮”范圍之內的行為要求。“恕”的思想由捉摸不定的情勢而生,即對一種特殊情況感到困惑,通過豐富想象而找到轉機,從而確定自己的行為。張瑞璠在其所著《中國教育哲學史(第一卷)》中將“恕”看作是與“忠”有所為相對應的有所不為。
最后“義”的含義為行天下之大道。“義”追求“成就人關系之最恰宜”,與“忠恕”直接相關。“‘恕是去發現,‘忠是去做的方式,‘義是在需要在倫理考慮的場合中發揮。”[2]220
參考文獻:
[1]李伯重.史潮和學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安哲樂.儒家角色倫理學:一套特色倫理學詞匯[M].孟巍隆,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
[3]羅哲海.軸心時期的儒家倫理[M].陳詠明,瞿德瑜,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4]范瑞平,方旭東.儒家倫理學:后果論還是美德論?[J].哲學分析,2020,11(06):176-189.
[5]黃勇.“美德倫理學”“德性倫理學”和“德行倫理學”與儒家倫理學[J].江海學刊,2020(06):20-29.
作者簡介:
尚猛(1999-),男,山東臨沂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哲學、教育文化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