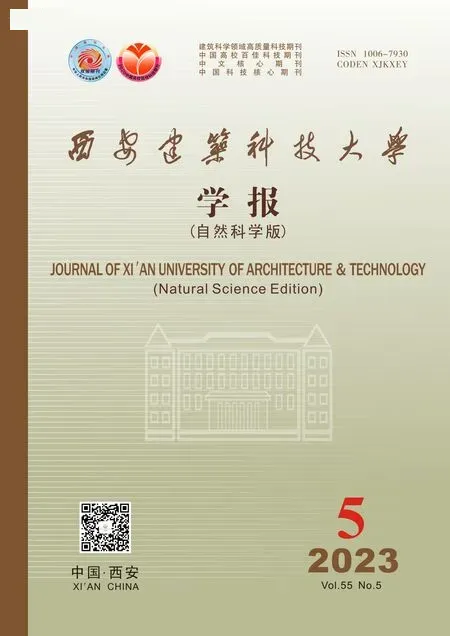關于國土空間規劃中城鄉建設用地統籌的思考
王 陽,郭開明,蘇練練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建筑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2.都市發展設計集團有限公司,遼寧 大連 116011;3.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廣東 深圳 518055)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歷了快速城鎮化發展階段,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增加到2020年的64%.快速的城鎮化不僅推動了社會經濟與城鄉建設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城鄉發展問題.在城鄉規劃方面,理論上,隨著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大量的鄉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與之對應的人均占地較大的鄉村建設用地理應向人均占地較小的城鎮建設用地轉化,全國城鄉建設用地總量應該逐步減少[1].然而,當前全國城鎮、鄉村以及城鄉建設用地總量均持續增長,鄉村建設用地向城鎮建設用地轉化的過程滯后于人口的城鎮化過程[2].從規劃的角度來看,表面上這一問題可能是城鎮發展過快、城鎮規劃控制不足導致,本質上其實是對鄉村規劃控制不足,城鎮與鄉村規劃缺乏聯動造成.因此,未來的規劃應更加關注并重視城鎮化過程中鄉村建設用地向城鎮建設用地的轉化.
在國外,空間規劃理論一直強調城鄉發展的聯動性.“田園城市”理論強調城鄉是一個發展共同體,理想的城市應該兼有城市與鄉村的優點[3].“城鄉連續體”[4]和“城鄉動力學”[5]等理論均強調城鄉的聯動發展.在國內,隨著城鄉統籌理念的提出,城鄉結構經歷了從城鄉二元到城鄉一元的轉變[6],雖然目前城鄉統籌的相關研究較多[7],但城鄉建設用地缺乏規劃統籌的現實問題依然嚴峻.
2019年5月,中央印發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若干意見》提出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來進行空間治理,統籌利用全域資源,這標志著國土空間規劃體系頂層設計和“四梁八柱”基本形成[8].在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視角下,國土空間規劃本質上是對全域資源要素的管控和統籌[9],既包括自然資源、生態資源、人文資源等的管控與統籌,同時也須關注城鄉資源要素的管控與統籌.國土空間規劃強調底線思維,注重規劃的戰略引領和剛性管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但是,我國不同地區發展差異大,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在不同地區可能發揮不同的作用.在發達地區,城市的國土空間總體格局基本成型,國土空間規劃側重空間管控和治理,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可能發揮的控制作用相對較弱;但是對于欠發達地區,國土空間規劃需要更側重空間統籌和發展,若沒有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將會影響空間發展的秩序和品質[10-11].而且,人均建設用地指標是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規劃抓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要求下,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理應發揮其應有的規劃價值.因此,實現城鄉資源要素的管控與統籌,既需要規劃理念的再認知與重視,也需要編制與管理模式的協同,以及管控技術方法的匹配.
1 問題提出
1.1 全國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均持續增長
從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來看,根據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歷年《城鄉建設統計年鑒》數據,1990年至2020年,我國城鄉建設用地總量增加了1 099.8萬 hm2.其中,2000年之前的縣城建設用地指標未納入城鎮建設用地指標,1990年至1999年,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了177.7萬 hm2,鄉村建設用地增加了188.6萬 hm2;2000年之后的縣城建設用地指標納入城鎮建設用地指標,2000年至2020年,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了722.8萬 hm2,鄉村建設用地只減少了111.2萬 hm2.總體來看,城鎮建設用地的增加量遠超鄉村建設用地的減少量,城鄉建設用地“城增村減”不協調的問題突出.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鄉建設用地總量持續增長,從表面上看可能是由于城鎮、鄉村數量的增長導致,實則不然.從城鎮、鄉村數量與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的關系來看,城鎮數量對于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的影響雖然大于鄉村數量對于鄉村建設用地總量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只主要體現在城鎮發展的前期階段.在城鎮層面,1990年至1999年,城鎮數量增加了0.7萬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了177.7萬 hm2,城鎮建設用地總量與城鎮數量呈正相關,這個階段,城鎮數量對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影響較大;2000年至2020年,城鎮數量較穩定,而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增加了722.8萬 hm2,這個階段,城鎮數量對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影響較小.在鄉村層面,1990年至2020年,鄉村數量減少了144.1萬個,但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卻增加了84.6 萬 hm2,鄉村數量的增減與鄉村建設用地總量的增減基本無關(如圖1).
從每個城鎮、鄉村自身建設用地面積與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的關系來看,在城鎮層面,城鎮自身建設用地面積的增長對于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增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2000年以后,2000年至2020年,平均每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從2000年的242.7 hm2/個增加到2020年的578.6 hm2/個;在鄉村層面,鄉村自身建設用地面積的增長對于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增長的影響在2000年前后均體現明顯,1990年至2020年,平均每個鄉村建設用地面積從1990年的3.3 hm2/個增加到2020年的5.6 hm2/個(如圖2).因此,每個城鎮、鄉村自身建設用地面積均增長是造成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增長的主因.

圖2 1990—2020年全國平均每個城鎮、鄉村建設用地面積與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統計圖
1.2 全國城鎮、鄉村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均“超標”
城鄉建設用地統籌的本質是平衡城鄉人口對于城鄉建設用地的需求.探究城鎮、鄉村建設用地配比是否符合城鎮、鄉村人口的需求,一般需根據城鎮、鄉村人均建設用地指標來衡量.根據《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50137-2011)》(以下簡稱“《標準》”),我國城市(鎮)的規劃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在65.0 m2/人至115.0 m2/人之間;目前,鄉村規劃的人均建設用地指標雖未有明確標準,但一般情況下規劃控制在150 m2/人以內.
僅從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指標來看,根據歷年《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的戶籍人口和建設用地數據,城鎮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的“超標”量遠高于鄉村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的“超標”量,城鎮的問題看似大于鄉村.在城鎮層面,城鎮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由2000年的123.6 m2/人增加到2020年的198.5 m2/人,增加了74.9 m2/人;在鄉村層面,鄉村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由2000年的166.2 m2/人增加到2020年的166.8 m2/人,增加了0.6 m2/人.以2020年為例,城鎮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比《標準》中規劃允許的最大城鎮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多83.5 m2/人;鄉村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比最大鄉村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多16.8 m2/人.城鎮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超標”量是鄉村戶籍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超標”量的近5.0倍(如圖3).

圖3 2000—2020年全國城鎮、鄉村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和城鎮化率統計圖
但是,在真實“人地對應”的情況下,即從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指標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的常住人口數據和歷年《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的建設用地數據,鄉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的“超標”量遠高于城鎮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的“超標”量,鄉村的問題實則大于城鎮.在城鎮層面,城鎮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從2000年的107.0 m2/人增加到2020年的134.6 m2/人,增加了27.6 m2/人;在鄉村層面,鄉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從2000年的178.9 m2/人增加到2020年的261.8 m2/人,增加了82.9 m2/人.以2020年為例,城鎮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比《標準》中規劃允許的最大城鎮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多19.6 m2/人;鄉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比最大鄉村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多111.8 m2/人.鄉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超標”量是城鎮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超標”量的約5.7倍(如圖3).因此,鄉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的嚴重“超標”是城鄉建設用地規劃統籌的關鍵.
1.3 全國城鎮、鄉村建設用地增減率與城鎮、鄉村人口增減率不協調
從增長率的角度來看,我國建設用地增減率與人口增減率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反映在用地指標上是“地隨人走”不協調,人均建設用地面積過快增長.從城鄉整體層面來看,城鄉建設用地總量的增減率與城鄉人口的增減率不協調.2000年至2020年,城鄉建設用地總量增加了611.6萬 hm2,年均增長率為1.3%;城鄉總人口增加了1.4億,年均增長率為1.8%.倘若將新增城鄉建設用地平均分給新增人口,那么每個新增人口將會分到436.9 m2的城鄉建設用地,其人均建設用地面積遠遠超過城鎮、鄉村規劃所允許的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最大值.
從城鎮、鄉村各個層面來看,城鎮、鄉村建設用地增減率與城鎮、鄉村人口增減率均不協調,而且兩者的不協調程度存在差別.在城鎮層面,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年均增長率為4.3%,城鎮常住人口總量年均增長率為3.4%,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年均增長率是城鎮常住人口年均增長率的近1.3倍.在鄉村層面,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年均減少率為0.3%,鄉村常住人口總量年均減少率為2.1%,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年均減少率是鄉村常住人口年均減少率的約14.3%.從增減率的不協調程度來看,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年均增減率與鄉村常住人口年均增減率的不協調程度更大.因此,整體來看,城鎮、鄉村建設用地增減率與城鎮、鄉村人口增減率不協調的問題主要源于鄉村層面(如圖4).

圖4 2001—2020年全國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增減率與城鎮、鄉村人口增減率統計圖
由于《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的2003年、2006年的部分數據缺失,以上統計計算中,2003年與2006年的相關數據未納入統計計算.
2 原因探析
2.1 城鎮化世界范式的差異落位
城鎮化作為社會發展的過程,具有一般規律.但是,因為各國城鎮化開始的時間不同,所以其又具有不同的特征.范式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一種與傳統認識論不同的科學發展模式[12].城鎮化的范式是英、美等較早開始城鎮化的西方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世界范式,這里的城鎮化世界范式指: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鄉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與之相匹配的人均占地較大的鄉村建設用地指標轉化為人均占地較小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且城鄉建設用地總量指標逐漸減少.以揭開城鎮化序幕的英國為例,它引領了世界性城鎮化的大潮.英國城鎮化的快速提升與工業革命和“圈地運動”有密切的關系[13].工業革命時期,城鎮中的工廠亟需大量的勞動力,大批的農村人口涌向城鎮,同時“圈地運動”迫使大量的農村人口失去土地,進入城鎮謀生,他們無法再回到農村生活,這使得英國城鎮人口激增,城鎮用地規模迅速增長.因此,在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人口的城鎮化基本與土地的城鎮化同步.
我國的城鎮化與西方的城鎮化存在較大區別,其主要區別源于以外出農業人口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在城鎮和鄉村同時被賦予建設用地,導致城鎮、鄉村建設用地總量都在增大.從城鎮層面來看,我國城市規劃中城鎮建設用地面積依據常住人口進行規模預測,常住人口包含所有戶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14],其中,外出農業人口是流動人口的主要來源,所以這部分外出農業人口在城市規劃中被賦予城鎮建設用地.以我國外出農民工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逐年增長,外出農民工被賦予的城鎮建設用地面積也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如圖5).其中,2019年全國外出農業人口中的外出農民工總量為17 425萬人.假如人均城鎮建設用地面積按100.0 m2/人計算,那么在城鎮規劃中2019年外出農民工會被賦予城鎮建設用地174.3萬 hm2(17 425 km2);如果按2019年全國現狀常住人口人均城鎮建設用地面積139.3 m2/人計算,那么2019年外出農民工被賦予城鎮建設用地242.7萬 hm2(24 273 km2).

圖5 2010—201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和外出農民工被賦予城鎮建設用地統計圖
從鄉村層面來看,我國城鄉二元的社會保障體制具有保障農民基本生活的制度優勢,外出農業人口一旦在城鎮中無法生活,還可以再回到鄉村,但同時存在鄉村宅基地短期內無法退出的缺點.鄉村規劃中鄉村建設用地面積也依據常住人口進行規模預測,鄉村的常住人口主要為鄉村戶籍人口,包含了外出農業人口,相應的外出農業人口在鄉村規劃中也被賦予鄉村建設用地.2010—2019年,外出農民工被賦予的鄉村建設用地面積也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如圖6).假如人均鄉村建設用地面積按150.0 m2/人計算,那么在鄉村規劃中2019年外出農民工會被賦予鄉村建設用地261.4萬 hm2(26 138 km2);如果按2019年全國現狀常住人口人均鄉村建設用地面積244.4 m2/人計算,那么2019年外出農民工實際被賦予鄉村建設用地425.9萬 hm2(42 587 km2).目前,外出農業人口數量總體趨勢還在增加,未來外出農業人口還會同時被賦予更多的城鎮、鄉村建設用地,而且相比于城鎮建設用地,鄉村建設用地將增加的更多.

圖6 2010—201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和外出農民工被賦予鄉村建設用地統計圖
2.2 鄉村規劃沿襲城市規劃的增量模式
城鎮和鄉村擁有和而不同的系統組成,規劃既應強調它們的統一性,也應關注它們的差異性.一方面,城鎮和鄉村都是承載居民生活的空間,理論上,城鄉之間本應相互聯系、相互依賴,規劃應該把城鎮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考慮,但以往“就城市論城市、就鄉村論鄉村”的城鄉二元規劃體系,沒有把城鎮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來關注,規劃缺乏城鎮和鄉村的協調聯動.另一方面,受發展要素和動力機制的影響,城鎮和鄉村擁有各自的特點,不能簡單等同視之.其一,城鎮和鄉村發展的核心要素不同.城鎮是第二、三產業的主要載體,通過優化城鎮布局結構和形態可以極大地促進產業發展,從而推動城鎮的快速發展;然而,鄉村發展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資源,鄉村的產業發展主要依附在居民點以外的非建設用地,居民點主要是農民的生活空間,并非產業的主要載體[15].其次,城鎮和鄉村發展的動力機制不同.城鎮發展主要依靠自身強大的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但對鄉村而言,鄉村發展主要在于提高農業科技化和機械化水平.
增量規劃是以往城市規劃的主要類型,是以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為主要目的,是政府調控地方經濟增長的重要空間手段[16],但以往很多鄉村規劃沿襲城市規劃的增量模式,導致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和人均鄉村建設用地面積都在增大.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鄉村人口不斷轉化為城鎮人口,與之對應的鄉村建設用地總量理應不斷減少.但是,很多鄉村規劃通過產業規劃或旅游開發等城市增量規劃模式不斷增加鄉村建設用地,造成鄉村建設用地總量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城鎮擁有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大量的農民離開鄉村進入城鎮工作生活,他們雖然長期居住在城鎮,但是其鄉村宅基地并未有序退出;同時,受我國傳統宅基地觀念的影響,農民對宅基地特別重視,為了擁有更多的宅基地,鄉村“一戶多宅”現象仍然存在,這進一步導致人均鄉村建設用地面積嚴重“超標”.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此來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但鄉村振興的本質絕不是沿襲城市規劃的增量模式,而是強調通過價值認知、布局優化、產業振興、生態宜居和鄉村治理方法和路徑消除貧富差距,改善民生,促進城鄉融合[17].城鎮和鄉村是一個共同體,要實現鄉村振興,就必須轉變類似以往城市增量為主的發展模式,重視鄉村的多元價值.鄉村不僅是農民生活的聚居地,還具有生態功能、文化功能、經濟功能、社會功能等,鄉村規劃應充分挖掘鄉村的空間基因[18],探討適合鄉村自身的規劃模式,提升鄉村的活力,從而實現鄉村振興.
2.3 城鄉規劃控制重城鎮輕鄉村
針對城鎮化過程中存在的城鄉建設無序蔓延的問題,規劃管理部門往往將問題的根源歸結于城鎮,因此通過各種方式控制城鎮建設,卻在較大程度上忽視了鄉村建設的控制.從以往的規劃類型來看,在城鎮層面,城鎮建設受到多種規劃的制約,城鎮未來的建設量往往小于城鎮的規劃規模.在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之前,一個城鎮或地區的建設發展直接受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規劃的約束,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城鎮的建設規模.例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城鎮建設用地進行指標約束,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著城鎮建設用地的規模,以此控制城鎮的實際建設,使城鎮的實際建設量一般要少于城市總體規劃的規劃量.在鄉村層面,雖然鄉村也有很多規劃類型,例如鄉村建設規劃、美麗鄉村規劃等等,但大部分鄉村規劃相互制約關系不足,缺乏對鄉村的規劃指標控制.
從城鄉規劃控制的方法來看,城市規劃擁有眾多開發邊界控制方法,但鄉村規劃卻缺少開發邊界的控制.我國城市規劃早期借鑒“綠帶”方法來限制城鎮空間無序蔓延,后續通過劃定“規劃區”、“城市增長邊界”等,以限制城鎮建設用地規模[19].以往規劃中的邊界控制方法主要對城鎮建設用地進行管控,未能將鄉村建設用地納入管控范圍.而且,我國鄉村規劃起步較晚、規劃編制體系相對不夠完善,這加劇了鄉村規劃控制方法缺失的問題.從城鄉規劃控制的管控難度來看,因為城鎮比鄉村擁有更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所以鄉村建設用地的管控難度一定程度上要高于城鎮[20],這也加劇了鄉村規劃控制的難度.
從城鄉規劃控制的效果來看,經過近些年的研究和實踐,城鎮規劃控制取得了一定成效,而鄉村規劃控制相對滯后.以陜西省為例,從城市層面來看,根據住房與城鄉建設部《2020年城鄉建設統計年鑒》數據,陜西省主要城市中心城區2020年實際常住人口規模約為1 190萬人;根據相應城市之前的總體規劃數據,規劃2020年中心城區常住人口規模約為1 253萬人.由此可見,陜西省主要城市2020年實際常住人口規模尚未突破規劃2020年人口規模.同時,2020年相應城市的現狀城市人均建設用地面積約為113.1 m2/人,并未突破《標準》中規定的規劃最大人均城市建設用地指標115.0 m2/人.因此,陜西省主要城市的城市建設用地面積還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反觀鄉村,陜西省鄉村常住人口數從2017年的1 950萬人減少到2020年的1 912萬人,但是鄉村建設用地總量卻從2017年的34.2萬 hm2增加到2020年的36.4萬 hm2,人均鄉村建設用地面積從2017年的175.2 m2/人增加到2020年的190.2 m2/人,遠超鄉村規劃最大人均鄉村建設用地指標的150.0 m2/人.總之,由于以往城鄉規劃的控制重城鎮輕鄉村,導致鄉村規劃控制不足.
3 國土空間規劃中對城鄉建設用地統籌的相關思考
3.1 深化城鄉統籌思維
針對長久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壁壘,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城鄉統籌思想,來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基于城鄉統籌,形成新型城鄉關系;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進一步強調了城鄉融合發展;黨的二十大提出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目前,國土空間規劃本質上是一定程度的“多規合一”[21-22],城鄉統籌思想是“多規合一”的理念來源與實踐起點,是解決城鄉問題的有效途徑,更是立足當前,著眼未來的戰略選擇[23].因此,針對城鄉建設用地統籌面臨的鄉村規劃控制不足的問題,城鄉統籌作為解決城鄉問題的有效途徑,理應繼續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國土空間規劃中,需要進一步深化城鄉統籌思維,強化城鎮與鄉村的整體性與時序性.一方面,國土空間規劃需要秉持城鄉整體觀.城鄉整體觀就是注重城鄉空間的完整性,在充分認識到鄉村地區的重要性的同時,重新認識和合理界定城鄉空間,淡化城鄉行政界限[24];改變過去城鄉分離的規劃思維,注重城鄉之間規劃的整體性與指標的聯動性.另一方面,國土空間規劃需要秉持城鄉時序觀.城鄉時序觀就是秉持城鄉動態規劃思維,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城鎮和鄉村.城鎮與鄉村作為時時刻刻進行信息交流以及資源轉換的兩種不同類型生活空間,城鄉建設用地統籌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需要摒棄傳統的“藍圖”思維,重視城鄉的發展過程,推動城鎮建設用地和鄉村建設用地之間的良性流轉.此外,國土空間規劃還要注重城鄉整體三生空間的時序變化關系,需要強調城鄉建設用地統籌與生態空間、農業空間的聯動性,用分期分階段的動態發展思維協調城鄉整體三生空間,以此實現國土空間整體的優化.
3.2 完善建設用地指標
國土空間規劃注重全域資源要素的管控和統籌,還需要進一步關注城鄉人口與建設用地指標的跨區域流動問題.城鎮化過程中人口的流動不局限于行政邊界,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但是建設用地并不能隨人口的流動而流動,這就導致上述以外出農業人口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在城鎮和鄉村同時被賦予建設用地,城鄉建設用地總量不斷增長的問題.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關注了此問題,并出臺了相關政策.例如,2021年0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城鄉建設用地增加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管理辦法》,從此揭開了城鄉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流動的序幕.未來,城鄉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流動應注重人和產業的發展需求,真正實現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相匹配.因此,國土空間規劃需要進一步關注城鎮化過程中城鄉指標的跨行政區流動和與之存在的問題.
人均建設用地指標是以往城鄉規劃最重要的規劃抓手,其是定量配置國土空間資源的有效方法,這一以人為本的配置方法具有科學合理性、公平正義性和管理彈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的生活空間品質,這就意味著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具有公共品的特征,是城鄉居民的一項基本權利[25].雖然國土空間規劃弱化了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問題,但是從以人為本的思想、地區發展的差異、城鄉關系的差異等方面來說,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理應繼續發揮其應有的規劃作用.因此,國土空間規劃需要重視人均建設用地指標的控制.
3.3 優化管控技術方法
規劃控制技術方法是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無序蔓延的空間管控工具.傳統規劃管控技術方法,如“規劃區”、“城市增長邊界”等,雖然擁有各自的優點,但是也擁有共同的缺陷:其一,它們的提出都是針對城鎮規劃控制的問題,只重視了城鎮的規劃控制,卻忽視了鄉村的規劃控制,導致對鄉村的規劃控制嚴重不足.其二,它們在進行規劃控制時沒有關注城鄉建設用地指標流動的問題,沒有將城鎮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來關注,導致城鄉建設用地指標流動失去平衡,城鎮、鄉村建設用地面積都在增加.其三,它們都是對生活空間中城鎮建設用地進行的控制,忽視了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農業空間的關系.目前,國土空間規劃要求科學劃定“三區三線”來進行國土用途管制,總體的政策目標很明確,統籌了生活空間與生態空間、農業空間的關系,但是當前劃定城鎮開發邊界所使用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對傳統規劃中相關邊界控制方法的延續與疊加,依然忽視了鄉村規劃控制的問題.而且,“三區三線”的劃定把城鎮和鄉村分割,城鎮屬于城鎮空間,鄉村卻被劃到了農業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鄉二元化.國土空間規劃的思想內涵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從管控技術方法上來看,“三區三線”的工具理性應與城鄉統籌的價值理性相協調.
在國土空間規劃中,解決城鄉建設用地控制不足的問題須在汲取傳統規劃管控技術方法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關注城鎮、鄉村建設用地指標的流動過程,采用“人地對應”相協調的集約式規劃方法,優化“三區三線”管控技術.一方面,加強規劃管控技術方法的整體性.管控主體不只是城鎮,而是城鎮、鄉村的統一體,將鄉村納入管控范圍,劃定城鄉建設用地管控邊界線,統一、同步管控.另一方面,加強規劃管控技術的動態性.規劃管控技術應淡化時間界限,通過分期、分階段調整三生空間管控范圍和規劃協調城與鄉的聯動變化關系[26].同時,規劃管控技術在城鄉建設用地中也要預留彈性空間,可通過“預留用地不定性”、“預留指標不落地”[27]等方法保證城鄉建設用地的底線指標.
4 結語
習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當前我國存在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不匹配、城鎮與鄉村建設用地規劃控制不足的問題,其本質源于城鎮和鄉村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品質存在較大差異,人民被動“兩棲”于城鎮和鄉村.解決問題的關鍵便在于提升鄉村的收入水平,改善鄉村的生活品質,使生活在鄉村的人民能同等享受城鎮般的生活品質.城鎮與鄉村都存在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空間代碼與秩序,城鄉統籌就是要遵循城鄉發展的各自內在秩序,使城鄉達到同等的生活品質,以便人民自由選擇定居在城鎮或鄉村.誠然,城鄉建設用地控制不足的問題不僅僅是城鄉統籌的問題,還需從戶籍制度、城鄉土地政策等多方面進行更為深入地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