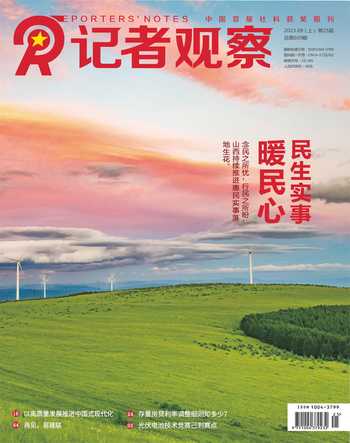張福鎖:讓科技小院扎根鄉(xiāng)土中國
朱一鳴 陳藝嬌


歷史的改變總是在不經(jīng)意間發(fā)生。
2021年10月,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灣橋鎮(zhèn)古生村度假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教授張福鎖,在偶然間碰到的一位騎行客牽線搭橋下,與大理州人民政府就推動洱海流域綠色轉(zhuǎn)型達成共識。同年,張福鎖帶領(lǐng)團隊從北京出發(fā),一路向南,在蒼山腳下、洱海之濱的古生村駐扎下來。
高原明珠洱海,湖泊面積252平方公里,是云南第二大高原淡水湖。從20世紀80年代起,受到長期過度開發(fā)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洱海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嚴重破壞和污染,水質(zhì)逐年下降,從貧營養(yǎng)狀態(tài)轉(zhuǎn)向富營養(yǎng)狀態(tài),曾經(jīng)風(fēng)光旖旎的洱海在20世紀90年代有過兩次藍藻暴發(fā)。
當(dāng)時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除了周邊旅游無序開發(fā)、非煤礦山生態(tài)破壞等,農(nóng)田面源污染也是重要原因。洱海流域農(nóng)民大水大肥的種植模式產(chǎn)生了大量富含氮磷的農(nóng)田尾水,這些尾水順著溝渠最終流入洱海,造成污染。
“從全球來看,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很多國家都還要大幅度地發(fā)展,但是資源不能再被浪費,環(huán)境不能再被污染。”張福鎖說,“中國正處在綠色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時期,如果我們能在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進一步提升的同時,減少投入、污染,那我們就是全世界綠色發(fā)展里最好的樣板。”
正是為此,2022年,由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和大理州人民政府三方共建的古生村科技小院正式揭牌,一場從生產(chǎn)到生活、生態(tài)的根本性嬗變在古生村迤邐展開。
接地氣的科技小院
提起科技小院,很多人并不陌生。2009年,張福鎖帶領(lǐng)團隊在河北省曲周縣創(chuàng)建了第一個科技小院,為農(nóng)民提供“零距離、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的科技服務(wù),在生產(chǎn)一線開展科技創(chuàng)新、社會服務(wù)和人才培養(yǎng),推動教書與育人、田間與課堂、理論與實踐、科研與推廣、創(chuàng)新與服務(wù)更緊密地結(jié)合。
科技小院,名從何來?這源于張福鎖的一次特殊實踐。有一次,團隊住在曲周縣一位農(nóng)民閑置的小院里,附近的村民遇到生產(chǎn)難題,都會來小院里問。“早上在地里看見葉子被蟲子咬了,他就摘一片葉子回來,把我們從被窩里叫起來,問這是怎么回事。晚上沒事,他們也跑到院子里聊天。我們那個小院后來成了村里面的活動中心。”張福鎖說,“后來村民就說,你們搞科技,把科技帶到農(nóng)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張福鎖覺得這個名字很好。“太接地氣了。”
如今,全國已建立1048個科技小院,覆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涉及222種農(nóng)產(chǎn)品,覆蓋國民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行業(yè)中農(nóng)林牧漁業(yè)的59個產(chǎn)業(yè)體系。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關(guān)于支持建設(shè)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68個培養(yǎng)單位建設(shè)780個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風(fēng)風(fēng)雨雨走過15年,張福鎖和他的團隊逐漸在實踐中形成了“科技小院精神”,在古生村的實踐中尤為明顯。
入駐古生村初期,張福鎖團隊了解洱海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舉措以及實際成效后,心中不禁泛起疑問:農(nóng)田面源污染對洱海水質(zhì)的影響真的有那么大嗎?
為精準解析洱海流域面源污染源特征,張福鎖團隊劃定兩個行政村、六個自然村為古生片區(qū),北起蒼山十八溪之一的陽溪,南至古生南路。在4.8平方公里范圍內(nèi)設(shè)六條面源污染產(chǎn)生過程縱線、七條污染負荷水質(zhì)響應(yīng)橫線,涵蓋面源污染排放—輸移—入湖全過程,形成“六縱七橫”面源污染動態(tài)監(jiān)測體系,監(jiān)測網(wǎng)涵蓋村莊、農(nóng)田、溝渠、濕地等單元。同時,創(chuàng)新性提出針對高原湖泊典型地貌的面源污染測算方法,評估農(nóng)田和村落面源污染對入湖氮磷負荷的影響。
“去年以來,開展水質(zhì)同步監(jiān)測90多次,投入人員1000多人次,分析備類指標2萬余個,揭示了面源污染對地表水質(zhì)的影響,基本摸清了面源污染的排放特征。”張福鎖團隊成員、古生村科技小院面源污染精控平臺負責(zé)人、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副教授許穩(wěn)表示,通過多源頭、全過程監(jiān)測和全系統(tǒng)考量,得出結(jié)論,農(nóng)田面源污染“貢獻”55%左右的入湖氮磷負荷,而村落面源污染“貢獻”約為40%。這就要求開展農(nóng)田面源污染防控的同時,加強村落面源污染防控。
在數(shù)據(jù)支撐下,面源污染排放特征逐漸清晰,為接下來的科學(xué)精準防控打下堅實基礎(chǔ)。而“六縱七橫”體系的構(gòu)建以及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的獲得,實屬不易。在沒有啟用智能化監(jiān)測前,團隊對雨水都是人工采樣。只要下雨,不管白天黑夜,科技小院的師生都會拎上監(jiān)測用具,穿上雨衣,腳蹬雨靴,騎著電動車奔向監(jiān)測點,而這一測就是一年。
提及科技小院師生不畏艱苦、持之以恒的科研品格,張福鎖倍感欣慰:“科學(xué)成就離不開精神支撐,這其中就包括堅持精神。即使科研路上荊棘遍布,認準的路,別問多苦,接續(xù)走下去,遲早會見曙光。”
科技創(chuàng)新一定要進入產(chǎn)業(yè)
弄清楚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后,張福鎖團隊著手開展轟轟烈烈的綜合防控。
古生村科技小院致力于推動洱海流域綠色轉(zhuǎn)型,旨在洱海水質(zhì)提升和農(nóng)業(yè)提質(zhì)增效。于是,圍繞面源污染防控,張福鎖團隊提出源頭減排、過程攔截、退水收集與回用的總思路。
為做好源頭減排工作,張福鎖和團隊成員列出“四個清單”。土壤清單用來精準把控區(qū)域內(nèi)土壤中養(yǎng)分基本情況;作物清單則在摸清土壤營養(yǎng)成分基礎(chǔ)上,選取既能保值高產(chǎn)、又不污染環(huán)境的適宜作物;用肥清單和用水清單則依據(jù)作物的需求量選取綠色智能肥,精準控制水量,減少排放。
農(nóng)田面源污染防控初期,張福鎖團隊依托積累的科技創(chuàng)新理論,沿用科技小院一貫使用的測土技術(shù),測定土壤中氮磷等指標含量,然后根據(jù)不同作物不同階段的養(yǎng)分需求,設(shè)計適應(yīng)作物在當(dāng)?shù)厣L所需的綠色智能肥。一旦作物實現(xiàn)養(yǎng)分充分吸收,那么排到洱海的氮磷等數(shù)量就會減少。
“我們的科技創(chuàng)新一定要進入產(chǎn)業(yè),要進入主戰(zhàn)場,你在那兒會有用不完的勁兒、會不斷地去創(chuàng)新,不像在實驗室里做了半天,自己也不知道有沒有突破,然后越做越?jīng)]信心。”張福鎖說,“在主戰(zhàn)場上,生產(chǎn)實踐會天天給你提各種問題,并且對于你的任何嘗試和突破,它都會激勵你、鼓勵你。”
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副校長、洱海流域農(nóng)業(yè)綠色發(fā)展研究院常務(wù)副院長趙正雄介紹,通過一年實踐,團隊使用綠色智能肥成效顯著,達到初期減排目標,同時也實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節(jié)本增效。
不僅在古生村,張福鎖對于科技創(chuàng)新與生產(chǎn)實踐要緊密聯(lián)結(jié)的思想貫穿始終。“對小農(nóng)戶來說,最關(guān)鍵的是技術(shù)到位率,對農(nóng)場企業(yè)而言,最關(guān)鍵的是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他總結(jié)道。
有一年,張福鎖帶領(lǐng)團隊在河北的一個縣里做試驗推廣,他們先把新的品種帶到田間地頭,帶著技術(shù)和農(nóng)民一起千。剛開始,當(dāng)時的縣長對試驗的情況和背景不了解,對他們推廣的品種和技術(shù)并沒有重視起來。等到玉米快要成熟的時候,這位縣長在村里就被農(nóng)民拉住了,老百姓掰下玉米棒子和他講:“我自己的玉米棒子芯很粗、種子短,科技小院的玉米棒子的芯很細、種子長,產(chǎn)量肯定高。”
經(jīng)此一事,縣長的觸動很大。不僅當(dāng)場給張福鎖打了電話,還在第二天全縣的現(xiàn)場會上,要求每個鄉(xiāng)鎮(zhèn)做一個百畝的示范方,在全縣推廣。4年后,農(nóng)民因為小麥玉米增收能多賺3億多元,這個縣后來也成了全國糧食生產(chǎn)先進縣。
“事實上,農(nóng)技推廣我們搞了那么多年,為什么搞不好?關(guān)鍵還是能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張福鎖是這樣說的,科技小院團隊也是這樣做的。
到田間去培養(yǎng)人才
提起科技小院精神的來源,張福鎖頗為感慨:1973年,周恩來總理作出“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qū)水利資源合理開發(fā)利用”的指示。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即現(xiàn)在的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石元春、辛德惠等教師奔赴曲周縣,開展黃淮海平原科學(xué)治堿大會戰(zhàn)。“治理不好鹽堿地,我們一輩子不走。”面對白茫茫的鹽堿地和曲周人民期盼的目光,老一輩農(nóng)業(yè)科學(xué)家立下錚錚誓言,把一生獻給了農(nóng)業(yè)、獻給了曲周大地,被譽為“改土治堿、造福曲周”的功臣。
為了把科技小院精神繼承和延續(xù)下去,張福鎖高度重視科技小院農(nóng)業(yè)人才成長。他認為,實現(xiàn)中國農(nóng)業(yè)騰飛,一代人兩代人是不夠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農(nóng)業(yè)英才接續(xù)千。
在實踐中總結(jié),在總結(jié)中求突破。科技小院成立15年來,張福鎖帶領(lǐng)團隊已經(jīng)建立起面向農(nóng)業(yè)綠色發(fā)展的知農(nóng)愛農(nóng)新型人才培養(yǎng)體系。今年,科技小院人才培養(yǎng)模式榮獲高等教育(研究生)國家級教學(xué)成果特等獎。
金可默是張福鎖團隊成員、古生村科技小院負責(zé)人、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副教授,她來古生村前,通過前期文獻搜集,準備帶領(lǐng)學(xué)生研究古生村一二三產(chǎn)業(yè)融合。來了之后,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古生村土地已經(jīng)流轉(zhuǎn)給公司,有二產(chǎn)挖掘潛力的只有村民自家腌菜,但將毫無產(chǎn)業(yè)基礎(chǔ)的腌菜培育成一個產(chǎn)業(yè),談何容易。至于三產(chǎn),古生村在旅游資源方面有一定優(yōu)勢,可僅僅依靠三產(chǎn)去做一二三產(chǎn)業(yè)融合,課題研究很難開展。那時,張福鎖就引導(dǎo)他們?nèi)ジ迕翊蚪坏溃叭绻习傩詹恍湃文悖闼械南敕ǘ己茈y落地”。依此思路,金可默帶領(lǐng)學(xué)生深入群眾,了解需求,圍繞洱海保護、鄉(xiāng)愁文化振興等內(nèi)容開展針對性的社會化服務(wù)和科研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對此,張福鎖團隊成員,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國家農(nóng)業(yè)綠色發(fā)展研究院博士后李亞娟深有感觸:“剛來的時候,學(xué)生和村民是路人,開展社會化服務(wù)后,村民有什么難題,會主動找學(xué)生,有什么好吃的,也會叫上學(xué)生,反過來關(guān)系的融洽也讓學(xué)生的駐村工作更容易開展。”
“農(nóng)村迫切需要農(nóng)大學(xué)生,農(nóng)大學(xué)生同樣也離不開農(nóng)村,要扎根農(nóng)村,到田間去、到群眾中去。不開展調(diào)查研究,科研活動范圍局限于學(xué)校,信息僅來源于文獻,很難做出對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和鄉(xiāng)村振興有推進意義的事情。”張福鎖說。
在采訪中,張福鎖提到這樣一件事。香港浸會大學(xué)農(nóng)學(xué)專業(yè)成立之初,招了15個人,邀請他做人才培養(yǎng)的經(jīng)驗分享,張福鎖就講了科技小院的故事。當(dāng)時,一個老教授舉手說:“張教授,我?guī)Я艘惠呑訉W(xué)生,我怎么感覺你的碩士生比我的博士生還厲害。”
“后來我想,不是我的碩士生比你的博士生厲害,是科技小院這個平臺比你的實驗室厲害。”他說,因為在村里,學(xué)生既可以向農(nóng)民學(xué)習(xí),也可以向企業(yè)的技術(shù)人員學(xué)習(xí),還能向老師學(xué)習(xí),很快就會是個“萬金油”,“學(xué)生在這里掌握的都是實戰(zhàn)經(jīng)驗,是綜合知識,不那么單一,能解決問題。”
培養(yǎng)學(xué)生,張福鎖的辦法之一就是讓學(xué)生給農(nóng)民做培訓(xùn)。
有一次,張福鎖的學(xué)生第一次給村民培訓(xùn),培訓(xùn)結(jié)束后,張福鎖問他講了什么,他卻說不知道,而且腿都在發(fā)抖。“這是很正常的。等講上幾次,學(xué)生就能把內(nèi)容搞清楚,弄明白,差不多一年多時間就能完成這個轉(zhuǎn)變。”張福鎖表示。
“小院給了作為老師的我們一個思考,那就是大學(xué)教育的問題在于,我們把什么都給學(xué)生弄得很好,連答案都想直接告訴他們,結(jié)果把鍛煉的機會全給弄沒了,學(xué)生反倒成長不起來。把苗子扔到角落上沒怎么照料,結(jié)果最后長成參天大樹了,反而是天天澆水會把苗子淹死,這就是教育的規(guī)律。”張福鎖說。
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2022級博士研究生應(yīng)飛宇介紹,2022年,為做好科技示范引領(lǐng),他在導(dǎo)師叢汶峰的指導(dǎo)協(xié)調(diào)下,在灣橋鎮(zhèn)南莊村開辟了鮮食玉米綠色高值試驗田,自己當(dāng)農(nóng)民。一開始周邊農(nóng)戶并不認可應(yīng)飛宇的種田方式,“更何況還是一個學(xué)生娃,產(chǎn)量指定上不去”。然而,事實打破了所有質(zhì)疑。經(jīng)過測算,應(yīng)飛宇的試驗田產(chǎn)量比周邊有的“老把式”還要高出不少。應(yīng)飛宇順勢就把高產(chǎn)“秘訣”——綠色智能肥集成技術(shù)分享給農(nóng)戶。就這樣,今年應(yīng)飛宇已從單打獨斗變成帶領(lǐng)30多戶農(nóng)戶一起千。
應(yīng)飛宇對取得的成就很滿意,一掃剛來古生村時的迷茫無措。“剛來到科技小院的學(xué)生,基本上都會經(jīng)歷茫然期,這時候除了積極引導(dǎo),榜樣的力量至關(guān)重要。”張福鎖說,老師首先要做好表率,學(xué)生在與老師共同生活和工作的過程中,就會慢慢在內(nèi)心深處認同科技小院精神,繼而把握好接力棒,做好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