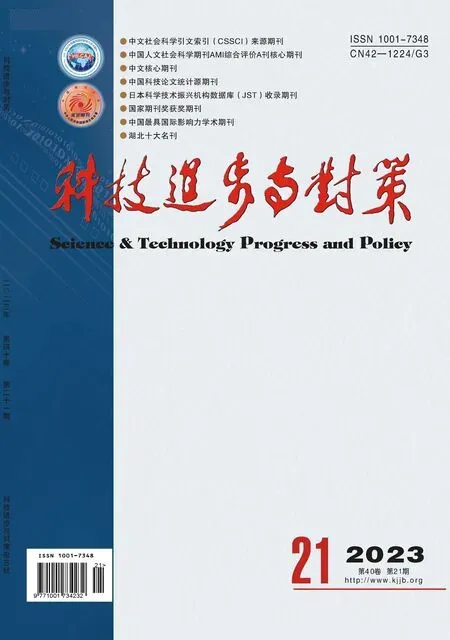數字技術嵌入下的創業生態如何提高青年創業績效
——基于混合方法的實證研究
孫俊華,萬 洋
(南京大學 教育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23)
0 引言
創業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徑,而青年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力軍。習近平總書記在致2013年全球創業周中國站活動組委會的賀信中強調,“全社會都要重視和支持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更有利的條件,搭建更廣闊的舞臺,讓廣大青年在創新創業中煥發出更加奪目的青春光彩”。新時代背景下,為打造經濟增長引擎、緩解勞動力就業市場壓力,青年創業行為具有一系列政策利好和發展空間。2022年,中宣部、教育部、人社部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試點的意見》,要求完善青年人才發現培養、評價使用、流動配置、激勵保障機制,倡導敬業、精益、專注、寬容失敗的創新創業文化,健全與新興產業相適應的包容審慎監管方式,打造近悅遠來的青年創業營商環境。2023年3月起,廣州市施行《廣州市青年創新創業促進條例》,成為城市探索青年創業立法的重大突破,以地方性法規為青年創業打造優質制度環境。然而,受制于創業經驗或者創業資源稟賦不足等問題,青年創業者往往會遭遇創業風險較高與創業可行能力較弱的困境[1],使得青年整體創業績效處于較低水平。根據《中國青年創業發展報告(2022)》,青年創業者主要面臨創業資金、社會資源以及知識能力儲備等方面的困難,導致超半數的青年創業者盈虧存在波動[2]。因此,作為青年創業的關鍵載體和資源框架,如何優化創業生態以提高青年創業績效,對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服務青年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創業生態是一種基于生態學理論和系統論視角的創業環境要素組合,強調創業行為作為構建在環境背景中的復雜社會過程,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主體影響,而創業過程中的主體間協同共生以及經濟社會價值實現的持久性成為創業研究者和創業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焦豪,馬高雅,2023)。值得注意的是,創業生態并非穩固不變,而是具有環境演化與主體互動特征。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打破了創業行為在空間、設施、資源等方面的限制,成為創業生態中極具活力的新要素。例如,數字創業平臺是典型的新型創業生態系統,其將數字技術嵌入外部生態環境,能夠系統整合有數字化需求的創業企業所需要素,使企業超越創業生態系統地理邊界,識別新的創業機會并對其進行開發和利用(魏江等,2023)。關于創業生態與創業績效間的關系,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的實證探究。如向賽輝和孫永河[3]圍繞規范的政府支持制度或寬容的創業文化等環境因素解釋創業者的創業績效。同時,數字技術發展創造出新的青年創業業態,《中國青年報》開展的“青年與數字經濟”調查顯示,75.1%的受訪青年愿意在數字經濟領域就業或創業[4]。然而,數字技術作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核心驅動力,在重塑創業模式、提振創業活力中的引擎作用以及與其它創業環境要素之間的耦合作用卻仍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5]。而且,關于青年創業行為的實證研究往往聚焦青年創業意愿,如胡元瑞等[6]基于社會互動視角發現,居住方式通過風險偏好、支出自由度和壓力預期的中介渠道顯著影響青年創業意愿,但對青年創業績效及其背后的驅動機制缺乏探究。此外,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獻多采用傳統計量方法考察創業績效的影響因素,關注某一創業環境要素與創業績效結果間的線性關系及其凈效應。這種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平均效應關系難以識別多因并發、因果非對稱等現實情境中的必要關系和充分關系[7],進而導致對青年創業績效形成機制中的復雜組態耦合作用存在認知“黑箱”。
綜上,盡管創業生態相關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但在數字技術嵌入情境、青年創業者對象以及組態分析方法上存在拓展空間。針對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借助創業生態理論,從傳統相對線性邏輯轉入多層次、多維度的系統邏輯,基于青年創業者的獨特性,構建數字技術、創業生態各要素與青年創業績效的理論模型,并采用回歸分析與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數字技術嵌入下創業生態驅動創業績效的作用機制和條件組態,對數字技術、創業生態與青年創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
1 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1.1 創業生態與青年創業績效
創業生態理論認為,創業主體通過創業行為與創業環境進行互動,其創業績效取決于創業環境中各類要素的可持續性與相互作用[8]。本文借鑒“政府—市場—社會”的三維主體互動框架[9],綜合考量創業政策中的政府主導邏輯、創業過程中的市場化取向以及創業行為的社會調控邊界,選取現有文獻重點關注的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作為創業生態的內涵與框架。
(1)政府政策反映政府對創業行為的規范與支持程度。政府規范制度與支持舉措作為完整創業生命周期中的關鍵要素,受到青年創業者廣泛關注,能夠為青年建立新創企業提供資源及政策扶持,對新創企業優化創業決策過程并獲取創業績效具有重要影響。在青年創業浪潮中,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經營輔導等政府支持行為不僅有助于激發青年創新意愿,而且對創業績效具有顯著影響[10]。此外,政府通過人才政策、產學研合作等方式營造良好的外部創新創業環境,不僅能為創業行為提供制度保障,也會對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產生顯著影響,并共同作用于青年創業者的創業績效(陳怡安,趙雪蘋,2019)。
(2)市場環境衡量創業活動是否擁有合理的市場需求、完善的融資服務、充足的人力資本等,能夠為創業行為提供各類外部資源。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能夠通過價格機制對經濟活動中的資源進行自發高效配置,并在資源調控過程中促成市場主體之間的學習互動和分工網絡,進而實現對發現型機會和創造型機會的識別開發,激發青年創業活力[11]。李新春等(2016)研究發現,地區市場化進程能夠弱化關系文化的制度約束,激發新創企業掙脫制度牢籠的戰略行動。在這一過程中,青年創業者通過掙脫制度束縛可以獲得更多決策自主權,同時破除企業結構同質性與戰略慣性,為新創企業發展帶來更多靈活屬性與競爭優勢。
(3)社會文化體現一個社會、地區以及群體對待創業及創業失敗的認同、支持和寬容程度。對于青年創業者而言,良好的社會文化能夠提供寬松包容的外部環境,其承載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建設路徑在培育青年創新創業精神中能夠發揮重要影響和輻射作用,并通過激勵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的學習和堅持行為幫助創業者深化創業信念、克服對創業失敗的恐懼心理(鄧建生,2000)。已有研究表明,高績效導向、高未來導向和高不確定性規避的現代主義文化與高期望創業活動、高創新創業活動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12]。而且,作為一種非制度化環境,社會創業文化能夠塑造創業作為一種市場經濟行為和個體發展活動的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有助于青年創業者在創業活動中更容易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資金與社會資源支持。這些都是取得高創業績效的重要因素(Stuetzer等,2018)。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a:政府政策正向影響青年創業績效;
H1b:市場環境正向影響青年創業績效;
H1c:社會文化正向影響青年創業績效。
1.2 數字技術與青年創業績效
在內涵和屬性上,數字技術是指嵌入在信息通信技術內或由信息通信技術支撐的產品或服務,包含數字組件、數字平臺和數字基礎設施等,其不僅具有數字程序、數據要素等應用功能性和產權專有性,也具備多主體參與、共享的開放性和關聯性(Nambisan,2017)。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技術創新由信息技術時代(IT)進入數字技術時代(DT)[13]。作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主導力量,數字技術正全面重塑創業活動中的商業模式、業務模型、組織結構等,并通過內部技術創新和外部要素嵌入兩種機制影響創業企業競爭優勢獲取和績效提高(Giudice &Straub,2011;Autio,2017)。
作為一種新生產力要素,數字技術能夠提高企業運行效率、管理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數字技術依托內部技術創新可以幫助新創企業打破企業成長面臨的結構性障礙并賦能青年創業績效(焦康樂等,2023)。在創業者個體層面,青年創業者通過發揮互聯網云平臺去中心化的特點,增強企業數字網絡的鏈接屬性,提升創業者識別創業機會的能力[14]。同時,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工具分析創業市場前景,為創業行為提供技術保障,從而使創業者針對性地選擇創業方向[15],提高創業預期收益。在企業發展層面,數字技術變革和創新能夠改變新企業創建和成長進程,與傳統技術驅動的簡單線性創業過程不同,數字技術具有可編程性和可重組性等特點,使產品/服務從生產到進入市場的全生命周期都呈現快速反饋的迭代過程,能夠極大壓縮創建新企業所需時間和資源成本[16]。此外,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能為青年創業活動的開展提供具有技術拓展性和跨域共享性等特征的全新商業模式及新興產業業態,如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等(Davies等,2017;王俊豪,周晟佳,2021)。青年群體作為互聯網原住民,更容易在數字經濟時代把握數字化創業機會并將其轉化為客觀可行的數字化產品與數字化服務,進而在極具復雜性和變革性的創業環境中獲取動態優勢。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數字技術正向影響青年創業績效。
在開放特性和關聯特征隨著互聯網技術變革日益凸顯的背景下,數據技術不僅能夠作為驅動創業績效的直接要素,也可以嵌入其它外部創業環境要素中,并通過良性協同機制提高青年創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首先,數字技術將原有創業過程中不可滲透、穩定的邊界轉變為日益滲透且流動的邊界,從而增強外部創業生態要素的可獲得性和資源整合屬性(Amit &Han,2017)。通過管理、制度和價值等途徑的多維互構,數字技術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政府、市場和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17],培育數字技術嵌入下的創業生態也成為推進創業實踐的重要趨勢。已有研究表明,在傳統創業生態要素相互競合從而推動新創企業價值實現的基礎上,新興數字技術嵌入與融合將改變原有創業活動的模式和邊界,并通過與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等創業資源建立緊密聯系,實施競合戰略,不僅培育自身核心發展能力,也能通過整合互補資源改善青年創業過程,創造更大價值[18]。其次,基于社會互動視角,數字技術在嵌入創業生態系統過程中,對創業活動的影響也會受到外部生態環境要素干預。對于采用數字技術的青年創業者來說,相關創業環境要素的政策互動和制度互動有助于降低數字技術運用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市場互動和資源互動有助于提高數字技術與潛在需求的匹配度并實現創業機會的客觀化和產品化,信息互動和社會網絡互動則有助于實現數字技術的知識溢出和多元主體智慧共創,最終將創業資源稟賦轉化為創業可行能力(段茹,李華晶,2020;郭潤萍等,2023)。換言之,高質量的創業生態可以提高數字網絡密度與強度,增強數字技術在創業活動中的聚合效應和賦能效應。由此,基于數字技術賦能與創業生態要素在提高青年創業績效過程中的協同驅動作用,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a:數字技術與政府政策在影響青年創業績效過程中存在交互促進效應;
H2b:數字技術與市場環境在影響青年創業績效過程中存在交互促進效應;
H2c:數字技術與社會文化在影響青年創業績效過程中存在交互促進效應。
1.3 數字技術、創業生態對青年創業績效的組態作用
在本文研究情境中,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因素具有多元性和復雜性,需要進一步探索數字技術嵌入下創業生態對提高青年創業績效的耦合機制。根據復雜系統觀,青年創業行為是一個涵蓋宏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微觀個體特征等多個層面要素的系統性過程(范冬萍,2008)。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等作為具有內部關聯的系統化生態要素,數字技術是典型的新興賦能要素,這些特征都可能使得青年創業過程呈現出無邊界和非線性特征(Fisher,2012)。例如,以政府政策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水平提升,不僅可以為青年創業行為提供重要資源扶持和制度保障,也有利于吸引金融資本、商業服務等市場資源要素集聚(唐開翼等,2021)。數字技術應用程度越高,越有助于通過數據要素、數字平臺等路徑增強政府政策、市場環境和社會文化等創業生態的驅動作用,進而提高青年創業績效。
然而,基于回歸的計量研究方法僅能識別創業生態、數字技術與青年創業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卻無法有效處理創業績效形成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非對稱性集合關系(如必要非充分條件和充分非必要條件)。雖然利用交互效應檢驗能夠識別數字技術與某一創業生態要素對青年創業績效的作用是否存在交互促進效應或交互抑制效應,但其本質仍是建立預測模型并通過顯著性分析少數變量間的依賴關系,在識別多要素驅動青年創業績效的耦合效應中存在局限。為揭示創業生態和數字技術等前因條件多重并發的影響,需要通過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深入挖掘所有關鍵因素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QCA從組態視角出發,關注因果非對稱性和組態等效性等復雜機制,能夠處理多因素互動而非獨立變量對提高青年創業績效的作用。因此,本文引入QCA方法,探究數字嵌入下創業生態對青年創業績效的耦合作用,提出如下假設:
H3:青年高創業績效并非單一創業生態或數字技術要素的產物,而是由多要素相互聯動、耦合構成的組態所驅動。
基于以上文獻回顧和理論分析,本文繪制回歸視角和組態視角下數字技術與創業生態共同影響青年創業績效的模型圖(見圖1)。

圖1 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綜合探討數字技術嵌入情境下創業生態對青年創業績效的驅動機制,通過回歸分析與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對各因素間的線性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解析。Teddlie&Tashakkori[19]指出,將回歸分析與QCA技術相結合,能夠在同一研究中同時回應驗證性和探索性問題,并由此檢驗和生成理論。回歸分析是一種基于自變量相互獨立、單向線性關系和因果對稱性的統計技術,假定關系具有恒定性、一致性、可加性和對稱性,關注自變量在總體中對結果變量的邊際凈效應(Net Effect)。QCA關注跨案例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包含多個相關條件組態引致結果以及多個不同條件組態產生同樣結果等邏輯關系,能夠為回歸分析結果提供更具情境性的解釋。作為綜合案例導向和變量導向的研究方法,QCA通過布爾最小化原理實現對案例的充分比較和分析,進而識別研究中相關要素的必要和充分因果關系。特別是在廣泛存在因果非對稱關系的現實情境中,QCA的優勢在于能夠剖析多種因素間互動過程對特定現象的聯動效應,并實現對回歸分析中線性和單向因果假定的突破[20]。相較于解決二分或多值條件的清晰集和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能夠對連續變量形式的因果條件進行處理。fsQCA不僅保留了子集關系這一分析因果復雜邏輯的核心,而且允許對模糊集中的隸屬程度進行校準,從而更充分地掌握前因條件在不同水平值上變動產生的影響(Rihoux等,2009)。
2.2 數據收集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方式獲取數據,被調查者為項目組借助多所高校創新創業學院和社會網絡資源尋找的青年創業者,年齡普遍在18~30歲之間。為契合研究主題,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樣方法選擇研究對象。首先,研究對象具有明顯的數字技術采用特征。參考數字技術創業相關文獻,綜合考量兩類數字技術產業鏈:一是包括數據要素、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信息通信、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產業化領域創業者;二是利用數字技術對服務、文娛等傳統產業進行業務升級和賦能的產業數字化領域創業者(李揚等,2021;王娟娟,2023)。其次,由于青年創業者創立企業的時間普遍較短,同時考慮到采用移動計算、大數據分析等數字技術驅動的創業活動屬于新興前沿類創業,本研究選取新創企業作為樣本(馬鴻佳等,2010)。此外,樣本企業成立時間較短也有助于降低問卷調查的后視偏見[21],特別是避免因企業過去業績和傳統觀念束縛導致的歷史遺留問題干擾,確保問卷信息準確、真實地反映現階段數字技術和創業生態對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基于此,與現存企業具有高度資源關聯性的內部創業也不納入樣本選擇范圍(李乾文,張玉利,2009)。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為鼓勵新型數字科技企業發展,多地啟動數字產業園建設(如北京園博數字經濟產業園、武漢星火數字產業基地等),通過集聚各類政策、市場和文化等創業生態要素支撐創新鏈和資源鏈構建。選擇新創企業作為樣本可以更好地借助這些機遇,為研究提供更加豐富和有力的數據來源。
問卷發放主要經歷兩個階段:首先,通過與項目組建立合作關系的多所高校創新創業學院,獲取學院記錄留檔的青年創業校友名單,在征得調查對象同意后發放紙質問卷;之后,邀請給予有效反饋的創業校友利用熟人網絡推薦開展相近創業活動的青年創業者填寫調查問卷,并將填寫好的電子問卷反饋給項目組。本研究采取紙質填答和電子問卷相結合的方式,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問卷548份。經過數據清洗,剔除作答不完整、填寫選項明顯趨同以及缺失值較多的樣本,最終得到創業者有效樣本417個,有效率為69.5%。對于不同調查方式可能帶來的數據差異問題,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對線上和線下兩種渠道收集的數據均值與標準差進行對比,發現樣本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有效樣本的統計學特征如下:從創業者性別看,男性占比70.26%,女性占比29.74%;從企業成立年限看,1年以內占比54.20%,1~3年占比24.94%,3年以上占比20.86%;從年凈利潤看,100萬元以下占比64.74%,100萬元~500萬元占比17.02%,500萬元以上占比18.24%;從樣本所在地區看,東部地區占比61.11%,中部地區占比20.53%,西部地區占比18.36%。總體來看,樣本統計特征分布與已有創業領域研究相近(張玉利等,2008;任澤平等,2022)。
2.3 變量測量
本研究在廣泛查閱文獻的基礎上,借鑒國內外成熟量表并根據研究情境進行修訂,最終完成量表題項設計。題項均采用李克特6級量表測量,1~6分別代表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1)創業生態。創業生態變量包括政府政策、市場環境和社會文化,參考Hechavarría&Ingram[22]基于全球創業觀察(GEM)視角和彭偉等[23]基于中國情境的研究,以“政府為創業提供優惠稅收政策”“政府為企業的創建經營提供便捷服務”“政府規范創業行為的政策制度完善”3個題項測量政府政策,以“創業成果具有巨大市場需求潛力”“市場上有多種創業融資渠道可供選擇”“市場上有成熟的租賃及商業服務類企業”3個題項測量市場環境,以“地方文化鼓勵創新和冒險精神”“社會大眾對創業失敗持寬容態度”“創業會得到家人朋友的支持”3個題項測量社會文化。
(2)數字技術。借鑒王杰和蔡志堅[24]的二層次劃分法,采用4個題項測量數字技術的應用情況和功能認知,分別為“我在創業項目中應用了數字技術”“數字技術改變了我的創業過程”“數字技術對于我的創業貢獻很大”“數字技術在創業中有巨大潛力”。
(3)創業績效。借鑒Cooper&Artz[25]提出的量表,綜合考慮企業發展與創業者心理兩個維度,采用4個題項測量創業績效,分別為“企業整體運營情況良好”“企業盈利狀況很好”“企業規模擴大很快”“我實現了創業前設想的目標”。量表測量題項載荷與信效度檢驗結果見表1。

表1 量表題項載荷與信效度檢驗結果Tab.1 Item loadings and reliability/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he scale
3 回歸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信效度與多重共線性檢驗
(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考慮到研究數據均源于自評式問卷,本文采用事先程序控制和事后檢驗避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首先,在問卷設計中盡可能保證題目措辭準確簡明并向被調查者強調研究的規范性與保密原則,降低因語言模糊和被調查者心理因素帶來的測量誤差,確保數據能夠反映被調查者的真實情況。完成數據收集后,通過單因子和納入共同方法因子兩種驗證性因子分析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其中,前者要求將所有量表題項共同負荷于單因子上,判斷無嚴重共同方法偏差的標準為單因子模型擬合指標比原模型差(Podsakoff等,2003)。結果顯示,χ2/df = 29.329,RMSEA =0.261,NFI=0.754,RFI=0.719,IFI=0.760,TLI=0.726,CFI=0.760,符合單因子模型擬合優度較差的預期。后者也稱為控制未測量的潛在方法因子(ULMC)法,要求在原模型基礎上再增加一個共同方法潛因子,判斷標準為加入共同方法潛因子后,模型擬合優度未得到明顯改善(周浩,龍立榮,2004)。結果顯示,Δχ2/df = 0.568,ΔRMSEA =0.004,ΔNFI=0.011,ΔRFI=0.005,ΔIFI=0.010,ΔTLI=0.005,ΔCFI=0.010。對比發現,RMSEA變化幅度不超過0.05,NFI等增值擬合度指標變化幅度不超過0.10,進一步印證了問卷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信效度檢驗。由表1可知,各變量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90,表明測量題項間相關性很強,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各變量的CR值均大于0.70的參考標準,說明組合信度情況較好。由表2可知,所有變量的平均萃取方差(AVE)均在0.90以上,結合CR值可知,變量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所有變量的AVE值平方根均大于該變量與其它變量的相關系數,表明數據具有較高的區分效度。

表2 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與區分效度檢驗結果Tab.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results
(3)多重共線性檢驗。首先,由表2可知,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與數字技術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大且接近于1,并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回歸模型中極有可能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朱鈺等,2020)。其次,以創業績效為被解釋變量,以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以及數字技術為解釋變量,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計算各解釋變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政府政策、市場環境和社會文化滿足容忍度(TOLERANCE)小于0.10或者方差膨脹因子(VIF)大于10的判定標準,說明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由于多重共線性會導致基于OLS線性回歸的參數估計值產生較大偏差,因而本文采用嶺回歸方法進行估計。

表3 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Tab.3 Results of multicollinearity test
3.2 嶺回歸
嶺回歸是一種適用于共線性數據分析的正則化線性估計方法,通過在正規方程組中添加對角元素K對最小二乘估計法進行改良,以損失部分信息、降低精度為代價使得回歸系數更符合實際且更加可靠(尹康,2013)。在進行嶺回歸時,需要確定對角元素即嶺參數K的值。鑒于通過嶺跡圖確定的K值存在一定主觀人為性,本文參照李明月等[26]的研究,采用方差擴大因子法尋找令各解釋變量回歸系數基本穩定的K值,具體為0.163。以K=0.163進行嶺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其中,F檢驗結果顯示,嶺回歸模型的顯著性P值為0.000,表明所有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共同影響顯著。同時,模型擬合優度R2=0.831,意味著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和數字技術能夠解釋嶺回歸方程中青年創業績效83.1%的變化原因,模型表現良好。以標準化系數為例,青年創業績效的嶺回歸模型可以表示為:創業績效=0.138×政府政策+0.117×市場環境+0.132×社會文化+0.513×數字技術。因此,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和數字技術均為正向影響青年創業績效的關鍵因素,H1a、H1b、H1c、H2得到驗證。

表4 數字技術、創業生態與青年創業績效的嶺回歸結果Tab.4 Ridg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on youth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3.3 交互效應檢驗
數字技術和創業生態各要素對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效果可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本文使用層級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數字技術、創業生態與青年創業績效之間是否存在交互效應。首先,構建以青年創業績效為被解釋變量,以創業生態各要素與數字技術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方程,稱為層級1。其次,構建層級2的回歸,即在層級1的基礎上納入創業生態各要素與數字技術的乘積項,通過乘積項的系數與顯著性判斷交互效應的影響方向和推斷的可靠性(方杰等,2022)。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影響,在構建乘積項之前,對其進行中心化處理,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數字技術與政府政策對青年創業績效的交互促進作用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模型4),H2a得到驗證;數字技術與市場環境對青年創業績效的交互促進作用在0.01的水平上顯著(模型5),H2b得到驗證;數字技術與社會文化對青年創業績效的交互促進作用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模型6),H2c得到驗證。總體而言,創業生態各要素、數字技術以及兩者的乘積項均顯著正向影響青年創業績效,表明數字技術能夠通過創業生態嵌入機制發揮互補效應。

表5 基于層級回歸的交互效應檢驗結果Tab.5 Interac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based 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采用Bootstrap方法對數字技術的交互效應進行穩健性檢驗,重復抽樣次數為5 000次,置信區間為90%。由表6可知,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交互效應分析結果與層級回歸基本一致,H2a、H2b、H2c得到進一步驗證,即創業生態要素與數字技術能夠強化彼此對青年創業績效的促進作用。

表6 交互效應的穩健性檢驗結果Tab.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
4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4.1 變量校準
交互效應檢驗能夠識別數字技術與某一創業生態要素共同影響青年創業績效的驅動機制,卻無法分析所有關鍵因素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為深入了解數字技術嵌入下創業生態對青年創業績效的聯動效應,本文在回歸分析基礎上進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首先,將回歸分析中417個樣本作為QCA視角下的案例,借由組態思維將案例看作多種前因變量的組合,以更精確地刻畫各個變量的狀態。雖然QCA多用于小樣本下的多案例比較,但在歸納和探索數百或數千的中大樣本案例所展現的組態特征中亦有良好表現(毛琪,徐愛軍,2018)。其次,選取回歸分析中的主要解釋變量作為前因,將被解釋變量作為結果,則共有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和數字技術4個前因條件以及創業績效1個結果變量。校準案例在變量集合中的隸屬度是進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的前提,本文基于理論知識和Ragin[27]、易明等[28]的研究,采用直接校準法,將樣本數據描述性統計的95%分位數、中位數和5%分位數分別設定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閾值。其中,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數字技術的校準錨點為6、5、1,創業績效的校準錨點為6、5、1.2。
4.2 前因條件必要性分析
遵循QCA研究標準,本文在條件組態充分性分析之前,先對所有單個前因條件及其非集是否構成高/非高創業績效的必要條件進行驗證。必要條件是指當結果發生時某個必然存在的條件,其判定標準為一致性水平大于0.90[29]。由表7可知,對于高創業績效這一結果而言,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和數字技術的一致性水平均大于0.90,是必要條件。在一致性條件得到滿足后,覆蓋度指標用于衡量前因條件對結果變量的解釋力,數值越大表示解釋力越強(谷志軍,2021)。根據覆蓋度檢驗,4個前因條件中數字技術的覆蓋度最高,說明該條件變量對青年創業績效的解釋力最強。可能的解釋是,青年創業者的新創企業往往更容易受到創業生態和數字技術影響,因為其在成長過程中需要不斷進行嘗試與改進,以實現對既有資源的利用拓展與價值發掘,同時由于缺乏傳統公司的強大資源稟賦,會更多地利用數字技術提升運營效率、降低成本、擴大市場(蔡莉,尹苗苗,2009;祝振鐸,李新春,2016)。

表7 單個前因條件的必要性檢驗結果Tab.7 Necessity test results for single antecedent condition
4.3 組態充分性分析
與關注單個條件的必要條件分析不同,組態分析嘗試分析不同條件構建的多重組態在引致結果發生中的充分性(張明等,2019)。在分析條件組態的充分性時,應當合理設置案例頻數、原始一致性和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閾值。頻數閾值需要根據樣本規模確定,本文根據實際情況將頻數閾值設定為2,保留至少80%的案例數量。Schneider&Wagemann(2012)指出組態的原始一致性水平不得低于0.75,本文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0。PRI一致性用于降低潛在矛盾組態,本文基于Greckhamer等(2018)的研究,將PRI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70。
鑒于中間解既能克服簡約解與現實相差較大的問題,又能對復雜解進行簡化從而利于后續組態分析,參考相關研究,本研究匯報中間解的組態結果,并輔以簡單解區分核心條件與邊緣條件(Douglas等,2020)。表8匯報了導致高/非高創業績效的前因條件組態。

表8 高/非高創業績效組態Tab.8 Configuration of generating high/non-high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由表8可知,產生高創業績效的條件組態有1個,其總體一致性和總體覆蓋度分別為0.964和0.916,遠高于最低門檻值0.75,說明S1是解釋高創業績效的條件組態,印證了H3。產生非高創業績效的組態路徑有兩條,分別命名為N1、N2,是解釋非高創業績效的條件組態。
S1表明,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以及數字技術是驅動高創業績效的重要條件,其中政府政策和數字技術共同發揮核心作用,市場環境與社會文化發揮輔助作用。該組態呈現出數字協同型創業生態,其對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是系統內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數字技術與創業生態要素的具體協同機制包括數字創業網絡嵌入機制、數字創業要素集聚機制、數字創業機會共生機制、數字價值共創機制和系統自組織機制,并經歷協同嵌入、協同集聚、協同共生和協同進化等階段,助力創業動態發展(朱秀梅,楊姍,2023)。戰略協同理論指出,創業生態各要素與數字技術共同為創業企業提供發展所需生態空間、技術支撐和配套資源要素,這些要素存在內在功能聯系,以協同組態形式直接影響環境承載力和生態位獲取[30],進而引致高創業績效的結果。只有重視數字協同型創業生態系統內各要素的聯動耦合,才能保障青年創業活動順利開展,進而驅動青年高創業績效產生。
N1表明,數字技術的缺失發揮核心作用,政府政策、市場環境和社會文化的缺失發揮輔助作用。根據資源基礎觀,組織通過獲取環境中的資源維持生存和持續發展,各類資源是企業提升效率與效益以及戰略實施的基礎[31]。新企業創建是個體和資源緊密結合的過程,對于缺乏資源的青年創業者而言,若無法有效獲取和整合創業生態中的資源要素,則難以驅動高創業績效產生。N2表明,在缺失數字技術這一核心條件的情況下,即使政府政策、市場環境和社會文化發揮輔助作用,仍會引致非高創業績效。N1的覆蓋度遠高于N2(原始覆蓋度N1=0.780,N2=0.439;唯一覆蓋度N1=0.411,N2=0.070),說明組態N2能夠解釋的樣本案例有限。考慮到數字技術對企業發展的影響效應具有異質性,組態N2可能更多的是解釋數字產業化領域相關創業案例,該類型企業的成長往往高度依賴以數據和技術創新為基礎的復雜網絡空間,數字技術的缺位會削弱企業的吸引力和適應性,并成為引致青年創業者非高創業績效的重要原因(王寧,2021)。
4.4 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改變校準與調整閾值的方式對組態分析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Schneider &Wagemann,2010)。首先,將完全隸屬、完全不隸屬錨點調整為上四分位數、下四分位數,交叉點保持不變。其次,將案例頻數閾值由2調整為5,將原始一致性閾值由0.80調整為0.85,將PRI一致性閾值由0.70調整為0.75。組態分析結果顯示,新組態與現有組態基本一致或呈現清晰子集關系,可以認為fsQCA的研究結論未發生實質改變,依然穩健。
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論
本文從多層次、多維度系統邏輯的創業生態視角出發,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構建青年創業者通過數字技術采用、創業生態賦能提升創業績效的理論模型。同時,采用回歸分析與fsQCA相結合的混合方法,利用青年創業群體調查數據,超越個案的特殊性,揭示數字技術嵌入情境下創業生態驅動青年創業績效的作用機制及條件組態。主要研究結論如下:首先,嶺回歸結果表明,政府政策、市場環境、社會文化和數字技術均對青年創業績效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同時,結合組態分析結果,數字技術、創業生態各要素與青年創業績效之間存在線性關系與子集關系,說明青年創業行為在缺乏經驗、資金的情況下具有明顯的資源依賴效應。其次,交互效應檢驗表明,數字技術與創業生態各要素在驅動青年創業績效的過程中存在交互促進效應,說明在創業生態影響創業績效的過程中,數字技術能夠發揮嵌入和賦能作用,通過互補方式幫助青年創業者將創業資源稟賦轉化為創業可行能力。最后,組態分析結果表明,存在1個驅動高創業績效的數字協同型創業生態組態,進一步驗證了青年創業績效形成路徑中多重因素相互依賴的協同效應。對比兩條非高創業績效組態發現,數字技術與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耦合關系的構建共同影響青年創業活動的開展,隨著數字技術嵌入創業生態的程度提高,青年高創業績效在多重因素并發下得以實現。
5.2 理論貢獻
第一,將數字技術引入創業生態分析框架并驗證其與創業生態各要素對創業績效的交互促進效應和協同驅動機制,不僅彌補了數字經濟時代創業生態系統研究的不足,而且在企業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具有極強的適切性,拓展并完善了傳統創業生態研究視角和理論范疇。第二,聚焦青年創業者,更細粒度理解青年創業行為,發現缺乏經驗或資金等“新生弱性”導致青年創業者更加需要外部良好的創業生態作為必要條件,而青年創業者的優勢在于更具創新思維,能夠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等新要素并協調各類政策、市場和文化資源,進而引致高創業績效的實現,進一步豐富了創業參與主體和創業績效相關研究。第三,采用回歸分析與fsQCA相結合的方法發現數字技術、創業生態各要素對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揭示了數字技術嵌入下創業生態驅動青年創業績效的交互機制,同時基于組態視角發現青年高創業績效是多要素協同作用的結果,為創新創業研究提供了更具系統性思維的理論參考。而且,引入結合案例導向與變量導向的QCA技術,對青年創業績效前因條件的聯動效應進行剖析,更加貼合創業行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過程的情境,對該領域相關研究中方法工具的使用作了補充和豐富。
5.3 實踐啟示
(1)關注青年創業活動的獨特性,針對關鍵創業生態要素進行精準施策和優化,打造良好的青年創業營商環境。青年創業肩負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雙重使命,需要政府、市場以及社會投入多元資源為青年創業活動提供支持。首先,政府應發揮政策主導作用,在知識產權保護、監測評估、法律資助等領域加強青年創新創業工作幫扶,為青年創業行為提供制度保障。其次,提高市場環境對青年創業項目的吸納和承載能力,推動“雙創”載體與投融資機構、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等第三方合作,組建眾創空間、創新工廠等企業服務聯盟和創業服務載體,提升青年創業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最后,打造企業初創期“種子培育”孵化園,集成創業網絡和創業榜樣等要素,發揮企業家精神在營造青年創業文化與環境中的輻射和示范作用,培育進取導向、勇于創業、寬容失敗的創業氛圍,強化青年的創業意識、創業情感和創業驅動力。
(2)發揮數字技術在培育青年創業能力、提高青年創新創業產出中的關鍵作用,鼓勵多元主體共享、擴散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打造多主體互動的數字創業生態系統。本文研究發現數字技術與創業生態要素良性耦合可以實現高創業績效,說明二者間存在互補關系而非替代關系,因而應重視發揮創業生態中數字技術嵌入的共棲互利作用。首先,各地政府需高度重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醫療等重點領域開展創新創業試點示范,激發青年數字創新創業活力。其次,由市場主體搭建數字創業服務平臺,提高數字技術的系統輻射能力,引導青年創業者作為互補者加入已有數字平臺并實施平臺鑲嵌戰略從而獲得成長。最后,加強全社會的數字素養培訓,通過數字技術開源社區等社會聯合體培養青年利用數字化工具進行溝通協作、內容創建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發揮數字化綜合能力對青年創業勝任力和創業績效的正向作用。
5.4 研究局限與展望
當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首先,創業具有高度復雜性,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因素是多元的,本文從數字技術嵌入創業生態的視角分析其對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難以避免遺漏其它影響因素,如創業者個體特質等。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創業者行為是個體和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張秀娥,李夢瑩,2019)。未來可擴展研究視角,從反映創業者認知潛質和積極評價的心理資本或應對創業資源約束情景的資源拼湊能力等多元視角出發,探討影響青年創業績效的其它因素及其邏輯關系。其次,本文僅使用417位青年創業者的截面數據探討數字技術嵌入下創業生態對青年創業績效的影響,在剖析青年創業績效提高機制中多重前因變量的動態演進路徑方面存在局限。未來可擴大樣本范圍并開展追蹤調查,構建青年創業者面板數據,獲取更多青年創業者個體動態行為信息,并通過控制時間等固定效應實現更準確的凈效應估計。此外,可在組態分析中嘗試采用動態QCA方法剖析青年創業績效中多要素、多軌跡的共演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