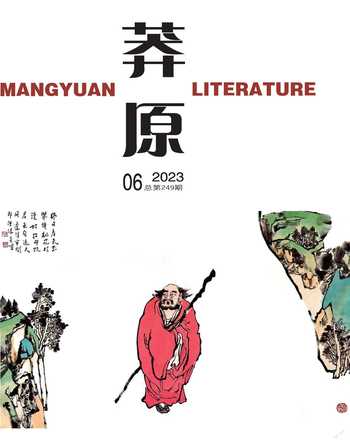行走在黃河岸邊
金光
湖邊老人
黃河水彎到這兒,被蒼龍河匯入時一頂,形成了一個偌大的湖。冬天,有許多白天鵝在湖上棲息,引來很多人觀賞;而在夏秋兩季,卻是孩子們的天堂。放學后割草的、放牛的、摸魚的,一群一群的少年來到這兒,脫了衣服泥鰍般在湖水里玩耍,把蒼龍湖鬧騰得雞飛狗跳。
早時候湖邊沒有路,來往的人就站在召公島迎祥閣上往湖里看,一圈粗壯的毛白楊包裹著清水湖,靠岸的地方長著叢叢蘆葦,或是有著厚葉子的蒲草,風一吹呼啦啦作響。貪玩的小家伙們就在草叢中扎猛子,有時候因為摸了一條黃河鯉魚而相互追逐著,那活蹦亂跳的場面像是過電影。
仲夏的一天,暑熱難耐,我驅車來到黃河邊,將車停在召公島下的公路上,走到湖邊的白楊林漫步。蘆葦和蒲葉已經長得很高了,不遠處還有人工種植的蓮花,幾朵剛剛從水里探出頭來的荷苞正隨風搖曳。野鴨子和鸕鶿聽到腳步聲,紛紛從岸上跳進水里,弄出“撲通撲通”的聲響。我知道打擾到它們了,很不好意思,就將腳步放輕了。
原以為能看到幾個小家伙在湖里洗澡或玩耍,那樣我會拍一些圖片發在微信朋友圈里。可轉了半圈兒卻沒有看到一個人影。失望之際,在丁香花叢旁的長椅上坐下來,想小憩片刻,再繼續沿著湖堤往前走。微風吹來,頓時清涼了。此時,楊樹上掉下一只雛鳥,張著翅膀,掙扎著亂叫,顯然落地時受了傷。遂上前捧起小鳥兒,檢查了一下,并無大礙。我將它端在手掌上,動了動它的翅膀,它抖了抖身子,尖叫一聲,展翅飛走了。
前面樹蔭下有兩頭牛在吃草,看我走來,從鼻孔里噴出一股粗氣,又低下頭,伸著舌頭,將嫩綠細草卷進嘴里,用牙齒咬緊后往上一揪,細草就吞咽了。
一位老者靜靜地坐在楊樹下,應該是牛的主人。他看著牛,也看著我,卻一言不發,擺弄著手中的一根長竹竿。我坐在他身旁,無話找話地問道:“放牛都拿鞭子或柳條兒,你咋拿根長竹竿啊?”
老者眉頭一展,賣了個關子說:“照你這樣說,我就不能拿竹竿啰?”
他這一反問,我竟無言以對了,就轉移了話題:“記得往年這兒會有孩子們下水玩,今天怎么沒看見?”
“你好久沒有來這里了吧?十年了,再也沒有孩子到湖里耍水了。”老人說著,揮動了一下他的竹竿。
“為什么?”
“我不允許。”
說這話時,他透出了一種倔強的表情。我有點不理解,孩子們到湖里玩耍是他們的天性,與一個老頭兒有何關系,你說不允許就不允許了?
我半開玩笑說:“這你恐怕管不了吧?”
“管得了。”他把長竹竿往空中一提,“哪個不聽話就打屁股。”
我終于明白了老人拿竹竿的用意,細細一想,覺得這里面肯定有故事,便挪了挪屁股,向他靠近了,和他拉起家常。
老人姓秦,蒼龍村村民。十多年前,他兒子已經上了高一,那年夏天和同學們到蒼龍湖邊打豬草,下湖游泳,溺水了。老人說,當時他兒子只是在湖邊玩,并沒有到湖中間游泳,但他們不知道蒼龍河上游下了暴雨,河水上漲沖進湖里,將一個孩子從湖邊往黃河沖去。他掙扎著,喊叫著,在水里不停地撲騰。老人的兒子稍有點水性,見狀就去救人,結果拉到那位同學的時候,求生本能讓落水者把他兒子死死地拽住,往水下按,他們都沉到了湖里。后來,他兒子拼著最后的力氣,用肩膀托住同學,硬是將那同學頂到了岸邊一棵小柳樹上,他兒子卻被洪水沖進湖心,淹死了。
老秦敘說的時候,陰沉著臉,竟然沒有流眼淚,有的只是一聲嘆息。我知道這是他最傷心的事兒,陪著長嘆一聲,終于明白他為什么不允許孩子們來這個地方玩水了。
老秦的孩子是見義勇為。團縣委和教育局聯合下發了紅頭文件,表彰了他的兒子,他接到那個紅頭文件時,看也沒看就把它放進了裝著他兒子遺物的木箱里。
“被救的那個孩子咋樣了?”我問。
“那孩子很有出息,上了大學,后來在一家科研所上班。”老秦說。
“了不起呀……”我又嘆了一口氣,“不過,可惜你家孩子了。”
老秦說,那個被救的孩子很懂得感恩,每次探家都來看望他,還要給他錢,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也就是從那以后,老秦常來湖邊,心里呼喚著兒子,眼睛巡視著湖面,看見有孩子下湖玩水,就吆喝著趕他們上岸。后來,他年紀大了,干脆就養了兩頭牛,夏天的時候把牛趕到湖邊放,為的是不讓悲劇在這里重演。
他晃著手中的長竹竿,說:“這個竹竿三種用途,一是吆牛,二是看到有孩子往湖邊來就拿它嚇唬他們,三是真有人掉進了湖里,就用它撈人。”
我明白了,看著滿面滄桑的老秦,看著他手中的竹竿,心里肅然起敬。
一只野鴨在湖里“呱呱呱”叫起來,許是碰見了天敵,引得一群野鴨驚恐地往遠處飛去。兩頭老牛抬頭看了看飛起的野鴨,調頭往我們這邊走來,停在了我們面前。
“走,回家嘍。”老秦站起身,拿竹竿在牛背上輕輕敲了兩下,趕著它們順著湖邊的小路往遠處的村子走去。
我沿湖向停車的方向返回,禁不住又往湖里看了一眼,仿佛看見了一個少年正在湖中拉著掙扎的溺水者,那少年的面部時而模糊,時而清晰。
湖面上似有一聲輕輕的嘆息。
割草的女人
黃河岸邊常有一片一片的灘涂。
每年汛期河水上漲便淹沒了灘涂,到了八月以后水位下落,灘涂就裸露出來,人們會在這個空檔期里,在灘涂上種些大豆或向日葵之類的作物。灘涂地是不需要施肥的,本就是黃河沖下來的淤泥,黑乎乎的,壯著呢。那些作物一旦種下去,正逢八月三伏天,出苗后瘋長,到十月下旬成熟。種地人就去河灘上搶收,能收多少是多少。
我曾在河邊撿過豆子。大豆成熟后,莊稼人用收割機收。可機器總不如人細心,常常是豆棵子的上半截兒被割走了,下半截留了四五寸長的茬子,上面結著稠稠的豆莢,留給我這樣的閑人撿漏兒。我是帶著妻子去看黃河的,黃湯一樣的河水已經退到了河心,站在河沿上看了一會兒,就被撿豆莢的人吸引了,便和妻子一起,加入撿豆莢的隊伍中。我們兩個拿出小時候打豬草的勁頭,一薅一把豆莢,不多久就裝滿了一大袋子。回到家,妻子坐在陽臺上把豆莢剝了,上秤一稱,竟有七斤多。
河灘上有很多野地,人們根本種不過來,任憑它自個兒荒去。野灘涂斷斷續續地在河灣處、陡崖下閑置著,由于泥土肥沃,很快便長出各種各樣的雜草。我能認識的有夾拉毛、雜葦子、鐵稈蒿、豬耳朵草、黏刺秧等。它們比莊稼長得快多了,幾天不見就長得掩住人了;再幾天不見,那草稈就由筷子粗細變成拇指粗細了。于是,各種鳥兒鉆進去,連野兔也藏在里面,灘涂的野草地里便有許多動物的故事發生。
正是八月下旬,眼前這一長溜兒野地,野草足有七八尺高,風一吹“唰唰”作響,一群麻雀鉆在草叢里,像我們小時候捉迷藏那樣,飛來飛去又咋咋呼呼。我漫步在草地邊的沙土路上,看著這一望無際的野草,仿佛置身于遙遠的荒野之中。突然,草叢中沖出一只兔子,也許是暈了頭,直接撞在了我的腿上。野兔愣了片刻,一折身緊跑兩步,又停了下來,兩只耳朵高高地豎起,像兩根天線不停地在空中搖擺。我拍了下巴掌嚇唬它,可兔子好像知道我拿它奈何不得,臥在那兒抽著鼻子不肯離開。我索性挽起袖子向它撲去,結果在騰起的一剎那間,兔子一抖身子便沒了蹤影。
這家伙分明是來戲弄我的。我自嘲地看著仍在抖動的草棵,搖了搖頭。為了釋放剛才的尷尬,我又跺了下腳,用手做了個喇叭形對著野兔跑過的草叢,可著嗓門吼叫起來:“喔喔喔——”聲音在廣袤的黃河灘上并沒有傳多遠,就像一塊小石頭扔進大海里。
“居然還有人來這兒旅游。”我聽到不遠處的草叢中有女人的聲音,愣了一下,尋著說話聲過去看究竟。
大約走了五六十米,眼前豁然開朗,一位中年女人正拿著鐮刀在割草。
看見我,女人住了手。她的身后,是一片已經被割光了草的空地,碼放著一鋪鋪剛被她割倒的野草,其中的一鋪草上,放著一壺水和一個錄放機,錄放機里正播放著豫劇《朝陽溝》里銀環的唱段。
“你不會是真的來河灘上旅游的吧?”女人半開玩笑地問道。
我隨口說道:“如果這樣也算旅游的話,我就是來旅游的。”
她哈哈大笑起來。
女人拿起水壺,問我要不要喝水。我擺了擺手,她自己喝了兩口,又把水壺扔到了草鋪上,準備繼續割草。
“這么熱的天,割這些雜草干啥?”我問。
“割草喂魚呀。”女人說,好像我有些少見多怪。
我看了看她割下的那些草,有的軟有的硬有的細有的粗,尤其是豬耳朵草和野向日葵,稈子都很粗壯,便不解地問:“魚,能吃這樣的草嗎?”
女人攏了一下被汗水浸亂的頭發,說:“咋不能,魚啥草都吃。”
說實話,我見過豬馬牛羊兔子吃草,從沒見過魚吃草,便問:“魚不是吃魚食嗎?”
女人大笑起來:“那是魚缸里養的,我們家要是養吃魚食的魚,那可養不起嘍。”
然后又說:“你沒聽說過嗎,草魚草魚,就是吃草的魚。”
她說她家在旁邊的土崖下挖了兩個魚塘,有五六畝大,春上放了兩萬多尾草魚苗兒,每天光喂草就得幾百斤。她和丈夫在農貿市場上開了個魚店,每天早上在店里賣魚,下午來黃河灘割草。她在這兒割,她丈夫負責往魚塘運草、喂魚,天天如此。
我看到她的手上有一層厚厚的老繭,手指似乎都變形了。
“這么粗的草稈子魚能吃下去嗎?”我指著地上的粗稈子問。
“再粗的稈子也能吃得了,別看魚那么小,吃起草來比牛還厲害哩。”女人說。她怕我不信,就指著遠處的一棵白楊樹,“有時候我們來不及割草,就折些楊樹枝子扔進魚塘,它們不僅吃了葉子,連樹枝也吃掉了。”
說實話,我只知道牛馬嘴大牙尖,除了吃草以外還能吃一些藤子,從來不知道魚也有這樣的本事,它那么小的嘴居然可以將粗壯的草稈子吃掉。
女人怕我不相信,說一會兒她丈夫來拉草,可以去魚塘里看看她說的話是不是騙人的。
說話間,一個男人開著三輪車三拐兩拐來到了跟前。女人告訴他說,這人不信魚能吃這么大的草。男人笑著說,那好辦,一會兒跟著去看看就清楚了。
為了一睹魚吃草的情景,我也幫他裝草。三下五除二把車裝滿,男人又用繩子煞緊,開著三輪車讓我跟著他往魚塘去。
到了魚塘,他松了繩子,抱起一捆雜草往塘里扔去。那草剛一落下,就有幾百條大魚從水面躍出,歡快地張嘴去逮去咬那些雜草。魚是在水里吃的草,看不見它們是怎樣吃的,但眼前的一切告訴我,那些魚肯定能將這些草連葉兒帶稈子吃下去,要不,那些粗壯的草稈子早就撐滿了池塘。
“這些魚都是吃野草生長的,沒有激素,也沒打什么藥,需要的話可以放心買。”男人告訴我他在農貿市場的幾排幾號,如果需要魚,他也可以送上門。說著,還給我遞了張名片。
返回的時候,又經過女人割草的地方,看見她還在揮鐮勞作,鐮刀所到之處,一叢叢雜草紛紛倒下。在我的眼中,偌大的河灘上,她是那樣的渺小,而在雜草面前,她又很高大,像個將軍。
女人又停了下來,用手捶了下背,說:“看到了吧,我沒騙你,魚吃野草吃得美著呢。”
我點了點頭。
“黃河灘地肥,野草長得太瘋了,幸虧我養了那么多魚,可以割了它喂魚,要不然它就白長了。看來,大自然的一切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啊。”女人像在自言自語。
我心一震,突然意識到這句富有哲理的話,竟從一位割草養魚的女人口里說出,便用異樣的目光看著她。我問她上過學沒有,她的回答更讓我吃驚。她說她當年讀了大學,畢業后分到了一家自收自支事業單位,不景氣,就和老公自己創業了。
我伸出大拇指,為她的勇敢點贊。末了又說:“這草不割也挺好的,它長在這兒環保。”
“這你就不懂了,十月份水位上漲,野草經水一泡就腐爛了,漚到明年天一熱就發臭,污染環境哩。”
女人一板一眼地說,意思是她割草也是一舉兩得的事兒。
天快黑了,我轉身往回走,出了灘地,仍能聽見女人錄放機播放的《朝陽溝》唱段。
落? 日
那次,二月河來了陜州,讓我帶他去古城尋找他兒時常騎的小鐵人。我們先在北門的亭子前打聽,有人說那鐵人四十多年前就被移走了,移到了什么地方卻說不清楚。
二月河告訴我,當時,陜州古城的北門是陜縣公安局辦公的地方,他的母親就在公安局上班,他當時在寶輪寺塔那邊的小學讀書,每天放學時母親還沒有下班,他就騎在門口一排小鐵人的肩膀上等母親,他對那些小鐵人的印象太深了。我打電話讓文旅局的朋友幫著去尋找,便帶二月河順著一條小路往西邊行走。
我們走到一處土崖邊時,二月河停下了腳步,他凝望著面前的黃河,愣愣地站在那兒,好長時間不說話。我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便不去打擾他。良久,他轉過身指著腳下的一處土凹告訴我,這地方叫羊角山,前面的河灣就是古時候有名的黃河太陽渡。
我問:“你對這個地方這么熟悉,小時候一定常在這兒玩吧?”
二月河的老家在河對岸的山西,解放初期隨父母南下來到這里。當時這里還叫陜州,他在這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他說,星期天他常常一個人坐在羊角山的土坎上看太陽渡,來來往往的船掛著白帆在他的腳下穿梭。初春,當太陽渡上游的冰凌解封時,整個河道洶涌激蕩,滿河都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透出一種巨大的力量,很壯觀。這印象太深刻了,讓他一輩子也忘不掉。后來他給自己起筆名時,第一個想到的是黃河解冰的情景,于是就叫了二月河這個名字。
如今,羊角山上的渡口旅館已蕩然無存,二月河小時候愛吃的崖畔酸棗也不見了蹤影,他口中描述的千帆競過的太陽渡,早已被一片黃燦燦的濕地所替代,濕地上長著齊整整的向日葵。有一群游客在看完黃河后,鉆進向日葵地里自拍。我們看了一會兒嬉鬧的游客,最后把目光聚焦在西邊的落日上。
因為接近黃昏,一輪黃里透紅的太陽,滿身的光芒已不再,靜靜地掛在中條山的頂端;隨著太陽光亮的減弱,兩岸山坡逐漸變成了褐色,影影綽綽的;曲曲彎彎的黃河由上而下,一彎一彎的河水變成了紅色,像一條紅綢飄在那兒,煞是好看。我想起兩句古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二月河好像不太感興趣,看了一眼落日,接著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這時候,我的電話響了,朋友在春秋路上的車馬坑博物館找到了小鐵人,于是我們就驅車往那兒趕去。
之后,我對那次看到的落日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恍惚總能聯想到什么,卻一直沒能找到感覺。直到三年后的一個秋日,我再次來到羊角山時,看著遠方的落日,猛然想到一件事,令我感到釋懷。
我站立的地方,是一處塌方的陜州古城墻。太陽渡的對面,是與黃河平行的中條山;再順著黃河往西看,夕陽下是隱隱約約的函谷關。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抗日戰爭中,為了補充兵源,正在陜西省讀書的八百青年學生踴躍報名,來到中條山上阻擊日寇南侵,由于敵強我弱,這些被稱為陜西“冷娃”的青年學生傷亡慘重,為了不當鬼子的俘虜,最后全部跳進滾滾黃河,譜寫了中華青年為國捐軀的壯舉。
慘烈的中條山戰役,是國人永遠的傷痛。如今,倭寇已除,國泰民安,那些曾經跳入滾滾黃河的“冷娃”們,得以含笑在九泉之下。眼下的河畔上,那一株株的金黃色葵花,不正是“冷娃”們的張張笑臉嗎!
順著黃河繼續向上望去,函谷關,這座矗立兩千多年的雄關,正隱藏在夕陽下的霧靄中,顯得無比神秘。
很多人知道,函谷關是老子著《道德經》的地方,那里充滿了神秘色彩。“紫氣東來”本來是關令尹喜盼望老子心切,觀天象時發現的一種吉祥預兆,可誰能想到兩千多年后,自東而來的不是紫氣,而是日寇進犯的陰氣。
那是抗日戰爭后期,岡村寧次指揮數萬日寇,翻越中條山,渡過黃河,向西進犯。我抗日軍民拼死堵截,將日寇阻擋在函谷關以東。瘋狂的日寇動用飛機大炮轟炸關樓,企圖沖破關口,但英勇的抗日軍民拼死抗擊,形成了一道銅墻鐵壁,使侵略者始終不能突破半步,最后以失敗而告終,扔下八百具尸體,退了回去。
函谷關,是侵略者的噩夢之地,從此日寇日落西山,為之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太陽在函谷關的方向慢慢往山后沉去,留下了一幅黛色的山影。我忽然從中悟了一些道理,莫不是那八百“冷娃”變成了天兵天將,讓侵略者夢碎于此,讓那面膏藥旗從這里落下……我常常站在這高高的古城墻上,遙望函谷關的落日,仿佛看見那些“冷娃”們在灰褐色的山坡上放聲大笑。
一對情侶嬉笑著從遠處走來,他們的腳步停留在了我的身后。
女孩兒說:“看,落日多漂亮,我們站在這兒拍個落日背景照吧。”
男孩兒緊跨兩步,打量了一下遠處的落日,說:“我們下次上午過來拍朝陽,不拍落日,不吉利。”
女孩兒似乎明白了,點了點頭。男孩兒伸出左手,握著空心拳頭,似乎要把遠處的太陽用手握住。
女孩兒說:“好,好,太好了,你就像夸父一樣,把太陽捉住了。”
說著,舉起手機,拍了一張圖片。
小情侶嘻嘻哈哈地走了,我卻對他們剛才說的話充滿了敬意。
后來,我發現很多人喜歡在這兒看落日,有年長的,也有青年人。我不知道他們從落日中看出了什么名堂,但相信多數人能悟出那一層深意。有時候,隱約可以聽到他們指著落日在爭吵,真希望他們爭吵的內容與八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有關。
責任編輯 劉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