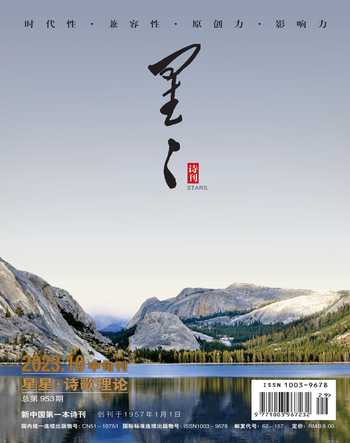鄉土敘事的現代性如何可能
草樹
《廢墟上升起一座博物館》是青年詩人劉娜參加詩刊社第38屆青春詩會后出版的詩集。詩集分四輯,每一輯依據主旨的大致內在相似性進行歸集,但詩中場景無不是玉竹坪和毗鄰玉竹坪的鄉村或縣域,從本質上說,這是一部鄉土敘事詩集。詩集名《廢墟上升起一座博物館》意味著詩人有意通過鄉土敘事去呈現城市化和現代化背景下鄉村的真實存在,審視這個山鄉巨變時代個體的精神境遇,挽留童年、少年時代的美好時光。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首詩都是詩人語言的遺物,歸集成一座紙上博物館,其本質是賡續“為天地立心”、為流逝的事物命名的古老傳統。
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以鄉土為載體的農耕文明,其形式是鄉土社會。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開篇即開宗明義,“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而在二十世紀后期至今的這一場偉大變革中,中國鄉土社會的廊柱已經在現代性的大舉進軍中土崩瓦解了。當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座座鄉村現代化別墅的升起,但是在挖掘機和鏟車離場的廢墟中,精神的大廈和心靈的木格窗遠未建成。在磚石和梁柱的廢墟中掩藏著童年的玩具、數代人傳承的器物以及祖輩的雕花床,包括雕梁上的飛鳥和宗祠上的對聯,或者石磨上把手的光澤和竹簍上篾匠的指紋,所有這些無不隨著鏟車的轟鳴和大貨車的開動被送入垃圾場。當代中國的鄉村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空間,鄉村別墅的現代化和被城市化掏空的村民讓人的遷徙和流動帶來生產要素的流動,傳統的人情關系向著契約倫理不斷改變,又形成新的懸空悖論。從《詩經》以降,中國的詩歌傳統最為清澈明媚的語言景觀無不是從鄉土敘事中呈現,而面對當下如此復雜的語言場景,中國鄉土敘事的現代性如何可能?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詩歌場域產生的第三代詩歌運動是以犧牲傳統為代價的。當傳統被作為一種現代主義開墾的資源后,文化尋根便淪為了意義圖解和個人化想象背景下反對意義、拒絕隱喻的手段,傳統自然成了先鋒文學運動的“革命對象”。正如所有的革命運動一樣,在歷經狂飆突進和摧枯拉朽的激情釋放后,激流終要抵達平緩。當代詩人激情之后又轉身重新打量傳統,尤其近二十年來傳統不再作為語言革命的對象,更不被當作一種語言資源,而是成為一種語言血緣。如果說我們今天的詩歌寫作完全脫離《詩經》《離騷》和“李杜、蘇辛”以來的傳統,不再是一個同時性的存在,而是一種孤立的當下敘事,或者效法西方現代主義的傳統成為一種唯我主義和本質主義的當代版,那么我們既背離了我們自身的傳統,也脫離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歷史語境。
在《魯迅談古典文學》一文中,魯迅先生說:“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今天也有越來越多的詩人談論杜甫而不是但丁、歌德或艾略特,也許我們已經真正明白杜甫就來自我們的傳統,更像一個我們的同時代人。一個詩人只有具備同時代性的意識,或作為一個真正的同時代人,才能深刻把握百年未遇之大變革時代在中國鄉村發生的一切,才談得上鄉土敘事的現代性生成。現代性的生成不應淪為田園牧歌式的浪漫主義歌唱,或成為反映論的現實主義頌詞,而是要在面對傳統和現代斷裂處的廢墟時有真正的語言作為。我們為什么要把鄉土敘事的現代性視為某種詩歌價值的高度?我們這個時代為何如此熱衷于談論現代性?因為,文學的現代性伴隨著對社會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鄉土敘事的現代性價值就在于它不是時代的依附和獻媚,而是面對傳統和現代的斷裂在批判和建構上有所作為。劉娜的詩集《廢墟上升起一座博物館》,就是一次語言的建構行動,伴隨其間的是深刻的反思和冷靜的觀察。
一個詩人面對出生地難免按捺不住鄉情的泛濫并受到自荷爾德林以來西方鄉愁傳統的裹挾,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浪漫主義的歌唱范式,從當下的鄉土蹈空進入一種田園牧歌式的修辭演繹,或羅列大而無當的形而上的具象。事實上,當下以鄉村為題材的詩歌有很大一部分依然沒有擺脫空洞的修辭或西方鄉愁傳統的魔咒,他們筆下的田園或者自然似乎可以屬于歷史上各個時代,但就是和當代無關,與當下無涉。這關乎詩人的寫作觀念和態度,而此中關要即是否具有現代性詩歌美學觀念并具備現代性的視野和態度。現代性的視野或態度是一種具備歷史意識和同時代性或當代性觀念的視野,是一種含有批判意識的客觀冷靜的態度,它落實在語言學層面就是具有一種專注于能指的自覺。在《挖機轟鳴時》一詩中,“當挖機轟鳴時”詩人的態度就顯而易見。現代性的入侵以挖機為具象再合適不過了,在打破鄉村寧靜的同時,占領了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童年的根據地——農舍、田地、荒草。挖機聲如此刺耳,在詩人的傾聽中并沒有引發類似辜鴻銘式的怒吼或者批判現實主義的道德姿態,而是和米沃什的《禮物》形成一次互文,“深藍色絲絨窗簾半掩的明亮里/一些塵埃正朝我涌來”。這是一個撤離當下的視點,詩人攜帶一束超越性的光亮返回,并未發出平庸的呵斥,而是相信塵埃會迅速落進“過去屬于我的日子/像是還有回轉的余地”。詩人的態度于此以一種不無憂慮又滿懷信念的、近乎中性的語調呈現,沒有任何主宰精神秩序者的唯我主義沖動,以靜觀甚至凝視去實現詩意的生成。
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中嚴重忽視了本土傳統。本土性或者地方性作為傳統和現代斷裂的豁口是一種存在的流逝,而那些如雨后春筍般聳立的大樓不足以彰顯現代性的生成,真正的現代性如那些高樓之間空地萌生的野草。因此,鄉村敘事獲得現代性的歷史機遇正當其時。劉娜的寫作自覺就在于沒有在語言的渡口被遠方的海市蜃樓迷惑,而是一開始就一頭扎入出生地,朝著正在變得陌生的熟稔土地開掘。“右拐就是玉竹坪”,劉娜仿佛在把她的故土指給你,那不是一個現代人期望的桃花源式的烏托邦,而是她深沉凝眸里的異托邦。詩人飽含深情又自我抑制,故鄉正如一扇小時候會“久叩”而現在放棄了久叩念頭的門。在《久叩》一詩中,玉竹坪恰似一幅市場經濟時代老人留守鄉村的素描,有現代文明的標志性符號——太陽能路燈,也有水泥馬路取代過去的泥濘小道,但是三奶的孤獨是顯而易見的;十幾年后舊屋坍塌了,三奶也不在了,只是在詩人心中“屋內似有嘆息般的微小火苗在閃動”。這種現實背后的真實存在,自然不會進入時代的新聞報道或歷史書寫中,唯有詩人去履行“詩的見證”使命,并以一個真正同時代的人將靈與肉都投入其中的態度去實現。
現代性詩歌美學中珍視的這些關鍵詞:個人化、在場、日常、口語……其本身就蘊含著現代性的反思。日常生活是無意義的,但正是這些鮮活而又蓬勃的無意義的人的存在支撐了意義叢生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劉娜的語言軌跡和形式特征不是離開詞語本體,而是使它們變得異常具體并令人信服。在《飄浮的塵埃》中,“我和弟弟讓出條凳/又被讓出房間/站起來環顧四周才發現/幾平方米的房間也可以這么空/只有一把抓不住的陽光和無數飄浮的塵埃”。這首詩描述了一次鄉村酒席后的情景,給我們帶來了現實主義的信息——桌椅不再從鄰居家借,而是租賃,鄉村的一切都變得商業化,但也在一定意義上提升了鄉村的文明程度。詩歌不是事功的,而是抒情的。劉娜的敘事與其說是抒情不如說是一種情感的濃縮,除了以真切的在場感和沉浸其中的身心付諸能指形式外,還在盛宴的喧囂之后有所發現——空。這不是虛無的悲觀,因為它有一把抓不住的陽光;更是本質的洞察,即所有盛宴之后是必然的荒涼,熱鬧人生不過是飄浮的塵埃。
地方性知識沉淀于鄉村倫理和習俗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古老遺存,它在鄉村有著比在城市更為貼近心靈的形式。在《代父母回鄉》中,劉娜敘述的是過去時代不曾有過的生活方式。父母隨兒女進城了,老家有人辦婚宴或喪禮,生活在城里的老人依然不敢不講“禮性”;自己年紀大了,受不了舟車勞頓就委托兒女回鄉。其實不單是劉娜,所有移居城市的鄉村人都有類似的經歷。劉娜回鄉看見酒杯微小的波瀾里有父母親年輕的倒影,看見地里的玉竹、三七正在合計一年的收成,舉起喜慶的酒杯卻分神于過去暴雨將臨的慌亂……對于此詩來說,正是過去成就此時,過去的慌亂成就此時的從容,過去的辛勞成就今天的喜慶。禮尚往來,禮失求諸野。古老的“禮”在現代鄉村得以留存,只是更換了場景、道具和形式。
鄉土敘事的現代性如何可能?劉娜的寫作從多個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我認為這樣的寫作是一種真正的根性寫作——根植于鄉村或城郊接合部,深掘地方性知識、鄉村倫理、古老習俗和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質言之,就是根植于過去和未來匯聚的當下,獲得某種生生不滅的大地性,拒絕形而上學、凌空蹈虛的公共經驗的意象化表達。因為鄉土敘事比起空渺的個人化形而上的鄉愁,更需要依傍古老鄉土和深厚的地方性知識,而詞語的光亮照亮的存在正是傳統文明最近的端口,語言的生成只有承接傳統、接續現代文明之鏈才能得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