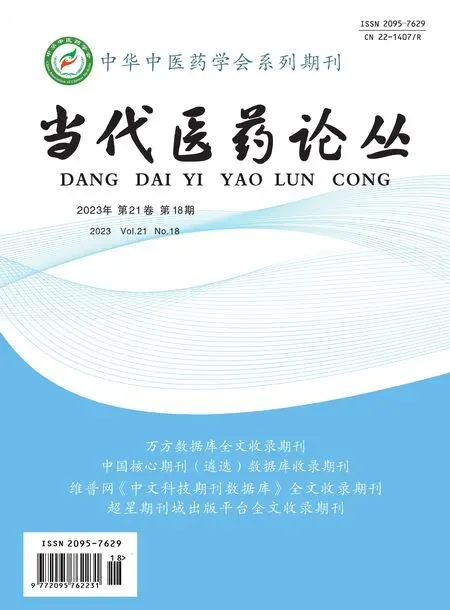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兒童過敏性鼻炎的研究進展
葉修文,范曼琪,黃樂輝,鄧 郡,葉子琴
(1.深圳市龍崗區第三人民醫院,廣東 深圳 518173 ;2.深圳市龍崗中心醫院,廣東 深圳 518116 ;3.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1499)
兒童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又稱兒童變應性鼻炎,是指特應性個體接觸到變應原后,在免疫球蛋白E(IgE)的介導下,鼻黏膜被機體所釋放的炎性介質及其他免疫活性細胞、細胞因子反復刺激,從而引發鼻部的非感染性、慢性炎癥反應。臨床通常表現為鼻塞、鼻部瘙癢、流清涕、打噴嚏等,還可能同時合并支氣管哮喘、上氣道咳嗽綜合征、分泌性中耳炎等,可明顯降低患兒的生活質量[1]。目前,現代醫學主要從避免接觸過敏原、藥物內服(主要包括抗組胺藥物、糖皮質激素、白三烯受體拮抗劑等)、鼻腔沖洗、特異性免疫治療等方面治療兒童AR,但癥狀反復發作,疾病遷延難愈。兒童AR 屬于中醫學中“鼻鼽”的范疇[2],中醫藥在治療AR 上,針對患兒體質、癥狀的不同,因人、因地制宜,從中醫內治、外治兩方面著手,在緩解患兒癥狀、降低疾病復發率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療效,故本文將近五年中醫藥治療AR 的研究進展梳理如下。
1 中醫內治法
1.1 自擬方、經方
黎燕珊等[3]將AR 患兒分為兩組,給予對照組患兒口服氯雷他定片,觀察組患兒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蒼耳子散(組方:蒼耳子5 g、辛夷花5 g、白芷5 g、魚腥草15 g、姜半夏5 g、制陳皮3 g、桔梗5 g、甘草3 g,每日1 劑,7 d 為1 療程),結果顯示在緩解患兒臨床癥狀及治療后4 周、治療后8 周的復發率方面,觀察組均優于對照組,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張敏霞等[4]將AR 患兒隨機分為3 組,分別選用不同療法:西藥組予丙酸氟替卡松氣霧劑噴鼻(早晚各1 次),中藥組予鼻鼽方內服(辛夷、蟬蛻各6 g,蒼耳子5 g,九節菖蒲3 g,煅牡蠣20 g,白芷、絲瓜絡、夏枯草、烏梅各10 g,劑型為免煎劑,2 歲以下兒童兩日1 劑,2 歲以上每日1 劑),聯合組用西藥噴鼻聯合鼻鼽方內服(藥物選用及劑量、使用方法均同上),經過2 周的治療,中藥組總有效率為88.23%,聯合組為95.58%,西藥組為55.88%,三組血清學指標﹝ IgE、白細胞介素(IL)-10、IL-17)﹞、鼻炎癥狀積分均較治療前降低,且聯合組降低幅度最大(P<0.05)。徐媛等[5]將AR 患兒分為兩組,對照組使用孟魯司特鈉咀嚼片嚼服及糠酸莫米松鼻噴霧劑噴鼻治療,觀察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小青龍湯合蒼耳子散加減(具體主方:白芷9 g、芍藥9 g、辛夷9 g、半夏9 g、五味子6 g、桂枝6 g、蒼耳子6 g、炙甘草6 g、麻黃6 g、薄荷3 g、細辛3 g、干姜3 g)口服,兩組均連續治療18 d;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的治療總有效率為96%,明顯高于對照組的84%(P<0.05),各項典型臨床癥狀積分比較,觀察組的降低幅度均明顯大于對照組(P<0.05),兩組IL-10、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水平均較治療前升高,IL-33、細胞間黏附分子-1(ICAM-1)水平均較治療前降低,且觀察組升高/ 降低幅度均大于對照組(P<0.05)。
1.2 中成藥
王艷[6]將AR 患兒分為兩組,對照組使用鹽酸西替利嗪滴劑(0.5 mL qd)治療,治療組同時給予通竅鼻炎顆粒(2g tid)內服,結果顯示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5.00%,高于對照組的8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謝良超等[7]在治療組及對照組AR患兒中均給予孟魯司特鈉咀嚼片治療,治療組加用鼻淵通竅顆粒(15 mg,tid,開水沖服,2 周為1 療程),比較兩組治療前后臨床癥狀的差異,并據此評估療效;結果顯示,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4.7%,對照組的總有效率為84.0%,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樊晉萍等[8]予對照組AR 患兒口服匹多莫德口服液(1 支/次,2 次/d)治療,治療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鼻淵通竅顆粒內服(15 g/次,3 次/d),兩組療程均為3 個月;結果顯示,治療后兩組在臨床癥狀積分、吸氣相和呼氣相氣流阻力、Der p1 和Der p2 血清特異性IgE 滴度方面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鼻孔解剖區面積均較治療前明顯升高,且治療組的改善程度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和治療組的總有效率分別為81.40%、93.02%,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馬文旭等[9]在實驗組AR 患兒中使用玉屏風顆粒內服聯合布地奈德鼻噴霧劑噴鼻,對照組AR 患兒則單純使用布地奈德鼻噴霧劑治療,治療2 周及3 個月后,實驗組的臨床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
2 中醫外治法
2.1 體針療法
何珊等[10]予西醫治療組AR 患兒口服氯雷他定片和外用鼻用糠酸莫米松噴霧劑治療,療程為4 周,中西醫治療組則在相同西藥(用法及療程均同西醫治療組)的基礎上加用針刺治療,選用迎香穴、印堂穴、上星穴、合谷穴、肺俞穴為主穴,采用飛針手法,每隔3 d 針刺1 次,每周2 次,共治療4 周;結果顯示,中西醫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1.8%,高于西醫治療組的79.6%,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隨訪3個月后比較,中西醫治療組的復發率較西醫治療組明顯降低(P<0.05)。袁龍等[11]予對照組AR 患兒內舒拿(糠酸莫米松鼻噴霧劑)鼻腔給藥治療,每側鼻孔1 噴(約500 μ),1 次/d,共治療3 周,聯合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針刺治療,選用曲池穴(雙)、印堂穴、迎香穴(雙)、上迎香穴(雙)、魚際穴(雙)、合谷穴(雙),每2 d 針刺1 次,治療3 周;結果顯示,聯合組的總有效率為92.31%,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6.92%(P<0.05),且在癥狀體征積分、總IgE及特異性IgE 水平、炎性因子IL-4、IL-10 水平三個方面,聯合組的降低幅度均優于對照組(P<0.05)。余韻詩等[12]予對照組AR 患兒氯雷他定片口服(每天1 次)、丙酸氟替卡松鼻噴霧劑噴鼻(每天1 次)治療,療程為4 周,治療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腕踝針治療﹝選用0.25 mm×25 mm 規格的無菌針灸針,患兒掌心向上,取上1 點(腕部掌面,腕橫紋上兩橫指,尺骨緣與尺側腕屈肌腱凹陷處)進針,然后調針至患兒不感覺酸脹和疼痛為度,最后用膠條固定針柄并留針30 min,每周治療2 次,左右手輪換,共治療4 周﹞,治療后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0%,明顯高于對照組的58%(P<0.05),且在臨床癥狀及體征積分、血清IgE 水平方面,治療組的下降幅度均優于對照組(P<0.05),治療結束3 個月后隨訪,治療組的病情復發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
2.2 掀針療法
張福蓉等[13]將AR 患兒分為三組,其中觀察組A 選取印堂穴及雙側迎香穴、足三里穴、肺俞穴行掀針治療,每周治療2 次,每次皮下留置撳針3 d,共治療3 周,并同時口服氯雷他定片,觀察組B 采用單純撳針治療,觀察組C 則使用外表與撳針相同的無針芯假針進行針刺(操作方法及療程同A 組),其藥物內服的劑量和療程也與A 組相同;結果顯示,A 組的總有效率為92.3%,B 組為90.0%,C 組為71.4%,A 組、C 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石磊等[14]予對照組AR 患兒口服氯雷他定糖漿(每日1 次,連服14 d)治療,治療組則在對照組用藥的基礎上取印堂穴、雙迎香穴行掀針治療,每次留針2 d,間隔2 d 再次埋針,共治療14 d ;結果顯示,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3.1%,高于對照組的6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后鼻部癥狀評分與治療前相比均明顯下降,且治療組的鼻部癥狀改善更優,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任光第[15]給予對照組AR 患兒雙百顆粒(主要方藥組成為太子參、炒黨參、炒白術、百合、灸百部、生山藥、北沙參、炒川芎各10 g,防風6 g,炙黃芪20 g,炙甘草5 g)口服,治療組則在口服雙百顆粒的基礎上加用掀針療法(進針主穴選用迎香穴、通天穴、合谷穴、足三里穴,每次留針2 d,每間隔1 d 施治1 次)治療,兩組療程均為3 周;結果顯示,治療后治療組的視覺模擬評分法(VAS)評分、總鼻阻力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4.44%,對照組的總有效率為75.00%,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灸法
羅偉君等[16]將AR 患兒分為三組,治療組A 采取蠟泥灸聯合掀針治療,蠟泥灸操作:將黃芪30 g、白術15 g、防風15 g、炒蒼耳子10 g、辛夷15 g、白芷10 g、葛根30 g、麻黃10 g、桂枝15 g、鹿角霜10 g、甘草6 g 研磨成粉,將藥粉與蠟泥250 g 均勻攪拌后用微波爐加熱,靜置到適宜溫度后將蠟泥均勻涂抹在患兒后背(大椎穴至腰陽關穴節段左右旁開3 寸),用保鮮膜覆蓋后并用電磁波治療儀保溫,每天1 次,每周連續治療5 d,療程共4 周;撳針操作選取迎香穴、上迎香穴、印堂穴、上星穴、列缺穴、足三里穴,每次留針2 ~3 d,每周2 次,療程共4 周;治療組B 則用單純掀針治療(操作及療程同上),對照組口服氯雷他定;結果顯示,在總有效率方面治療組A 為92.0%,治療組B 為79.2%,對照組為58.3%,組間對比有統計學差異(P<0.05);與治療組B、對照組相比,治療組A 癥狀評分下降幅度最大、遠期療效最優、對患兒生活質量的改善最佳(P<0.05)。
2.4 推拿療法
趙李清等[17]在觀察組AR 患兒中運用二部(仰臥位、俯臥位)五法(按揉法、旋推法、抹法、擦法、捏脊法)推拿結合藥物治療(口服仙特明,每日1 次;內舒拿每鼻孔一噴,每日一次,或雷諾考特每鼻孔一噴,每日2 次,共治療8 周),推拿選穴:頭面部:開天門、推坎宮、太陽穴、迎香穴、經外五穴;胸腹部:天突穴、膻中穴、中府穴、云門穴;小兒手指部:肺穴、脾穴、肝穴、腎穴;背部:風門穴、肺俞穴、脾俞穴、腎俞穴、肝俞穴;下肢:足三里穴,推拿每次25 min,隔日推1 次,4 周為1 療程,共治療8 周;對照組則單用藥物治療(與治療組藥物的用法、療程均相同),治療后觀察組的總有效率為93.3%,顯著高于對照組的63.3%(P<0.05),觀察組的鼻炎癥狀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孫琪等[18]在治療組AR 患兒中采用鼻部九法推拿治療,推拿九法包括:起式開天門、鼻周三穴(迎香穴、鼻通穴、印堂穴)按揉、雙鳳展翅、點風池風府大椎、橫擦項背之交、捏脊、橫擦腎俞、通元四穴(按揉膻中穴、天樞穴、關元穴)、拿肩井,隔天1 次,一周3 次,共治療3 個月;對照組AR 患兒每天口服1 次孟魯司特鈉,共治療3 個月;結果顯示,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兩組的鼻塞、鼻癢、噴嚏、流涕癥狀均改善(P<0.05),但組間對比無差異(P>0.05)。
2.5 穴位貼敷
王巍等[19]予對照組AR 患兒每晚睡前口服鹽酸西替利嗪滴劑,連續服用21 d,治療組則予益氣養陰方(黃芪30 g、南沙參15 g、山藥12 g、地骨皮10 g、黃精10 g、烏梅12 g、防風10 g、炙甘草6 g,每日1 劑,連服21 d)內服,并聯合穴位貼敷治療,貼敷藥物組成:芥子、細辛、延胡索、生半夏、甘遂,按照3:2:1:1:2 比例干燥后粉碎為末,并用姜汁調為膏狀,選用雙肺俞穴、膻中穴、天突穴、大椎穴、印堂穴,每次貼2 h,每3 d 貼1 次,共7 次;結果顯示,治療后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93.44%,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0.49%(P<0.05),且治療組各癥狀積分、總IgE定量、IL-4、IL-33 水平、血清嗜酸性粒細胞(EOS)計數的下降幅度均比對照組更明顯(P<0.05)。胡彬雅等[20]觀察三伏至三九期間穴位貼敷聯合鼻腔沖洗治療兒童AR 的療效,穴位貼敷取大椎穴、肺俞穴、腎俞穴、天突穴、膻中穴、足三里穴為主穴,將細辛、白芥子、甘遂、麻黃、延胡索、肉桂研成的細末按特定比例混合,再用姜汁調膏后貼至上述穴位上,對照組則單純用生理鹽水沖洗鼻腔;結果顯示,治療后治療組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且治療組鼻分泌物EOS 密度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
2.6 穴位埋線
楊艷艷等[21]選取大椎穴、肺俞穴、腎俞穴、迎香穴,采用穴位埋線配合呼吸補瀉之補法治療兒童AR 共44 例,2 周埋線1 次,3 次為1 個療程,共治療2 個療程,觀察其臨床療效,結果顯示治療有效率達97.50%。
2.7 耳穴壓豆
張小燕等[22]給予對照組AR 患兒常規服用氯雷他定片,并行中藥穴位貼敷,貼敷藥物組成:白芷30 g、延胡索30 g、肉桂30 g、白芥子15 g、細辛15 g、丁香10 g,打成粉末,用生姜汁調膏,貼于大椎穴、定喘穴、肺俞穴、風門穴、脾俞穴、腎俞穴上,觀察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耳穴壓豆,選用耳部的鼻、肺、腎上腺、內分泌穴,用王不留行籽粘貼置于一側耳穴部位,每隔3 d 更換為另一側耳穴,雙耳輪換,連續治療60 d,觀察兩組治療后的免疫功能及癥狀評分,并比較療效的差異;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的有效率為93.33%,高于對照組的77.78%(P<0.05),且觀察組CD3+、CD4+、CD4+/CD8+水平均優于對照組(P<0.05),而在各癥狀(鼻塞、噴嚏、流涕、鼻癢)評分方面,觀察組均低于對照組(P<0.05)。曾春蓮等[23]隨機選取50 例AR 患兒行王不留行籽耳穴貼壓治療,耳穴選取內鼻、外鼻、腎上腺、過敏區、內分泌、耳尖、肺、脾、腎及陽性反應點,每次選取6 個耳穴,耳穴貼3 d 更換1次,雙耳交替,10 次為1 療程,共治療3 個療程,結果顯示治療總有效率為82.6%,且治療后癥狀體征評分低于治療前(P<0.05)。
3 小結
兒童AR 屬于臨床多發病、常見病,中醫藥治療本病從綜合調理患兒的體質出發,辨證準確,具有安全性高、副作用小的優勢。另外,考慮到患兒服藥困難、依從性差的情況,多種中醫外治法的早期介入在減輕臨床癥狀、縮短病程、降低疾病復發率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此外,由于兒童AR 是在接觸變應原后發病,故患兒在采取積極治療措施的同時需堅持家庭護理,比如避免接觸變應原、多加鍛煉提高自身免疫力、飲食得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