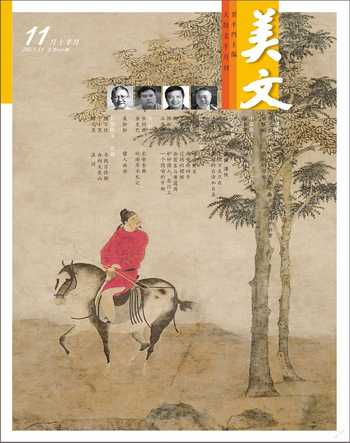嶗山冊頁
王川
一
赴嶗山那夜的路上,大巴車顛簸得久久不能入睡。歪頭一直看著田野上的茫茫夜色,大地仿佛消失了,偶爾出現(xiàn)在極遠處的路燈、村燈螢火蟲般跳蕩、游走,一團團黑乎乎的樹影似并無惡意的鬼魅急呼呼地朝身后掠去。我感覺游蕩的思緒都被夜染黑了,一縷縷融化在深廣的虛空里。
此時,初夏的手掌遍撫膠東大地,泥土與草木的氣息在物候深處布散。嶗山也已全然張開它拖曳的綠色裙裾,游人蜂擁而至,迤邐于它巨大胸襟的每個可以駐足的褶皺、紋理。一個偉大的道場變作了一座波浪起伏、心旌搖蕩的花園。人們希望在他們出現(xiàn)的地方,那些古代的神仙也能同時出現(xiàn),伸出一根手指為他們指點各類迷津。但只有山峰的手指從大地直插蒼穹,寂然無語,應答一切。對嶗山而言,沒什么不是過客。一群群人走了,嶗山還在那里;一片片云飛了,嶗山還在那里;一樹樹花謝了,嶗山還在那里。嶗山永遠峻拔。此在,空寂、不生、不死,只有綻放的當下。神仙們的昨天,在嶗山永遠都是今天,那些道場剛剛散去,便又與所有空間的道場再度共謀著另一次開始與繼續(xù)。香煙繚繞之間,嶗山不改亙古容顏。
二
古時,嶗山卻沒這般熱鬧。顧炎武在《嶗山志校注·序》(明·黃宗昌著)中說它“其山高大深阻,磅礴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即便如此,自漢至金元乃至明清,亦多有隱居、修道其中者,嶗山道教的“家族譜系”更可上溯到齊地的方仙道、黃老道、黃老之學。所以,“三圍大海,背負平川,巨石巍峨,群峰峭拔”(《道藏》)的嶗山自古即匯聚了齊地浩浩湯湯的“仙氣”。《太平寰宇記》有“秦始皇登勞盛山(即嶗山)望蓬萊”的記載。始皇東巡,無非為了訪仙問藥(也有捎帶尋根問祖一說),舉全國之力而為一己之不死。因為一個皇帝的私欲,嶗山才第一次被大規(guī)模地打擾。對此,顧炎武憤然有言曰:“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挽而后上也。……一郡供張,數(shù)縣儲偫,四民廢業(yè),千里驛騷而后上也。”始皇勞民傷財,嶗山由是得“勞山”之名,正所謂“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但他也許無意中給嶗山“開了光”,證明此處確有“仙跡”存焉,因處東海之濱,因距人間邈遠,因清寂到除了看看東海,便是餐餐紫霞,神仙而外,凡人怕是居大不易吧。就連批評秦始皇的顧炎武不也贊嘆嶗山是“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嗎?始皇心向往之,良有以也。秦之后,漢之張廉夫、五代之李哲玄、北宋之劉若拙、宋元之全真諸子,皆擇嶗山修真悟道,所以,“神仙窟穴”的古稱的確名副其實。這些“不凡”的人中,最著名的大概要算丘處機、張三豐與憨山德清了。邱長春云游嶗山時,干脆給它定名“鰲山”,“以為棲真處”。張三豐更是從海島帶來耐冬花植于庭前,它還有個好聽的名字叫“絳雪”,“正月即花,蕃艷可愛”;嶗山還有張仙塔、邋遢石等遺跡、景觀附會其羽化故事。憨山到嶗山后于樹下掩片席為居,卻不以為苦,七個月過去,始有人幫他結廬、造庵,他卻言:“吾三椽下容身有余矣!”果是大德氣派,身外無物,則不勞鋪張。我覺得這幾位高人中,張三豐更像個詩人,把養(yǎng)花種草當做一種修持的美學,也為嶗山植物增加了品種。試想:寒風獵獵,大雪空山,谷中庭院中,唯有綠葉紅花更其靜定、絢爛,如肉與靈的孤絕火焰,照亮著寂滅且永恒的道途。那番情境,有幾人體驗得到?
道人、佛僧們在遙遠的時空中出現(xiàn),即使在“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非神完骨強者,不敢久居”(明·藍田《巨峰白云洞記》)的冬季,他們仍能衣衫襤褸、枯瘦如柴、目光炯炯、道骨仙風地步上山巔。他們不是一步步登上去的,而是慢悠悠飄上去的,然后,從容自在地坐在石頭上、樹木上、云朵上,一坐就是天荒地老、地老天荒,一坐就變成了石頭、樹木和云朵,終于化成一道光,倏然而逝,無聲無息。在那些幾乎死去的古書里,我讀到過很多仿佛脫離了肉體累贅的深奧言說,玄幻而渺遠,我相信其中保留了某類存在的真相。修道者并行于兩個世界,文字記錄描述的不過是他們在人間的投影罷了。然而,作為俗人,我們卻僅有一個世界,從沒離開過山下的煙火氣。不過,即便作為俗人,偶爾也需要瞥一眼山上的紫霞,體會一下將塵世遺忘的滋味——盡管不可能盯著那高處的紫霞看上一輩子。秦始皇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他可以為嶗山寫下一首詩:“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不過是借李少君忽悠漢武帝的話吹吹牛而已,學道不成,只好寫寫詩、用用典罷了。巡游求仙的結果是勞民傷財,只皇帝做得;吹牛夸張的恣意出乎偉大的想象力,僅詩人可為。而今天的我們,可能僅剩下跋山涉水的耐力和盲目了。
三
曾三訪嶗山,相隔二十余年。第一次,從沙子口抑或王哥莊的某處山腳下往上攀爬一小時,幾近躬身躑躅,不斷左顧右盼,如前路時被阻斷的螞蟻,腳力十足地在山體襞褶里輾轉移動。抬眼間,滿眼綠色,濃稠如剛剛涂抹在畫布上的油彩,感覺迷失在一片巨大的葉子上,尋不到折返之路——那些棕紅色巖石的“披麻皴”如蒼老的樹皮般在遠處裸露、嶙峋。那次我們是去尋找“海底玉”,順便在山腳下走了走。我對嶗山的興趣遠大于“海底玉”。“海底玉”即嶗山綠石,產(chǎn)于嶗山東麓的仰口灣畔,按說屬于稀缺資源,但我當年的印象卻是——這東西多得到處都是,根本不稀罕,在村子里轉悠,幾乎每家院子里都有堆成一座座小山的“海底玉”原石。數(shù)百年的玩賞歷史,好似突然又“熱”了起來,一時成為市場新寵,叫響大江南北,也不過是炒作的生意。客商們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般接踵而至,導致過度開發(fā),嶗山突然更換了“面目”,變作了被市場經(jīng)濟拖出“深閨”的“暴發(fā)戶”。當?shù)赜袀€村民告訴我,一小推車“海底玉”原石不過一百多塊錢,簡直是暴殄天物。明黃宗昌《嶗山志·卷六》中有言:“綠石,出豐山,邑多好之,而侄孫貞麟之綠屏為難再得。”這些蘊藏于海濱潮間帶的石頭,因為開掘技術的進步,遭殃甚重,我親眼所見的比黃宗昌所述之綠屏更龐大的物件也不在少數(shù),還有雕成彌勒佛的,大大小小、胖墩墩地坐滿農(nóng)戶的半間屋子,個個都是“容天下之事,笑可笑之人”的完美表情。我真怕嶗山下面都是“海底玉”,若按當年的開發(fā)架勢,不消幾年,就可能是一片狼藉。
第二次是從景區(qū)正門進入,緩步至玉清宮。其實,最迷人的景致出現(xiàn)在沿海公路兩側,移動、旋轉的山麓,林蔭與碧海、云霞與礁巖,像空間鏡像上閃回的最美畫幅。之后的漫長行走中,嶗山始終以冷峻而泰然的方式打開,路旁清寂的樹木,在繁盛中隱含著一種落寞而沉思的表情,像是躲在時間深處的等待與持念。潔凈的山道深掩于植物的氣息里,每一步上升都沐浴著陰涼,卻聽不到一絲季節(jié)的回響,好似時間靜止了。仰頭觀望,樹木、花朵、石階、院墻、道觀、神像,皆沉默無語,空氣在它們上邊睡眠、擴散、垂落,陽光于若隱若現(xiàn)的縫隙間棲止、晃動、漂移,就像道士們的身影與表情,攜著恍惚、縹緲又輕盈的節(jié)奏閃過。嶗山是一個讓人放下執(zhí)念的地方,它的陳述只有一個詞語:無為。因為無為,一切才如此茂盛,連潮濕的地面與方磚上的苔蘚也茵茵如毯,從未被人踩踏過。蜂蝶和鳥兒在花叢里、樹葉間、房檐下飛來舞去,像是在展示時空的無目的性或合目的性。下清宮茂盛的耐冬讓我想起韜光尚志以為清虛元妙的張三豐,好似他剛剛灑掃完庭除,身影在枝葉間一閃,就不見了。古書有言:“夫古之至人,其動也天行,其靜也淵默。” 大概就是說他這樣的人吧。雖居嶗山之下,與下清宮未必有什么瓜葛,但他移栽的植物卻蔓延整座嶗山,枝葉芳菲,如他穿越時空的玄想。其實,下清宮乃憨山所留禪趾處,明高弘圖《勞山九游記》有記載:“諸勞皆道院,上人(指憨山)于此起禪林……”坐在半路的石階上看小徑蜿蜒,那一刻,我感覺有些恍惚,不見憨山,不見邋遢,不見古人來者,卻在時空的景深處,看到了自己的虛影,被花樹與殿宇的虛影籠罩著,一寸寸沉入萬物之淵默,心相與物象,實無任何差別。當夕陽斂去大地的光澤,山下的城市華燈閃爍,不知怎的,忽然產(chǎn)生了強烈的“出離”之感。
第三次登嶗山,全然是享受松松散散的寬泰,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如禪悟,如隨意的翻書,腳步跟著感覺走,了無牽掛得很。那是從背面山陰進入北九水,行不多久,便和幾位好友在一池碧水邊的小亭子里談天說地,雖是初夏時節(jié),景色蕃盛,所見也不過亂花迷眼,清香蔌蔌,雜樹欹斜,翻風自亂,并無甚拈心留意處。卻唯獨對北山門旁的農(nóng)家宴記憶深刻:金黃色的炒笨雞蛋、嫩綠的嶗山蕨菜、香噴噴的燉柴雞、味道濃郁的蘑菇、爽口清脆的桔梗……都是山里的道地土貨,味道足令人惦記多日,以至有朋友兼詩人名“華清”者建議:大家湊錢買棟山間別墅,退休后來此度假,偶爾尋訪一下嶗山道士,學學長生不老之術,豈不自在快活?……嘻嘻然談笑間,捋一把胡須,仿佛將希望與妄想都留給了以后的歲月。
三年過去,我已非我,嶗山依舊乎?
四
還是從沙子口登山,完成一次對嶗山的縱向穿越。
晨曦初露,前方一片微亮暗藍的天光。我們抵達了“大河東”。這也許是一個村莊的名字,只見一條很窄的公路深入到一片稠密的玉米地里。天略陰。迷蒙中有細涼的雨絲飄拂,若有若無。一夜顛簸,剛剛襲來的困倦被黎明前的熹微一掃而光。背起裝滿水、食物、應急工具的包,跟隨一隊人馬朝那塊高翹到天際的巨石進發(fā)。
布谷鳥的呼叫出現(xiàn)在起步之初的開闊地帶。這種性格孤僻的大杜鵑就像離群索居的詩人,躲在初春的冷寂和晚春的寥落之間,抒發(fā)著不被回應的情愫,那種間隔著等待的叫聲單調、圓潤,如語詞簡樸的歌吟,重復丈量著大地的廣度。也許很多詩人從中領悟了表達的真諦。“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誰說王維沒有把遼曠的詩境投放到唐朝的山水和此間、此刻呢?那些詩歌的光芒飄過緲緲歲月呈現(xiàn)為眼前的婆娑景象。如果你到過春季的嶗山,聽到嘹亮的布谷聲聲,會覺得,唯有它叫得你靈魂出竅、虛虛飛升,也許“望帝春心”的古典背景在此間又多了一個明媚而廣遠的維度。
我們就在這樣的背景中走進了一個村子。村南,嶗山正在大地上落座。
村子的房屋均由赭色石頭砌成,院落毗鄰,高低錯落,周邊花木蔥蘢,棲落著一層層斑斕與靜謐。走勢、布局與材質均取自嶗山。有位早起的、須發(fā)皆白的老者將爐子搬到路中央,生起第一縷炊煙,那炊煙就像他身著的藍衫一樣,被微風蕩起一層層順滑柔軟的褶皺。他并不好奇身邊出現(xiàn)的一隊行人,自顧彎腰揮動著蒲扇。那種與鄉(xiāng)野渾然一體的神態(tài)、表情和體征,沉靜、恬然,仿若嶗山的一抹投影。平淡的生活在這里依舊續(xù)接著遠古的歲月,只安靜地占據(jù)著清晨一個最小的角落。
沿路的麥田邊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櫻桃樹,成熟的紅櫻桃在濃密的綠葉間閃射出鮮艷的光澤,圓潤紫紅,像一簇簇墜在枝葉間的珊瑚珠,掛著晶瑩透亮的雨露。正是嶗山櫻桃成熟的季節(jié),果園如滑落到山腳下的綠色云海,成行成片的櫻桃林在視野里綿延、擴散,鋪排著一種珠玉瑪瑙般的豪奢,宛如盛大的宴筵,那蘊含在飽滿果肉里的汁液流動著大地額外的慈悲,布散著炫彩多姿的詩意和啟迪味蕾的光芒。
《嶗山志》有載:“櫻桃,有家櫻桃,味甘。而蠟珠尤大而肉豐,水多;有山櫻桃,味兼酸,調以糖,蒸食最佳。二種皆可作干。”所見皆“蠟珠”也,帶著溫潤的“寶光”。當穿過村莊,行走到一座水庫和公路間的櫻桃園時,我不止一次停下腳步,望著滿樹的紫紅出神。與此前所見不同,居然是小櫻桃樹。我熟悉這種小櫻桃甜美、柔糯的滋味和口感,小時候曾在故鄉(xiāng)的親戚家大把大把地朵頤過。我的故鄉(xiāng)泰山周邊多植這種櫻桃樹,果實雖小,樹樁卻高,采摘困難,不易保存,因而城市人難得品嘗,終被碩大如棗、保質期長、便于長途運輸?shù)拇髾烟宜〈谑牵粋€櫻桃的時代倒下去,另一個櫻桃的時代站起來。
五
清晨,大亮的天光籠罩剛剛覺醒的事物。
嶗山腹地。粗糲、繚亂的植物毛發(fā)開始包圍、糾纏我們,在時隱時現(xiàn)的小徑上或仰或俯,或左或右,或停或奔,像一群被豐茂的綠色盛宴弄得不知所措的山羊,一群久困城市圈欄剛剛逃入山林溪泉的野獸。
天氣薄陰,霧靄繚繞,沁涼的微風在皮膚上游走。巨大的巖石從云霧中探出來,嶗山高聳在前,不知到底是山在云海里,還是云海在山里。厚厚的植被包裹著它,蔥蔚蒼郁。我們很快陷入到一團密不透風、東西莫辨的綠海莽叢之中。山不見了,眼前晃動著濃釅的綠,不時又被繚繞的霧氣遮擋。細雨飄飛。橫七豎八的枝條掃過赤裸的胳膊,時常要抬起手臂遮住頭面。許多大樹的長根裸露地表,橫穿路徑,像大地騰起的筋脈。
焯爍、明艷的花樹是大地最絢爛的辭章,令人欣悅。嶗山處亞熱帶和北溫帶交接處,所謂亞熱帶之終,北溫帶之始,一些樹明顯帶有熱帶叢林樹種的特征,長長的葉尖兒垂而朝下,像是總要準備滴水的樣子。但更多還是那些北方常見的胡枝子、荊條、黃櫨、映山紅、小葉鼠李、薔薇、赤松、稠李、華北落葉松等,在斜坡、峪谷、沖溝、崖縫間蓬生、交疊、纏繞、沖蕩、競逐、蔓延,活生生地泛濫著,占領了幾乎每一寸土地。而在駁雜、紛亂的溫帶灌木叢下,那些多年生草本植物更以最自然無序的方式,繁生蓬勃著各種或長或短或寬或扁或尖或圓的葉子,開著花的或不開花的——白茅、地榆、鵝掌草、桔梗、柴胡、百里香、玉竹、百合、結縷草、遠志、石葦、木半夏……好似一片從未有人闖入的茂密蕪雜的草藥園。沿途一簇簇開著白花的稠李時常吸引我的視線,它的花型很像家養(yǎng)的茉莉,卻居然開在樹上。錦帶花比稠李多得多,潔白、淺粉色喇叭狀花朵一叢叢綻放,密密麻麻,格外艷麗。青澀的剛成形的核桃、山楂、桃子上沾滿晶瑩的水珠,微距鏡頭下也有一番驚心動魄之美。各種花草和植物的氣息雜糅在一起,芬芳濃郁。地質、氣候、土壤,造就了嶗山植物的奇跡,繁盛、質樸的萬物偃臥其上,讓它成為一個豐富、內向、壯碩的母體,成為一個坦然、深沉、多趣的男人。通過這么多植物,它表達著道法自然、普度眾生的宏愿。
在山麓腹地,雜草與灌木濕漉漉、綠生生地覆蓋了黝黑蓬松的腐殖質土壤,蒼白或肉紅的巖石偶爾露出一星半點的堅硬質地。植被逐漸淹沒了所有的路徑——其實根本就沒有路,我們完全是踩著一條石塊和石條擺放成的“路”行走。這是人的智慧,只有不朽的石頭才能抗拒泥濘,節(jié)省足力,在四季輪回的叢莽深處標識出前行的方向。也許動物不需要什么路徑,在嶗山,我們從未遭遇一只野獸。那些兔、獾、獐、貉、狐貍等都消失了影蹤,其實它們足跡遍布,隨處可以遁跡。我只能解釋為,這片貌似原始的叢林尚未遭遇人的過度侵占,而嶗山更是具備“足以容物”的博大宏闊:“……高山峻嶺,弋獵者罕至,則獸不駭,鳥不驚,山之足以容物也。”
德國占領青島時期(1897—1914)在嶗山開辟了16條通道,我們選擇的這條路不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條,于是,只能聽從于石塊、石條的引領,不敢稍涉亂草一步,腳板盡量踩在翹起的石棱上,步履謹慎而快捷,怕稍作停留,前邊的人便會像站立奔跑的蜥蜴一樣倏忽不見影跡,若遇岔路,很可能迷失于山野莽叢之中。走在最前面的領隊時常喊山,如虎嘯猿鳴,其用意便在于讓后邊的人隨時判斷、矯正自己的方位。既然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去參觀“九宮八觀七十二庵”,就應選擇這樣的方式穿越叢林、谷地和山脈。確實,在水泥筑起來空間里呆久了,一旦進入山林與荒野,我就有種強烈的穿越感,有種對現(xiàn)世的恍惚感。離開城市的燈紅酒綠、市聲喧囂,寫字間、辦公桌、會議、學習、匯報、表格、飯局,不必矛盾地、揪心地,甚至憤懣地生活,被與生命無關的東西活埋、窒息,該是多么敞亮與幸運,哪怕只有一瞬,哪怕沒有未來。我想,做過高官的耿介之士黃宗昌在崇禎三年(1630年)辭官后即探勝嶗山,遍訪道長與宮觀,于家鄉(xiāng)建玉蕊樓,滿懷激憤地書寫《嶗山志》,其最初的心境大抵正如萊陽人張允掄在其書《序》中所言吧:“嗟夫!君子不幸而與山為緣,猶幸而得不愧于兩間,則舒慘嘯歌,亦安在不可一日百年哉!此志之不可以已也。吾悲夫先生處晦而困心,衡慮不得一伸,乃作山志。其亦重有憾也夫!”沉浸山野,黃先生一定有遠離官場的解脫與慶幸,人生如幻的恍惚也會更強烈——相比嶗山之宏闊、高峻、有容,那些世間遺憾又算得了什么。難怪他在《自序》中直抒胸臆:“余不敏,不見容于世,……嶗山乃容余乎?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環(huán)視天下,獨有嶗山耳。嗟乎!時所在,命所在也;命所在,性所在也。人道不昧,其嶗山之力乎?余無足重于嶗,而嶗為有余,則嶗所自立于斯世,斯人之會者,因緣不偶,是安可忘哉。……嶗無心也,心乎嶗者,其恍然于所見、所聞之外乎?”他已把嶗山對他的意義以及他與嶗山的深層關系說得非常明白、透徹了。他深知兩段毫不相干的人生履歷必然浸染出不同的靈魂底色,即使僥幸逃離黑暗的官僚系統(tǒng),靈與肉都需要持久的撫慰與重塑才能存續(xù),投入家鄉(xiāng)附近的嶗山懷抱,對于他這樣的文人來說,幾乎是命定的選擇。嶗山讓他悟到了生命的本相:“人生如幻,我不識我。幻復生幻,爾又為誰。”古往今來有此感喟者又何止一個黃宗昌呢?
六
漸漸地,腳下這條石板路已很難再定義為路,隨著坡度增大,大多地方失去了路的形態(tài),更像是一堆亂石崗。由于雨季水量豐沛,原本靠下滑的力咬合擠壓在一起的石條,被一瀉而下的山洪沖亂,橫七豎八,泥漿變成了潤滑劑,修路者只好放棄進一步的努力。
盡管水沖雨打,石頭下面一定隱藏著一條年歲久遠的山間小徑。我不明白在這半原始的山林中鋪設石徑的意義,它不像是城市舊街巷里的經(jīng)年石板路,被踩踏、車碾,被歲月磨洗——越是光可鑒人,越是容顏蒼老,越會保留更多的追憶和回聲,銘刻更多的悲喜與蒼涼……但它卻給了我們一次在泥濘春雨中攀登嶗山的機緣,也讓我再次感知到時間與空間在城市與莽野中截然不同的流速和張力——我們在其間來回挪移,既要于輕度的冒險里突圍生命短促且無聊的屏障,又要在庸碌的日常中服從命運悠長且重復的安置。這大概就是生命存在的語境吧。在嶗山兩天的跋涉中,我看到了它們交疊的折光在我心中不停地掃過。
石板很快消失了,只好踩踏著灌木叢間的青草陷入泥濘,小心翼翼地蝸行。濕滑的泥水不斷修改著重疊在爛草上的足跡,腳步變得猶疑而遲緩。雨仍在下,忽而淅瀝,忽而傾盆。風鼓蕩于樹冠之上,雨便時疾時緩,沙沙之音忽近忽遠地掃掠。挓挲著濃密枝條的灌木橫阻、擗打著身體,我的頭發(fā)和衣服已經(jīng)濕透,眼鏡片罩上了一層水霧,視野一片模糊。途中,只在一個山脊的小樹林中稍作休息,便重新組合起癱軟在地上的骨架,向更高處攀爬。跟腱酸脹,雙腿顫抖。已經(jīng)行走數(shù)小時,有人祈禱雨停下來,在山頂看到太陽和云海。
當行程過大半,步上一個山間平臺時,幾塊高聳的巨石后面射出了一道被雨水洗過的金屬箭簇般的陽光。每張頭發(fā)緊貼額頭的濕漉漉臉龐瞬時被涂了一層油亮。于是歡呼一片:天晴了,天晴了。
拐上一個緩坡,一塊巨石橫搭的“橋”棲落在出斜上方兩塊并列的石頭上,前行之路恰從下方穿過。近人周至元《游勞指南》里記載過這處奇景:“南北兩巖特起,有巨石,穹覆之雄,暢宏闊大如城門。”自“橋”下仰望,一層薄霧覆蓋的白色山峰高高挺在濃密的樹梢上,峰頂數(shù)塊巨石堆砌,褶皺間鼓起一塊塊硬邦邦的“贅肉”,如巨人肢體的一部分,如被冰川磨去了棱角的圓潤發(fā)亮的傷疤,傷疤周邊亂蓬蓬地拱出幾綹灰綠色“毛發(fā)”。它以丑陋的形態(tài)顯示著一種高不可攀的凌厲冷峻與先聲奪人的滂沱氣韻,以一種岞崿峭拔的雄美霸氣,巍然聳峙于亂云飛渡的天空之下。
進入石階引路的“巨峰風景游覽區(qū)”,腳底爽靜了。路邊有鵝卵狀巨石兀立,皆似從天外飛來,盤桓落定于億萬年前。作為嶗山的“鼻祖”,此間“群峰環(huán)列,巍然巨觀”。那座高聳的“自然碑”,在云霧中忽隱忽現(xiàn)。第四紀冰川曾把它周圍的巖石拖蝕,只留下這孑然一身的孤影傲立。在一處平臺從背后看它,簡直就像一只站立的猴子,楞呆呆地目視著前方。它是在訝異周遭的洞壑之奇,還是在訝異倏忽之間就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明代文人曹臣在《勞山周游記》中寫它“直削千尺,本修額短,儼若天質之妙,因笑秦皇漢武,何不于此勒功德而遂失之也!”問得好。好大喜功、睥睨天下的秦皇漢武怎就沒像登泰山那樣,也在嶗山勒石以記呢?那可是流芳萬世的“重大舉措”。何況,秦始皇刻石亦非一無是處,《文心雕龍》不是有句話嗎——“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對此,還是周至元的一首詩回答得有趣:“巋巋豐碑矗,樹來不計年。鑿應施鬼斧,題尚待飛仙。苔篆蝌文古,云浸螭額鮮。秦皇空一世,不敢勒銘篇。”他的意思是,嶗山奇峻,勒石須鬼斧神工,只有神仙和大自然做得,你秦始皇有啥資格或本事呢,雄霸一世也不過身后空空,竟不敢在嶗山的巨石上任性恣意。不過,話說得還算客氣——該是秦始皇面對嶗山有自知之明,只能望峰息心吧。嶗山阻斷了他的癡心妄想,站在嶗頂遙望,大海已是天涯盡頭,浩瀚無際的洶涌波濤豈是他能征伐占據(jù)的領土,踏海耕濤者自有比他能耐更大的仙人、方士,他們飄忽無跡的身影則更為他的人間凡掌所不能抓取,只能望洋興嘆而已。
嶗山是膠東半島龐大的存在,其根脈深探入海,無處不是風景,所謂“游覽區(qū)”,僅僅是人為圈定的很小一部分。《嶗山志》記載,能稱得上“名勝”的就達六十余處,有山、有水、有泉、有嶺、有崮、有澗、有橋、有宮、有殿。其實,古人的腿腳實比今人強健,涉足廣遠,不辭辛勞。而寫嶗山游記者,明清文人居多,亦說明此前的嶗山主要是一座“神仙穴窟”,除了皇帝感興趣,一般人不會無事去耍,故中間那么漫長的時間,只有神仙們在里面逍遙自在,不被叨擾,閑云野鶴,飛來飛去。似乎明清之后,嶗山才熱鬧了起來,文人雅士像飛過嶗山的鳥一樣,灑落下大量明麗婉轉、逸韻深采的動人語詞,嶗山也多少有了點人間氣息。
嶗山是道教名山,景區(qū)內自然少不了體現(xiàn)道教文化的建筑。距自然碑不遠,有一石牌坊,名“離門”。左右石柱上鐫刻著一副對聯(lián)“乾坤知造化,登易學堂奧,瞻視無礙, 天地任作為,入術數(shù)門庭,悟法有方”。往上走,又進入“巽門”,則是一處并無院子的圍墻了,一門兩側也有一副舒體對聯(lián)“山川通氣千古秀,江河蘊德萬物新”。我對門邊的仿古建筑、環(huán)廊斗拱、飛檐彩繪、黑瓦白墻無甚興趣。不過,在山頂立“巽”“離”二門該是有所講究:巽為木,為風;離為火,為電。……回顧方才的經(jīng)歷,覺得也算恰當。
穿門而過,峰頂在望。那是“靈旗峰”,于“金剛崮”上卓然聳峙,直入云霄。“秀削而薄,如旗展開”,其高雖僅次于右側的巨峰,卻堪稱諸峰的“精神領袖”。“領袖”實由位置決定,不必“個頭”最高。它周邊遍布“嶗山之碑”“嶗山之穴”“嶗山之槽”“嶗山之洞”“嶗山之峰”“嶗山之臼”,林林總總,不可計數(shù),似乎拜見“領袖”之前,總要有點鋪敘和前奏,讓你覺得嶗山千奇百怪的石頭都具有音樂般高高低低的節(jié)奏,雖是默音和鳴、各自為政,但也是必不可少的烘托與陪襯。
一步踏上峰頂,視野何其雄闊,風光排闥而來。巨石連片,自山頂迤邐四方。北面的卦峰上,陽光正好剝開云霧,照耀在天文臺迷彩一般斑斕的穹頂上,閃射著暗綠色光輝。東面的環(huán)山?jīng)]入云海,峰巒像漂浮在海上的島嶼凝然不動,在白亮的云影折射下顯得神秘莫測。站在靈旗峰頂一塊暗紅色巖石上往南眺望,嶗山盡收眼底。綿延的綠和綿延的山,在忽聚忽散的白云間撩撥、沖蕩著視線。光色跳蕩,陰晴不定,云霧籠罩的山體危巖倏忽間變得隱約可見,蒙上一片灰藍色,天光暗淡,竟如傍晚;又倏忽間,太陽復鉆出云海,山間的霧氣野馬般奔逸四散,白色的山巖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巖石褶皺間的植被重又浮現(xiàn)出錦緞般的碧綠蒼然……
盤桓間,忽見兩塊山體縫隙間有座橋,名“先天橋”。其下一道深澗,即“一線天”。很多人擁到“橋”上拍照,云霧繚繞中,個個仿若仙人。
已近正午,有人從山頂漫步到附近的摘星樓里休息,有人則行至更遠處的山巖邊,扶著長長的護欄向遠處眺望。此刻,你想到了什么?是所謂“意義”么?那些透明、切近而本然的事物,那些晦暗、遙遠而混沌的虛無?比如生命與愛情,比如此在與遺忘,比如歲月的睡與醒、夢與真?一個異峰突起的高度或許會讓你奢望平庸“異變”的可能性,就像日常的瑣碎會變做夢中的奇跡,就像行走中驚異地遇到了另一個少年的自己。恍然的追憶。流逝的光陰。跋涉的莽野。匆迫的步履。那些聚散與追緬。那些淺悅與深涼。這就是意義嗎?如果“意義”終結于所有外在的現(xiàn)實、沉重的肉身,只有一個精神的“當下”,那就有可能擺脫迫不得已的自慰,擺脫虛妄的努力導致的持續(xù)損毀。遠古的仙人們,也許早就跨越了“身心”這個封閉而狹隘的范疇,不再覓求某種意義,只把嶗山也看做心相的投影,則“履愈高,心愈平,目愈曠,神愈斂……”之論,豈不等而下之了么。
但觀眼前之境,我還舍不下這番“等而下之”。此類貪著,歷代文人雅士更有甚焉。明紹興會稽人陶允嘉在《游嶗山記》中寫道:“陟其巔,眼界驟寬,山與海交,海與天接。上下一色,似凈琉璃……遠島累累,淡若修眉,晚霞映波,縹綠萬里,與碧落無異……”那般景致,無非嶗山動態(tài)長卷的一個霎那、一個邊角。在同一處地點、同一個角度,時間的手指總能翻動出連貫又迥異的畫幅。此刻卻是正午,云霧明亮,飽蘸陽光的粉末,在天空涂來抹去,哪還能看到海天相接、遠島累累?但它們就在那里,那邊——那邊,還有那邊,在虛空之下、萬物之上,矗立于凡塵之外的時間廢墟里,如大海的遺孤。凈琉璃的世界當在天地與人心皆纖塵不染時方可得見,如佛之示現(xiàn),那自然不能淪為“等而下”之論,豈僅“目曠”所能及之。
美色也會令人目盲。困意突然襲來。許多人享受著陽光的照射與撫摸,躺在一塊塊平整的巖石上睡著了。我也美美地睡了一覺。在山頂四仰八叉地蓋著天空睡覺還是第一次。身邊摔打撲克和嬉戲吵嚷的聲音慢慢淡下去,廣闊天地把一切嘈雜變得清脆易落,花瓣一樣飄落。而在醒來的一刻,四周的聲音隨即復活,杳杳冥冥如宇宙初音,如鳥兒的翅音一樣遙遠,如浮云投下的陰翳一樣飄動。
下山時,決定走先天橋下的“一線天”。兩截幾乎垂直上下的鐵梯子在一個冷森森的山洞里拐了個180度角。小心翼翼地下來,眼前——面朝南,是萬仞夾壁間一條狹窄的藍天和一條伸向腳下的陡峭石階。左側的石壁上沾滿了一層干枯的藍灰色苔蘚,一條繩索懸垂而下——難道曾有過攀巖者,想用一根繩子把自己從嶗頂順到“一線天”下的石階上?那的確需要膽量。方才有人在下鐵梯子時的幾聲驚呼,讓我感到此處連回音都是險峻的。危險總強調肉身的存在。
到達一座韓美林風格的巨大石龜?shù)袼芮暗氖品粫r,霧氣又變得濃重起來,煙雨迷蒙中,公路上車輛奔馳的嘈雜聲越來越近。剩下的只是長途步行了。我們抄近路橫穿盤山公路,到達仰口農(nóng)家旅館已是下午四點。坐在海邊的巖石上,看著近海幾艘隨波起伏的捕魚船,我度過了一個沒有落日可看的黃昏。暮靄漸起,海浪喧嘩,天地沉寂。
七
第二天,自另一條山路進入北九水。那的確是個美麗的去處,不知有多少沁涼、清澈的溪水從豐厚、磅礴的綠色里溢出,且億萬年抗拒著時間的耗損與圍堵。
綠樹掩映的石階山道邊,一道溪澗垂瀉,流水淙淙,在石頭上撞擊出細小的浪花,相隔不遠,積水成潭,清澈見底。我不知道北九水距我們進山之處有多遠,更不記得鉆入那巖岫繚繞、沈沈蒼釅之中是否真的涉水九次,我想,也許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這種自虐的方式造訪嶗山了,于是有了一種相見即是別離的“悲愴”。
身后漸漸迫近的隆隆雷聲和山下涌起的云霧強化了這種悲愴,天驟然陰黑下來。沉悶的雷聲很快在頭頂?shù)臉渖疑献冏隽嗣土业呐Z。大雨合著冰雹猝不及防地從天而降,擊打出一片啪啪、唰唰之音,且越來越響。榛蕪處處的密林間,我的一次性雨衣很快被扯出了幾個大洞。疾雨冷風中每個人渾身瑟縮打顫,急需找個避雨的所在。沒想到,附近果真有個防空洞。滂沱雨水澆淋一個多小時后,我們終于一個緊跟一個,貓身進入了那個只能容一人進出的洞口。
洞內又黑又冷,好在還干爽。進去的人大都在離洞口不遠處站著,觀察雨勢。有幾個帶著頭燈和強光手電的年輕人深入洞中勘察了一番,回來報告說洞很深,不止幾千米,里面還有許多“房間”,有銹跡斑斑的發(fā)動機等設備。這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時代留下的遺跡,但這深山中耗資巨大的戰(zhàn)備工程并不靠近市井可以改做他用,一旦廢棄,只能做路人的避雨之處了。
涼風嗖嗖從洞內吹過來。幾對情侶彼此擁抱著取暖。有人拿出食物在黑暗中咀嚼。我深入洞中,找了個無風的拐彎處站著,有好幾人跟著進來,圍在我身邊。
完全聽不到雨聲了。我們都沉默不語。黑暗中,時間再次靜止。進入這冷冰冰的黑暗,我覺得緊縮成了一塊石頭。我想盡快離開。我感到冷。我沒有可以擁抱、可以互相取暖的人。
出洞口,雨小了。在一片山水的嘩嘩聲中繼續(xù)行走。大家決定留下個遺憾,不去北九水,而是下山返程。我這才知曉,我們沒過北九水,而是被浩瀚的嶗山收藏在一個小角落里。
剛走上山間公路,瓢潑大雨再次驟降,狂風像一只橫貫天地的巨大的手掌,強推著我們踉蹌前行。山崖飛瀑雷震,左側的河谷激流奔騰,轟鳴貫耳,所有的驚呼被大風扯碎。每個人都拼命靠緊右側的山巖,緊緊抓住斜逸的枝條,生怕被大風吹到天上。身上的雨衣被撩起,蒙住了整個頭,只能不停地用手緊緊拽住上下翻飛的那層薄薄塑料,還是淋了個精透。四周的山完全隱沒在水霧里,一片昏暗,天地攪在一起。鼓蕩的風雨攜裹著我們跌跌撞撞、東踅西倒,像一群喪失了家園、被白日夢迷醉的流浪者。
忽有一輛面包車開到身邊,招呼我們上去,每人五元,送到山下。此刻還猶豫什么。車門拉上后,有人說:“什么叫幸福?這就是幸福!”
雨終于徹底停了。我們在一個出售櫻桃的門店前下車,大伙魚貫而入,一邊讓司機掉頭去接后面的人,一邊打探起了櫻桃的價格。待大家聚齊,幾盒櫻桃早被搶光。我拎著一塑料袋櫻桃大方地與別人分享。櫻桃真好吃啊,應該是“另一個櫻桃的時代站起來”后的那種。
再次回到仰口的農(nóng)家吃飯。說不上是午餐還是晚餐,都吃得很香,大口喝酒,大口吃肉。醉眼迷離地往上面一看,天怎么驟然間就大晴了,果是一塊凈琉璃。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