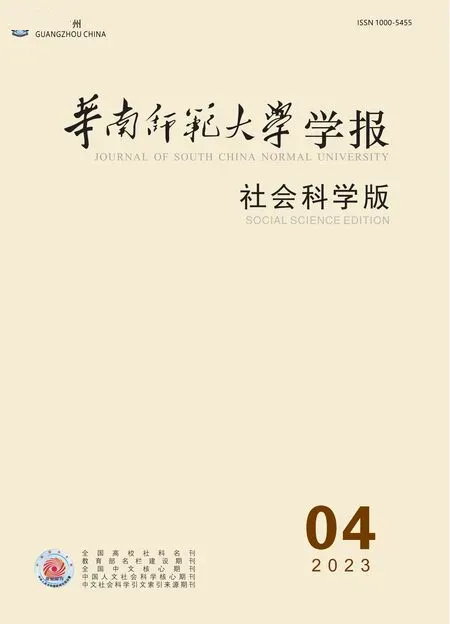孟子“仁政”:上古三代國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
魏衍華
(孔子研究院,曲阜 273100)
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孟子曾“受業子思之門人”,研習的自然是孔子、儒家之道。在“道既通”之后,孟子曾經游說齊宣王、梁惠王等戰國時期的大國諸侯國君。由于他所“述唐、虞三代之德”與當時社會中“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的主流思潮不相容,最終不得已選擇了“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第2343頁。。既然《孟子》是“述唐、虞三代之德”,是“述仲尼之意”,那么,它自然就屬于接續此前中華圣王之道最經典的儒家文獻之一。就《孟子》一書的性質而言,東漢時期學者趙岐在《孟子題辭》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大賢擬圣而作者”,“則而象之”(2)阮元:《十三經注疏(清嘉慶本)》,中華書局,2009,第5792-5793頁。的說法。這里的“大賢”自然是指孟子,所“擬”之“圣”無疑是指孔子,所“則”之“象”理應是指《論語》。對此,學者們似乎并沒有明顯的觀點分歧。所以,《孟子》一書天然地具有顯著的“切事”特點,自然也就屬于傳世經典中教化社會人心、關注社會治理的思想載體,它的核心就是孟子所規劃的“仁政”學說。當然,“仁政”并非孟子個人的獨創。孟子從此前的圣王、周公以及孔子那里汲取天下國家治理的思想智慧,進而試圖從根本上解決或化解戰國時期的社會危機,成為繼孔子之后中國傳統社會國家治理思想的又一位集大成者。
一、孟子“仁政”與“堯舜之道”
在傳世本《孟子》一書中,堯、舜通常是被連稱的,也幾乎是該書出現頻率最高的兩位圣王,成為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學的重要思想源頭。盡管《孟子·公孫丑上》篇中記有“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以及“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3)《孟子·公孫丑上》,載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第234-235頁。本文對《孟子》的征引皆同此版本,以下只注篇名。等孔門弟子對老師的贊譽之辭,但在孟子看來,堯、舜仍屬于此前圣王序列中的被“祖述”者。“堯”字在《孟子》各篇中先后出現了61次(其中包括“堯典”1次),“舜”字則先后出現了101次,分別見于《梁惠王》上、下篇以外的其他所有各篇,其中以《萬章上》最為集中。在孟子心目中,堯、舜應該是一體的,比如《滕文公上》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離婁上》的“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告子下》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這樣的角度說,“堯舜之道”理應是孟子“仁政”學說的“根”,是他解決戰國時期社會問題的思想之源;而《公孫丑下》中“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一語,代表了他對“堯舜之道”與天下國家治理思想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刻理解。
在孟子的內心深處,中華上古、三代時期的圣王是有一套相對完備的思想傳承體系的。這套體系的起點至少可以追溯到以堯、舜為代表的上古圣王時期。此后,夏、商、周三代時期的開創者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人,通過禪讓或革命的方式接續堯、舜治理天下時的思想精髓。當然,由于時代不同,不同時期的圣王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不完全相同,這就要求他們對治理天下國家的具體方略進行“因革”“損益”式的調整或變革。不過,其中蘊含的精神則是一以貫之的,內核應是《論語·堯曰》開篇說的“允執其中”,而它也成了理解“堯舜之道”的關鍵點。朱熹在解釋此語時說:“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93頁。錢穆先生解釋說:“允,信義。中,謂中正之道。謂汝宜保持中正之道以膺此天之歷數……茍四海人民皆陷于困窮之境,則君祿亦永絕。”(5)錢穆:《論語新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456-457頁。由此推論,傳統學者差不多皆將“允執其中”一語與“四海之人”的生活狀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只要不使天下的百姓陷入窮困,“君祿”也就不會“永終”或者“永絕”。
孟子“仁政”學說的內在精神與此前的中華圣王思想體系是一脈相承的。在周游列國的過程中,孟子曾極力勸說諸侯國君效仿堯、舜,為國內百姓提供和平的政治環境,創造和睦的生活氛圍。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傳統意義上的“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在與諸侯國君的問對或交鋒中,孟子極力推薦他的“仁政”學說,并且非常明確地將“仁政”與“堯舜之道”聯系在一起:“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語的內涵并不復雜,其要義是說,在治理天下國家時,堯、舜等早期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同樣需要實施“仁政”,闡釋了“仁政”應該處于天下國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孟子接著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自行。”(《孟子·離婁上》)這里的“先王之道”,就是他心目中的“堯舜之道”,就是他一再闡釋的“仁政”學說。當然,這段話的背景是在齊國游說齊宣王,企圖勸誡他在國內推行“仁政”,勸誡他將先天具有的“仁心仁聞”惠及國內甚至天下的普通百姓,進而為后世為政者提供一種樣板。
在孟子心目中,堯、舜是以“仁政”治理天下的標桿式的圣王。堯、舜首要的品格是具有一顆心懷天下的“公心”,尤其注重從天下國家治理的角度將最賢能的人選拔出來,也就是《孔子家語·禮運》篇說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鄭玄認為,“大道”指的是“五帝時也”(6)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本)》,第3061頁。;王肅認為,“大道”指的是“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楊朝明則將“大道”解釋為“夏、商、周三代‘圣王’時期治理天下的準則”(7)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社,2009,第364頁。。學者的上述分歧并不影響圣王把“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為政理念實施于天下國家治理的全過程之中。孟子認為,堯、舜應是這一思想理念的締造者、踐行者和傳承者,在與許行的信奉者——陳相的辯論中,他做了更為詳細地闡釋和說明: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
面對“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以及“五谷不登”等社會危機,“堯獨憂之”一語體現出上古時期圣王關懷天下百姓的品格。堯依據“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原則,果斷地啟用來自民間的虞舜,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舉舜而敷治焉”。根據此前學者的理解,“敷”的意思是“治”,是“分”,“敷治”的意思就是“分治”,也就是“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這種說法恰好與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8)焦循傳,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第374-375頁。的意思相一致,應該是接近孟子本意的。
如果說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解決的是當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的問題;那么舜命“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化解的則是當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的問題,最終取得“中國可得而食”的結果。堯、舜、禹等圣王的此次努力,無疑屬于孔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9)《論語·憲問》,載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59頁。的范疇,理應是孟子“仁政”學說思想的重要根源。盡管孟子對大禹化解此次危機過程的闡釋輕描淡寫,但是治理洪水的歷程卻是極為復雜的,“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一語就是最好的佐證。應該說,這里的禹是以堯、舜之臣的身份出現的,他的政績自然屬于堯、舜之“仁政”的重要范疇,屬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的內涵,同時也歸屬于“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孟子·滕文公上》)。可以說,禹治理洪水的過程,是堯、舜等圣王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精神的一次具體而生動的實踐。
從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看,協助堯、舜治理天下國家的賢能大臣應該還有多位。孟子從與天下百姓生活最密切的角度又列舉了其他兩位賢能的功臣: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孟子·滕文公上》)
在解決“洪水橫流”的危機后,堯、舜又任命后稷“教民稼穡”,重點解決天下百姓的日常生活問題,諸如吃飯、穿衣和居住等。當然,由于人倫教化長期被中斷,社會中逐漸出現了“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后的“近于禽獸”現象。堯、舜又將契選拔出來,授予司徒的官職,其主要職責是負責社會中的人倫教化問題。契則結合社會教化的實際,最終制定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一綱領性的措施,被后世譽為“五倫之教”。
從本質上說,堯、舜之臣契所制作的“五倫之教”與《中庸》的“達道五”“達德三”(10)《中庸》中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三者一也。”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8-29頁。精神是一以貫之的,進而與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社會的天下治理都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里的“達”用鄭玄等人的說法就是“常行”,就是“百王所不變也”(11)鄭玄等注:《十三經古注》,中華書局,2014,第1078頁。。從這樣的角度說,堯、舜之臣契所制定的“五倫之教”,也是“百王所不變”之常行之道。朱熹在解釋此語時說:“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1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59-260頁。如果按照傳統的說法,《中庸》篇是子思子所作,那么孟子的“五倫之教”就應當被視為“達道五”“達德三”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只不過是通過堯、舜時期的大臣契所制定教化的形式傳遞出來。
在闡釋“五倫之教”后,孟子接著引用一句話做總結,說:“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這里的“勞之來之”的意思是“勉之以勤”,“匡之直之”的意思是“正之以義”,“輔之翼之”的意思是“助之以教化,使能自得其本善之性”,(13)沈知方主編,蔣伯潛注釋,上海辭書出版社哲社編輯室整理:《孟子讀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第111頁。這應該是沒有什么異議的。趙岐最早提出此處的“放勛”是“堯號也”,這段引文自然就被認為是堯的訓誡之辭:“放勛,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后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14)焦循:《孟子正義》,第389頁。朱熹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放勛”是“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說:“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60頁。其實,無論此語是堯本人的話,還是堯之史臣贊譽堯之辭,都不會影響它屬于“堯舜之道”的一部分,更不會影響孟子將它作為“仁政”學說源頭的初衷。
從孟子的論述來看,上古時期的圣王堯、舜是治理此次洪水以及次生災害的主導者,他們的賢臣禹、益、皋陶、后稷和契等人則是堯、舜之政的執行者,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姚永概先生對此深有感觸,說:“此段歷舉群圣之功,以明所以不并耕者,一由于無暇,一由于憂民,正駁其厲民自養之說。向使無群圣之憂,則洪水、禽獸之禍何由除?稼穡之教何由布?人倫之教何由明?吾儕欲安于耒耜以修神農之教,亦不可得矣。”(16)姚永概撰,陳春秀校點:《孟子講義》,黃山書社,1999,第89頁。這段話提醒讀者要注意孟子說話的背景,其主要目的是駁斥陳相“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觀點,提出即便是人們心目中的圣王堯、舜在治天下時同樣需要社會分工,需要分為“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 《孟子·滕文公上》)。唯有“各盡其責,天下為公”,才算是“孟子心目中最為理想的社會”(17)張定浩:《孟子讀法》,譯林出版社,2020,第160頁。。由此推論,孟子此處盡管并非“堯舜之道”的專論,也并非單純闡釋“仁政”學說,但人們卻能從中體悟到堯、舜時期獨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治天下”之“道術”以及他們對“仁政”的理解和實踐。
二、孟子“仁政”與“三代之治”
這里所說的“三代之治”,主要是指以禹、湯、文王、武王等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時期的圣王治理下呈現出的一種清明狀態。盡管孟子并沒有親見“三代明王”其人其事,但傳世文獻中有不少相關記載,即孔子說的“有記焉”(18)《孔子家語·禮運》,見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第363頁。。這些記載是孟子論述“三代之治”的文獻基礎,也是解決戰國時期社會問題的重要思想來源。傳世本《孟子》一書中“禹”字出現30次,涉及《公孫丑上》《滕文公上》等7篇;“湯”字出現38次,涉及《梁惠王上》《梁惠王下》等12篇;“文王”出現35次,涉及《梁惠王上》《梁惠王下》等10篇;“武王”出現10次,涉及《梁惠王下》《公孫丑上》等5篇。通過征引、闡釋三代圣王的言語或事跡,孟子汲取了他們治理天下國家的思想智慧,并將其融入他所構筑的“仁政”體系之中。
大禹是夏朝的真正奠基者,也是孟子最尊崇的三代圣王之一。在孟子看來,大禹最優秀的品格首推“好善言”,也就是《孟子·離婁下》篇中說的“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旨酒”的意思是討厭美酒,“好善言”的意思是喜歡聽善的言語。大禹“好善言”多見于先秦時期的傳世文獻,如《尚書·大禹謨》《皋陶謨》等篇中皆有“禹拜昌言”的記載(“昌言”的意思與“善言”相通),《孟子·公孫丑上》篇中也有“禹聞善言則拜”的記載。朱熹在注解此章時說:“《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19)同①書,第239頁。換言之,大禹善于聽取他人意見,并能將自己的過失消滅在萌生之前,從而始終保持為政的正確方向,這對于天下國家的治理來說至關重要。
在孟子看來,大禹最大的功績或者說對天下作出的最杰出貢獻毫無疑問是治理洪水,體現了他治理天下國家的最高水平。一般地說,大禹治水首先是遵從了堯、舜的命令,造福了天下的百姓,最終使夏獲得“天命”。《孟子·滕文公下》篇記載孟子與公都子二人的對話,借機明確闡釋大禹“仁政”的內核:
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大禹治水從亂到治,體現的是孟子“一治一亂”的歷史觀。“洪水為一亂,禹治水后一治;堯舜之后,治亂非一。”(20)姚永概撰,陳春秀校點:《孟子講義》,第106頁。由于“禹之相舜”而“施澤于民久”,自然也奠定了夏朝“天命”的根基。
如果說大禹的夏朝之治是通過禪讓方式取得的話,那么商湯、周武王的政權則是通過革命方式承繼“天命”而來。與堯、舜、大禹的禪讓不同,湯武革命通常會受到后世的非議。比如齊宣王就曾問孟子說:“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說:“于傳有之。”齊宣王接著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此處拋開了君臣固有關系的束縛,以是否遵守仁義為標準判斷為君的資格。正如趙岐注解說:“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其君也。”(21)焦循:《孟子正義》,第145頁。既然是殘賊之人,那么,人人皆可以誅之,何況是“在下者有湯武之仁”(22)同①書,第221頁。者呢?
據《孟子·滕文公下》篇記載,商湯的征伐是從不行“仁政”的鄰居葛國開始的,并獲得了天下百姓發自內心的歡迎,這也是其行“仁政”的一個側面反映。孟子描繪說: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蕓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這段話的背景是孟子極力勸誡齊宣王在齊國實施“仁政”,否則就有可能出現歷史上曾有過的混亂,進而出現類似于商湯這樣的征伐者。孟子認為,商湯討伐葛伯,征伐四方,之所以會受到天下百姓的歡迎,一方面是因為以葛伯、夏桀為代表的為政者殘害百姓,使天下處于悲慘之中;另一方面是因為商湯的仁愛之心及其推行的“仁政”措施俘獲了天下百姓的人心,自然也就為商朝獲得了“天命”。
在孟子看來,商湯和周文王皆是三代明王中典型的仁者,是“能以大事小”( 《孟子·梁惠王下》)的典范,是“以德行仁”而王者,其中商湯“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孫丑上》)。當然,在孟子看來,作為殷商的開創者,商湯為政的最顯著特征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離婁下》)。這里的“執中”應是“允執其中”的簡化,“立賢無方”就是任用官吏以“執中”為標準。焦循在總結此前學者的注解后說:“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之為無常也。”(23)焦循:《孟子正義》,第570頁。應該說,商湯精準地把握到“堯舜之道”的精髓,在選人用人上以賢能為準則,提拔最合適的人任命最合適的事,伊尹就是最有力的明證。
在孟子心目中,姬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和建立者周武王皆是仁民而愛物的典范,是三代圣王中實施“仁政”的樣板。《孟子·梁惠王下》篇記載了孟子心目中周文王在岐山下治理國家時的情形: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這里的“耕者九一”強調的是井田制度,“仕者世祿”強調的是官員的繼承制度,“關市譏而不征”強調的是商業運行制度,“澤梁無禁”強調的是不與民爭利制度,“罪人不孥”強調的是對犯人的懲罰制度,對社會中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的特殊關照,更是孟子心目中“仁政”藍圖的核心內容之一。
孟子認為,周文王治理天下最突出的品格是“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離婁下》)。傳統上,“視民如傷”一語的內涵并沒有太大分歧,也就是像照顧受傷者一樣小心謹慎地對待天下的百姓。“望道而未之見”一語則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趙岐將“見”解釋為“至”,二是朱熹將“而”解釋為“如”,二者都用了“變換法”,皆是為了闡釋“文王謙虛不自滿”的意思。“望是遙相遠望,見是執手相見,望道而未之見,是在明確自己這一生的目標之后,依舊始終清晰地知道自己未曾抵達終點,如此才能激勵人一生求索。如此,也才可以體會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境界。”(24)張定浩:《孟子讀法》,第275-276頁。這既是周文王一以貫之的圣王精神的體現,同時也是孟子構建“仁政”學說極為重要的資源。
如果說周文王“仁政”是周代的真正奠定者,那么周武王則是文王的繼承與發展者。孟子認為,周武王突出的品格是“不泄邇,不忘遠”(《孟子·離婁下》),此語的意思并不難理解,說的是武王對臣民的真誠態度。朱熹解釋說:“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2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正是周武王的德政和仁愛之心使他獲得了天下百姓的真心擁護,成為繼商湯之后的又一位典范和圣王。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孟子·盡心下》)
孟子極力反對不義戰爭,并將“善為戰”者視為天下的“大罪”。在他看來,只要“國君好仁”,天下就自然會出現“無敵”的狀態,自然就不需要戰爭。如果不得已而發生征伐,天下也會出現類似于“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的奇觀,甚至會受到百姓“若崩厥角稽首”般的歡迎。
應該說,大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人之所以分別成為夏、商、周三代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自身德行極高,能自覺成為“堯舜之道”的繼承者、弘揚者和踐行者,尤其是堅持“允執其中”思想,成為“天命”的接受者;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能將“允執其中”思想與具體社會問題相結合,將“仁心仁聞”實施到天下的治理之中,澤被百姓,自然也就能獲得百姓的真心擁護了。孟子從中也得出“仁政”思想的內核,唯有領悟“民為貴”“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思想的精髓者,也就是唯有“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孟子·盡心下》)的圣者,才有可能被天所選定,進而成為像殷湯、周文這樣一個嶄新時代的創立者。
三、孟子“仁政”與“周孔之教”
《中庸》所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戰國時期儒者們的共識。他們在構建學說時,自然會從堯、舜和三代時期圣王處尋求思想智慧的資源。如果說“堯舜之道”是孟子“仁政”學說的“根”,那么“三代之治”就是“脈”,并決定其“仁政”學說扎根于中華文明沃土的圣王智慧。由于這些圣王時代上相對久遠,孟子只能算是“聞而知之”者,所以在尋求“仁政”學說資源時,會更多地將重心放在孔子及其生活的那個時代。由于孔子將周公視為人生的楷模,并以夢見周公作為人生目標,而以“乃所愿,則學孔子”( 《孟子·公孫丑上》)的孟子,在構筑“仁政”學說時,自然也會汲取周公及其精神品格。從這樣的角度說,孟子“仁政”學說與“周公、仲尼之道”是一脈相承的,可以視為以“周孔之教”化解戰國時期社會危機的一種政治思想智慧。
盡管孟子曾游說齊宣王、梁惠王等多位諸侯國君,但是唯有“滕文公是孟子的知己”,“只有滕文公聽了孟子的話,只有滕文公把孟子的話當成一回事,而且落實到自己的生活當中,落實到自己的治國理念當中”。(26)陳來、王志民主編《〈孟子〉七篇解讀》,齊魯書社,2018,第252頁。正是因為滕文公按照孟子“仁政”學說治理滕國,才吸引了當時其他國家的百姓(如許行、陳相兄弟等)自愿做滕文公的臣民。《孟子·滕文公上》篇記載說: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為圣人氓。”
許行的“聞君行仁政”和陳相兄弟的“聞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等語,是對滕文公行“仁政”的一種高度贊許。這里的“圣人”究竟何指呢?趙岐和朱熹并沒有明說。焦循在注解此語時給出了較為明確的答案:“《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儒之效,首推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為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27)焦循:《孟子正義》,第367頁。可知,孟子此處所說的“圣人”和“圣人之政”,應當首推周公及其天下國家治理的實踐,兼及孔子及其為政思想。
“周公”二字在《孟子》中先后出現了18次,涉及《滕文公上》《滕文公下》等7篇。盡管文字并不算特別多,但內容卻極為豐富而重要,不僅闡釋了周公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并首次提出了“周公、仲尼之道”的概念。在孟子看來,周公最重要的貢獻應是接續周文王之道,協助周武王完成政權的建立以及輔佐周成王完成政權的鞏固。正如《公孫丑上》所說:“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后大行。”又如《滕文公下》言:“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很顯然,周公是“堯舜之道”的傳承者,是“文武之治”的守護者,尤其是使社會從亂重新回到治,自然也就成為早期儒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理想的重要實踐者。
當然,周公不僅是“文武之治”的守護者,而且也是大禹、商湯等圣王之治的繼承者與發展者。孟子曾說: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離婁下》)
盡管這里分別闡釋的是大禹、商湯、周文王以及周武王施政時的主要精神品格,但毫無疑問的是,此處突出強調了周公與此前圣王“仁政”的關系。正如朱熹評價說:“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于行也。”此外,朱熹還借用程子的話,對周公所施“四事”做了更深層次的闡釋:“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圣人亦無不盛。”(2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從這樣的角度說,周公是上古、夏、商以及先周時期圣王之“仁政”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成為孔子“仁學”以及孟子“仁政”學說的最直接的源頭。
周公之所以與孔子、孟子等早期儒家的思想密切相關,是因為周公、孔子、孟子與此前的圣王都不同,其顯著特征是皆“不有天下”(《孟子·萬章上》),皆是“堯舜之道”“三王之治”的繼承者和踐行者。正如韓愈在《原道》篇中所說的,“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29)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8頁。,所以周公就成為中華圣道的承上啟下者,也就是上承“先王之道”,下啟“孔孟之道”,其制禮作樂是對中華文明最杰出的貢獻。通過制禮作樂,將“先王之道”注入他所創立的制度和具體為政實踐中,進而奠定周代禮樂教化的范式,“詩教”則處于核心位置。《孟子·離婁下》篇中首次提出“《詩》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題。此語的大意是說,在周初確立的遒人采詩制度消亡之后,孔子所作的《春秋》填補了這一教化空檔期,甚至使亂臣賊子都感到了恐懼。
按照孟子的理解,“《詩》亡”的前提是“王者之跡熄”,通常是指西周以來確立的“圣王教化”影響的衰退或者消亡。正如趙岐解釋說:“王者,謂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跡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于衰世也。”(30)焦循:《孟子正義》,第572頁。朱熹的注解與趙岐略有差別。他說:“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由此可見,傳統注釋主要是從王官之跡的消失闡釋“《詩》亡”的。那么,進一步從人們常說的“禮壞樂崩”,即以詩教為代表的、周公確立的禮樂制度的全面崩塌的角度,或許更有利于理解孔子所作《春秋》的教化意義。
傳統經典教化體系的崩塌導致社會固有秩序的混亂,甚至引起社會的動蕩。按照傳統社會的“天命轉移”理論,這時應該會有像禹、湯、文、武等這樣的圣王橫空出世。不幸的是,孔子似乎看不到救世圣王的出現,甚至預示圣王出世的麒麟也在被捕獲后死亡。或許出于這樣的考慮,《春秋》的下限在麒麟被捕之年(魯哀公十四年)。據《孟子·離婁下》篇記載,孔子作《春秋》引述的主要事情發生在“齊桓、晉文”,依據的核心文字是魯國的“史記舊聞”,而選編的內在標準是“義”。朱熹將此處的“義”解釋為“定天下之邪正”和“為百王之大法”(3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5頁。。從這樣的角度說,“《詩》亡”后的《春秋》本應由天子來作,孔子卻以布衣之身代行天子之事,自然會有僭越的嫌疑,所以他才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所作的《春秋》這部經典僅有1 800余字,它有著怎樣的魔力,能使孟子將它視為“亂臣賊子懼”的大本大法,能使后世的學者將它視為“王道備,人事浹”(32)《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第504頁。的“禮義之大宗”(33)《史記·太史公自序》,第3298頁。?問題的答案或許應該與《春秋》自身蘊含的微言大義有關。這個“大義”可以被理解為是周公之禮的微言大義,是“誅討亂賊以戒后世”的微言大義,是“明辨是非”“撥亂反正”的微言大義(34)魏衍華:《〈春秋〉“禮義之大宗”解》,《孔子研究》2021年第2期。。由于亂臣賊子害怕當時或者后世的史官以《春秋》為標準對他們進行“貶責”,自然會有所顧忌,自然也就起到一定的“禁未然之前”的功效。所以,與戰爭、征伐等熱暴力相比,《春秋》的冷提醒或許更有利于護佑天下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無疑也是孟子“仁政”學說極為重要的內涵。
孟子極具觀察力,他認為引發戰國時期社會陷入混亂的根源是“圣王之道衰”。此時期的社會混亂,一方面,“諸侯放恣”,各國諸侯國君為滿足自己的私欲而草率地發動戰爭,致使“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另一方面,“處士橫議”,社會出現“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的思想混亂局面。在孟子看來,“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楊朱、墨翟的思想對“圣王之道”和“周孔之教”是極具殺傷力的,甚至會引發社會輿論朝著不可控的態勢演變,而該態勢則是孟子欲推行“仁政”學說所不得不逾越的一道鴻溝。因此,孟子“無比堅定地把批判楊朱、墨翟之學作為他一生的事業,并將這種批判視為繼大禹治水、周公治亂和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國歷史上的第四件大事”,目的就是要引導“社會重新回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狀態”。(35)魏衍華:《孟子“以承三圣”的歷史、思想、哲學世界》,《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應該說,盡管“堯舜之道”“三代之治”以及“周孔之教”之間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差別,但其內核是一以貫之的,皆是“允執其中”思想精髓的承載與創新,皆是為了營造一個政治清明、河清海晏的生活環境,進而為人數眾多的普通百姓創造幸福安定的生活,以實現孔子追求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這也正是孟子“仁政”學說追求的最核心目標。當然,為保障普通百姓的最基本生活,孟子特別強調使百姓能夠維持基本的“養生喪死無憾”“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的生活狀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孟子設計的“仁政”藍圖并非只是紙上描述,也并非通常說的“載之空言”,而是以一套相對完整的制度為支撐的。對此,張定浩先生認為,孟子給出的策略可以歸納為以“施仁政于民”為中心,并輔以四個方面即法治上的“省刑罰”、財政上的“薄賦稅”、經濟上的“深耕易耨”以及教育上的“暇日”修其“孝悌忠信”。(36)張定浩:《孟子讀法》,第19頁。應該說,這種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我們在研究孟子“仁政”及其國家治理思想學說時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