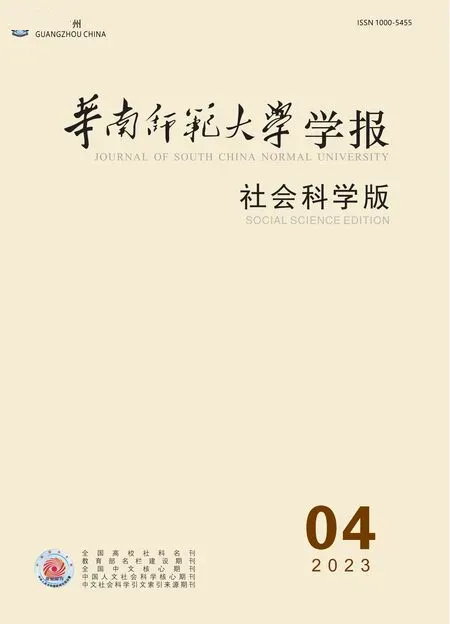杞柳與駢拇
——人性的真與善
趙金剛
(清華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084)
《孟子·告子上》諸章記述了孟子與告子的諸多辯論,透過這些“辯性善”的章節,可以深入理解孟子人性論的基本立場和傾向。(1)牟宗三在《圓善論》第一章《基本的義理》中就專門順著這些章節的疏解,展開了他對孟子人性論的理解,討論孟子人性論的研究者應該關注這些章節的義理空間。參見牟宗三:《圓善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0。第一章《性猶杞柳也章》是這些論辯的發端。然而,古今孟學詮釋者對此章的關注卻不如其他幾章——“湍水之喻”由于與宋明理學人性論說的復雜關聯而被學者關注,《生之謂性章》有理學與辯論邏輯的雙重加持,之后兩章涉及“仁內義外”等哲學論證,第六章涉及對當時人性論的總結、孟子思想中的“情”“才”問題、“四心”問題,因之思想打開的空間均比較豐富。敞開第一章思想言說空間的,當屬唐文治先生。《孟子大義》特有一“愚按”表達他對此章的總體理解:
杞柳不能自然為桮棬也,必戕賊而后成之。桮棬成而杞柳之本性失矣。以此而喻性,則人將曰:“吾欲適吾自然之性,寧拳曲臃腫而不中于繩墨也。”此即莊子以仁義易其性之說也。(見《駢拇》篇。)如是則人皆畏仁義,故孟子斥之曰“禍仁義”。(2)唐文治:《孟子大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356頁。
這里比較關鍵的有兩點:一是“自然之性”與“繩墨”的關系,這是古今注家都會注意到的問題;二是將這一章討論的人性問題與莊子(特別是《莊子·駢拇》)聯系起來,將此章“禍仁義”的思想意涵打開,這是以往孟子人性論研究較少關注的。惜乎唐文治先生之論僅止于此,更進一步的比較有待今人申說。之后的學者,較為明確地提出此章與道家人性論關系的,則為徐復觀先生。(3)當然,這還涉及告子思想流派的歸屬問題,趙岐以為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于孟子”(焦循:《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第731頁)。古今學者相關考證,可參黃俊杰:《孟學思想史論》,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第212、214頁。當代學者中李景林先生承繼錢穆先生,以為告子屬于道家(李景林:《孟子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第50頁),楊海文先生以為告子屬于“以道為主,兼采儒墨者”(楊海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世界》,齊魯書社,2017,第102頁)。本文以為告子屬于儒家學派的孟子前輩學者,如若不然,此章“禍仁義”的論證力度便會弱了很多。然而徐先生的論說也集中在對《孟子》此章的文義闡發上,哲理空間還有待展開。
孟子與莊子同時,然而《孟子》文本中沒有提到莊子,《莊子》中似乎也沒有孟子的身影,這不得不說是思想史的一個遺憾。《駢拇》雖屬“外雜篇”,但也可以反映“莊學”或道家某一流派的思想氣質。透過杞柳與駢拇的對照,或可在孟告之辯外再打開一個辯論的空間。
一、杞柳與桮棬:人性與“制作”
徐復觀先生以為,“告子的人性論,是以‘生之謂性’為出發點”(4)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第114頁。。本章開始,告子以比喻的形式,說明了他對人性與仁義關系的理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告子上》)
趙岐以為,“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干,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桮棬也”(5)焦循:《孟子正義》,第732頁。。“才干”即焦循所謂“枝干”(6)同上。,為待成就的“材料”;“成器”即完成品,是材料經由制作而成就的。人性與仁義為二,二者并非“內在性關系”,而需要外在的“為”,“必待矯揉而后成”(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第325頁。。“制作”對于仁義的長成,是主導性的因素,而非輔助性的。牟宗三先生指出:
告子以杞柳喻性,是把性看作材料,是中性義的性,并無所謂善惡,其或善或惡是后天造成的,因而其中亦無所謂仁義,仁義亦是后天造成的,因而仁義是外于人性的。(8)牟宗三:《圓善論》,第3頁。
告子認為人性是無規定性、無內容的“材料”,不認為仁義為人性所“固有”,不認為“仁義”可以以某種形式作為人性的“內容”。但這里依舊需要討論告子能否接受仁義作為人性的“潛能”。徐復觀先生認為:
由他這一譬喻,可以導向兩種結論。一個是杞柳的本性無桮棬,以杞柳為桮棬,乃傷杞柳之性,因之以人性為仁義,也是傷了人之性,這是道家的結論。另一種結論是杞柳不是桮棬,而可以為桮棬,人性無仁義,也可以為仁義,以見主張性無分于善惡,并無傷于仁義之教。就告子的基本立場說,似以前一結論為合于他的原意。但就此段話的問答的情形說,則又似以后一結論為合于他的原意。孟子則是以后一結論作基點而加以詰責的。人性既無仁義,則各人自己亦無為仁義之意欲,則為仁義不能順各人自然的要求,而只有靠外在的強制力量。順人性之善以為仁義,這是順人的自由意志以為仁義,這是人的自由的發揮。靠外在強制之力以為仁義,則只有以人類的自由意志作犧牲。(9)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120頁。
按照第一種結論,告子的人性不包含仁義作為潛能;按照第二種結論,則無所謂有何種可能,或者說是有一種開放性的可能。可以說,告子言說的重點在于外在的“強制力量”,即制作,即“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為桮棬,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為仁義”(10)焦循:《孟子正義》,第732頁。。告子所講的人性自然性,排除了傾向性(性能),排除了性本身的一切動態可能,是純然靜態的,相當于“樸”(11)李景林先生以為告子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人性“白板論”,參見《孟子通釋》,第211頁。。告子的性完全是被動的,不含有任何主動的“動能”。其從人性到仁義的過程,是制作的邏輯,而非生生的邏輯:制作以一外在于質料的形式來“規范”“材料”,生生則是形質合一的事物自身的變化發展。(12)參見吳飛:《論“生生”——兼與丁耘先生商榷》,《哲學研究》2018年第1期;丁耘:《〈易傳〉與“生生”——回應吳飛先生》,《哲學研究》2018年第1期。
孟子思想中,人性與仁義是內在性關系,從四端到仁義是生生的邏輯,強調主體內在的道德動能,“仁義即人性之實,從人性而發的仁義是人性本然的表現。從人性而仁義呈順成之勢”(13)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第324頁。。故孟子自然不能接受告子的觀點: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后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孟子并未明確言說自己的觀點,而是指出了外在力量作用在材料上的兩種模式:第一種是順性而為,保持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第二種是戕賊破壞本性,改變事物原有的存在方式。(14)傳統技術多為第一種模式,而現代科學則傾向于第二種模式。第一種就必須承認仁義要么為人性之內容,要么為人性之潛能,這顯然不是告子的立論基礎。告子本人似只主張一“中性”的制作,但從制作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關系來看,這種“中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不承認第一種模式,就必然要承認第二種模式,即此種制作徹底改變了“材料”;在制作完成后,桮棬就不再是杞柳,人們直接觀察完成品,甚或無法知曉其來歷。對于普通材料而言,這種制作站在有主體的制作者來說,可能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有用性”;而站在人性這種材料來講,則是對人的本真狀態(原初狀態)的破壞。這其實就涉及了真與善的關系問題。真或本真意味著“因其自身之故而存在”,“不再為他者(他人與它物)所規定,而是僅僅自我規定著”。(15)陳勇:《生存、知識與本真性——論亞里士多德與海德格爾的實踐哲學》,《哲學研究》2017年第4期。在中國哲學的語言中,此種真往往與自然有關;善則是道德、倫理的價值,包含著個體乃至共同體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樣地,在中國哲學的語言中,此種善往往與仁義有關。這就牽涉到真善是否合一的問題,以及如果真善不合一,那么在價值序列上,真與善誰更重要等一系列問題。
在孟子與告子的第一個論辯中,人性屬真是雙方都接受的。在告子的思想中,顯然真與善是分離的,“杞柳是質料,而桮棬是由此質料制成的器具。告子這一比喻的要點在于指出,義不是人的自然,而是以人的自然為質料‘加工’而成的”(16)楊立華:《穿越告子的叢林》,《讀書》2005年第12期。,善非真是告子立論的前提。并且,從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善要重于真——成器比材料更為有用。這就可能導致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在價值上重視真,將真視為優先的、值得呵護的,他會如何看待第二種制作模式下“對真的破壞才能成就善”這一問題?他是否會接受此種制作?他是否還愿意為善?在強調真的絕對優先性的人看來,這種制作所達到的善是一種“偽”。為了保持真,那就不能接受虛偽的外在善。“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究竟指怎樣的行為,歷代注家似討論得并不顯白。朱子以為,“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25頁。。顯然朱子所講的“不肯為”只有站在對真的優先性強調的基礎上才可能發生。徐復觀先生指出了兩種情況:“一是為了保持自由而不談仁義,這是許多道家的態度,也是西方文化20世紀的主要趨向。另一則是犧牲自由而戕賊人以為仁義。”(18)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120頁。第一種依舊是強調真勝過強調善;第二種是對強制之力的過分推崇,甚至有可能將強制力本身異化為目的,把仁義當成是強制力的手段。從孟子使用“戕賊”一詞來看,“戕賊”不包含對強制力的推崇之義。孟子認為的可能因制作傷害本性而不為仁義的行為,主要還是指向第一種(19)陳冀博士指出,“以人學以成仁義視為對人性的戕賊,這一理解很可能是孟子出于對楊朱學派的焦慮以至對告子進行了過度的道家化解讀,將其塑造成了類似于莊子的形象,這一形象為后世大部分重要詮釋者所接受”。見陳冀:《從孟告之辯看告子思想》,《孔子研究》2018年第2期。,也就是徐復觀先生所指出的道家的態度;而在文本上與之呼應的,則是唐文治先生指出的《駢拇》篇。
二、駢拇與仁義:以真黜善
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中以為“道家不承認仁義是人的本性”(20)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5,第314頁。,特舉《駢拇》篇為例進行說明,道家認為“仁義并非常然之性,奔命于仁義,亦是以物易性;認仁義為性的思想,乃是亂人之性。仁義是在性外的”(21)同上書,第315頁。。此正是《孟子》擔心的“禍仁義”者的言論。
關于《駢拇》篇,陳鼓應先生指出,“道家人性論議題始于《莊子》外篇。《駢拇》列外篇之首,有學者指出這是一篇道家的人性論。從《駢拇》《馬蹄》到《在宥》,常被學界視為內容相連的一組文章,其主題在于闡揚任情率性與安情適性”(22)陳鼓應:《莊子人性論》,中華書局,2017,第76頁。引文中“有學者指出……”,指曹礎基的《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22,第119頁。。陳引馳并以為,“《駢拇》一篇,述《莊子》之自然人性論,主旨以為儒家所提倡的仁義之類非人性之固然,因而是必須加以反對的,正當的途徑不過是尊重人性的本然,自適自得而任性命之情”(23)陳引馳:《莊子講義》,中華書局,2021,第283頁。。這些均可看出《駢拇》篇在儒道對話上的意義。
《駢拇》篇的立論出發點即“仁義是對人之存在的‘侈’——即多余之物”(24)趙帥鋒、郭美華:《仁義對道德的阻礙與中斷——論〈莊子·駢拇〉對仁義的批判》,載《諸子學刊》第1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83頁。,也就是認為仁義這種一般被認為是善的價值,相對于存在之真、存在之自然而言,是外在的,“仁義作為造作之物,是對于道—德之間自然暢然關聯的阻礙和中斷”(25)同上。。此即宣穎解釋《駢拇》時所說:“圣門言仁義即是性,莊子卻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26)宣穎:《南華經解》卷八,載《中華續道藏》初輯(影印本),新文豐出版社,1999。當然,這里的“圣門”當是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者,告子在此一辯論中何嘗不將仁義當成“添出之物”呢?只是《莊子》所強調的“添出”的負面意義是告子不愿意接受的罷了,畢竟告子還要承認仁義的正面意義。
《駢拇》開篇就講: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27)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第231頁。
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是“天生”的,但相對于“德”“性”則是多余的,對人來講是“無用”的。仁義與之類似,仁義并非“道德之正”。按照徐復觀先生理解,“這里所說的‘道德’,即是德,即是性”(28)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228頁。鄭開教授也以為:《老子》中盡管沒有“性”字,但其常說的“德”與“命”“樸”與“素”“赤子”與“嬰兒”,皆相當于后來的哲學概念“性”;同樣,《莊子》里的“德”“真”“性命之情”等概念,也相當于“性”。鄭開:《道家形而上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第325-326頁。,也即仁義不是“人性之正”,不是按照人性之“自然”所當擁有的,“凡是后天滋多蕃衍出來的東西都不是性,或者是性發展的障礙”(29)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228頁。。相較于駢拇等的多余而無用,仁義的多余則是有害的,是更要避免的。“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30)同⑤書,第232頁。曾史即曾參和史鰌,是主張仁義的儒家代表。在《駢拇》的作者看來,“曾參、史鰌作為五臟稟性侈于其性者,以一己肝之仁為普遍之德,標榜拔擢以為至道,阻塞人性以求聲譽,讓他人汲汲于競逐他們天性所不及之物,荼毒他人生命、扭曲天下之大道”(31)同②書,第83-84頁。。對照《孟子》的語境,曾參和史鰌就是“戕賊人以為仁義”,《駢拇》即是以仁義為禍。在《駢拇》的語境中,“道德之正”即“性命之真”,也即人性之自然;仁義則是以制作破壞真的行為,“是對自然真實之情的虛偽化”(32)同②書,第84頁。。
多余之“德性”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種類似駢拇、枝指,雖是多余,但還是天生,可以納入自然,只要不以其為不善,在自己的性分中適性而行,那就不會有害。(33)參見趙帥鋒、郭美華:《仁義對道德的阻礙與中斷——論〈莊子·駢拇〉對仁義的批判》的相關詮釋,載《諸子學刊》第19輯,第81-94頁。孟子講:“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34)《孟子·告子上》,載《四書章句集注》,第334頁。以下所引《孟子》,皆同此出處,只注篇名。在孟子的邏輯中,人有“同類意識”,如果指不若人,就會有求若人之心,這是孟子對人情的理解。而如果回到《駢拇》的邏輯當中,“無名之指屈而不信”是“自然之真”;而要求伸,則是害真。第二種多余則類似仁義,完全是后天的制作,不但多余,反而有害。張岱年先生以為,“自然與人為的關系本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人為是對于自然的改變;另一方面,人為對于自然的改變也是自然而然的”(35)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中華書局,2017,第95頁。。在《駢拇》的邏輯中,仁義顯然不屬于自然而然地對自然的改變,而是含有某種“刻意”的“造作”在其中。“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36)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第235頁。這里的“續”“斷”都是以外在的善為標準,對自然進行破壞;回到人這里,則是以外在的仁義之善破壞人性之真。成玄英在解釋《駢拇》時特別強調,“自然之理,亭毒眾形,雖復修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遙。而惑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37)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中華書局,1998,第184頁。。對照《孟子》,可以說“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即變杞柳為桮棬的過程——杞柳不需要成為成器就有自己的價值;而這樣的造作過程,是違背萬物本真的行為。林希逸也講:“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嘆而言之。使仁義出于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38)林希逸:《莊子虞齊口義校注》,中華書局,1997,第140頁。《駢拇》始終將仁義置于自然之外,將仁義看成是“失真”;而在價值序列上,始終將自然之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39)同上書,第141頁。,認為“儒家吹噓仁義來撫慰天下人的心,這也破壞了人的本然之性。所以要保持人的自然本性就應該彎者自彎、直者自直,自圓而不用規,自方而不用矩”(40)張岱年:《中華的智慧》,中華書局,2017,第102頁。。“自然”本身就包含著最高價值——最高的“善好”,不需要破壞了這種“善好”再去追求外在的善。“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41)同⑤書,第186頁。成玄英此疏中的本末之說,更是點出了真在價值序列中的位置。當然,這里的本末也不是生生的自然展開邏輯,而是一種價值上的對舉。
《駢拇》篇的內容意旨雖不見得與《莊子》“內篇”相同,但卻有能反映莊子乃至先秦道家思想的一般傾向之處,即對自然之真的高揚,對制作出的超越人性之真的善的貶黜。與《駢拇》呼應較為緊密的是《馬蹄》篇。“《馬蹄》《駢拇》皆從性命上發論。《駢拇》是盡己之性,而切指仁義之為害于身心;《馬蹄》是盡物之性,而切指仁義之為害于天下。”(42)劉鳳苞:《南華雪心編》,中華書局,2013,第220頁。《馬蹄》篇講:“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43)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第244頁。這里“燒之”等一系列動詞,即“矯揉”“為”的過程,就是對“材料”的制作,而這一切都是破壞性的,即“戕賊”。《馬蹄》以為“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44)同上書,第247頁。。此道德即“道德之正”,也就是自然之真。不獨《馬蹄》有此觀點。早在《老子》那里就已經強調萬物只要能保持自己的“樸”,不受外力干擾,就能實現自身的完滿,達到彼此的和諧。《莊子·大宗師》意而子和許由的對話,也認為儒家的仁義是對人的“黥”“劓”,所謂“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45)同②書,第207頁。。而這些,可以說是潛在于孟告杞柳之辯背后一個不容忽視的思想史背景。否則,就無法理解孟子為何會“敏感”地講出“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這樣的結論。
可見,告子并沒有意識到,一旦把真和善分離,把自然與仁義看成是完全外在性的關系可能導致的哲學質疑。特別是,如果像道家一樣強調真的圓滿、自足,就不會有仁義的位置,而這也是孟告這一辯論中,告子最為致命的思想問題。孟子顯然對此保持了高度的思想敏感。而孟子之所以能保持這樣的思想領會,則與其對“人性善”的理解密切相關。即,孟子在講善的時候,并非只看到了道德、價值的意涵與意義,而是“收真于善”。孟子講的善是真善合一的,必須要看到其言說中真的面向,才能對孟子人性論有更深入的理解。
三、孟子人性論:真善合一
學者們已經指出,“十三經無‘真’字”,真字始見于《老子》《莊子》諸書,但這卻不意味著真字要表達的思想意涵在儒家思想中有所缺失,儒家思想中會以貞、正等字代替真。(46)參見楊少涵:《十三經無“真”字——儒道分野的一個字源學證據》,《哲學動態》2021年第8期。更為重要的是,真字所表達的本真、源發、本始等意涵,在儒家則以其他概念指代、收攝。這些概念對真的收攝,反而體現出儒家思想的特色。
真的思想所指被儒學收攝進自身的概念之中,這一現象在誠這里體現得最為充分。《大學》講“誠意”,直接對峙“自欺”等虛假的意識活動,而《中庸》的誠更是被視為形而上學的“誠體”。(47)同上。《中庸》之誠是“真實”與“善性”的合一,其真的面向重點體現在“為物不二,生物不測”(《中庸》第二十六章)。朱子以為“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4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1頁。。如是,人的“誠之”就可以視作對自己本真的復歸,成善的過程本身就是成真的過程。這就不存在《駢拇》所批評的破壞本真而成善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仁義對人的戕賊了。
隨著對出土文獻的釋讀,孟子承繼子思這一觀點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相較而言,誠在孟子思想中雖然沒有在《中庸》中那么突出,但其真善合一的特性卻在孟子言說“人性善”時繼承了下來。
首先,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其特重“本心”。此“本心”即人原本自足、自身規定自己的心,四端是“本心的乘機而作”。后天損害、玷污、放逐的心,即被外在環境影響作用的心,是“非本心”。這一“本心”可以說即是“真心”,只是相對于道家純粹無內容的、虛的真心,孟子的本心具有先驗的道德意識。但在其排除后天經驗性這點來說,依舊可以強調其本真性。孟子講“可欲之謂善”(《孟子·告子下》),可欲的就是以仁義禮智為內容的人性(49)《孟子通釋》,第311頁。,而此種可欲是發自本心的自我追求、自我實現的欲望,人對仁義的追求本身就是內在仁義,而非外在力量強制作用的結果。李景林先生指出,“‘可求’‘可欲’,構成了人性之先天內容”,這與孔子講的“求仁得仁”“欲仁仁至”有一致之處。(50)同上書,第312頁。
其次,孟子成就仁義的路徑是“擴充”“求放心”,而不是“制作”。這也是對自然自然而然的改變,順著人性的自然而成就自然。孟子講要對四端之心“知皆擴而充之”(《孟子·公孫丑上》),知就是對自身性善的肯認。在此基礎上,將善端擴大,此“擴充”是本真的自我實現,而非外力的強制作用。孟子的比喻類講法,多能說明這一點,如他講“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孟子·公孫丑上》),這里的“燃”和“達”都是內在力量的自我成就,而非外力的加入。因此孟子反對拔苗助長,認為此種外在的強制不是正確的工夫。而“求放心”(《孟子·告子上》)這樣的講法,更是蘊含了本真、本善的自我復歸的意涵。成仁義是人“以自身為對象”(51)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281頁。,是人的內在轉化,是自我轉化,而非外在形式對自己的強制的制作。
可以看到,后世基于孟子展開論說的儒家思想流派在論述善的問題時,往往會強調善有真的面向。如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就特別強調“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52)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二六《寄正憲男手墨二卷》,中華書局,2015,第1141頁。,這里的“誠愛惻怛”即是真與善合一的道德狀態。陽明更是講“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53)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 傳習錄》,中華書局,2015,第104頁。,良知是“扎根于仁體之中、帶著鮮活的生命同體的體驗的一種覺知”(54)陳立勝:《知情意:王陽明良知論的三個面向》,《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這種對道德本體真善合一的講法,是對孟子思想的自然發揮。
當論者強調孟子的道德觀是自律的形態時,就要意識到,如果真沒有被收攝進善當中,自律是不可能成立的。根據孟子對人性的理解,仁義本身就是人性的內容;而這樣以善為內容的性,本身已經攝真于善,其思想展開自然不存在告子那里的“制作”義,不包含工夫對本真的破壞。相反,成善本身就是成真。因此,在孟子這里也就不存在為成就仁義而對人性有所戕賊的問題了。當然,道家或可質疑孟子攝真于善的真還是一種不真;然而,孟子自有對性善的論證。站在孟子的角度也可透過“人禽之辯”去質疑道家所講的真不是人的本真。這就涉及各自立場的根底問題了。
在《性猶杞柳也章》孟子與告子的論辯中,孟子已經注意到將真、善分離可能導致的對善的質疑,此種言說模式終將導致“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孟子當時的論辯對象既是告子,更是高揚真的道家。而孟子的思想對手,在今天則更為常見。徐復觀先生以為,“為了保持自由而不談仁義,這是許多道家的態度,也是西方文化20世紀的主要趨向”(55)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120頁。。把此處的“自由”理解為真毋寧更為恰當,今天多見“活出真我”的口號、多見以天性的名義對教化的質疑,即是明證。
真、善的分離,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實然與應然的分離。如是,人類的一切道德就可能失去“自然之基”,而都成為后天的建構,成為某種形式的契約。這樣,道德的相對特性就會愈發明顯,甚至可能撕裂道德本身并使其碎片化,將一切相對化、虛無化。此外,如果將真、善徹底割裂開來,那么不同的對真的理解空間也將無限打開,會面臨各種以真為旗號的對善的質疑。當善被理解為外在強制的“規訓”,而非人的自我實現,還有可能理直氣壯地要求善嗎?當然,在現代語境下,面對著真對善的質疑,對善的強調者自身也要反省,對善的理解是否失去了真的維度,而僅僅是某種主張?對善的實行是不是成了強制?對善的主張有異化為“偽善”的可能,完全可能出現“人人都在‘行善’,而‘惡’卻周流于天下的悖論”(56)格非:《雪隱鷺鷥》,譯林出版社,2014,第114頁。。
此外,對真的高揚者也需反思,高揚的真究竟是什么樣的真?真是不是只能是“現實欲望的率性真機”(57)同上書,第125頁。?在主張“真欲望”時,是否需要思考“真欲望”對“主體”一定好?純粹的任情能否構成“善好”(此“善好”可以剝離儒家或任何道德主義的立場,而僅從自我保存的角度理解)?當真被主張到極致時,會不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妄”?“我”以為的真會不會也是被某種觀點(比如“消費主義”)建構起來的,而“我”完全“無思”?
孟子以諸多形式對善進行論證,很難完全歸于社會物質力量構成某種社會文化心理的過程,孟子的論證有其普遍性訴求,而此種普遍性是包含了真與善兩重維度的。當孟子用“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去論證人性善時,他著力要排除的就有因為要譽等私欲導致的“偽善”,而格外強調“本心”自身的力量帶來的善與真的合一。這種對于人性理解的方向,或許應成為今天重新思考善的重要維度。這,或許也是我們今天再去看待孟子人性論辯需要打開的思想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