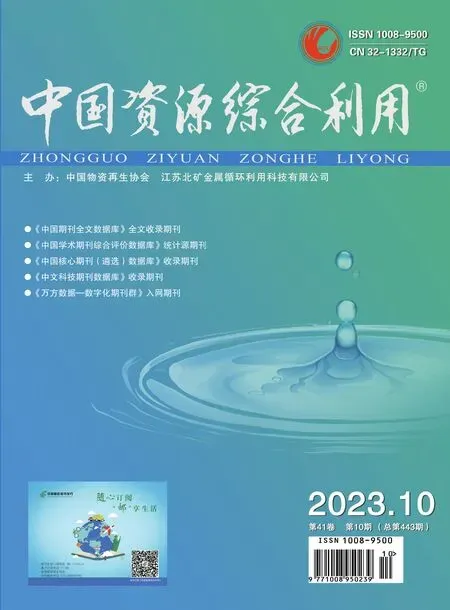協同治理視角下新加坡海岸帶保護與利用研究
王 璇,丁 葉,陳志祿
(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廣州 510000)
新加坡沿海區域集聚密集的經濟活動,包括航運、石油開采、工業、娛樂在內的各種功能利用主體相互競爭,利用相對有限的海岸空間。受土地資源的限制,填海造地成為新加坡長期以來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新加坡的海岸線20世紀初以來不斷外擴。然而,盡管海岸生境和持續的海岸線大量消失,但如今在新加坡仍然可以找到大量的生物有機體:35 處紅樹林、12 處海草、255 種珊瑚及多種其他海洋生物。這得益于新加坡有效的城市海岸綜合治理機制。它加強了各方的協調,使得海岸利益相關者在優化利用沿海資源過程中以可持續的方式保護敏感的海岸生境,積極保育沿海的生物多樣性。新加坡這一治理模式的成功得到國際上的認可,被公認為在平衡沿海開發、海洋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樹立標桿。我國在海岸治理方面起步相對較晚。沿海大城市大多缺乏有效的海岸帶綜合治理框架。分析新加坡海岸的綜合治理經驗,對我國海岸帶的綜合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1 新加坡海岸帶保護與利用情況
1.1 空間受限,持續向海要空間
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人地矛盾非常突出。向海洋要空間成為新加坡唯一的發展出路。1960—2015年,新加坡填海造地面積高達140 km2,約占國土面積的20%[1]。目前,新加坡仍在持續填海,以求得進一步的發展空間,填海后的岸線占新加坡總岸線長度的比重過半[2]。在1960—1980年工業主導的開發利用階段,新加坡大規模地填海造地,企圖向海洋索取發展空間,海岸帶利用方式以工業開發為主導,如大士工業用地等;在1980—2010年的岸線空間多元利用階段,雖然新加坡的填海造地規模爆發性增長,但填海技術不斷優化,以減少對海岸帶的環境影響。2010年后,在經濟持續轉型、環境保護理念不斷受到重視的背景下,新加坡填海規模稍有下降。
1.2 功能協調,形成“西港東城”格局
海岸線可按照功能分類,分為生活岸線(居住等)、生產岸線(港口等)、生態岸線(山體等)、未利用岸線四大類型。從空間結構上看,東側岸線以生活岸線、未利用岸線為主,承擔生活服務、旅游休閑功能;西側岸線以生產岸線為主,承擔更多的港口運輸、工業開發功能。綜合考慮城市規模與港口規模,港城關系可分為大港小城、世界級港口大都市、沿海小港口、沿海大都市等類型[3],由于港口以貨物等集聚為主,城市以人的集聚為主,新加坡“西港東城”的港城分離格局在功能布局上更為協調有序。
1.3 集約高效,高強度開發布局功能
對于土地如何開發這一問題,新加坡政府與民眾已達成基本共識,認為城市應該優先考慮通過更新和集約化的方式發展,而不應該擴展到目前保留的綠地、生態區域[4]。在這樣的話語體系下,新加坡海岸線的功能利用體現出集約高效的特征。以新加坡港為例,其全球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全球領先,在土地利用、作業效率評價等方面是國內城市的標桿。據統計,新加坡港土地集約利用程度高,單位長度岸線的年集裝箱吞吐量高達2 300 TEU/m,是廈門港的近4 倍。
1.4 生態強韌,物種多樣性恢復快
在長期填海大開發的過程中,新加坡幾乎所有的自然海岸線被人工設施、海堤建設所取代,原有的沿海生境和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的破壞。20世紀90年代,管理部門加大對沿海和海洋生境的保護。典型做法包括重新進行人工紅樹林的種植,補償因開發第一個離岸衛生填埋場而損失的紅樹林。在此之后,所有的海洋開發項目都采取相應措施,以盡量減少生物多樣性破壞。2006年,新加坡國家公園局成立國家生物多樣性中心,重點保護陸地和海洋的生物多樣性[5]。在一系列措施作用下,新加坡紅樹林達35 處,生物多樣性快速恢復。
2 新加坡海岸帶的協同治理
協同治理是一種將公共和私人利益相關者聚集在一起的,以共識為導向的決策模式。它是指一個或多個公共機構直接讓非政府利益相關者參與集體決策過程的一種治理安排,這種集體決策過程是正式的、以共識為導向的、慎重的,目的是制定或實施公共政策,管理公共項目或資產[5]。廣義來看,協同治理是公共政策決定和管理的過程,使人們建設性地跨越公共機構、政府部門、私人和公共領域的界限,以實現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公共目的。在各地社會治理實踐中,協同治理模式越來越多地取代對抗性決策模式。協同治理模型有4 個主要變量,即啟動條件、制度設計、領導力建設和協作過程。其中,啟動條件包括權力/資源的平衡、參與的鼓勵機制、敵對或合作的歷史、外部環境等,是協同治理形成的前提條件;制度設計為合作發生設定基本規則或基本協議,為治理過程的程序合法性提供制度保障;領導力建設指可統籌全局的部門,是將利益相關方集聚在一起的重要途徑,為合作過程提供必要的調解和促進,對建立信任、促進對話、互惠互利有重要作用;協作過程是周期性的持續工作,包括確定共識性目標、開展密集的溝通協作、擁有協作的技術支撐等。為了讓脆弱的海岸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新加坡以綜合方式對海岸進行全面治理,由此開發出城市海岸帶綜合治理模式(IUCM)。該框架旨在加強利益相關者的伙伴關系和協同作用,旨在解決城市環境中沿海管理問題的復雜性質。新加坡的綜合治理成效顯著,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棲息地管理計劃、水質管理和環境災害管理等核心領域達到績效預期。新加坡海岸帶空間功能結構如圖1所示。

圖1 新加坡海岸帶空間功能結構
2.1 啟動條件
2.1.1 環境問題影響城市發展的問題驅動
新加坡有限的海岸帶空間承載航運、工業、生活、娛樂等多種功能。各種功能相互競爭,尋求更高強度的開發,侵占剩余未利用地海岸線。在這種背景下,自然資源的保護受到忽視,沿海生境、海洋水質問題構成新加坡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2.1.2 開發與保護部門權力失衡的現實條件
新加坡位于主要的航運貿易路線上,以航運為基礎的海洋相關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此條件下,城市開發部門與環境保護部門權力長期處于失衡狀態,自然資源保護與海洋污染治理問題也受到忽視[5]。這為海岸區域的協同治理帶來不利條件,導致新加坡海岸區域的協同治理更加依賴統一的領導機構。
2.2 制度設計
2.2.1 形成完善的法律框架
海岸帶區域治理是一個由眾多部門管理的共享體系,各機構的任務和目標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制度體系,加強這些機構的協同。有效的法律/制度框架是協作成功的先決條件。新加坡沿海區域治理建立在一系列法律組成的框架上,相關法律制度如表1所示。

表1 新加坡沿海與海洋區域制度框架
2.2.2 建立現有法律的審查與優化體系
新加坡國家公園局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學院開展合作,制定審查新加坡現行海岸及海洋有關法律制度的合作框架。通過對現有法律制度的評估,新加坡政府部門可以及時發現法律架構的漏洞,完善相關法律。
2.3 領導力建設
2.3.1 形成一體化的統籌組織機構
受限于開發與保護部門權力失衡的現實,海岸帶區域的綜合治理需要統籌領導機構的介入。新加坡嘗試采取兩種模式實現沿海區域的一體化管理,一是由規劃相關部門組建委員會,二是由港務局負責。1996年成立海事和港務局是后續一體化領導機構的雛形。然而,與環境保護事項相關的統籌機構仍有待建立。為強化對沿海區域的綜合治理,2009年,沿海和海洋環境政策委員會成立。其主要負責各部門的管理協調,制定海岸帶開發建設活動、環境保護、港口活動的管理方法。除了組建統籌協調機制外,涉及沿海娛樂設施、沿海住宅開發、港口碼頭建設、漁業等的項目均需要沿海和海洋開發委員會審批。
2.3.2 組建技術委員會,強化領導能力建設
為加強領導能力建設,沿海和海洋環境政策委員會建立國內外專家網絡,以加強新加坡海岸帶治理能力。此外,還成立沿海和海洋環境技術委員會,由國家公園局和國家環境局共同擔任主席推進海岸帶的保護與利用。該委員會囊括新加坡農業食品與獸醫局、交通部、建設局、國家環境局、海事和港務局、環境和水資源部、新加坡國立大學等機構,涵蓋政府部門與研究機構。同時,廣泛吸納公眾建議。該機構為沿海和海洋環境政策委員會提供技術支撐。
2.4 治理過程
2.4.1 將海岸帶治理目標納入規劃體系
共識性的目標是多方合作的重要基礎[5]。在海岸帶開發與利用過程中,各機構都有不同的發展目標。新加坡海岸帶區域綜合管理框架的目標得到許多規劃的響應和落實,包括城市總體規劃、公園和水體規劃、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規劃、國家氣候變化戰略、清潔和綠色計劃、可持續發展藍圖等。新加坡定期調整規劃,使其及時適應城市人口、社會與經濟發展趨勢。在規劃調整過程中,對沿海地區利益相關者的建議進行高度整合。
2.4.2 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廣泛參與
新加坡海岸帶綜合治理框架鼓勵利益相關者和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通過“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社會組織”的協同效應,沿海區域的開發與利用取得更大的成功。一是政府。不同的政府機構負責特定方面的管理,如海岸保護、污染治理、航運、海岸土地利用規劃和棲息地保護等海岸和海洋環境項目。目前,各政府部門已制定與公眾部門合作的策略,如實施教育項目、建立志愿者隊伍、出版生活雜志與科學期刊、舉辦工作坊等。二是企業。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在海岸帶區域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如設置自然保護信托基金。此外,各種環境咨詢公司也在新加坡成立分部,主要評估潛在的發展影響,并提出緩解措施,還參與環境政策和質量標準制定。三是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如自然協會、水道觀察協會等)在沿海環境保護中發揮積極作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聚焦于物種多樣性,培養公眾的環保意識。
2.4.3 構筑多源數據平臺的支撐體系
海岸區域受到陸海交互作用,生態系統更為復雜,而協同治理模式導致利益相關者數量多。基于此,協作過程更加依賴數據平臺的支撐作用。通過綜合數據采集、專用數據庫建設、重復審查、長期監測制度共同支撐海岸帶區域治理。一方面,衛星遙感在新加坡海岸管理中廣泛應用,服務海洋生境測繪、水質監測、船舶尾流探測、溢油檢測、赤潮監測和填海活動測繪;另一方面,多元化數據平臺連接著各類海岸區域治理的參與者。其中,典型的平臺項目是生物多樣性和環境數據庫系統,它是生物多樣性的一站式存儲庫與各類環境數據的儲存庫,長期監測新加坡的海草、珊瑚和紅樹林,跟蹤生物多樣性,收集環境影響的基線信息進行評估。
3 結論
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新加坡提出城市海岸帶綜合治理模式,強調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積極的伙伴關系,共同參與海岸帶保護與利用。新加坡這一治理模式的成功得到國際上的廣泛認可,對我國海岸帶的綜合治理具有借鑒意義。我國的協同治理實踐在改革開放后萌發,在區域合作、環境保護領域展開探索。然而,我國沿海區域的實踐經驗有限,僅12%的海岸線納入海岸帶綜合治理框架。我國最早的海岸帶綜合管理計劃(ICM)于1994年在廈門市啟動,在第一輪框架結束后,廈門市利用政府資金啟動第二輪海岸帶綜合管理計劃。這一框架在完善多方協同治理體制、啟動立法和相關制度擬定、沿海環境改善、提升生態系統價值、提升社會經濟水平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然而,對比新加坡的協同治理經驗,我國海岸帶治理在制度設計方面仍不全面,且未建立政策的評估和及時修正機制;政府部門協同治理的技術服務部門尚欠缺;企業與社會組織在海岸帶治理中的參與不足,進而導致相關項目資金來源有限;海岸帶發展目標與相關規劃缺乏銜接機制。以上問題將是我國未來海岸帶治理提升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