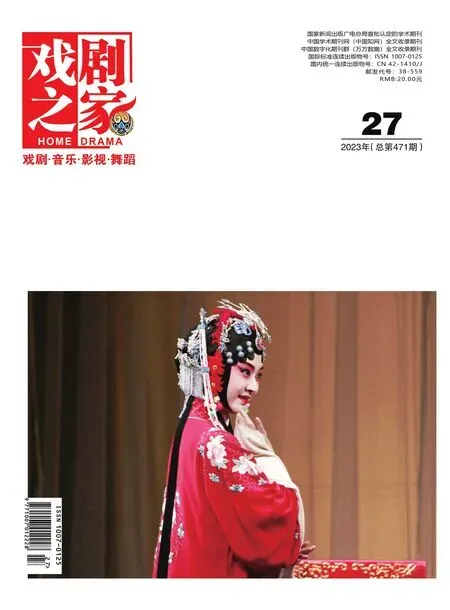李睿珺電影中的鄉土影像敘事
張臨亮,王麗莎
(青島電影學院 山東 青島 266520)
1935 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序言中正式提出了“鄉土文學”這一概念,此后,“鄉土”“農村”作為具有特殊標識意義的概念進入文藝批評范疇,而在后期發展的電影批評理論領域,“農村題材電影”與“鄉土電影”也主要來源于文學批評概念的延伸。學界關于“鄉土電影”的概念辨析比較豐富,學者凌燕對“鄉土”與“農村”的概念辨析進行相關論述:“鄉土似乎更多聯系美好的自然風光、淳樸的民風民情;而農村似乎聯系著貧窮落后的社會學意義、守舊的文化以及階級斗爭和社會變革等意識形態方面的色彩。因此,可以說‘鄉土’可以歸入文化層面,而‘農村’則是政治意義上的概念,前者重主觀情感,后者偏重于客觀敘述。”[1]學者路春艷則將“鄉土電影”定義為“以鄉村生活為背景的影片,不僅包括常提的‘農村題材’,也包括那些表現歷史中鄉土社會生活的影片”[2]。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文化語境中的“現代性”逐漸將“農村”與“鄉土”的概念邊界消融,21 世紀以來,學界對于“農村”“鄉土”的概念爭議漸熄,其探討的案例多是既能深刻捕捉并凸顯具有鮮明地域特征的鄉土風情,同時也富含時代烙印,飽含深厚的社會學內涵的作品。本文鄉土影像敘事的概念基于“以鄉土生活為主要敘事背景,以表現鄉土人物的生存、倫理與情感狀態以及鄉土社會裂變為主要敘事內容。”[3]80 后新生代導演李睿珺從自身成長環境入手創作了諸如《老驢頭》《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路過未來》《隱入塵煙》等作品,借助西部鄉村、耕地、老人等元素完成鄉土影像的畫面詮解并通過展示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化發展沖突進行文化反思以及對現代性的批判,具有強烈的作者視角特征。本文從導演現有的幾部影片著手,綜合敘事空間設置、符號隱喻與詩意美學風格等角度論述分析李睿珺導演的鄉村影像敘事的外在美學表達以及內在文化意義。
一、敘事空間:鄉村影像的景觀塑造
鄉土電影的題材本身帶有鮮明的地理空間屬性,這決定了其空間敘事的特性相較其他電影更加明顯,“鄉土”是導演常用的敘事空間,它是城市的“他者”,同時也蘊含著“前現代”性的鄉村文化圖景。對電影文本的影像文化意涵分析主要借助影片中的畫面表達進行,通過影像所指分類將其劃定為影片中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自然景觀指的是出現在影片中的自然界景觀;而人文景觀則稍顯復雜,指的是那些能夠體現人性、文化、情感信息的影像畫面。”[4]李睿珺導演的幾部鄉土電影皆以自幼生長、熟知的鄉土環境為敘事背景,通過對風光元素的使用,不僅表現了鄉土影像的自然景觀,展示了獨特的藝術和審美感,更是寓言性地反映了鄉土的人文精神和情感底蘊。如《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中展示了枯燥荒漠的“沙丘”,與肥沃豐饒的“草原”形成鮮明對比,這種雙關式呼應通過影像張力將影片主題含義進行了升華。在《老驢頭》中,電影畫面充斥著無盡的黃沙和廣袤的沙丘。主人公鞭策著瘦弱的毛驢從遙遠的地方運送冰塊,為他所種植的紅柳和草地澆灌。電影通過諸如“沙丘、祖墳、毛驢……”等符號意象將老驢頭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對比生命還要珍貴的事物的執著追求,從平淡的視角展現了這種徒勞的掙扎,揭示著傳統農耕文明的消逝以及社會現代性進程中鄉村景觀的消解。
李睿珺還善于運用魔幻的表現主義手法“制造”虛擬的影像景觀。阿多爾諾在《美學理論》曾對模仿“自然美”的“藝術美”作出論述,他認為具有真實性的現代藝術的意義在于對異化的社會現實具有反思、批判、否定的功能。李睿珺則通過“人為的”影像畫面將他自己感知、審視社會的視角濃縮在鏡頭敘事中,從而構建出帶有“人文審美”的鄉土影像景觀。西北村落是李睿珺所有影像創作中最為突出的一點,閉塞的環境造就了熒幕中人物的性格、村落文化特征,因而當時代發生變化、社會文明的發展進入矛盾后,“與常規空間對抗”的新型景觀被賦予了新的解讀意義。在《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中通過對“仙鶴、墳墓、煙囪冒煙”等人文景觀的展示,揭示了底層群眾根深蒂固的歸土意識以及在社會制度變革下命運所面臨的不可預測的變化與無能為力的恐懼。土葬不僅是對殯葬文化的認同,更是鄉土背景下現實蒼涼與小人物生活的悲喜呈現。《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中通過敘述裕固族尋找精神之鄉的故事,將死的駱駝把孩子帶到水草豐茂的地方這種超現實的畫面描摹,借助空間景觀上的象征完成人物精神歸宿的指引,同時也展現出導演的鄉土情結及其背后的浪漫精神。
二、符號隱喻:鄉土影像的文化能指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將語言結構進行處理,將符號與其指代物總結為“能指-所指”的關系,“能指”承載符號內容的表達層面,即電影中的影像文本,而影片中的“所指”是以“相似性”為原則的“實在物”本身,更包含其“語象隱喻”即創作者或觀影者通過外在化“電影語言”解讀文本而得出的內在化的表達意象。從景觀意象的文化表達上來看,李睿珺導演的作品集從鄉土出發,審視當下生活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并保持絕對冷靜的情感表達,立足鄉土這一背景進行勾勒與傳述,傳遞人文主題。無論是《隱入塵煙》還是《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還是《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其中都有不同空間的符號,或馬或驢或白鶴、駱駝、塵土等。馬在《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中經常被解讀為“物質清貧、精神無處歸依”的困境暗示,這是人物生存境況的關照與思考,片中老馬的執拗讓人唏噓;《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中,隨著爺爺的去世與白馬的不辭而別,原先馬背上的希望逐漸消失,這既是舊文明消亡的隱喻也是新文明即將出現的訊息。爺爺生命消失后卻化身白馬奇跡般地出現,這種超現實主義手法的呈現展示著政策變遷發展的失衡與邊緣個體生命生存權利被剝奪之間的矛盾;《隱入塵煙》中老馬的那頭驢是他生存下相互為伴的朋友,同時也是他在遇見貴英之前的希望與寄托;《路過未來》中的白馬既是耀婷生肖的一種鏈接,也是命運的一種暗示,她奔波勞碌了一生到頭來卻無法安身立命。《路過未來》是一部關于尋根與生命的主題影片與故事,通常創作者會選擇情節張力較強的故事來展現這一主題,在李睿珺的創作中,他反而采用了散文式的風格借助生活感的結構與拍攝方式表現了就業、醫療與鄉土之間的情感締結;《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看似是農村留守兒童與老人之間的故事,實際上借助“白鶴”這一意象將民間宗教與信仰的悲哀荒涼處境表現了出來,那種凄涼與無能為力是直擊觀眾內心的重要因素;《老驢頭》中土地被侵占、土地被沙漠淹沒、老驢頭無處可依地悲哀死去,這些場景都足夠戲劇化且極具沖突性,但李睿珺仍然選擇淡化戲劇性情節,強調自然的鏡頭,用一種近似于“冷漠”的客觀視角敘述,借用現實存在的符號作為精神導向的景觀,從而隱喻其命運的無力與蒼茫,使觀眾在銀幕敘事中從個體角度理解這類群眾在社會時代變革浪潮中的悲哀,從而喚起更多的思考與共鳴。
扎根鄉土敘事背景的李睿珺聚焦生活事件與松散的結構模式去反映較為真實的生活,以近乎生活底色的平和敘事口吻及節奏中創造出直擊觀眾心靈并引發哲思的內在效果。正如作者以往的作品一樣,他通過對鄉村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岌岌可危的處境的描繪,揭示了鄉村文化在適應和抵抗現代化進程的壓力下,其維持自我身份和傳統的困難。它本質上反映了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累積起來的焦慮感,與其他鄉土電影不同的是,李睿珺并沒有將鄉村建構成符合工業現代化想象的具有“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烏托邦,而是通過“鄉村主人公”個體意志向“社會現代化”進程發起對抗的過程中反思個體與社會、自然的關系。
三、創作風格:鄉土敘事的浪漫意象
李睿珺在采訪報道中提到意大利新浪潮電影對其自身創作的影響,這也是他創作風格的參照根基,這種直接的、真實的記錄拍攝方法從第五代導演后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作為“巴贊美學”的證明者,從賈樟柯開始,追蹤鏡頭、開放構圖、長鏡頭、場景調度等細節處理構成了此類影像的獨有審美。區別于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藝術語言的使用與表達,李睿珺擅長采用冷靜客觀的長鏡頭視角與遠景鏡頭客觀展示“看到”的現實。這種現實區別于作者型導演的主觀介入,反而滲透著一種明確的深邃與冷靜,借用“觀察與陪伴式”的鏡頭呈現凸顯著現代性的批判與思考。
《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最后老馬自己挖土的情節段落中連續使用了兩個長鏡頭展示生命消亡的過程,冷靜客觀的表現使觀眾頓感壓抑與凄涼。在其他導演的創作中,展示這一細節往往會采用特寫、閃回、沉穩的鏡頭表現方式,人物的動作、表情細節被逐一放大,才能勾勒某些對抗生命的節奏,引人深思。李睿珺的作品中,除去鄉土這一宏觀大背景,人物的對話、行動、生活基本都完成了全景交代,仿佛人的眼睛觀看著所有狀況的發生,反而構成了一種奇怪的釋然與無力。孩子天真地以為爺爺的不快樂是因為鄰居爺爺有的他沒有,當他們嬉鬧著把老馬的坑填上,夕陽西下,一切歸于安靜,沒有人找得到老馬了,這種詩化呈現死亡的方式更讓人唏噓。由此也可看出,李睿珺鄉土影像所尊崇的藝術美感就是這廣袤的具有強烈生命變遷與重生的土地。
《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與貴英的無家可歸的心酸、遭人嘲笑的窘迫、奔波的路途與被迫“獻血”是農村底層苦難的真實顯現,但大雨中的依偎,溫暖的雞舍燈,勤勞耕種反而形成人與人、人與土地、動物之間個體與個體相互依附的浪漫化表達,使影片本身帶有的苦難情緒被弱化,而呈現了關于生命與時間的深刻思考。馬有鐵與貴英看似通過勞作“馴服”了房屋、麥子與雞,同時也被更高的階級“馴服”——抽血以及搬進樓房,但其中恒定的巨大力量則是時間與土地。《隱入塵煙》中人類個體生命(時間)的長度是有限的,即便上層階級可以靠下層階級的輸血來實現“資本”與“生命”的延續,但其永遠無法改變自然時間的延續以及物種代際的更迭。正如影片中說的“雞蛋變成小雞,小雞變成大雞,大雞再變成蛋;麥粒變成麥苗,麥苗變成麥子,麥子變成麥粒,麥粒再回到麥地里。土變成泥巴,泥巴變成磚,磚變成墻變成房子再變成土。”這就是生命的無始無終的輪回,片尾,即便男主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間),但手中的麥苗仍隨著自然時間的延續而生長。這種對時間、土地的至高“崇拜”恰恰體現了鄉土敘事中農耕文明世界觀的浪漫表述。這種浪漫與克制并存的電影意識與風格使導演對世界的觀察與表述最終指向了一種起于個體、止于族群,在克制與冷靜中對時代進行全景記錄的創作風格。
四、結語
李睿珺導演從個人的成長經歷出發,基于有限的資金以及技術條件將現實與電影意象結合,不僅體現了中國鄉村的景觀美感、詩意審美,更塑造了一種鮮明且獨特的電影審美體驗。李睿珺的電影語言豐富且精煉,通過長鏡頭、追蹤鏡頭以及場景調度等藝術手段,使得電影的敘述不僅僅是現實的再現,而是一種喚醒觀眾深層次感知的方式。他以鮮明的鄉土背景來深化人物的內在情感,同時又將人物的生活緊密地綁定于鄉土,形成了特有的敘事風格。他通過對電影中人物與土地、時間關系的時代性描摹,不僅展現了他對鄉土生活的深入觀察和對農村生活困境的批判性反思,更展現了他對人類存在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雙重反思,構建了一個復雜而生動的生命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