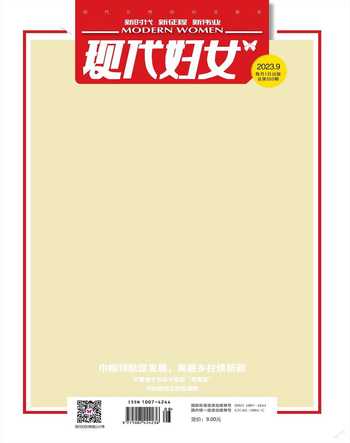親情的“陌生時段”
姚文冬

月底的一個清晨,天略微涼了,眼前飄著一層薄霧。因為起得早,腦子還有點混沌,頗有一種不知置身何處的夢幻感——才6點,我已驅車幾十里回到了老家。走進院中,畫面有些“陌生”。從濕漉漉的菜畦里,父親抬起頭來,臉上也掛著“陌生”——他沒料到我在此時回家,張了張嘴,竟沒發出聲音。母親從堂屋出來,除了一貫的慈祥,表情里也多了一層“陌生”。
直到我把時令鮮貨放在門口,父親才說了一句:“這么早?!”母親也隨之開口,還是那句老話:“在家吃飯嗎?”
就像我乍走進這個夢幻的清晨有些不適——我極少在這個時段回家;父母也不適——他們應該好多年沒在清晨見過他們的兒子了。我們共同置身于一個“陌生時段”。
這些年,有過多少這樣的親情缺席的“陌生時段”呢?
中年之后,我養成了回老家看望父母的習慣。父母也習慣了我的習慣。漸漸地,便形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規律——我回家總是在下午,日落之前;從不吃晚飯;放下東西,說幾句話,便完成任務似的返城。在這個時段,父母呈現的是等待狀態——父親要么在院中侍弄那片菜地,要么在屋里擺弄撲克牌;母親則盤膝坐著,像是在專門等我。只要我一進門,母親一準會說:“剛才還跟你爸說呢,今天你肯定回來。”仿佛她未卜先知——盡管我回家的次數并不固定,有時一連幾日天天去,有時一周一次,最長時隔半月、20天,但總在這個時間段。我便有了一種錯覺,以為在這個時段的所見,便是父母的生活常態。
也許他們是因為我的習慣,養成了固守那個特定時段的習慣吧。而別的時段,我們相互陌生。所以,這次清晨的臨時起意,出乎他們的意料,彼此竟都不適應。
這樣的“陌生時段”何其多?
雖然心里記掛著他們,但我感覺,回家已成了一種機械的慣性,仿佛是去完成一項任務。對他們來說,則是生怕錯過——無論我幾天一回,還是一個月一回,他們都盡量不在那個時段缺席。其實離開那個時段,才是他們真實的自由生活。
從20歲離家,我久違了父母的日常。曾經,我熟悉他們的夜晚,也熟悉他們的白天,就拿這個秋日的清晨來說,曾經,我都是被母親在廚房弄出的響動、父親在院子里干活時的咳嗽聲喚醒的。我閉著眼睛都能勾勒出家中的畫面。這司空見慣的場景,如今卻陌生了。雖然我常去看望,但父母也對其他時段的我陌生了。
除了日落前的那片刻時光,我與父母之間,已被大片的“陌生時段”占據。每個人都能見到年夜飯上的父母,但又幾個能見到清晨6點的父母呢?只有將那些割據的“陌生時段”統一,親情才會連成一片吧。
于是,我破例與父母共進早餐。母親高興壞了,熬了暖胃的稀粥,炒了一盤韭菜雞蛋。她問我還想吃啥?我說:“想吃豆腐,南街做豆腐的那個老王,還天天來門口叫賣嗎?”母親笑著說:“傻孩子,老王要是還活著,都超過100歲了。”我鼻子一酸,并非因為老王。
(潘光賢摘自《今晚報》)(責任編輯 張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