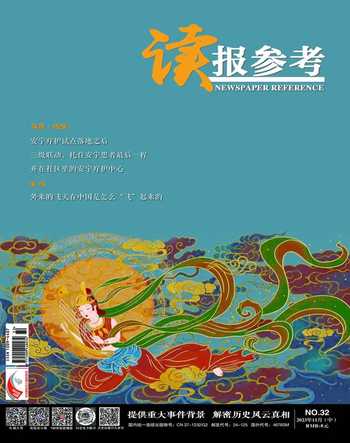三級聯動,托住安寧患者最后一程
從協和醫院到普仁醫院是兩公里,從普仁醫院到蒲黃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也是兩公里,在北京城的一塊小小的核心區域里,一群有志于從事安寧緩和醫療的人們共同編織了一張網。三級醫院出技術,二級醫院出病房,社區醫院做居家,寧曉紅和她的“大團隊”托住了臨終患者不同階段的需求,也激活了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的資源,為安寧緩和醫療落地基層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
新專業領域
李波是東北人,10多年前就把父母從老家接到北京。2022年初,李波的母親被確診為胰腺癌,之后一直在協和醫院腫瘤內科治療。化療了半年多,瘤體終于有所縮小,可一家人還來不及高興,今年3月的復查結果顯示,母親的肝腎各項指標都出現了異常,已經不再適合化療。李波急得睡不著覺,主診醫生建議他帶母親去醫院緩和醫學中心掛個號。
診室里,中心主任寧曉紅向父子倆拋出問題:“她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嗎?”父子倆有點含糊:“大概差不多知道……”“那最后呢?她想回老家嗎?想在哪兒離世?”寧曉紅語氣平靜。李波說:“沒說去世,我們沒說過這事兒……”
后來,寧曉紅向記者解釋,在首診中如果能夠問清患者和家屬的“離世地點”和最終打算,更有利于幫助他們確定接下來的可行的治療計劃,就像是一種先確定結果之后的逆向推導過程,“如果病人想在家,就要考慮居家照顧的可能性;如果要回老家,那么什么時候回去,回去之后怎么安排,也都要開始準備了”。
連續兩天的門診中,記者曾聽見寧曉紅數次問出這個問題。患者答復不一,他們有些剛剛確診,還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有些在協和醫院附近租了房,準備有問題隨時去急診處理;還有些在離開診室前偷偷問:“到底怎么樣才能住進協和?”老李則在兒子出門打電話的時候告訴寧曉紅,如果那一天到來,他們還是想回東北老家。
一個人想在哪兒離世,往往能反映他對自己生命最后一程的期待。協和醫院老年醫學科博士生金爽則在針對174位社區老年人的調查中發現,離世地點在患者心目中往往并不是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它們甚至會在6個月內發生數次轉變,因此,醫生更應該適時、靈活地和患者討論。
寧曉紅是北京市最早開始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理念的專家之一。2012年,她作為北京癌癥康復與姑息治療委員會的成員,和來自北京7家醫院的11名同道赴臺灣安寧照顧基金會學習。在那里,她看到一種與既往觀念不同的照顧模式——在安寧團隊身體、精神、心理等多方面的幫助下,進入疾病終末期的患者,可以選擇不做治愈性治療,不插管、不搶救,做好疼痛和癥狀控制,就能有質量地走好最后一程,他們的家屬也能因此擁有生死兩相安的人生。
寧曉紅倍受感動,回到協和醫院后,她先是在科里分享經驗,又在會診時把安寧緩和醫療的理念向院內其他科室普及。2014年,寧曉紅調到醫院老年醫學科,正式將幾乎全部精力放在安寧緩和醫療工作中,并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開設“舒緩醫學”課程。在她和其他同仁的努力下,“安寧療護”也逐漸從一個安寧緩和醫療專業的小眾名詞走向大眾視野。2017年,“安寧療護”正式成為各級醫院需要關注的新專業領域。
三級聯動
政策落地,一直為此大聲疾呼的寧曉紅卻越來越覺得力不從心了。院內會診量越來越大,團隊人手不足,即使是作為“巨無霸”的協和醫院,在面對如此龐大的終末期患者的需求時,也難免感到無能為力。
2018年,曾有一位腮腺癌術后復發的患者找到寧曉紅,他復發的腫瘤長在頭上,每天都在滲血,患者不愿意再住院治療,想問她的團隊能不能上門換藥。寧曉紅咨詢醫院醫務處,三級醫院的醫生在社區執業是否符合規定?得到肯定的答復,拿到家屬的《知情同意告知》后,寧曉紅和護士利用業余時間為患者上門換了兩次藥。回到醫院,中心和醫務處共同總結經驗——這樣的服務患者滿意,但協和醫院的定位是疑難重癥患者的診治中心,類似的上門服務應該由更接近患者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來提供。寧曉紅想,如果能搭建一個安寧緩和醫療轉診網絡,由協和把這些患者的需求轉派到社區,這些問題不就能得到解決了嗎?
從協和到普仁醫院只有兩公里,對于寧曉紅來說,是騎自行車10分鐘就能到達的距離,但如果沒有技術和資源的對接,這兩公里對許多想要尋求安寧療護的患者來說,就是一段難以逾越的距離。2020年起,寧曉紅和她的“飛行團隊”開始定期出現在這里的老年科病房大查房,試圖一點一點拉近這兩公里的距離。
今年5月15日8點,寧曉紅和記者的第一次見面就約在普仁醫院。科室里12張床位都住滿了,4位需要緩和醫療照顧的患者,寧曉紅一共查了兩個半小時。一位63歲的結腸癌患者,做手術后腹部留下傷口,醫生給他下了“芬太尼”貼片鎮痛,奇怪的是,他的疼痛只要平臥不動就能緩解,起床一活動就又加劇,醫生們拿不準該不該再給他多加止痛藥。
圍在患者床邊,寧曉紅輕觸患者腹部的敷料,又請同來的鄭瑩醫生檢查患者的傷口恢復情況:“我們必須明確疼痛和什么有關。它既可能是由于炎癥,也可能是情緒、工作、家庭等各個方面的非身體原因導致的……貼劑有一個特點就是需要起效時間,我們調好總量之后,最好從小的劑量往上提,千萬不要覺得這個好,然后一貼,患者之前沒有使用過的話耐受不了,副作用很大,他就不愿意再用了。我們本來也沒幾個武器。”她習慣把治療方法稱為“武器”,寧曉紅認為,癥狀控制是引導患者接受安寧理念和進行情感溝通的大前提,“我覺得藥物使用是第一關,不管誰會診找你,如果你不能解決癥狀,立馬就沒有地位了。你一旦能控制好,你再說什么他都容易接受”。
鄭瑩帶著普仁醫院的護士們繼續觀察患者的傷口,試圖幫他撕掉一部分結痂,看是否能解決運動時牽扯疼痛的問題,“護士也要知道癥狀,咱們病房的護士都必須和醫生一樣熟悉用藥”。寧曉紅又對照病歷,和科室醫生們聊起如何幫助患者作醫療決策的問題。
今年4月,蒲黃榆衛生服務中心開設安寧病房,專門解決居家安寧中無法處理的急性癥狀,他們也因此成為北京首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轉型的安寧療護機構。病房開診后,北京市衛生健康委老齡健康處處長丁衛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要推進綜合連續、機構和居家相銜接的安寧療護服務體系,大力發展居家和社區的安寧療護。根據2022年發布的《北京市加快推進安寧療護服務發展實施方案》,到2025年,北京每區將至少設立1所安寧療護中心,提供安寧療護服務的床位不少于1800張,讓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能夠普遍提供社區和居家安寧療護服務,老年人安寧療護服務需求得到基本滿足。
這對寧曉紅和她的“大團隊”成員都是一種挑戰。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學中心成立那天是世界安寧緩和醫療日,作為主任的寧曉紅在會議上宣布,除了要在院內加強醫患服務外,還要繼續在醫聯體內開展系統培訓、上下轉診、查房和科研指導,進一步構建完善北京協和醫院-二級醫院-社區和家庭連續服務的“協和安寧緩和醫療模式”。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