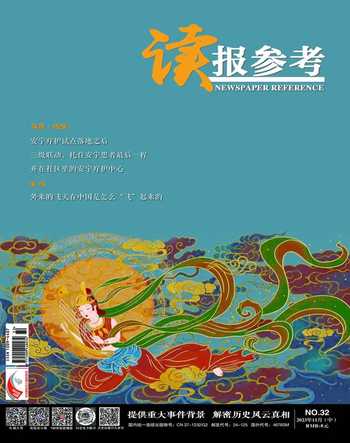老年情感經濟,如何跳出“騙”字
男“秀才”、女“傾城”,他們在短視頻平臺超過1000萬的粉絲群體和高齡粉絲畫像,讓年輕人驚呼——父母們原來也有自己的“頂流”。9月2日,“秀才”的平臺賬號顯示被封。從悄聲吸粉到突然破圈,再到被調查被禁號,類似的故事走向似曾相識。同樣是瞄準老年人的錢包,人們或許該意識到,只要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未被妥善地承托,這樣的事件便難以落下帷幕。
“秀才”憑什么
不少闖進“秀才”直播間的年輕人,會被其夸張的神態和過于赤裸的情感表達震得高呼“受不了”,繼而陡生疑惑——一個略顯土氣與油膩的中年男人,憑什么吸粉千萬?
“秀才”的視頻,內容基本同質。田間地頭,“秀才”常著襯衫或Polo衫,衣服下擺被掖在西褲內,帶著他標志性的笑容對口型唱歌。固定幾首歌的重復演繹,卻能收獲點贊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第三方數據平臺“蟬媽媽”的數據顯示,即使“秀才”在較短時期內發送相同的主題,獲贊數并不會因同質化發布而有所降低。運營這類賬號似乎不需要費盡心思地“整活”,唯一辛苦的是要保持高頻率的更新與直播。但正是這不斷重復的簡單、“深情”和接地氣,成為了“秀才”脫穎而出的理由——這種內容,專為迎合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而設。
早在2020年,層出不窮的“假靳東”詐騙案曾刷屏網絡。詐騙團伙截取演員靳東的視頻形象,配上拙劣的特效和幾句文字,便引得部分對手機不熟悉的中老年人認為,視頻另一端正是靳東本人,而他正對著自己表白。一名60多歲的女性曾在江西衛視《幸福配方》欄目中袒露自己追捧“靳東”的原因。她說:“我的好、我的美、我的人、我的心、我的善,全部被他(靳東)唱出來了。”
看似瘋狂的表象背后,是老年人對自己情感需求的一次大膽表態。他們不僅需要兒女的陪伴,他們同時需要愛情。或者說,即使年老,他們也想從另一種層面再次確認,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自己魅力猶存。步入老年后,《銀發世代》的作者路易斯·阿倫森在書中感嘆:“人們尊敬、愛戴,甚至真心愛我們,只是我們不再值得他們傾聽。”
這是一種數量龐大的孤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50歲及以上網民規模達3.29億,占整體網民的30.8%。
然而,在高齡人群加速“觸網”的當下,主要的內容生態卻仍然圍繞著“主流”的年輕市場。品牌們圍繞在年輕人身邊,爭做其人生中第一口白酒、第一杯咖啡、第一個名牌包……而老年人,無人在意。于是,第一個“秀才”出現了。
無獨有偶,“秀才”的第一條視頻發布在2020年7月。這不一定與“假靳東”事件密切相關,但無疑,其創作者捕捉到了類似的需求,并給出了回應。事實上,除了“秀才”外,還有許多畫像類似的創作者也出現在2020年前后。他們對口型唱著類似的歌,用《愛情十八拍》《小妹妹送我的郎》等歌曲,俘獲了大批老年粉絲群體。
當時,因居家隔離等因素,社交軟件得以觸達更廣的群體,而“秀才”們,用一次次模式化的視頻,試驗出一條精細化的情感經濟之路。其直播間高達幾十萬的打賞,也許是這種探索應得的回報。真的是這樣嗎?
“第三階段”經濟
讀者也許會發現,前面引用的數據中,“老年人”被解釋為“50歲以上群體”。如此表述,固有統計便利的原因,但這一群體也契合英國歷史學家彼得·拉斯利特所定義的“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一詞最早出現在1970年代,法國人將針對退休人士的教育和社會活動項目稱為“第三階段大學”或“老年大學”。這一概念傳到英國后,由彼得·拉斯利特進行了普及。拉斯利特認為,人生可被分為四個階段,邁過前兩個階段的“童年”與“工作”后,人生將走入第三階段“順利地衰老”,隨后則是第四階段“虛弱和依賴”。其中,“第三階段”被拉斯利特看作人生的鼎盛階段,一個無需為工作和身體擔憂,專注于“自我實現和滿足的時期”。
這群幾近或完全退休,但仍然身體健康,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群體,正與“秀才”們的主要觀眾畫像相符。第三方數據平臺“蟬媽媽”數據顯示,“秀才”的直播觀眾中,87%為女性,58.17%為40歲以上,50歲以上群體占全部直播觀眾的38.22%。
這個概念,重塑了人們對“年老”的想象。老年人不再被看作經濟的邊緣人群,相反,他們可以是“社會上活躍的大眾消費群體”。在我國老齡人口占比、老齡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均在增加的當下,“第三階段”人群的需求,也將成為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第三方數據機構QuestMobile發布的《2022銀發經濟洞察報告》顯示,2022年8月,銀發用戶(50歲以上人群)月人均使用移動互聯網的時長達121.6小時,平均每人每天約使用4小時,線上消費能力達1000元以上的月活躍用戶規模為1.98億。這是個高度活躍的市場,但在當前,談到老齡產業經濟,被關聯想象到的卻總是“欺騙”。在短視頻吸睛之前,種種線下保健品商店早已踩中老年消費者的健康需求和情感需求,哄騙他們投錢無數,最為矚目的便是2018年的“權健傳銷”。而當高齡人群“觸網”,其強烈的需求碰上更陌生的網絡環境,此時,要理性判斷自己的行為,顯得更為困難。
捕捉到老年用戶需求的主播們,若只是趁著這一市場尚未成熟時,放肆借用粗制的視頻吸粉,以享高額打賞,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在推動塑造一個消極的老年形象,即老年人是缺少辨別力且容易受哄騙的,這是一種更隱形的欺騙,因缺少選擇而沉浸其中的老年用戶,更難為自己辯護。
走向文化“適老”
近5年,在全民數字化浪潮中,老年人的數字參與率快速增長。2018年初,騰訊正式啟動“科技向善”項目,提出要利用科技,緩解數字化社會的陣痛。騰訊創始人之一張志東在項目會議上表示,騰訊是在有龐大的用戶群后,才開始意識到“用戶”涵蓋的不同的社會角色、年齡層、職業與偏好等特征。當時,針對年輕用戶設計的產品,讓高齡人群面臨著一條令人畏懼的“數字鴻溝”。
2020年11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方案圍繞日常需要及文化參與,提出了7個解決老人“數字鴻溝”問題的重點任務,其中便包含“推進互聯網應用適老化改造”。
簡化的操作,讓高齡網民能更便捷地使用應用,但隨之帶來的“防沉迷”問題,也成為另一個數字難題。老人們擁有更多的自主時間,因此更易沉溺于短視頻的信息流中。2022年8月,QuestMobile發布的《銀發經濟洞察報告》顯示,銀發群體的月均短視頻App使用時長,大部分高于該 App用戶的平均使用時長。
如今,互聯網產品的升級重點,需要從“操作適老”進一步擴展到“內容適老”。更多商業機構已先一步開拓了這個市場。據第三方數據平臺AgeClub統計,早在2019年,短視頻平臺上已有機構孵化出老年KOL(關鍵意見領袖)。而在“秀才”被封號之前,“三只羊”創始人“瘋狂小楊哥”也曾短暫接洽過他,雙方共同現身直播間。“小楊哥”旗下主播多偏重年輕粉絲,“秀才”的粉絲畫像剛好能補足另一半。在更完善的行業生態出現以前,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正被層出不窮的模仿號填上縫隙,在適老化經濟這條路上,不應是詐騙團伙走得最快、最遠。
(摘自《南風窗》王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