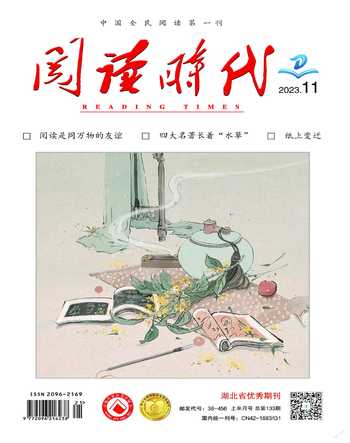李漁的窗子
大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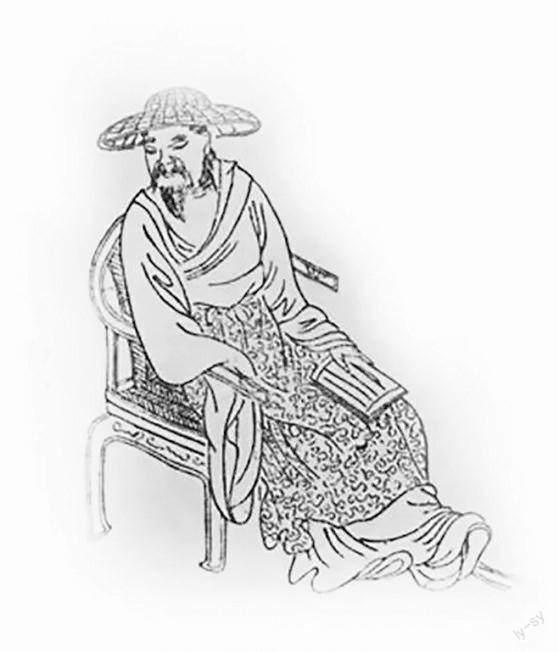
李漁的人生有一大恨。
當年他住在西湖湖畔時,很有些想法:買一只畫舫,旁的不求標新立異,只需在窗子上做做文章。在《閑情偶寄》里,李漁把他的設想寫得清清楚楚:畫舫四面包裹嚴實了,只在左右兩側留下虛位,“為‘便面之形”。“便面”這個詞聽起來有些費解,說白了就是“扇面”。
于是舟行湖上:“則兩岸之湖光山色、寺觀浮屠、云煙竹樹,以及往來之樵人牧豎、醉翁游女,連人帶馬盡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圖畫。”
這不正是“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卻裝飾了別人的夢”?
李漁覺得自己的更高級之處在于,他將畫舫的窗子設計成了扇形——那么多能工巧匠、設計人才,哪個似我這般有想法!
李漁最終沒能如愿。在杭州時財力不逮,有心無力,后來移居南京,再無可能。于是他長嘆一聲:“何時能遂此愿啊,渺茫渺茫。”
說到窗子,可不能等閑視之。
兩千年前的某個晚上,酒喝到恰恰好的曹操對著月色,思緒萬千,長吟一句:“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欲上青天攬明月的渴望,大概從古至今從沒斷絕過——古人造的那個“明”字,就是明證。一個“明”字,今人脫口而出“日月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兒,而是“囧月明”。
“囧”,正是定格了月亮的窗子。夜闌人靜,明月在窗,內心不由得“膨脹”:此刻的月亮,豈非只為我而存在?
窗子的歷史自比文字的歷史要久遠得多,窗戶紙卻是后來的事。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春天,江州司馬白居易呼朋引伴,又請來東林寺、西林寺的長老,備了齋食茶果,慶祝他的新居廬山草堂落成。
這是白居易被貶到江州的第三年。他不得已收起兼濟天下的豪情,轉向獨善其身。
搬進新居已經十來天了,眼前的草堂仰可觀山色,俯可聽泉音,白司馬很滿意。三間屋子,中間是廳堂,兩側是內室。夏天,打開北邊的門,涼風習習來;冬天,南面的陽光照進來,屋里暖洋洋。內室的四扇窗子,貼上窗紙,掛上竹簾麻帳,窗外竹影隨風而動。
不過,白居易坐在窗前時,大概也不免遺憾:不能推開窗,探出頭去,看有沒有新筍冒出來——唐代,墻上開的窗子,多是沒有啟閉功能的直欞窗,欞條縱向排列,是固定的。能啟閉的窗子倒也不是沒有,李白就寫過“開窗碧嶂滿,拂鏡滄江流”,只是遠沒到普及的地步。
宋代的窗子,就高級多了。南宋宮廷畫家劉松年筆下的宅子,單薄程度多少讓人心疼古人。外面白雪皚皚,宅子的墻卻是一水兒的格扇——由上至下,都是一縱一橫的木條構成的方格子,格子上只覆著薄薄的窗紙。窗紙白透,是標準的宋代文人的審美,雖云淡風輕,卻不免讓人哆嗦:就算里面生著火爐,就算一千多年前的臨安比如今暖和些(有考據如此說),不冷嗎?
一到夏天,窗子又搖身一變。比如范成大說的“吹酒小樓三面風”,四圍的隔斷只留下一堵背墻,其余三面,統統鑿窗!簡直太任性了。只用一面墻撐起整座建筑?不錯。中國的木結構建筑,不要說拆掉三面墻,四面都去掉也不在話下。
津津樂道于窗子的文人向來很多,否則蘇州的留園不會單單園林取景用的漏窗就有六十多款,滄浪亭的漏窗款式則奢華至一百零八式。
花木蘭從戰場歸來,“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李清照卻在那個秋日,三杯兩盞淡酒,梧桐更兼細雨,心情蕭瑟,“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李白的“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窗戶”,也許是在某回醉舞狂歌之后;杜甫流寓成都,所幸還能見到草堂“窗含西嶺千秋雪”;而蘇軾十年夢回,眼前竟是早已故去的結發妻子“小軒窗,正梳妝”。
十年寒窗,浮生一日,悲歡離合。窗子內外,一幕幕劇情在歲月里上演。
(源自“通雅軒古籍書店”,有刪節)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