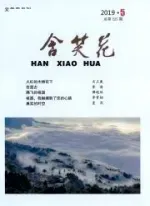曼竜村的蝶變
陳選芳 劉云梅
曼竜村,位于西疇縣雞街鄉,是一個典型的彝族花倮支系聚居的村落,這里居住著128戶近600名花倮同胞,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花倮聚居村寨之一。
據說,曼竜村與廣南縣挖龍村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彝族花倮支系聚居處,全國的總人口尚不足兩千人。
花倮,他們有自己的語言、服飾、節日,又能歌善舞。婦女同胞頭飾高高聳起幾多花球,身穿艷麗服飾,腰后還有一個紅佩帶,至今仍然沿襲著千年前的彝族傳統文化習俗,有著古樸而獨特的民族風情,讓外來的人驚嘆不已。
深冬,天有些干冷,車子從雞街的低熱河谷,順著山間的盤山公路,一直盤旋而上,翻過一座座高山,位于高山之巔的曼竜村便呈現在了眼前。
一排排新房錯落有致、熠熠生輝,一條條村道平坦開闊,暢通山鄉,種植業、養殖業等特色產業發展如火如荼。
曼竜村四面環山,海拔高、氣溫低,受自然環境和區位條件的制約,長期以來,生活在高山頭上的曼竜村村民延續著靠天吃飯的生活方式。田地里種的是苞谷、紅薯等傳統作物。春天播下種子,如果遇上風調雨順的年份,能有一定的收成,若是年份不好的時候,秋天收獲的那點糧食養家糊口都難。
貧困和苦難在這里根深蒂固。到處是破爛不堪的土坯墻和著幾間搖搖欲墜的茅草屋,殘瓦斷墻,衣衫襤褸,一群無所事事的村民懶散地坐在村頭,目光呆滯、眼神空洞地望著腳下方圓幾里破敗蕭索的村莊。當記者舉起相機,年輕的婦女們怯生生地連忙躲開鏡頭,“嗖”地從地上爬起,向各家殘破的房門跑去……
偏居深山,山高路遠,近乎與世隔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居住在高山上的花倮同胞在惡劣的生存環境里艱難度日。土地少、耕種條件差、產業單一、生產方式落后;茅草房、人畜混居、出行難、信息閉塞;孩子聽不懂漢語、村民發展意識淡薄、不良的生活習慣……這些成了曼竜村彝族花倮同胞貧困交加的根源。
近年來,在國家各項政策的扶持下,在全縣各級黨員干部和全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家家有了新住房,戶戶通了自來水,村內道路寬敞,產業發展興旺,2018年底,在全縣全面實現脫貧摘帽之際,曼竜村沒有一戶人家拖了后腿的。2019年底,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9000多元,2020年,曼竜村的100多戶人家和全國人民一道同步邁入小康社會。
在一旁的老主任王志昌突然插了一句話,這一切得感謝黨的好政策啊,近些年來,隨著國家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政策的持續開展,村里的村容村貌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也讓我們這個藏在大山頭上的彝家兒女過上了幸福生活和看到了新的希望。
說到底,農民要致富,發展產業才是關鍵。一個村子要找準一種適合自己發展的產業也并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曼竜村在探索產業發展的道路上,也是幾經探索,幾經波折。
1996年,曼竜村發展過烤煙,但因村民不掌握烘烤技術導致烤煙一爐爐烤壞;種過花椒,但種出的花椒只長株不掛果,也宣告失敗;種植核桃,因水土不服,不見效益;發展甘蔗種植,雖然長勢茂盛,但糖分含量低,糖廠拒收,加之又遭受霜凍危害,村民對于發展產業的積極性遭受打擊。
直到2013年,縣委政府推廣種植甘蔗,還有政府補貼,雞街鄉黨委政府通過認真研究,仔細了解甘蔗種植需要的土壤氣候等條件,發現甘蔗種植特別適合曼竜村,決定引導群眾大力發展甘蔗種植作為曼竜村的支柱產業。
但因為曾經發展產業幾經失敗之后,大部分群眾的積極性都不高,面對村民發展產業消極不配合的心態,鄉政府工作人員動員村干部、黨員帶頭做示范。
說干就干,王志昌認種8畝、趙顯亮6畝、趙顯友6畝……2016年,18戶黨員干部共種下80多畝甘蔗。由于品種改良、管理到位,畝產達到7.4噸,當年每噸收購價430元,畝產值3182元。之后的幾年,群眾看著大家種植甘蔗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益,大批群眾栽種甘蔗的激情被點燃了,相繼加入到了甘蔗種植行列。
截至2022年,曼竜村小組種植甘蔗的農戶已經達到85戶,種植總面積達到1160畝。2023年又新增種植146畝,總種植面積達到1300多畝,甘蔗產量近6960噸,年產值達313.2萬元。曼竜村通過發展產業獲得了持續的發展動力,村民的腰包漸漸鼓起來了,日子也好起來了。
我們聽著老主任講述著曼竜村的變化與發展,他無疑是那一代人一步一步走來慢慢擺脫貧困,并走上致富路的一個縮影。現如今,像老村長一樣思路變了,走上致富奔小康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些年來,老主任一生踏踏實實的苦干,公平公正地為同胞服務,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帶領鄉親們有一天能走上一條致富的路子,能過上好日子。眼看自己年歲越來越大,眼下最急切的是要有新的年輕人來接過他手中的這根接力棒,繼續為曼竜村的未來發展出力!
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雞街鄉海子村監委主任王有金,從小感受著曼竜村的落后和父輩同胞們生活的艱辛和不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要一邊上學,一邊幫著家里的父母干農活,奈何日子依舊過得緊巴巴。與父輩不一樣的是,他想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看一看。
2006年,在外打拼幾年的王有金,積攢下了一些經驗和存錢,當得知西疇縣通達公司有一批為農村群眾服務的趕街車時,他便有了要回到曼竜的想法,買農村客運班車,為當地群眾服務,但由于種種原因,他的這一愿望直到2012年才得以實現。
通過朋友介紹,王有金以高價從別人那里轉手到了一輛破舊的二手中班車,專門跑縣內的鄉鎮線路,運送各地農村的群眾上街來回往返。兩年后,他又拿出自己在外多年積攢的積蓄和家人的支持,自費換了一輛嶄新的東風超龍客車,但好景不長,隨著市場經濟和運輸業的變化發展,私家車越來越多,逐漸地,農村客運班車市場遇冷并被慢慢取代,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王有金不得不把剛買回來不久的新車低價虧本轉讓了出去。
車賣后,王有金和媳婦商議著在家幫著兩位老人把家里當季的莊稼栽種后,就外出打工。
“有金,你是什么學歷?”2017年5月的一天,王有金接到海子村委會支部書記打來的電話。
“我職高畢業,學習的是汽修專業……”
“現在村委會有一個崗位空著,也就是還差一個人。工資不高,每個月1500元,這個跟你在外面打工的收入倒是無法比,不過工作量不大,每個月上十五天班就可以了,你愿意來嗎?”
初夏夜晚的農村格外寧靜透明,晚風吹拂著整個山谷,激蕩起樹枝搖曳發出的“唰唰唰”聲。窗外,蛙聲蟲鳴陣陣,此起彼伏,躺在床上的王有金輾轉反側,難以入睡。
“是外出打工?還是選擇留下來?”白天村支書的那通電話,深深印刻在了王有金的腦海,久久揮之不去。這也讓他想到了很多過往與村里有關的事情。
王有金想到了自己2012年6月4日入黨宣誓時的情景,雞街鄉政府的大院里,在鄉黨委領導的帶領下,他右手握緊拳頭半舉起來,跟著領誓的領導開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就是這短短的幾句話,讓他內心充滿了興奮與自豪,同時也使他深刻認識到,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身上肩負著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還有一件事情,讓年輕的王有金記憶尤為深刻,這也是觸動著他選擇留下來的原因之一。
2014年開始,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的勁風吹遍了村村寨寨,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深入推進,各地村莊的面貌也在發生著驚人的欣喜變化,但王有金卻發現,緊鄰曼竜村的其他村寨都在忙著翻蓋新房,而曼竜村納入建檔立卡戶人家的房子卻沒有動靜。后來,一經了解后才得知,其他村子的檔卡戶都是先到銀行借貸款建房,建好后有3萬塊的國家補助。而曼竜村的村民在到銀行借款時,卻遇到了大麻煩,銀行的工作人員聽不懂村里人說的話語,村里的群眾也無法表達他們要做的事情,三番五次、幾經折騰下來后也沒見到效果。
王有金整夜都沒合眼,但心里卻已經有了答案。
“留下來!”的聲音在這個寧靜的夜晚顯得清晰透亮,發出宏亮而悠遠的聲音。
是的,他要選擇了留下來。他的心被深深刺痛著,他不能在眼睜睜的看著村里的同胞這樣落后下去,村莊再繼續破敗下去。
一個月后,當王有金再次接到村委會領導打來的電話時,他爽快地答應了。
從建檔立卡戶情況核實到危房拆除重建,從收入核算到產業推導,從基礎設施建設到綠美鄉村行……王有金總是一件一件工作細致落實,一項一項政策做好宣傳。如今的王有金早已成為曼竜村與外界連接的橋梁和紐帶。
基層的工作,千頭萬緒而又繁雜。當初說的一個月只上15天的班早已時過境遷,周末加班加點早已成為常態,沒有多余的時間顧及家中勞作,但王有金至始至終都沒有打過退堂鼓。
采訪中,王有金這樣打了一個比方:如果只從個人利益出發,留在村委會肯定是不劃算的,而自己選擇留在家鄉,哪怕經濟會不寬余,比起周邊的群眾也會落后些。但是,留在村里,村子終究會一天天、一點點發生變化。哪怕自己一人只有1千元錢,但是自己在里面帶動,其他家能有1萬元,那么村里的100多戶人家,就將會有100多萬元,這就值得!
村莊的一旁,一派熱鬧景象。
這是曼竜村嶄新的學校,教學樓的正前方,鮮艷的五星紅旗正高高飄揚,一群穿著色彩鮮艷的少數民族服裝的孩子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在操場上歡快地做著課間操。
在這里,我們見到了學校負責人——宗富春。
宗富春是這個大山間走出來的孩子,也是該村少有的文化人,她的談吐和舉止溫和而熱情。
她和村子里的許多同齡人一樣,當年差點中途輟學。但是在父親一再的教育和引導下,省吃儉用,節衣縮食,千方百計,供她上學。
2010年,大學畢業的她本來可以留在城市工作,但是她認為,自己是從這里走出去的,更應該走回來,當年目睹了村子貧窮受苦的狀況,目睹了父老鄉親因為沒有文化的思想困境,也親眼目睹了自己同齡小伙伴中途輟學外出務工的情境,而如今的曼竜村,有了更多的孩子在上學,他們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和她一樣走出去,更需要有人去從事文化教育。她毅然回到了故鄉的懷抱,來到曼竜小學當起了一名傳播知識文化的老師。
她告訴我們說:現在學校開啟了“雙語”教學的模式,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彝族和苗族學生都能聽懂漢話,漢族學生也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少數民族語言。宗富春也成為花倮民族文化傳承人。
她還告訴我們,曼竜民族希望小學,現有學生有253名,已全面普及到了小學六年級,近兩年來還辦起了幼兒園,全村的適齡兒童全部上學,我們的教學質量,也在逐年提升。
她介紹村里及學校的情況,如數家珍。
我們為她而高興,為曼竜的未來而欣慰。
學校的秩序井井有條,曼竜的新一代,在這里茁壯成長著……
“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阻斷貧困代際,讓更多彝家孩子受益,他們將是改變這里的希望種子。”宗富春說。
她明白,教育才是脫貧致富的根本。教育跟不上,就想不到那么多,看不了那么遠,觀念陳舊,甚至封閉。
山區的條件是艱苦的,但是宗富春卻一直堅守留了下來,哪怕曾經有過多次能調到縣城工作的機會,她毅然堅決放棄了,她要把根深深扎在這片土地,守望著大山深處的孩子們。
學校的另一側是曼竜村彝族花倮“葫蘆笙舞”傳習館和傳承基地。
一個民族存在的根基和靈魂是文化,同時文化也是民族發展凝聚力的核心因素和活力源泉,少數民族文化以其獨特迷人的風采以及鮮明的特征成為中華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據史料記載:曼竜村花倮人源于西北高原南下的游牧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花倮人創造出了屬于自己的濃郁獨特的民族風俗和民族文化,他們熱愛歌舞,他們最崇拜的“神物”是蕎和魚。
蕎菜節,每年農歷四月初四或十四屬兔之日,被定為彝族花倮的重要節日。曼竜村花倮人的蕎菜節,是花倮人大展文化風情的日子。
這一天,他們殺豬宰雞,祭獻祖宗和神靈;這一天,他們熱情洋溢,有遠方的客人來歡聚一堂;這一天,他們身著盛裝,通宵達旦跳弦子舞或葫蘆笙舞,青年男女借此談情說愛。韻律悠揚的葫蘆笙吹起來,姿態優美的葫蘆笙舞跳起來,多姿多彩的舞裙擺起來,這一天熱鬧非凡,這也預示著彝家兒女日子富裕起來的歡快與灑脫,從容與自信。
1987年10月,原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女士來到西疇考察民間舞蹈時,稱曼竜村的葫蘆笙舞是“中國式的迪斯科”,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價值。
2006年5月,曼竜村的“葫蘆笙舞”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08年1月,代表性傳承人宗天珍被命名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代表性傳承人。
同時,為了讓彝族花倮葫蘆笙舞得以傳承和發展,西疇縣委政府和雞街鄉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為了讓彝族花倮葫蘆笙舞得以傳承和發展,在曼竜民族小學開展了彝族民間傳統文化進校園活動,由該校的彝族教師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傳授彝族民間音樂、繪畫、舞蹈、體育、文學、傳統手工藝等內容,使小學生能夠從小受到彝族優秀傳統文化熏陶,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傳統文化知識和技能,培養青少年從小熱愛本民族文化。同時,成立了曼竜彝族花倮葫蘆笙舞蹈隊,利用彝族花倮的“蕎菜節”等節日,組織民族民間文藝展演,并組織隊伍到縣內外及州外交流學習,展示民族歌舞技藝、服飾,促進文化交流與宣傳,提高群眾參與曼竜彝族花倮葫蘆笙舞保護的意識。
今年已有78歲的宗天珍老人,依然承擔著花倮文化傳承的重任,每到花倮人的節日或農閑之時,宗天珍就會組織村里的“文藝骨干”匯聚在傳習館,教授花倮孩子學習葫蘆笙舞、弦子舞和吹奏、彈奏民族樂器,以讓寶貴的花倮傳統文化傳承和發揚下去。
在曼竜村我們還欣喜地看到,像王有金、宗富春這樣年輕一輩的年輕人,他們有文化、有學識、有情懷、有擔當,他們將接過老一輩的接力棒,繼續帶領曼竜村的群眾在新的征程上向前邁步。
采訪中,我還發現,新一代的村干部也在思考,如何在下一步的鄉村振興戰略中,把民族文化與旅游結合起來,打造鄉村游。把自己民族的文化繼續傳承和發揚光大,因地制宜把產業發展好,助力農民繼續增收致富。
新一代年輕人的想法,信念如山,深情似水。我們看到了新一代年輕人對家鄉發展的熱情、期望與奉獻,我們更看到了曼竜村未來的發展情景和希望。
漫步在如今的曼竜村,村內道路縱橫交錯、住房生活環境條件極大改善、甘蔗主導產業規模化發展,呈現出的是一片欣欣向榮、和諧發展的美好景象。
昔日貧窮落后的彝族花倮人民,正在帶著希望和夢想,開啟幸福的新生活。
離開曼竜村,我們似乎聽到了曼竜村葫蘆笙響起,悠揚動聽的聲音,由遠及近,回旋在這個明媚村莊的上空,縈繞在我們的耳畔……
在未來,我們堅信這個崇尚歌舞像火一樣民族,在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上,一定能創造出新的更大奇跡,迸發出新的更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