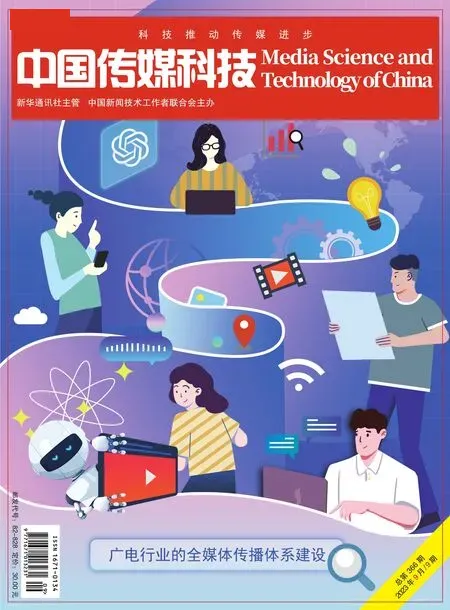媒介技術變遷視角下的教材概念演變研究
陳明朗
(沈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在一定的政治、歷史、文化的語境下,某一詞語由于使用的頻率不斷增加而具有了專有的意思和指向性的功能,這些意思和功能促使它逐漸地固定下來,最終成為概念并被大家所認可和接受。這也就意味著概念存在積聚性意義,充當著社會交往所需要的媒介,構成社會活動與交往所需要的基礎。而概念史研究的關鍵是,挖掘不同歷史時期,概念的內涵是怎樣變化的,占據主導地位的概念是怎樣形成的,以及在怎樣的社會政治條件下被定義和概念化的。[1]
最開始創造性研究概念史的學者,更傾向于用語義學代替詞匯學來研究出現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概念的意義,不再將詞匯的演變過程作為主要的研究內容,同時還關注概念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的聯系。這一研究直接導致了認識論上的重要轉變:首先是詞匯不再等同于概念,一個概念可能對應多個語詞,概念的演變過程可能伴隨著語詞的轉變,但不是一定的。概念更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個概念從最初的飽受質疑到最終被大眾所接受這一過程,不僅是歷史不斷演變的結果,還是概念間互相博弈的結果。不同概念之間是充滿競爭的,原因是不同概念的背后是不同的學者、學派針對某一詞匯或相似詞匯界定著不同的概念內涵,因此不同的概念內涵往往代表著不同學者或學派的意圖,這也就導致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變化并相互競爭,但卻沒有一個占據主導性地位的概念出現。因而出現概念界定不清,概念時空邊界模糊的現象。[2]教材這一事物的存在史可以橫跨古代至今,從四書五經到當今的數字教材,其傳播媒介在不斷變化,不同的傳播媒介對應不同時期特定的教材。
因此,有必要從媒介技術變遷史的視角出發,將媒介變遷過程與教材概念演變過程相對應,特別是在當前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于教育領域并給教育領域帶來深刻變革的背景下,通過媒介技術的演變過程理解教材概念的演變過程,一方面可以將當今的教材概念重新放回到它產生的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時空范圍內,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和理解現存的紛繁復雜的教材概念,對現有教材概念的進一步厘清提供幫助;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更好地重新定義教材概念提供一些啟示。
借助哈特對媒介所做的分類,可將教材在歷史過程中的存在狀態分為三種:(1)以“示現媒介”傳播的“示現”型教材。“示現媒介”傳播信息,重在面對面的直接展示與交流。(2)以“再現媒介”傳播的“再現”型教材形態,所謂“再現”型教材,指那些把“示現”性知識轉換成“符號代碼”,用“再現媒介”傳播出來的教材。(3)以機械/電子為傳播媒介的教材形態。機械/電子媒介是互聯網產生后才出現的信息傳播新方式。借助機械/電子傳播媒介傳播知識,應該是為適應現代傳播手段而作出的積極選擇。以機械/電子為傳播媒介的教材,與“示現型”“再現型”教材有根本性的不同,這一形態的教材,必須借助于機械/電子設備,通過無線電波和網絡去發布,使用者也必須使用網絡設備才能使用。[3]
1.言傳身教與“教材”的樸素認識
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教育形式是在日常的生活、生產勞動中將如何制作并使用生產工具、生產經驗以及生存經驗教授給下一代。他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人們需要生存,生存下去就需要生活資料,獲得生活資料就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必須把生產勞動的知識和技能一代代傳下去,進而這些知識和技能就構成了當時的教育內容。在之后的時期,農業逐漸發展起來,使得農業知識和與農業發展有關的天文歷法知識逐漸增多,這些積累的知識與技術經過世代相傳而流傳下來,進一步擴展了原始社會時期的教育內容,形成了遠古時期的教育內容。但在這一時期,并沒有相關文字記載這些知識和技能,教授的方式是言傳身教,主要是在勞動實踐的過程中進行現場的教授和學習。[4]在這一時期,文字都沒有誕生,“教材”兩字、“教材”概念更是無從談起,所以我們不能將近現代對教材概念內涵的判斷不加思考地套用在尚未形成教材概念的史前時代。但不可否認這一時期的確存在知識的傳授,并且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一代代傳下去。所以當從媒介技術的維度來理解原始時期的知識的傳授時,可以將這一時期的“教材”概括為“示現型教材”,這樣有利于與近現代教材概念形成歷史與時空邊界,進而推動近現代“教材”概念內涵和外延的進一步統一。
2.物質載體的出現與紙質教材的形成
2.1 文字和物質載體的出現
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文字出現了。文字的出現打破了教材的時空限制,它可以通過不同的物質載體呈現出來并進行信息的傳遞。然而,文字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并經過了多種演變形式,只有經過特殊訓練才能掌握。文字的載體也并非一成不變的,不同地區在不同時期甚至是相同時期的文字載體都是不同的,如古印度的貝葉棕,古希臘的羊皮紙,中國的龜甲獸骨、巖石、青銅器、簡牘、絹帛與植物纖維紙,古埃及的莎草紙,兩河流域的泥板等都曾作為特定時期和地區文字的載體,這可以表明早期的文字物質載體是昂貴或者笨重的。[6]可見,不論是文字還是文字的早期物質載體都決定了早期掌握文字和物質載體的只有少數部落,也就決定了早期受教育50 的也只有少數。這一現象不僅僅出現在原始社會,直到古代仍然存在。中國表現在“學在官府”,并且這一時期的教材主要是經書典籍,例如:《五經》《四書》、漢代的經書;晉南北朝的《老》 《莊》、唐初孔穎達編訂的《五經正義》、宋代朱熹的《四書集注》等。[6]當然還有自然科學類教材,例如西周的《周髀算經》是最早的數學教材,唐代則專設有“算學”,是我國最早的數學專業,其教材為《算經十書》《記遺》《三等數》等,其中《算經十書》是自隋至清學校的主要數學教材。[7]西方同樣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教材范圍為七藝,中世紀時期《圣經》成為主要教材,再到文藝復興時期以古希臘、古羅馬的著作代替圣經作為教材。可見,這時的教材同樣決定了只有少數人受教育,因為教材中的文字只有少數人習得。西方的拉丁文是這一時期的教材主要用語,與人們日常用語截然不同。這也表明了教材的主要目的不是教育,而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教材已經初步形成,并且教材概念可以概括為典籍與當時著名學者的著作。
2.2 紙質教材的形成
紙張和活字印刷術的出現以及新興階級的產生打破了知識的壟斷。紙張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新的媒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不僅可以讓文字突破時空的限制,也讓普及教育成為可能。教科書的出現豐富了教材概念,并且從教材到現代意義上的教科書經歷了兩次轉變。其一是從教材到新式教科書。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新式教育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式教育的主體是新式學堂,而新式學堂的核心是新式教科書。其二是新式教科書到現代教科書。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學制的確立為現代教科書的產生的前提條件,新式學堂數量的增加為現代教科書的編寫提供必要條件,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的成立是現代教科書產生的決定力量。現代教科書正是在這些條件的共同促進下從新式教科書轉變而來的。
但要明確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教材不是教科書。這里需強調一下,教材與教科書的關系是,教科書是教材的一種,教材不完全等同于教科書,也就是說教材包含教科書。現在所說的教科書應該是根據學制、學年、學期、學科而分級、分冊、分科編寫的,并且需要有與教科書相配套的教學參考書用以對教師的教學提出具體的建議。依照這個標準,可以說不論是以前的“三百千千”,抑或是“四書五經”都不算教科書,它們僅僅是特定時期的教材而已。原因有三點,一是它們是不分年級的,學這些書目的人的年齡跨度很大;二是不分課時的,沒有固定的課時來教授這些書目,教學進度主要依據教師教學的進度;三是不分科的,教學內容僅僅是這些書目里的內容,沒有豐富的教學內容需要去分科而學。[8]也就是說,從教材到教科書的轉變,不是教科書替代教材,而是教科書作為教材中的“主教材”而存在,除此之外的教材均屬“副教材”。[9]這一時期的紙質媒介作為一種新的媒介技術,打破了只有少數人受教育時期存在的知識壟斷現象,讓人們的生活邁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知識平權時期。然而,在一定時期內由于技術特性和資本政治決定了印刷媒介被少數人獨有、使用[10],所以,基于印刷媒介和超越時空限制的文字而制成的教材并不意味著知識平權。相比于“示現”型教材,存在于物質載體中依賴“再現媒介”傳播的“再現”型教材打破了時空的限制、階級劃分以及地理壁壘,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受教育者的同時拓寬了受教育面。隨著普及教育的發展,知識平權至少在義務教育階段得到了一定的實現。
3.網絡社會的崛起與數字教材的產生
1960—1980 年之間,阿帕網的出現表明計算機技術經歷了一次巨大的改良,因為阿帕網使得一開始被看作孤立存在的計算機轉變成一種可以跨地域跨時空而相互關聯的通信設備。如果說在物質作為字體符號載體而存在的時代,傳統教材以紙質作為媒介載體有很多弊端,如文本是靜態的、承載的知識是有限的、傳播起來耗時耗力并且不易保存。那么隨著信息技術與網絡的發展,教材正以其他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數字教材的概念逐漸進入大眾視野,數字教材結合智能終端設備、App 學習軟件及在線教育平臺等的使用,已經催生出一套現代化的學習體系,衍生出一種全新的教育生態環境。通過大數據、云服務及云計算等信息技術衍生的數字教材將傳統教材、信息技術、軟件開發融為一體,構建出具有學習資源開放化、學習方式個性化、學習工具智能化、學習評估精準化等特征的數字教材,實現了科技與教學的完美融合。[11]數字教材相比于紙質教材有了許多優勢。首先,數字教材促進了教學方式的轉變。在數字化時代,紙質媒介的傳播知識的方式已經逐漸淡化,因為伴隨著紙質教材的往往是缺少生機的文字,學習者更傾向于無紙化學習,如超鏈接等。[12]這樣可以使學生的參與感增強,促進學生主體性的提升,轉變傳統以教師作為主導者的教學方式。其次,數字教材促進了教學目標的實現。數字教材可以根據不同的教學目標的設計出不同的媒體呈現方式,進而能夠使教學目標得以更高效地達成。對于教授知識類這種需要不斷記憶的內容,可以采用圖文的呈現方式;對于需要學生理解的內容,可以以演示視頻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以此類比,對于教授需要學生學會運用所學知識來分析并解決具體實踐問題,可以呈現一個編程實訓練習或者一個案例分析試題。可見,數字教材在促進教育教學發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3]最后,數字教材保證了課程目標的達成。數字教材能夠基于平臺給予的支撐,可以更好地呈現教學內容,更好地設計教學活動及更好地覆蓋教學環節,并將教學活動、教學內容及教學環節更好的融合,保障了課程目標的有效達成。[14]
但不可否認的是,從紙質教材到數字教材的轉變存在障礙。首先是數字化研發主體自身存在短板,數字教材的開發需要全面發展的人才,不僅僅需要互聯網技術方面相關的知識,還需要教育學相關知識。但往往研發數字教材的企業出于盈利的考慮,缺少對教育領域所需要的數字教材的深入解析,致使研發出來的數字教材不符合教育的實際需要。其次是數字化信息傳遞方式跳躍,數字教材的優點之一是突破了以往傳統教材內容以線性進行排列的局限,讓學生超越教材呈現的線性知識,但這樣也使得非連續的知識出現在教材中,導致了學生的邏輯思考變得非理性化。[15]最后是數字化教學資源建設標準滯后。數字教材是互聯網時代催生出的新產物,建設標準還未建成,也沒有一個典型的規范的數字教材作為參考,意味著需要用紙質教材的建設標準來建設數字教材,但兩者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可以預見數字教材建設的規范性不會太理想。[16]盡管如此數字教材還是轉變了以往紙質教材的特征,如紙質教材是一個點對一個面的、是單向傳播的。可見數字教材豐富了現存的教材樣態,這也意味著數字教材的存在對教材概念的界定產生了影響。從學科邊界模糊,學段邊界模糊、教師和學生的邊界模糊三個方面挑戰了教材概念的邊界。這些使得原本就含糊不清的教材概念變得更加難以界定,由于缺少概念系統使得各類教材無法得到歸類和理解。因此,伴隨著數字教材的產生,首先要做的是明確界定數字教材的概念,明確其與紙質教材的區別與聯系,在此基礎上重新界定教材的概念。
已有研究從不同的視角界定數字教材的概念。首先在教育視角下,數字教材的本質仍然是“教學文本”,但是其教學內容已經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并且具有與紙質教材不同的特征,如內容更豐富、交互性更強、能夠突破時空限制。其次在出版視角下,分為廣義的數字教材概念和狹義的數字教材概念,廣義的數字教材是一個組合系統,具有特定的目的,系統的內容、教/學工具與設備;狹義的數字教材就是具有數字形態的教科書。廣義的數字教材概念與狹義的數字教材概念之間的關系與廣義的教材概念與狹義的教材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還需要明確,數字教材與紙質教材之間的關系,數字教材并不是電子版的紙質教材,其有自身不同于紙質教材的特征,是當今數字化時代對紙質教材建設進行升級而得到的產物。我國現在的數字教材還無法替代紙質教材,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將紙質教材與數字教材配套使用,互為補充。另外,數字教材和紙質教材在本質上都是教材,進而它們的基本特征都應該是教材所具有的。因此,數字教材的內涵不應該過分泛化,在把握其內涵時要明確這一點。[18]可見數字教材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明晰,并且明確了數字教材與紙質教材的區別,這對于教材的重新界定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不同于媒介相同時期對教材概念的探討或分歧往往發生在持有不同教材理念的不同學者或組織之間,有學者認為教材與“教學材料同義”;有學者認為教材是指學科知識體系;還有學者認為教材是指學科課程內容。[19]基于互聯網產生的數字教材對現存的教材概念的分歧主要是因為媒介的轉變對現存的教材概念產生的具有顛覆性的變革,這也迫使教材概念必須進行重建。將對教材概念的關注點進一步擴展,從只關注紙質教材擴展到同時關注紙質教材和數字教材,并明確紙質教材和數字教材的區別。
回溯教材概念演變的過程可以發現,古代的教材也就是經典著作使得人類的教育活動得以發生,紙質教材的出現使得人類的教育活動得以普及,數字教材的出現使得人類的教育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伴隨著互聯網的崛起,數字教材將以自己的獨特方式重建著互聯網下的教材。將媒介技術變遷史作為考察教材概念演變的新視角,將增進對教材概念的進一步認識,并為網絡時代如何重新定義教材概念提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