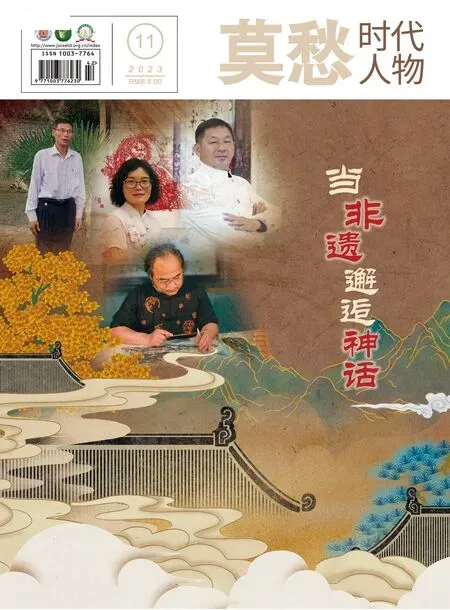吳文化的靈魂和本質
文/吳躍農
吳文化區域一直發揮著江蘇的文化中心作用。江南水鄉,詩意靈動,山溫水軟,鳥語花香,映現著吳文化區域山清水秀、地綠天藍的水韻之美。
水是吳文化的靈魂
水是吳文化的靈魂,充沛的水源即是吳文化的命脈,吳國盛衰可以說是與水和水源水運共命運的。吳文化核心地蘇州控三江、跨五湖、通長江、臨大海,交通便捷,北宋著名水利學家郟亶說,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無過于蘇州。吳文化筑基于精于“水利”、以“水利”筑城立國,治水患、開運河、建水軍攻楚伐齊,興農田水利取得糧食豐收,“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地理交通,加上造船技術先進,大力發展水上交通等事業,從而帶動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
秦漢以來,吳地就是進出口岸,是海外來吳的登陸點,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西方文化的輸入,也是因水網交錯之便。而長江的特殊防衛功能,使吳地可據守而生活安定,這對吳文化創造奇跡具有重要意義。大海、長江、運河、太湖可以說是吳文化生生不息的天然淵源。
蘇州城內河道縱橫,湖蕩星羅棋布,被稱為水都、水城、水鄉。13 世紀的《馬可·波羅游記》將蘇州贊譽為東方威尼斯,蘇州古城被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稱贊為“鬼斧神工”。“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河流湖泊縱橫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地區。山水富饒,特產豐盈,有“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吳文化因水而成就自己獨特的歷史經濟地位。
約一萬年前,太湖三山島上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巨大的獅面人身石雕像至今還在。從古文字解析來看,“吳”本身就是指水生魚類動物,“吳”天生是與水相關聯的。吳地之水是包容天下之水,內連河湖,外接江海,是通山外之山、聯水外之水的。吳文化得水之天時地利,因水而生,依水而成,順水而長。
伍子胥治水建城,蘇州城因水而興。蘇州城有世上規模最大、時間最早的城市治水體系。蘇州古城的建立,表明吳國的生產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已相當高。蘇州作為國內和世界上現存最為古老的城市之一,地域水面占42%,我國第三大淡水湖太湖,三分之二在蘇州轄區內;我國最長的河流長江,從北面呈半弧形拱圍蘇州,東奔大海;我國最長的運河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綰結了蘇州古城,南接錢塘江。長江、太湖和京杭運河豐沛而清澈的水哺養了蘇州,為蘇州城市建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間。唐人杜荀鶴的《送人游吳》詩云:“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水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

獨特的歷史文化遺存
“水在城中,城在水里”“水陸并行,河街相臨”的蘇州創造了數不清的歷史文化遺存,有著獨特的風土人情。從遠古的“荊蠻之邦”到人文薈萃的“人間天堂”,水是吳文化區域民眾不可缺少的物質與精神元素,深刻影響了民眾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形態,造就了區域的經濟發展特色,培育了民眾溫良、平和、達觀、儒雅的外柔內韌性格,由此創造了極富人文特色和水鄉情誼的絲綢藝術。
得益于水的滋潤,蘇州成為舉世聞名的錦繡江南水鄉,呈現柔美詩意詩情,讓世人皆知蘇州古城好、蘇州水鄉美,使人對夢里水鄉產生魂牽夢縈、揮之不去的絲絲縷縷牽念記掛。這樣的人文地理及文明推進,自古就是商船云集、商埠繁榮。
吳文化從本質上說屬于工商文化,是蘇商文化,吳文化精神與蘇商文化精神一致。吳文化與蘇商發展是血乳臍帶關系。蘇州煙波浩渺,太湖中的東、西洞庭山崛起了洞庭商幫,以洞庭商幫為代表的蘇商有著輝煌的歷史、燦爛的現在和光明的未來。
自隋唐全國經濟中心南移后,加上多次人口遷徙南入,以蘇州為核心的吳文化區域成為全國無可爭議的經濟發動機,同時也是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蘇州自古至今一直是全國冠名或不冠名的“一線城市”,也是歷代王朝重要的錢糧寶庫。南宋開始流行諺語“天上天堂,地上蘇杭”,后來演變成家喻戶曉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蘇商趨于活躍,漸漸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力量,他們在明清崛起,成為全國棉布加工業和絲織業的中心,有“蘇布名重四方”之譽,最盛時,從事棉布紡織加工布莊多達76 家。蘇州城東的居民,家家從事絲綢織作,號稱“郡城之東,皆習機業”,乾隆年間“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在此基礎上,蘇州城鎮人口集聚,商業日趨繁榮,為“東南一大都會,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上自帝京,遠連交廣,以及海外諸洋,梯行畢至”。蘇州及吳文化區域的實業和海內外商貿代表了國內最高水平,吳文化區域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地區。
吳文化的本質是工商文化
吳文化孕育了吳地“工商皆本”的務實重商思想。蘇州是絲綢之鄉,資本主義萌芽首先通過絲織業表現出來。明代中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部分人上升為手工作坊主,而大部分人則淪為自由勞動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雇傭勞動關系。清朝乾、嘉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得到進一步發展,不僅行業增多,包括了絲織、棉布加工(踹染布)、造紙、印刷等,而且地區分布更為廣泛,據雍正年間的《奉各憲永禁機匠叫歇碑記》云:“蘇州機戶,類多雇人機織,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雇傭勞動關系已經蔚然成風。明清兩代,吳地進入極盛時期,不但農業生產發達,而且手工業、商業也極為興盛,冶金、棉織、蘇繡、緙絲、制扇、裱畫、印刷、雕刻、建筑、陶瓷等行業技藝水平在全國領先,蘇州成為全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國內外貿易居全國首位。
吳文化催生了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祥。洞庭商幫得風氣之先,適時應變,包容融通,全面進入上海金融業,蘇南區域成為近代中國出國留學、舉辦洋務、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和傳播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主要基地。由此,在蘇、錫、常和南通以及周邊浙、滬地區,率先開展近代工業化,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祥地、崛起地。
20 世紀60 年代,吳地積極從事工商業,通過社辦工業和鄉鎮企業,推動商品經濟面向全國開放發展。改革開放初期,吳地人率先投入市場建設,經商的足跡遍于全國,并為吳文化抒寫了“四千四萬”精神——“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遍千辛萬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拓奮進,傳承和發展著工商文化精神。
正是因為堅持務實重商,吳文化具有強盛生命力。吳文化推動蘇南邁開踏實、堅實的發展步伐,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更是激發了蘇南、江蘇以及長三角地區的創新與發展。
如今,吳文化成為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力量之一,使蘇南及長三角地區成為全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由此,以吳地為經濟中心的江蘇確實發揮了“鐘靈毓秀、人文薈萃”之地對全國的文化影響力、經濟推進力。
應該看到,吳文化核心地和中心區域,工商文化、蘇商文化長期處于較明顯的文化主導地位,務實重商、“趨利”追求個人和社會發展,以及義利兼顧的社會文化集體心理,形成吳文化的唯實精神和穩健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