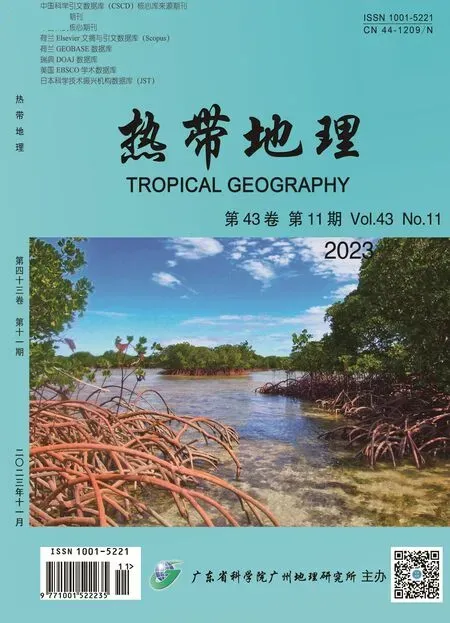回溯與反思:旅游記憶建構對自我概念擴展的影響
羅 強,白 凱,董寶玲,李貝貝
(1. 陜西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西安 710119;2. 貴州師范大學 國際旅游文化學院,貴陽 550025;3. 新疆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烏魯木齊 830054)
從繁華都市到恬靜鄉村、從“醉”美苗鄉到世界屋脊,從革命圣地到災難遺址……旅游不僅承載著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踏尋與造訪,也寄托著人們對自己珍貴往昔的回憶與追思。每一次短暫的旅游經歷,無論體驗愉悅與否,都已形如抹不去的痕跡鐫刻進旅游者的腦海,不斷勾起他們的重游欲望,也影響未來的旅游決策(Oh et al., 2007)。諸如此類的旅游經歷如同散落在旅游者人生旅程中的記憶碎片,經旅游者識別、篩選和建構,形成對目的地的回憶拼接與認知想象。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越來越多人熱衷于旅游后將經歷以“曬照”“拼圖”并附文案等形式分享給他人,以此回味自己難忘的旅程。研究表明,旅游者通過旅游分享,重塑自己的旅游體驗(Wang et al., 2012),同時也加深對旅游經歷的存儲與刻畫,引發對于自我的追問與反思,通過內省的方式深化并拓展旅游者的自我認知(陳瑩盈 等,2020)。旅游分享過程中,人們主動提取存儲在大腦中的旅游記憶,并基于“記憶腳本”將旅游體驗融入到“講故事”(storytelling)的解釋過程中(Schank,1999),實現對記憶的選擇性重構(Tung et al.,2011a)。Kim 等(2012)認為旅游記憶是特殊的自傳體記憶,其編碼和提取過程受到主體認知和個人態度的影響,能為自我認知的動態發展提供支持(Conway et al., 2000)。旅游分享后,旅游者通過與他人互動,增進社會聯系,促進自我認知的升華。因此,在后旅游體驗階段,旅游分享作為旅游者“記憶外包”的一種形式,為旅游記憶與自我認知、自我發展提供了媒介。
旅游作為個體逃離日常現實生活及尋求自我發展的途徑,其產生的旅游記憶與旅游者自我概念的擴展密切相關(Brewer, 1988)。作為一種特殊的自傳體記憶,旅游記憶具有強化自我認知、引發自我內省、提供對話材料以及促進社會互動的功能(Bluck et al., 2005)。從記憶研究的視角看,過往研究大多按照心理學范式探究記憶的應用性問題,多基于客體層面展開研究,然而,從主體層面出發,探討記憶如何影響個體自我認知的研究較少。從旅游研究深度看,旅游記憶作為在場體驗的存續,其相關理論研究明顯遜色于在場體驗相關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旅游記憶和自我擴展理論為切入點,深入剖析旅游記憶建構與旅游分享及自我概念擴展的關系,解釋其內在機理,以期豐富旅游記憶研究的內容構成,助推體驗經濟背景下旅游目的地有效營銷與科學管理。
1 文獻回顧
1.1 旅游記憶
“記憶”一詞源自心理學,是人們對過去經驗進行回想的一種能力和心智活動(Schacter et al.,1993)。認知心理學有關研究表明,記憶不是簡單地提取人們過去經驗的原始痕跡,而是一個對過去的加工和建構過程(Bartlett, 1932; Braun, 1999)。從理論上講,記憶是由多種結構相互耦合而成的系統,涉及內隱記憶、外顯記憶、語義記憶和情境記憶等多種類型,其中人們對生活經驗和具體事件的有意識存儲屬于記憶系統中的情景記憶(Tulving,1972)。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情景記憶中具有鮮明自我特征和情感色彩的一部分記憶(Conway, 1996)。在旅游情境下生成的旅游記憶屬于自傳體記憶的范疇,有助于個體尋求自我認識和指導決策行為以及促進社會交流(Fivush,2011)。
作為旅游領域的新熱點(Chandralal et al.,2015),旅游記憶研究從旅游體驗研究發展而來,是旅游者在地體驗后對事件與行為的回憶,是被以記憶形式存儲下來的有意義的旅游體驗(Kim et al., 2019),具有主體性與動態建構性。通過有意義的體驗回溯,旅游者加深了對目的地的印象并觸發了對自我的體悟。旅游記憶是旅游體驗的重要結構,更是對在場體驗的升華。通過文獻梳理,研究發現旅游記憶是獨特且重要的,但目前其還尚未被國內旅游研究充分挖掘,國內旅游研究仍大量聚焦于在場體驗階段,而忽視了游后記憶的特殊作用。旅游者回“家”后對旅游經歷的反省是建立在游后記憶之上的,因此,有必要給予旅游記憶研究更深入的理論關切。
國內外旅游記憶研究主要聚焦在旅游記憶概念的提出、影響因素、內容構成與作用機理等方面。旅游記憶(tourism memory) 一詞最早被Larsen(2007)以獨立概念提出,后由Kim(2009)將其發展為“難忘的旅游體驗(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MTEs)”。國內學者關注到旅游記憶的特殊性,將旅游記憶視為MTEs的等價概念,并對其進行概念界定(袁振杰 等,2020)。通過文獻梳理,研究發現旅游記憶包括認知要素(如服務評估、新穎性等)、情感要素(積極與消極情感)、行為要素(參與、計劃)(Kim, 2009)以及時間要素(關鍵時間點)(桑森垚,2016)。具體來說,Kim(2012)提出了旅游記憶的7要素:享樂、新奇、恢復性、意義感、當地文化、涉入感和知識性。Tung等(2011a)認為旅游記憶包含情感、預期、結果和回憶4個維度。此外,也有研究提出旅游記憶涉及環境與文化、個人心理及人際關系三維因素(Coelho et al., 2018);愉悅、知識、意義、放松與地方感五維因素(Lee, 2015)。潘瀾等(2016)則在中國語境下提出旅游記憶的結構包括再現性和生動性。旅游記憶作用機理的研究大多關注記憶的外部效應,如其對旅游者態度(Kim, 2018)、行為意愿(Wirtz et al., 2003)和目的地形象(Sharma et al., 2019)的影響等,而關于旅游記憶對旅游者自身意義的研究目前仍缺乏理論關照,旅游記憶建構研究也尚未成熟。鑒于此,本文擬通過扎根理論提煉出旅游記憶建構的具體維度,并進一步驗證旅游記憶建構各維度對旅游者自我概念擴展的影響。
1.2 自我概念擴展
自我概念(self concept)是指人們思考自己的特定方式,是個體對自我的主觀看法和感受(喬納森·布朗 等,2015)。Tajfel(1982)提出個體自我和社會自我的二元自我劃分,個體自我強調人們通過自身特質來定義自我,一方面,個體能通過所屬的物質實體認識自我,如消費者可以通過其擁有物(如照片和游戲角色等)展示自我的不同方面,以此構建延伸自我(extended self)(Sirgy, 1982;Belk, 2013),另一方面,個體也可以通過其內在精神品質定義自我,如依托個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反映自我的內在精神層面。社會自我則強調自我是通過他人看法和社會地位映射的,強調自我的社會屬性,Belk(1988)認為人們通過消費行為彰顯自我身份,并在與他人的交互中定義自我,反映其他個體或群體對自我概念的影響。
由于自我概念的動態性,個體的自我概念會在流變的人生經歷中發生橫向擴展或縱向深化。個體可以通過生活中特定的人或物或經歷來豐富自我概念,即自我擴展(self expansion)。從概念看,自我擴展是在自我概念中增加新的觀念、身份和資源后體驗到的自我成長感(Aron et al., 2003),包括關系情境的自我擴展和非關系情境的自我擴展。
關系情境中的自我擴展是指個體在某種程度上會將重要他人的資源、觀念及身份納入自我,從而使自我概念獲得拓展延伸(Aron et al., 1998)。非關系情境中的自我擴展是指個體不僅可以通過參與新奇性或挑戰性的活動實現自我擴展,還可以從周圍熟悉的事物(如手機或網絡環境等)中獲得自我擴展(Gordon et al., 2009)。在非慣常環境下,旅游經歷是非關系情境中自我擴展的重要來源(Mattingly et al., 2014)。個體的自我概念會在“生活世界-旅游世界-生活世界”的歷程中發生共時性演變與歷時性建構(黃清燕 等,2017),因此,某種程度上,個體也可以從旅游體驗中獲得自我擴展。
盡管自我擴展研究已關注到非關系型來源對自我概念的影響,但作為旅游體驗階段性要素的旅游記憶能否擴展自我概念,還有待驗證。因此,本文基于Tajfel 的自我概念二元劃分,將旅游者的自我概念擴展分為個體自我擴展和社會自我擴展,以探究旅游記憶建構與自我概念擴展的關系。
1.3 旅游分享行為
隨著社交渠道多元化和生活時間碎片化,人們習慣于游后重溫自己的旅游經歷,并將分享文字、圖片與Vlog等作為個人旅行軌跡、心情或態度的抽象表達。在記憶的視角下,旅游分享帶來個人對旅游地印象和體驗感受等綜合記憶的時空延伸。旅游者通過“曬”和“秀”的方式重溫自己的旅游記憶,以此進行自我敘事,建構自我身份(Ahmad et al., 2016)。尤其當旅游成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方式時,旅游的社交貨幣價值逐漸凸顯,因旅游分享而獲得的社交關注成為旅游者“體面”的重要表現,因此,在社交媒體時代,旅游分享成為大部分旅游者的行為偏好和生活習慣。
研究表明,旅游分享行為受旅游者的身份特征、人格特質、社會文化背景和信息通訊等內外因素的影響(陳瑩盈 等,2020),但具體來說,當旅游者回歸日常生活后,其旅游記憶的重溫與建構是否會引起分享行為的生成尚不明晰。此外,旅游分享會影響潛在旅游者的信息搜索與決策行為(Xiang et al., 2010),也會影響旅游目的地形象,調節分享者的旅游體驗,有助于維系社會關系等(陳瑩盈 等,2020),但旅游分享后是否會導致個體自我概念的擴展,該問題有待驗證與討論。因此,亟待從旅游者自我角度進行反思,對旅游分享行為的主體性影響展開更多理論探討。
2 旅游記憶建構的維度挖掘與模型構建
2.1 基于扎根理論的旅游記憶建構維度挖掘
本文采用建構扎根理論(Constructive Grounded Theory)提取旅游記憶建構的關鍵維度。該方法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視域融合,認為理論是對原始資料進行解釋性分析,不是完全客觀的實際再現(陳向明,1996)。旅游記憶的呈現正是個體基于實際經歷建構的結果。因此,建構扎根理論的解釋思維有助于旅游記憶建構維度的探索分析。
首先,從攜程①https://you.ctrip.com/、去哪兒②https://www.qunar.com/及馬蜂窩③https://www.mafengwo.cn/三大主流平臺采集共計110 篇網絡游記,參考成錦(2019)的處理經驗,根據以下標準篩選有效游記并對其進行預處理:1)為保證游記內容是旅游者的長時記憶,而不是瞬時的體驗記憶,有效游記的撰寫時間應與實際旅游時間存在一定間隔(至少7 天);2)游記內容完整詳實,描述的是獨特且富有情感的旅游經歷,以體現游記的真實性和旅游記憶的生動性;3)為避免因樣本集中而導致分析結果偏差,有效游記樣本需包含不同旅游目的地、不同年齡段和性別的旅游者;4)刪除純攻略類游記和具有廣告性質、過分專業化的游記。最終確定了23 篇游記,共計約19萬字,并將每篇游記單獨編號,其中20篇用于編碼分析,3篇用于理論飽和度檢驗。
然后,借助Nvivo 11.0 軟件對游記文本進行三級編碼。為確保編碼取得較好效果,筆者首先對文本進行獨立編碼,然后再交由2位旅游專業的同行分別進行編碼,經反復討論,修改編碼結果,發現范疇已基本飽和,編碼可以停止。
最終,從103個初始節點中提取出24個開放性編碼的概念,將其歸納為8個副范疇,并參考現有的MTEs 內容結構劃分,將8 個副范疇進一步歸納為3個主范疇,分別對應“認知評價”“互動感知”“情感涉入”。其中,認知評價指旅游者經過在場體驗后,將目的地吸引物信息錄入感官系統,并以一定的思維模式進行理解和評價,其涵蓋旅游經歷的獨特性、文化性、學習感和意義感。互動感知是旅游者對記憶中與他者進行交互的具身性感知,包括主客互動以及游客間互動。情感涉入是旅游者基于認知評價和互動感知而產生的情緒反應,包含愉悅、驚喜、成就感及值得等積極情感,失望或遺憾等消極情感。具體編碼過程如表1所示。

表1 旅游記憶建構的編碼分析結果Table 1 The coding results of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
2.2 假設提出與模型構建
2.2.1 旅游記憶建構對旅游分享行為的影響 旅游記憶一方面涉及目的地屬性等客體因素,另一方面也包含旅游者的情感和態度等主體因素,這些進入個體長期記憶的體驗要素是旅游記憶建構的載體。根據前文可知,個體通過認知評價、互動感知和情感涉入對旅游記憶的主客體內容加以建構,使其成為旅游分享的刺激源。
首先,認知評價是旅游者依托記憶中旅游目的地客觀環境而獲得的認知性體驗,涉及旅游體驗中的“人-物”關系(彭丹,2013)。已有研究表明,旅游者對目的地的認知與態度會影響其后續的行為意向(白凱 等,2010)。根據認知評價理論,旅游者對目的地的評價是其基于具身體驗的信息處理結果,會激發個人特定的情緒反應,進而引發反饋行為(Manthiou et al., 2017)。因此提出假設:
H1a:旅游記憶建構中的認知評價正向影響旅游分享行為
其次,社會互動涉及旅游世界中“人-人”關系的體驗。在旅游過程中,旅游者離不開與他人互動,無論是在主客的分野對視中,抑或是在旅游者間的邂逅相遇中,其互動體驗都影響旅游記憶的生動性和深刻性(Morgan et al., 2009)。相關研究表明,旅游者在這種非慣常環境下感知的人際互動會對旅游體驗產生積極影響,進而會激發旅游者的分享意愿(Richards et al., 2004),由此提出假設:
H1b:旅游記憶建構中的互動感知正向影響旅游分享行為
最后,情感性話語是自傳體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ubin, 2005)。通常來說,旅游記憶中既包括積極情感,也包括消極情感。基于不同情感,旅游者也會產生明顯不同的反饋行為,而不同行為取決于正負情感的相對效力(Jang et al., 2009),當旅游記憶中積極情感占主導時,旅游者更有可能采取接近行為,如口碑推薦;相反,則會產生回避反應(Yalch et al., 2000),如避免重游或負面口碑傳播。由于旅游記憶的建構更強調積極體驗的提取(Kim et al., 2010),旅游者更容易記住美好、積極的旅游體驗(Chandralal et al., 2015),而對消極情感的記憶印象不深,從而更傾向產生正向的反饋行為。因此提出假設:
H1c:旅游記憶建構中的積極情感涉入正向影響旅游分享行為
2.2.2 旅游分享行為對旅游者自我概念擴展的影響 旅游分享不僅是旅游者呈現旅行經歷,以此維持“存在感”和增進社會關系的積極實踐,也是其通過對旅途時光的回憶和感悟完成對自我價值體認的途徑。一方面,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分享行為是旅游者追求社交、尊重及自我實現需要的依據,能提高個人關注度,增強人際聯系(Pinel et al., 2010)。另一方面,根據印象管理理論,旅游者通過分享旅游記憶,塑造自己樂意向觀眾展示的自我形象,并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定義自我,提升自我認同(Lo et al., 2015)。尤其在強關系平臺中,受熟人關系的影響,中國游客更愿意在固定圈子內進行自我呈現,以便通過分享獲得面子資本(陳瑩盈等,2020)。可見旅游分享為旅游者的自我呈現和理想形象塑造搭建了舞臺,使旅游者能通過分享平臺將他人反饋的觀點和獲得的面子資本納入自我,實現個體自我和社會自我的擴展,因此提出假設:
H2a:旅游分享行為正向影響旅游者個體自我擴展
H2b:旅游分享行為正向影響旅游者社會自我擴展
2.2.3 旅游記憶建構對旅游者自我概念擴展的影響 相對于程式化的日常生活,旅游是從“慣常”到“非慣常”再回歸“慣常”的時空變化過程,能讓旅游者獲得心境的跨越,引發對自我的重新觀察(White et al., 2004)。建立于旅游儀式化體驗基礎上的旅游記憶是留存在個體腦海中具有深刻意義的旅游經歷,經個人選擇建構而成,對自我的影響比在場體驗更有影響力。Aron等(2013)指出旅游也是自我擴展的重要來源,旅游記憶建構在保持自我認同、拓展自我認知,增進社會聯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Kim et al., 2019)。因此提出假設:
H3a:認知評價正向影響旅游者個體自我擴展H3b:互動感知正向影響旅游者個體自我擴展H3c:積極情感涉入正向影響旅游者個體自我擴展
H3d:認知評價正向影響旅游者社會自我擴展
H3e:互動感知正向影響旅游者社會自我擴展
H3f:積極情感涉入正向影響旅游者社會自我擴展
2.2.4 旅游分享行為的中介效應 自傳體記憶及
MTEs 的研究認為,旅游記憶為旅游者提供了一種對話方式。通過分享體驗記憶,旅游者可以加強人際聯系,獲得他人的反饋與評價(如點贊和評論),進而將以往的經歷和他人的觀點納入自我,實現自我擴展。同時,由于人的記憶是有限的,對于美好的旅游經歷,人們往往會采取一系列手段來加以強化(Dong et al., 2013),旅游分享是個體對目的地體驗情況等綜合記憶的喚醒和強化,這段被以分享形式存續的記憶也是旅游者認識自我的刺激物。由此,根據文獻基礎與現實情況,提出假設(圖1):

圖1 “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的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on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selfconcept expansion"
H4a:旅游分享在認知評價與個體自我擴展間起中介作用
H4b:旅游分享在互動感知與個體自我擴展間起中介作用
H4c:旅游分享在積極情感涉入與個體自我擴展間起中介作用
H4d:旅游分享在認知評價與社會自我擴展間起中介作用
H4e:旅游分享在互動感知與社會自我擴展間起中介作用
H4f:旅游分享在積極情感涉入與社會自我擴展間起中介作用
3 實證分析與結果
3.1 量表設計
正式問卷包括3個部分。為保證旅游者喚起真實旅游記憶,在問卷第一部分設置4個主觀題,如“您前往的旅游地是哪里?大概什么時候去的?在那里待了幾天?和誰一起去的?”,以提高主體量表測量的真實性。第二部分主要對旅游記憶建構、旅游分享行為和自我概念擴展3個變量進行測量(表2)。其中,旅游記憶建構分量表的測量題項根據前文扎根編碼得出的主副范疇并經過量表初測修改后編制而成,包括3個維度,共16個題項;旅游分享行為量表采用Hsu等(2007)的單一維度量表,并結合Kim等(2022)的量表改編而成,共4個題項;自我概念擴展量表參考Gordon等(2011)和牛更楓(2017)的量表,包括個體自我擴展量表和社會自我擴展量表,共9 個題項,以上所有題項均采用Likert 7級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第三部分為樣本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共5個題項。問卷設計完成后,邀請6名旅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預填答卷,并對問卷合理性進行判定。筆者根據反饋意見對題項詞匯和語句進行調整,以提高問卷的內容效度。

表2 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模型測量指標Table 2 Indices of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selfconcept expansion"
3.2 數據收集
問卷收集采用線上滾雪球式發放和線下隨機發放的方式。于2021-11-15—16 在線上進行預調研,共收集了120份問卷。結果顯示,量表整體及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α值均>0.8,KMO 值均>0.7,各量表Bartlett 球形檢驗均在0.001 的水平上顯著。總體上,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正式調研共發放問卷476份,其中在線調查問卷372 份。課題組于2021-11-27—28 前往西安賽格商城、陜西歷史博物館及城市公共休息區等地進行隨機問卷調查,共發放104份線下問卷。經過篩選,剔除無效問卷后,線上線下共回收有效問卷438份,有效率為92.6%。樣本描述性統計顯示,男性和女性分別占比47.7%和52.3%,分布基本均衡。年齡以18~30 歲(82.2%)和31~45 歲(11.2%)的中青年群體為主。受教育程度方面,由于樣本多集中在城鎮地區,調研對象基本是本科/大專(54.6%)和碩士及以上學歷(37%)。月收入集中于3 000元以下(65.5%)。職業分布均有涉及,主要以學生(53.9%)和公司職員(23.5%)為主。總體上,樣本人口統計學特征符合實際情況,能滿足研究需求。
3.3 結果分析
3.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通過采用認真編排問卷、匿名測量以及沒有告知被試真實調查目的等方式從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未旋轉的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值>1的因子共6個,最大因子方差解釋率為38.931%(<40%),故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 2003)。3.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于旅游記憶建構量表是本研究開發設計的,且其余各變量的題項也是經本研究改編所得,量表測量的有效性和適切性有待檢驗。因此,為確保各分量表的結構效度,首先將樣本隨機排序后,抽取前200份問卷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結果顯示,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和旅游分享的KMO 系數分別為0.873、0.864和0.762,Bartlett 球形檢驗均為P<0.001,表明數據適用于因子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1的公因子,發現旅游記憶建構量表經過5次旋轉后提取出3個公因子,將其分別命名為認知評價、互動感知和積極情感涉入,同理,將自我概念擴展的2個公因子命名為個體自我擴展和社會自我擴展,三者的累計方差解釋率均>50%的標準值(表3),表明各分量表對問卷數據具有較好的解釋力,量表結構較為合理。

表3 “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模型的因子分析結果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factor analysis on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self-concept expansion"
3.3.3 驗證性因子分析與模型擬合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整體量表的信效度,對包括438個樣本在內的整體量表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CFA)。根據因子分析結果,量表總體Cronbach'sα值為0.940,各分量表的Cronbach'sα值也均>0.8,說明量表通過信度檢驗,應進一步進行效度檢驗。根據分析數據可知,量表中29 個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全部在0.60~0.94,標準化因子載荷越高,表明該觀測變量越能有效地反映其要測量的內容,即量表中所有題項均能較好地反映其所在維度。所有變量的組合信度(CR)均>0.7,平均萃取方差(AVE)均>0.5,說明各變量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見表3)。區分效度需通過平均萃取方差(AVE)的平方根與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比較來檢驗。經分析,各變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表4),說明問卷具有很好的區分效度。綜上所述,該測量模型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4 “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模型的相關系數與區分效度Table 4 Correlations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self-concept expansion"
最后,運用Amos24.0 對模型進行擬合檢驗,結果顯示,χ2/df=2.104(標準為<3),P<0.001,RMSEA=0.049(標準為<0.08),GFI=0.898(標準為>0.9),CFI=0.959(標準為>0.9),NFI=0.925(標準為>0.9),RFI=0.911(標準為>0.9),IFI=0.959(標準為>0.9),TLI=0.951(標準為>0.9)。上述擬合指標中除GFI指標差一些,其余均達到可接受的標準值,說明該模型與量表匹配較好,模型成立。
3.3.4 假設檢驗 采用Amos24.0 繪制模型路徑圖對假設模型進行驗證,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計算模型的路徑系數和各項擬合指標。本研究假設模型的χ2/df=2.055, RMSEA=0.049, GFI=0.900, CFI=0.962,NFI=0.928,RFI=0.913,IFI=0.962,TLI=0.953,均達到所要求的擬合度。模型路徑圖如圖2所示。

圖2 “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的模型路徑Fig.2 The graph of model path on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self-concept expansion"
由圖2可知,除H3f(“AI→SSE”)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之外,其余各條假設路徑均獲得實證數據的支持。具體地,首先,從旅游記憶建構的3個維度對旅游分享行為的影響路徑來看,認知評價對旅游分享的標準化影響路徑系數β為0.206,P值為0.003,<0.01的顯著水平,即該正向關系顯著。除判斷P值外,還需誤差變異達到顯著水平,即t值>1.96,該路徑的t值為2.989,因此H1a成立;H1b和H1c說明互動感知和積極情感涉入對旅游分享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互動感知(β=0.123,t=2.186,P=0.029<0.05) 和積極情感涉入(β=0.245,t=3.734,P<0.001) 均顯著正向影響旅游分享,H1b、H1c 也得到證實;其次,從旅游分享對自我概念擴展2個維度的影響結果看,旅游分享顯著正向影響個體自我擴展(β=0.303,t=6.702,P<0.001)和社會自我擴展(β=0.214,t=4.097,P<0.001),H2a、H2b得到證實;最后,從旅游記憶建構對自我概念擴展的路徑檢驗結果看,認知評價(β=0.219,t=3.763,P<0.001)、互動感知(β=0.220,t=4.511,P<0.001)和積極情感涉入(β=0.200,t=3.649,P<0.001)都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個體自我擴展,因此H3a、H3b、H3c獲得實證支持。根據路徑檢驗結果,認知評價(β=0.145,t=2.141,P=0.032<0.05)和互動感知(β=0.403,t=6.436,P<0.001)也均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社會自我擴展,H3d 和H3e 得到證實。對于H3f,該路徑的t值為0.694,<1.96,P值為0.488,>0.05 的顯著性水平,因此H3f 不成立,說明積極情感涉入對社會自我擴展沒有顯著影響。
3.3.5 中介效應檢驗 通過Process插件采用Bootstrap 方法進行5 000 次重復抽樣來檢驗中介效應。如果Bootstrap法檢驗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中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成立(Hayes et al., 2011)。如表5 所示,旅游分享在旅游記憶建構的3 個維度與個體自我擴展之間起到顯著中介作用,其95%置信區間分別為[0.111 3, 0.245 3]、[0.065 2, 0.168 6]、[0.106 3, 0.238 0],表明H4a、H4b、H4c 成立;旅游分享在認知評價、互動感知、積極情感涉入與社會自我擴展之間也起到顯著中介作用,其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65 6, 0.201 7]、[0.033 2, 0.111 6]、[0.070 4, 0.211 8],表明H4d、H4e、H4f 成立。進一步分析,若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顯著,則表明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若直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顯著,則中介效應為完全中介。由此可知,除旅游分享在積極情感涉入與社會自我擴展間(“AI→TS→SSE”)起完全中介效應外,在其余5 條路徑中均起部分中介效應,表明積極情感涉入需通過旅游分享行為的中介間接實現社會自我擴展。

表5 旅游記憶建構-自我概念擴展間接效應的Bootstrap分析Table 5 Tourism memory construction-self-concept expansion Bootstrap analysis of indirect effect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本研究基于自傳體記憶及自我擴展理論,通過扎根理論挖掘出3個旅游記憶建構維度,進而量化分析旅游記憶建構、旅游分享與自我概念擴展的作用關系。得到如下結論:
1)作為一個穩態和動態共存的心理機制,旅游記憶的建構包括認知評價、互動感知和情感涉入。其中,認知評價是旅游者依托記憶中目的地客觀環境而持有的認知性感受;互動感知是旅游者對主客互動與旅游者間互動的參與性感知;情感涉入體現了記憶的情感屬性,是旅游者基于認知評價和互動感知而產生的相應情緒反應。3 個要素間彼此關聯,共同貫穿于建構個人旅游記憶以及凸顯旅游者主體性的過程中。可以說,旅游記憶建構是對游后階段人地關系的一次深入剖析,既塑造和解讀了旅游景觀,也構建了自我認同(袁振杰 等,2020)。
2)旅游記憶建構顯著正向影響旅游分享行為。具體來說,旅游者通過認知評價塑造并解讀了目的地景觀環境的符號意義,生成了對目的地的主觀印象,進而刺激其通過分享來描繪和重建自己的具身體驗。這證實了基于非慣常環境的旅游記憶是旅游者對目的地最終的認知體現,這種經個人篩選的特殊經歷更容易引發分享行為(Tung et al., 2011b)。在旅游世界中,除了客觀環境,旅游者可能還關注與他者的人際互動,如很多旅游者所說:“我不在乎去哪玩,我更在乎的是跟誰一起去玩”。說明在中國的人情語境下,人的因素也是旅游者的記憶點,能強化旅游記憶,激發分享意愿(Tussyadiah et al., 2009);旅游記憶作為在場體驗的存續,嵌入了個人的主觀情感,并且回憶往往比真實體驗更具情感特征(Wirtz et al., 2003)。研究表明,在旅游者追求愉悅的動機下,消極情感很少被記住,但也難免因旅游者個體差異等主觀原因導致消極記憶的產生。本研究發現無論積極或消極的情感涉入,都會被旅游者記住,但旅游者更愿意傳播“正能量”,展示旅游記憶的積極面。
3)旅游分享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自我概念擴展。通過分享,旅游者找到了自我概念擴展的新場域,一方面,對旅游者而言,分享是具有生活儀式感的行為,人們可以通過圖文等“舞臺”設計,構建出記憶中的“前臺區域”(李淼 等,2012),以便形塑與展演理想自我形象,并在分享中回溯自己“在路上”的記憶,感悟在異地的旅游時光,紓解生活的壓力,追尋生命的不同意義,引發對自我的思考(陳曄 等,2020),從而實現旅游者個體自我的擴展;另一方面,分享的同時也帶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使旅游者建立新的社會關系或加深原有關系,并通過分享互動強化他人對自我所扮演社會角色的評價,從而在被關注和被認同的過程中實現旅游者社會自我的擴展。因此,作為個體自我敘事和自我表達的方式,旅游分享也開啟了旅游者對自我主體性意義的深入思考(朱竑 等,2020)。
4)旅游記憶建構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自我概念擴展。首先,認知評價實質上是旅游者認識事物并獲取知識的過程,因此由旅游活動提供的具身性認知為旅游者的自我概念擴展提供了現實來源;其次,通過記憶中的互動感知,旅游者獲得一個社會比較途徑,能對自我及其周圍關系產生更多在生活世界中不曾注意到的認識,使自我在個人與他人的交織互動中得以發展;最后,積極情感涉入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者個體自我擴展,說明因環境補償和人際互動而帶來的情感宣泄是旅游者心理調適和精神寄托的方式,通過積極情感喚起改變旅游者個體的心理狀態,實現個體自我擴展。由于積極情感涉入是個體主觀的心理感受,在認識個人與他人關系方面的作用較小,對社會自我擴展影響不顯著,但可以通過分享行為間接影響社會自我擴展,分享過程中的情感流露可以引起他人的共鳴,旅游者可以通過分享搭建起對外交流與社會認同的平臺,從而在“他者”與“我者”的對話中實現社會自我擴展。
4.2 理論貢獻
1)厘清了旅游記憶建構的維度,補充了以往旅游體驗研究中游后記憶層面的理論不足,明確了微觀日常實踐中旅游記憶展演對自我的主體性意義,并以旅游分享行為作為中介變量,將記憶與分享行為的影響路徑從關注外部效應拓展到關注自我反身性影響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記憶與分享行為的研究視野。
2)將自我擴展概念引入旅游研究情境中,分析了該情境下大眾旅游者的自我擴展機制,補充了非關系情境中的自我擴展研究,并在Aron 等(2013)基礎上,進一步驗證了游后積淀的旅游記憶是旅游者省察自己,實現自我概念擴展的來源,為后續研究個體旅游記憶的自我價值提供新視角和切入點。
4.3 管理啟示
1)旅游記憶是在場體驗的建構與升華,對此,目的地管理者可以圍繞“認知、互動和情感”三要素為游客創造難忘的旅游記憶。在強調基礎設施和服務水平等認知因素的同時,旅游地也要注重對意義性和情感性因素的挖掘,使其植入游客的記憶系統,以獲得令游客滿意的記憶效果。如鄉村旅游地可以通過場景營造與情感烘托,激發鄉愁記憶來增強游客對目的地的情感聯結。此外,由于記憶中的人際互動能帶來自我概念的擴展,旅游地也應設計交互式體驗項目,促進同伴間、游客間以及游客與原住民間的交流互動。尤其對于歷史文化類目的地而言,通過采用新技術等手段,設計游客可觸可感的活動,讓游客在沉浸式體驗中,增進友誼,了解地方文化,從而發展“自我”。
2)旅游分享既是旅游記憶存儲的載體,也是游客自我呈現的舞臺,所以對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分享是能善加利用的機遇,也是對目的地旅游產品和旅游服務質量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的一大挑戰。旅游地可以借助分享潮流,使之成為吸引回頭客的關系營銷手段,充分利用游客面子需要等心理需求,通過話題制造、情境帶入及打卡紀念等方式,促進游客利用微信等新媒體進行正面口碑傳播,以此實現價值共創。此外,旅游地也需不斷提升與完善自身產品和服務質量,盡可能多地刺激游客產生現場記憶點。同時還需重視游客的評論反饋信息,及時查漏補缺,避免游客負面口碑的傳播。
4.4 研究局限與展望
首先,本研究雖然證實旅游記憶建構對自我概念擴展的影響機制,但由于游客的個體差異,不同類型的游客所具備的思維模式、人格特質和記憶偏差等因素都會影響旅游記憶的建構,進而對自我擴展產生差異化影響,比如在家庭旅游中,成年人與兒童由于旅游需求和興趣的差異,其旅游記憶往往存在偏差,因此未來有待開展不同年齡和性別的分眾研究。其次,已有旅游記憶研究從美食旅游(Tsai, 2016)及主題公園旅游(匡紅云 等,2019)等方面展開討論,未來可將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模型放在其他不同旅游情境中進行拓展與深化。最后,本研究質性資料主要收集了網絡游記,數據來源相對單一,將在后續研究中增加訪談文本以保證數據來源多樣化,使編碼更為全面。此外,文化因素也會影響個體對自我的認知(Markus et al., 1991),如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與東方集體主義文化下,人們在回溯旅游記憶時是否存在:選擇性側重點不同,從而導致自我擴展的差異?這一問題也值得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