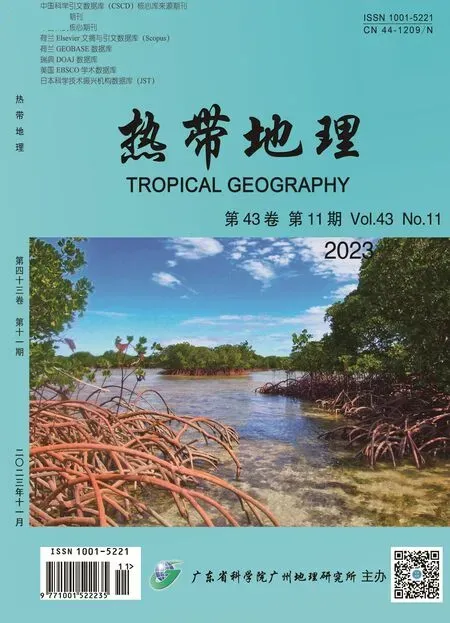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路徑探索與機制解析
王銘杰,張冰逸,孟 凱,袁浩文,唐佳欣
(1. 海南大學 旅游學院,海口 570228;2. 暨南大學 深圳旅游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3)
隨著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和絕對貧困的歷史性消滅,“三農”工作進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階段。2021 和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分別提出協同鞏固脫貧成果和鄉村振興實現鄉村發展的任務和目標。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問題的論述與科學判斷指出村民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主體地位,村民作為鄉村經濟社會的基本單元,其生計不僅是基本生活保障,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問題,即鄉村振興的根本是村民生計振興(張軍以 等,2022)。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到鄉村發展對村民生計的雙向影響,從多元視角出發闡釋村民的生計轉換過程與結果。隨后,部分學者以此為指引,進一步嘗試對生計轉換的影響因素進行解構重塑(左冰 等,2016;劉相軍 等,2019)。與此同時,伴隨鄉村旅游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助力,旅游背景下的村民生計轉換成為關注的焦點,諸多學者以DFID(1999)提出的可持續生計框架為基礎,探究經濟、物質、人力、自然、社會五大生計資本類型對生計轉換的影響(孔令英等,2021;黎春梅 等,2021)。然而相關研究通常運用各項客觀指標說明生計資本與旅游發展背景下生計策略之間的靜態關系,且普遍忽略村民作為能動主體在生計轉換進程中的作用。隨后,部分學者關注到村民的重要作用,開始將村民主觀意愿納入生計轉換影響因素的考慮范疇(崔冀娜 等,2018;孫鳳芝 等,2020),但探討的大多是影響因素與生計結果之間的二元線性關系,忽視了不同影響因素組合對生計轉換結果的復雜異質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首先通過訪談和文本編碼歸納識別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影響因素,再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進一步探索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路徑與機制。以期揭示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與意愿形成之間因素組合和路徑機制之間的復雜關系,完善旅游發展探查階段和以村民為主體的生計研究成果,豐富可持續生計框架,為旅游發展初期的政策優化提供依據。
1 相關理論與研究回顧
“生計”一詞最早是為了解決貧困問題而提出的,其定義可追溯至1992 年Chammbers等(1992)認為的“生計是基于自身擁有的生活手段所需的能力、資產(商店、資源、索賠和獲取)和活動而開展的謀生方式”。DFID(1999)基于上述定義構建了可持續生計框架,迅速發展為理解和研究村民貧困問題的理論工具。學者們將該框架應用于扶貧減貧、生態保護、社區發展、村民福祉等諸多領域,逐漸被視為實現村民公平和鄉村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郭華 等,2020)。
隨后,學者們關注到不同地區生計的轉變過程與結果,并將村民生計變化與鄉村發展相聯系,嘗試從不同視角闡釋村民生計轉換受到的多元異質影響。如左冰等(2016)從農民資本著手,發現人力資本是影響村民轉換生計策略的關鍵因素,其次是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劉秀麗等(2018)從滿意度切入,分析不同類型農戶生計轉換前后生活滿意度的變化,得出各類生計資本和農戶生活滿意度均呈正相關;劉相軍等(2019)由個人建構理論出發進行剖析,以此解釋生計轉換帶來當地傳統文化和村民生活方式相適應的過程和結果。由此可見,相關學者關注到多元視角在展演村民生計轉換過程與結果時的廣闊闡釋空間,并以此為指引對生計轉換的影響因素進行解構重塑,從而對生計轉換進行更全面深入的詮釋。
事實上,生計在定義之初就被認為存在于一個多因素交織的動態脆弱環境中(Shen, 2008; Speranza, 2014),因此生計并非一成不變,其可能因生態問題(王國萍 等,2022;Tasnuva et al., 2023)、政策制度(龐潔 等,2021;何羽豐 等,2023)等外部驅動力致使被動轉換,也可能因鄉村城市化、旅游化進程等發展需要引致主動轉變(崔曉明 等,2018;Rongna, 2022)。不論受何種因素驅使,生計轉換的目的均是利用有限資源優化生計策略,提高生計能力,追求更好的生計結果,以實現生計可持續目標。近年來,諸多學者嘗試以可持續生計框架為基礎,以生計資本為核心,探究經濟、物質、人力、自然、社會五大生計資本類型對生計轉換的影響。如孔令英等(2021)認為自然資本是決定農戶選擇純農型生計策略的基礎,而金融、人力、社會、物質、民族文化等共同決定該地區農戶傾向于選擇純農型轉變為非農型的生計策略;黎春梅等(2021)在分析生計資本對農戶生計分化的影響機理時提出,社會資本有助于農戶由單一型經營向兼業型農戶轉變,自然資本有助于農戶向農業經營型轉變。同時,政策制度和機構主體作為重要的外部力量,也能對生計轉型產生關鍵影響。如劉格格等(2021)發現外部生態政策通過影響農戶可實際運作的生計資本,從而對生計策略選擇發揮作用;許揚等(2022)在探討“阿者科計劃”對當地農戶生計變遷的影響機制時發現,政府結合高校的合作形式能有效改變當地的生計結構與制度,從而對生計資本產生影響。除此之外,部分學者還探討了諸如信息獲取媒介(楊檸澤 等,2018)、生產技術(張軍以 等,2022)、地理區位(李龍 等,2021;蘇偉鋒 等,2023)等可持續生計框架外的因素對生計轉換的影響,相關研究大多以人地關系為切入點,因地制宜地提出促進農民生計轉換和農村生計轉型的作用機制(Chen, 2023)。總的來說,現有研究雖對生計轉換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進行了探索,但大多是基于不同地區某個時刻既定的生計現狀或轉換結果,運用各項生計指標統計量化生計資本、生計轉換影響因素與生計策略選擇、生計轉換結果之間的靜態關系;或囿于可持續生計框架,遵循“生計資本變化—生計策略抉擇—生計轉換結果”的傳統邏輯探究生計轉型機制,但卻無法在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從無到有的完整過程中展現影響因素的動態作用,且村民作為能動主體在生計轉換進程中存在缺位。
此后,部分學者關注到村民在生計轉換中的主體地位和能動作用,將村民主觀意愿納入影響因素的考慮范疇。如崔冀娜等(2018)關注移民的生計轉變過程,從移民主觀感知出發構建量表,利用二元Logistic 探究發現城鎮融入是增強生計轉換意愿的重要因素;孫鳳芝等(2020)通過結構方程模型實證了居民支持度、居民參與度、生活滿意度等主觀因素對生計資本的影響,及其對生計策略轉變意愿的多重鏈式中介作用。可見,相關研究逐漸回歸生計概念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將村民主觀意愿和客觀生計資本相結合,在轉換過程中審視生計的動態變化。然而,相關研究大多沒有考慮影響因素和結果之間的因果復雜性,即給定的單一因素或因素組合可能并不是產生某個特定結果的唯一路徑,其他組合可能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綜上,生計轉換影響因素豐富多元,其與轉換結果間的因果關系和作用機制復雜異質,其中尤其不能忽視村民作為主體的主觀意愿。鑒于此,本文將從村民主觀意愿出發,通過深度訪談和文本編碼歸納識別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影響因素,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探索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路徑和機制,為生計理論研究和旅游發展提供參考。
2 方法與數據
2.1 案例地概況
案例地選自海南省海口市北港島。北港島隸屬海口市美蘭區演豐鎮,地處海口市和文昌市交界處,下轄道頭村、后溪村、上田村3個自然村,是海口市唯一的島嶼行政村。400多年前,北港曾是數十個成片村莊的一部分,后因瓊北大地震導致周邊村莊淹沒,北港島因地處陸地中心而幸存。因北港島地理位置特殊,數百年來島上村民僅能通過乘船方式進出。2019年5月,《海口江東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海口市規劃委員會,2021)正式批復,其中多次提及以通橋解決困擾北港島的交通歷史問題;2019年11月,北港互動工程開建,并于2021年2月海文大橋北港匝道正式通車,自此結束了北港村民400多年來靠船出行的歷史,村民進出島嶼的便利性得到顯著改善。得益于北港島可進入性的根本改變,其長期以來與世隔絕的自然風光吸引大量周邊游客,旅游成為北港島和當地村民關注的熱點話題。
選取北港島作為案例地主要基于以下考慮:1)該地具有代表性。通橋后游客的進入擾亂了島上村民的原有生產生活節奏。游客的進入使部分村民萌生生計轉換的想法;2)該地具有典型性,生計轉換是當地村民討論的重要話題。長期以來,島上村民以捕魚、養殖、開船、村委辦公等傳統生計為生,在大量游客進入島嶼后,當地政府出臺政策限制村民捕魚養殖活動以保護旅游景觀。因此,是否放棄原先生計并參與旅游經營,成為村民討論和村委同上級部門商議的重要議題;3)當地村民對生計轉換看法存在差異。因此,厘清村民對生計轉換的不同看法,有利于全面把握生計轉換意愿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為解析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路徑與機制提供參考。
2.2 數據收集
通過半結構式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對案例地展開深入調研,數據收集分2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調研時間為2021-12-26—2022-01-10,共訪談24名當地村民(表1),訪談時間為30~60 min,在征得受訪者同意后對訪談過程進行錄音,訪談問題主要包括對現在生計狀況的描述和對未來生計轉換的看法2方面。其中,現在生計狀況的問題包括:你現在有哪些生計來源、你對現在生計方式的滿意程度怎么樣、你覺得現在生計方式面臨哪些困難、你覺得現在生計方式的未來發展情況怎么樣等;未來生計轉換的問題包括:在大量游客進入后,你對北港島未來發展旅游有哪些看法、你對轉變生計有哪些想法、推動或制約你產生上述想法的原因有哪些等。此外,還觀察記錄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節奏和對相關重大歷史事件的態度。訪談結束后將錄音轉譯為文本共得到13 余萬字。如表1 顯示,從受訪者構成看,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分別為54%和46%;年齡區間為21~62 歲;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為主,占比75%;從生計形式看,受訪者多以出海漁民和水產養殖為主,部分村民以開船或在村委辦公為生。第二階段調研時間為2022-03-26—28,結合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將第一階段通過村民訪談文本編碼歸納得出的影響因素轉換為對應結構化問題后,再次對上述24 名村民進行訪談,訪談時間控制在10~15 min。旨在根據受訪者回應內容,深入了解村民對各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的真實想法,以完成后續變量賦值等操作。

表1 案例地受訪村民基本情況Tab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villages interviewed in the case site
2.3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訪談和文本編碼歸納結合的質性方法。以Glaser 等(1967)提出的扎根理論為基礎,通過對原始實證數據的編碼歸納生成原始概念和范疇。在第一階段以訪談收集文本數據,通過文本編碼歸納,探索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影響因素,以此進行關于生計轉換意愿的多元組合路徑的探討。隨后,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該方法由拉金提出(Ragin, 2008),既可以處理類別問題,也可以處理程度變化和部分隸屬的問題,且具有分析處理定性數據、有限多樣性和簡化組態的優勢。本研究所關注的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且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作用,且受訪者數量滿足fsQCA適用中小樣本的要求(張明 等,2019),因此適宜采用fsQCA 方法對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路徑展開研究。
3 結果分析
3.1 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
根據研究主題和材料屬性對訪談文本內容進行編碼操作流程。考慮后續理論飽和檢驗需要,將所有材料按訪談對象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為前21個訪談對象文本,約11萬字,用于編碼;第二部分為余下3 個訪談對象文本,約2 萬字,用于理論飽和檢驗。首先,對前21 個訪談對象文本進行開放編碼,提取文本中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詞語,形成108個原始概念。其次,進行軸心編碼,根據相關性、互斥性和周延性的分類理念將原始概念按其內在關聯歸并為不同類屬,提煉出15個初始范疇,再將初始范疇進行選擇編碼生成7個主范疇。再次,對余下3個訪談對象文本進行獨立編碼,并未發現新的原始概念產生,且無法進一步提煉新的潛在范疇,證明理論已達飽和。最后,通過文本編碼歸納共獲得108 個原始概念,提煉為15 個初始范疇并生成7個主范疇(表2)。將7個主范疇作為研究生計轉換意愿的影響因素,分別為政策引導、游客進入、人力資本、地方情感、生計滿意、經濟資本和家庭壓力。
“政策引導”是村民在訪談過程中提及次數最多的信息,這與吳吉林等(2017)在探究傳統村落農戶生計轉換適應性過程中,提出眾多政策制度是影響農戶生計策略的根本性原因的觀點形成印證。在訪談中部分村民表達出“限制捕魚”“取締千秋網”“收繳船只”等消極政策對現有漁業生計的影響,也有村民提到“拓寬修路”“修停車場”“做海鮮市場”“海洋牧場”等積極政策對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和未來生計的引導。一方面,因旅游發展、鄉村規劃需要所引致的政府部門的介入,限制了島上漁民的現有生計來源,對村民漁船、漁網等生產工具進行強制剝奪,由于政府部門未給出明確補償方案,大部分村民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另一方面,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等積極政策落實改善了鄉村基礎公共設施,優化了地方環境,再加之北港島通橋后游客的陸續進入,在很大程度上激發村民對地方旅游發展的憧憬。
“游客進入”給當地村民生產生活帶來顯著改變,進而引致想法觀念的轉變。吳海濤等(2015)在探尋滇西南農戶生計模式演變時,認為可進入性和道路通達影響村民開展非農生計活動,這在北港島同樣適用。通橋通路后進出當地的便利性大大提高,村民和游客均可乘車自由出入,如村民多次提到“市區回來方便多了”“現在周末會堵車”“橋下站滿了人”“人多了影響正常生活”等,表明游客流量的快速增加打破了村民原本生產生活節奏,與外來游客的主客凝視和話語溝通深刻影響村民對現有生計和生計轉換的潛在看法。
“人力資本”包括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2方面,訪談中“從小又不好好讀書”“不懂做什么”“不會其他技術”等描述體現村民對人力資本要素的反思。在村民看來,文化水平低、掌握技能單一是他們在考慮轉變生計時的重要因素,導致村民在生計轉換的選擇中處于被動。同時,也正是因“人力資本”的薄弱,致使部分村民在面對旅游發展機會時,對轉換旅游生計持開放態度。
“地方情感”是村民受北港島閉塞環境和過去生活記憶持續性影響所產生的認知和情感反應(Jampel, 2016),即使通橋后當地村民仍傾向于與該地保持密切情感關系。訪談中頻繁出現的諸如“住著舒服不愿離開”“從小在這長大”“希望大家來北港游玩”等分別對應環境依戀、身體歸屬和地方認同3個初始范疇。對村民而言,原先與陸地分離的北港島是成長之地,更是生命階段的見證地,與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系使村民在交通條件改善后仍愿意留在本地轉換生計。個人地方情感需要的滿足,成為大部分村民在考慮生計轉換時的關注焦點。
1.成長記錄。建立學習記錄袋,學生把自己一段時期內所學知識、技能等成長過程記錄下來,以便對自己有一個更明確的了解。如:作業、課堂表現、測驗成績、評價日記、自我反思等各種有關英語學習情況,以此進一步展示自己在大學生活的成長歷程。在這期間,教師可以為學生制作學習成長記錄的資料夾,如:學習表現、興趣高低、工具使用頻率、自學行為等。最重要的是學生應該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一套適合自己關于移動學習英語的記錄袋,如:英語新聞、國家信息、聽讀練習、移動工具的錄音、英文電影等,同樣也可以對自己的英語水平做自我評價。[5]
“生計滿意”由生活狀況和經濟追求2 方面構成,側面印證孫鳳芝等(2020)認為村民對現有生活滿意程度影響生計轉換策略的實證結果。在訪談中“生活一般”“希望能更好”等語句,反映村民對當前生活狀況的認知,部分村民試圖借游客進入后所帶來的機會,通過“做副業”“開民宿”“做餐飲”“出去打工”等方式實現更高經濟追求以提高生計滿意程度。
“經濟資本”是村民在島上生活所積累的主要經濟資源,“收入還算可以”“夠一家人吃喝”“擁有空地”“出租房子”等概念,反映村民在表達生計轉換意愿時對個人收入和房產資源的倚重。部分擁有較高收入和多處土地的村民往往在談及生計話題時,對轉換生計持開放態度。相反,經濟資本薄弱的村民對生計轉換表達“走一步看一步”和“見機行事”的謹慎態度。
“家庭壓力”反映村民對自身在家庭中承受的父輩壓力和子輩壓力認知。“家庭”是探討生計的基礎單位之一(李文龍 等,2019),村民提及“爸媽老了需要我出力”“父母辛苦出海一輩子”和“養小孩不容易”“供小孩讀書上學”等分別反映其在家庭中所承擔的壓力。家庭壓力使部分村民對游客進入后島上蘊含的旅游發展機會抱有更高期待,但也因此產生更多顧慮,部分村民在表達對生計轉換相對積極和期待態度的同時,仍會透露出對“上有老下有小”“不敢輕舉妄動”的畏難和隱憂。
3.2 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路徑
通過文本編碼歸納得出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后,發現政策引導、游客進入、人力資本、地方情感、生計滿意、經濟資本、家庭壓力7個影響因素具有非對稱性、復雜異質性和動態過程性特征。影響因素之間本質復雜又界限模糊,一個給定的因素組合并不是產生意愿的唯一路徑,其他組合也可能會產生同樣結果。因此,運用組態理論將有助于深入理解前置影響因素和后置結果之間的關系。基于此,以生計轉換意愿為結果變量,7 個影響因素為條件變量,分析影響因素不同組合與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路徑機制關系。
根據QCA 的處理步驟,下一步需對各受訪者感知的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進行賦值。通過回溯訪談文本,將變量轉換為對應問題后依次向相同受訪者提問,再根據描述內容對各變量進行六值賦值,如“政策引導”作為條件變量轉換后的對應問題為“各類積極或消極政策會影響你目前的生計情況嗎?”,0表示無影響;0.2表示影響很小;0.4表示影響較小;0.6 表示影響較大;0.8 表示影響很大;1表示完全影響。以此類推,完成所有變量賦值后,將數據導入fsqca3.0進行運算。
3.2.1 單因素必要性分析 根據QCA 分析步驟,需對單因素是否為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進行檢驗,即判斷單個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是否為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必要條件。通常來說,當單因素一致性水平>0.9 時,可認為該條件因素是導致最終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王鐵 等,2021;李洋洋 等,2021)。
表3為生計轉換的必要因素分析結果。對推動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影響因素來說,“游客進入”和“地方情感”的一致性均>0.9,為必要條件。村民對“游客進入”的認知集中體現為交通通達后大量游客進入給其帶來生活狀態的改變。北港村在通橋后進出便利性大大提高,其原本相對與世隔絕的自然風光獲得廣泛關注,部分游客自發驅車前來打卡。隨著進入游客的逐漸增多,部分村民產生從事旅游經營的想法。正如受訪者(P11)所說:“只要天氣好,從橋上開車下來的游客會非常多。現在島上只有一家便利店和一家農家樂,有時候看他們生意好會眼紅,想著要不自己也做點小生意。”因此,游客進入使村民萌生改變生計的想法,成為推動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必要起始因素。“地方情感”表現為村民在原本閉塞的島上普遍已生活數十年,島上不僅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安然愜意的生活方式,還承載著村民的成長記憶和個體成就,具有豐富地方意義和緊密情感聯系。正如受訪者(P18)所說:“小時候在水里游泳,在島上讀書,長大了在這邊碼頭出海捕魚。雖然大家聚在一起經常說島上過日子這不好那不好,但時間長了也就有感情了。”積極的地方情感聯系使村民產生對當地環境的守護和未來發展的期盼,尤其當他們意識到因交通改善而帶來大量游客后,均表示歡迎且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與幫助,受訪者(P5)表示:“看到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小島現在這么受歡迎當然很開心,常會想在家里開個飯店、水吧之類,這樣就能更好招待大家了。”可見,生計轉換意愿形成以村民深厚的地方情感為前提,成為推動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必要驅動因素。綜上可知,“游客進入”“地方情感”成為推動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必要條件。但所有單因素均不構成村民生計轉換的充分必要條件,因此,需進行多因素組合分析以探究多元組合路徑。
3.2.2 條件組態充分性分析 多因素組合分析旨在揭示多個條件因素的不同組合對結果構成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即深入挖掘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不同影響因素組合,通過對要素組合進行歸納,可進一步提煉出上層路徑邏輯類型,這一過程在相關研究中也已得到運用(孫佼佼,2021)。本研究設定最小案例頻數閾值為1,一致性閾值為0.8,滿足組合路徑對實際現象的解釋力(Rihoux et al.,2017)。對24個受訪案例數據進行分析輸出復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在實際分析中一般采用中間解識別充分條件的組合(張圓剛 等,2021)。采用上述方式,7 個變量共產生128 條組合路徑,其中滿足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組合路徑共4條(表4)。組合路徑的總體一致性為0.796 610,總體覆蓋率為0.783 333,均高于0.75 臨界值(Schneider et al.,2012),表明實證分析具有較高解釋力度,可進一步識別不同影響因素在推動生計轉換意愿形成中的適配關系和內在邏輯。
組合3的原始覆蓋率分別為0.433 333,表明該路徑能夠解釋約43.33%的案例。符合組合3的村民在過去工作中積累了一定經濟基礎,但由于家庭壓力較大,只能勉強滿足贍養父母和撫養子女的需要。一位36歲的受訪者(P19)表示:“我家里有3個孩子,他們在市里讀書開銷特大。我每天熬夜出海捕魚經常覺得很累想停下來休息幾天,但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生活開銷,沒有辦法只能逼著自己繼續干。”該類村民對現有生計狀況表示不滿,并承受著身體和精神的較大壓力,但受制于家庭壓力和外部環境,始終缺少轉換生計的動力。因此,他們在發覺通橋后大量游客進入北港島所帶來的潛在發展可能后,逐漸對轉變當前生計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但也會從家庭實際情況出發,考慮生計轉換的可能結果。由此可見,該類村民習慣從家庭角度出發,評估生計轉換帶來的可能影響,在此過程中逐步推動潛在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因此,可將該類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邏輯歸結為家庭責任驅使型。
組合4的原始覆蓋率分別為0.233 333,表明該路徑能解釋約23.33%的案例。符合組合4的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與其現有個人收入和土地房屋資源直接相關,他們希望能將自家島上的空閑房產改造成飯店、民宿或出租給外來老板獲得租金收入,如受訪者(P2)所說:“我在島上有好幾棟房子,自己住著一棟,旁邊還有四棟都是我們家里幾個兄弟的。他們現在不在島上生活了,房子由我來管,我是挺想把他們做成民宿的。”又如受訪者(P22)所說:“最早聽說政府出了規劃要在島上做海洋牧場、紅樹林觀光區、觀鳥臺時,我就覺得有戲。最近還聽說政府要把碼頭沒有證的漁網漁船都沒收了,說影響景觀,這意味著北港發展旅游是板上釘釘的事!如果現在不抓緊先把飯店、民宿這些做起來,等之后做的人多了就不好賺錢了。”由此可見,該類村民在具有一定經濟資本后渴望進行生計轉換。他們在得知漁網漁船取締和旅游發展的相關政策后,主動將這些信息與游客數量激增相聯系,渴望在當地旅游發展中獲得先機,從而促使其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因此,可將該類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邏輯歸結為外部環境推動型。
3.3 生計轉換意愿形成機制
在辨析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條件組合路徑后,根據生計轉換意愿影響因素、形成路徑和生計轉換意愿強弱之間的關系,提出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機制(圖1)。由表4可知,個體認知導向型包含2種組合路徑,組合1和2同時具備游客進入、人力資本、地方情感、生計滿意因素,但經濟資本和家庭壓力因素的存在與否具有差異。這說明組合1 和組合2 雖都能引致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但村民的意愿也因經濟資本和家庭壓力的不同而存在群體差異。該類型中組合1 和2 的原始覆蓋度均>0.6,具有最高解釋力度。家庭責任驅使型圍繞游客進入、地方情感、經濟資本、家庭壓力發揮作用,該類型中組合3 的原始覆蓋度在0.4~0.6,解釋力度次之。外部環境推動型以政策引導、游客進入、地方情感、經濟資本為核心,該類型中組合4的原始覆蓋度<0.4,解釋力度較弱。

圖1 案例區概況Fig.1 The profile of case area

圖2 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機制Fig.2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illagers' livelihood transition intention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深入分析3類路徑邏輯所對應村民的訪談發現,不同路徑邏輯所對應的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強弱存在差異。個體認知導向型具有最高解釋力度,代表多數村民的集體意愿,但其生計轉換意愿強度相對較弱,表現出等待觀望的態度。在過去的北港傳統社會中,村民傍海而生,大多從事與海洋相關的生計方式,一家只要有1~2個勞動力從事出海捕魚或水產養殖等“做海”工作便可維持生活,且在通橋前與外界相對隔絕的生活環境讓大部分村民難以接觸到外部環境而相對安于現狀,并對漁民身份和海洋生計產生情感依戀。因此,在面對大量游客進入所帶來的機會時,該類村民對生計轉換表達出相對較弱的意愿,即在合適時機愿意嘗試旅游生計方式,但不愿意放棄“做海”權力,正如P20所言:“現在游客越來越多,政府讓我們發展旅游我肯定是贊成的。但做旅游肯定有賺有虧,況且現在也沒見什么太好的賺錢機會。如今政府一句話就要收我們的漁船漁網,那讓我們怎么賺錢?靠什么吃飯呢?”
家庭責任導向型的解釋力度適中,有一定數量村民的生計轉換意愿遵循該形成邏輯,且該類村民對生計轉換表現出相對謹慎而又有所期待的態度。部分中年村民因有限的物質條件而同時承擔著贍養父輩和撫養子輩的較大壓力,訴諸以海為生的傳統生計方式能獲得一定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但常年“做海”讓其疲憊不堪,且隨著漁業生產和漁民地位在現代社會中的衰落和下降,該類村民對轉換生計抱有一定期待。與此同時,較大的家庭壓力和責任使該類村民對生計轉換可能帶來的負面結果的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較低,再加之較低的人力資本積累,讓其普遍質疑自身的文化知識和工作技能是否足以適應轉換后的新生計方式。因此,該類村民對生計轉換表現得相對謹慎,總體意愿強度適中,正如P1所說:“如果時機成熟,開民宿做飯店能賺到錢的話那當然愿意嘗試了,誰都想在自己家里又能當老板又能把錢賺,還可以兼顧老人孩子。出海打漁或者岸上做水產都太累了,累了十幾年真心想換個事兒干。但你看現在這情況,所謂的旅游也才有點苗頭,上有老下有小要靠我吃喝,我真不太敢輕舉妄動,怕賠錢。”
外部環境推動型的解釋力度最低,表示僅有少部分村民符合該邏輯類型。該類村民所具有的經濟資本使其與傳統北港社會產生分化,相對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較高的受教育程度,使其敏銳捕捉到游客進入增加和當地政府陸續頒布的政策引導。因此,該類村民對生計轉換表現出積極參與的強烈意愿,如P3所說:“最近北港島真是越來越火了,前陣子回島上還聽說政府在給北港做鄉村規劃和旅游規劃,現在身邊的市區朋友知道我是北港人都來向我打聽旅游攻略。我最近正在和家里人商量打算趁這個機會把村里的房子裝修布置起來開個民宿,爭取做島上第一家住宿。”
進一步分析發現,符合個體認知導向和家庭責任驅使2類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路徑邏輯的北港村民以常駐村民為主,符合外部環境推動生計轉換意愿形成路徑邏輯的北港村民以非常駐村民為主。值得一提的是,個體認知導向和家庭責任驅使邏輯的2類村民,對待生計轉換等待觀望和謹慎期待的意愿態度,反映其既希望從事旅游經營,又希望能保持傳統生計的“旅游兼業”愿景;外部環境推動邏輯的村民則對發展從事旅游生計表現出積極參與態度,呈現為一種典型的“旅游主導”形式。研究發現,支持旅游主導的村民僅占少數,該類村民往往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且大多往返于農村老家和城市新家之間。經濟資本的豐富使該類村民逐漸擺脫對傳統生計的依賴,新的業緣關系使其具備的經濟資本作用逐漸放大,致使其在旅游發展過程中不僅承擔著因地緣關系而存在的村民角色,還承擔著因社會分層和經濟積累所賦予的市場資本角色。于是該類村民迫切想要抓住機遇參與旅游經營,實現旅游生計的轉換。但受限于該部分村民在整體村民中的較低占比,其與大部分常駐村民對待生計轉換的等待觀望和謹慎期待的意愿態度產生矛盾,這從村民主體能動層面解釋了案例地在旅游發展初期生計轉型較為緩慢的原因。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文以海口北港島為案例地,運用訪談、文本編碼歸納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等方法,識別了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影響因素,并對其形成路徑和機制展開探討,得出的主要結論有:
第一,本文探索得出政策引導、游客進入、人力資本、地方情感、生計滿意、經濟資本和家庭壓力7個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影響因素,影響因素之間具有非對稱性、復雜異質性和動態過程性特征。以往關于村民生計轉換的研究多以可持續生計框架為理論基礎,以五大生計資本切入,探究其與生計策略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未能體現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從無到有的完整過程中影響因素的動態作用以及村民在生計轉換過程中的能動作用(崔曉明 等,2018;孔令英 等,2021;劉格格 等,2021)。本文從村民個人主觀意愿出發,編碼歸納了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影響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上述缺失,并以此作為探索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多元組合路徑和機制的前因要素。
第二,在7個影響因素中,游客進入和地方情感是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必要條件,但所有單變量均不構成充分必要條件,各影響因素必須以條件組合形式發揮作用。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共產生4 條組合路徑,根據其形成邏輯可劃分為3 類——個體認知導向、家庭責任驅使和外部環境推動,3 類邏輯在生計轉換意愿形成中發揮不同水平作用。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并非只依賴單因素作用,也并非所有影響因素的存在與交互就能對生計轉換意愿產生影響,需從條件組合角度分析不同影響因素對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作用關系。
第三,對于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邏輯來說,個體認知導向邏輯解釋力最高,反映人力資本、地方情感和生計滿意的綜合作用,是高度個人意志的邏輯體現;家庭責任驅使邏輯解釋力適中,包含經濟資本和家庭壓力組合,體現收入、房產和父輩、子輩壓力對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正向影響;外部環境推動邏輯解釋力最低的,該路徑脫離人力資本和家庭壓力等因素影響,依靠政策引導和游客進入等外部條件,再加之較強的經濟資本來促使意愿形成。代表個體認知導向和家庭責任驅使形成邏輯的村民以常駐村民為主,其對待生計轉換表現出等待觀望和謹慎期待的意愿,希望通過“旅游兼業”實現旅游生計轉型,整體意愿較弱;代表外部環境推動形成邏輯的村民以非常駐村民為主,渴望通過積極參與旅游經營實現生計轉換,表現為一種典型的“旅游主導”形式,整體意愿較強。常駐與非常駐村民在主觀層面對不同生計轉換意愿在形成路徑構成要素上的差異,造成不同村民群體的意愿強弱分異,成為當地生計轉型受阻的主要原因。
4.2 討論
本研究在尊重生計轉換進程中村民主體地位和主觀意愿的基礎上,分析旅游發展初期村民生計轉換意愿的形成路徑和機制,拓展了現有生計轉型理論。同時,將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引入生計研究,為分析生計轉換前置影響因素與后置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提供新的方法。
事實上,農戶作為可持續生計框架中的基本動力單元,是目的地社區生計研究的主要對象。然而,將生計轉型研究過多聚焦于農戶會忽視因村民個體主觀意愿差異而對農戶內部造成的異質化影響。尤其在農戶內部意愿不一致的情況下,需經歷農戶內村民個體間的爭論和協商才能進入到生計轉型的決策與執行階段。因此,本研究對村民個體對生計轉換形成意愿的關注有效解決了生計轉型的邏輯起點和關鍵節點問題,但從個體尺度到農戶尺度的生計轉換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路徑障礙和效應機制仍是未來需要關注的重點。
本文具有一定實踐啟示:1)深化村民對本地旅游發展趨勢認知和地方情感感知。游客進入和地方情感是實現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必要條件和無法回避的組態條件。因此,可利用村委、鄉賢等構建的熟人網絡對普通村民施加影響,進行有關當地文化特色、旅游資源稀缺性、旅游發展趨勢等方面的宣講、溝通,在提升村民對地方的依戀、歸屬、認同的同時,加強村民對旅游發展現狀的認識,為生計轉換意愿路徑形成提供必要條件。2)完善旅游生計轉型激勵制度。經濟資本薄弱和家庭壓力較大是阻礙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相關部門應綜合考慮村民當前生計現狀,因地制宜地制定退出傳統生計方式的補償標準,確保村民生計轉換意愿形成的經濟基礎,并對發展餐飲、民宿等參與旅游經營的農戶給予貸款和稅收優惠支持等方面激勵,讓村民切實感受到旅游發展帶來的增收效益和經濟保障。3)加強旅游知識技能的教育培訓。可針對不同年齡段和文化層次的村民群體進行旅游技能培訓,鼓勵村民結合當地特色資源和自身傳統生計技能學習民宿經營、導游講解、直播售貨等領域知識技能,解決部分村民因自身人力資本無法滿足旅游發展需要而產生的畏難與顧慮情緒。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由于受調研條件和案例地村民語言溝通的限制,僅將部分村民作為受訪者進行深入訪談,未來可進一步擴大受訪者樣本范圍,驗證結果的外部效度。2)結論主要基于定性數據,通過橫向跨案例比較,分析復雜關系間的因素組合,未能像縱向案例研究對形成路徑和機制進行深度演繹。未來需對個案進行深入探討,對結果進行三角數據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