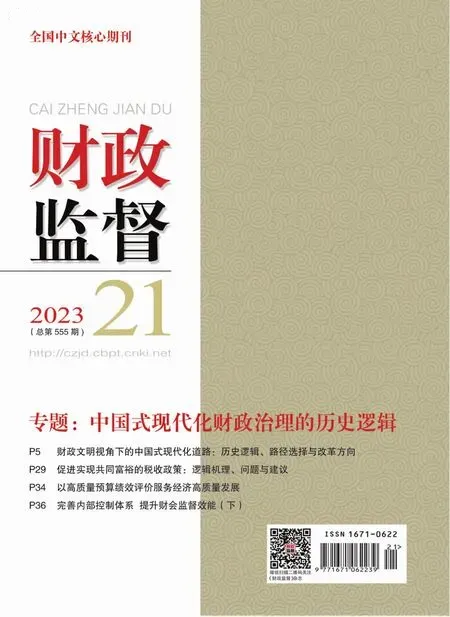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研究
——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
●魏吉華 肖 青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是政府履行財政職能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亦是政府財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衡量指標。我國于1994 年實行分稅制改革,與之相伴而生的是“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分權財政體制, 使得我國地方政府在事權與支出責任錯位的壓力下財政收支出現巨大的缺口, 長期以來面臨著嚴重的縱向財政失衡問題。 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 再加上增值稅留抵退稅等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持續推進、 新冠疫情反復和國際局勢動蕩等事件的沖擊, 地方財政收入增速持續放緩。 與此同時,我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支出卻呈現剛性增長的態勢,導致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地方財政自給率呈現趨勢性下降,對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態, 它的誕生與蓬勃發展, 不僅深刻影響著每個微觀主體的生產及生活方式,也影響著全球經濟的整體格局及長期發展趨勢。 在全球整體發展環境不確定性風險進一步加劇的背景下,數字經濟的逆勢增長逐漸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為地方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機遇與挑戰。 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會影響地區間的稅收收入分配;另一方面,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會給地區間的稅源建設、稅收征管甚至稅制改革帶來沖擊,對地方財政收入產生較大影響,進而影響著地方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那么,數字經濟的發展如何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這種影響通過何種機制產生作用? 對不同區域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 數字經濟能否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影響鄰近省份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這將是本文后續探究的核心問題。
“數字經濟”是近年來學術界的重要研究焦點, 現有文獻主要圍繞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展開: 在微觀層面上, 驗證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Tortora et al.,2021)、企業避稅(張乾等,2022)以及企業價格加成(柏培文和喻理,2021)等方面的影響。在宏觀層面上,驗證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創新、產業結構、經濟發展以及財政分權等領域的影響。 數字技術的進步與發展顯著地促進了我國區域創新效率的整體提升(白俊紅和陳新,2022;張慧等,2022),通過改造傳統產業(馬曉君等,2022)、催生新產業新業態(Pradhan et al.,2019)、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和城市研發創新能力(韓健和李江宇,2022) 等途徑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趙濤等,2020; 徐曼等,2022)。 張紅偉等(2021)指出數字經濟發展主要通過擴大增值稅規模、增加個人所得稅規模和提升經濟開放水平三條途徑強化財政分權。
關于財政可持續性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財政可持續性內涵的研究方面,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首次對財政可持續性的內涵進行闡釋,他從國債發行角度出發,指出國家財政喪失可持續性的情況,即一個國家無法承擔利息和新債的發行。 在此基礎上,財政可持續性理論不斷完善,眾多學者分別從政府債務(Bohn,1995)、償債能力(Greiner et al.,2006)、財政收支平衡(崔惠玉等,2022) 和籌資能力(Bajo-Rubio et al.,2019)等角度對財政可持續性進行了分析。 第二,在財政可持續發展影響因素方面,學者們多從疫情沖擊(呂冰洋和李釗,2020;叢樹海和黃維盛,2022)、減稅降費(鄧曉蘭等,2021)、人口老齡化(張翕,2021; 邱國慶和楊志安,2022) 和金融環境(劉建國和蘇文杰,2022)等方面展開討論。 在數字經濟發展與財政可持續性之間關系方面, 鄧達等(2021)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探究,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顯著提升地方財政可持續能力,且具有一定的區域差異性。 由于固定效應模型忽略了空間交互效應,劉建民等(2021)將空間因素納入考量,在構建空間杜賓模型時分別使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和經濟距離權重矩陣,從空間溢出視角進行深入分析,認為本地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鄰地的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負向空間溢出效應。
綜上可知,目前大部分文獻側重于對數字經濟或者財政可持續性單方面的研究,直接探討數字經濟發展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之間的因果聯系的文獻較少。 此外,現有文獻并未明確清晰地闡述數字經濟通過何種路徑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因此,本文基于我國30 個省份2011—2021 年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指標體系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水平,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及影響效應,可能有的邊際貢獻包括:第一,拓展了數字經濟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相關研究。 不僅能夠拓展數字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也能夠細化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研究內容。 第二,細化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影響路徑的研究。 從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以及政府債務三個角度進一步深入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 第三,多角度證實了數字經濟發展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 從作用機制、空間溢出效應與區域異質性的角度探討了數字經濟發展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之間的時空演化特征,較為全面地量化研究了二者間的關系。 此外還采用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方法對實證結果進行檢驗。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直接影響機制
數字經濟發展對財政收入端產生直接影響進而推動財政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升,主要體現在稅收收入和稅收征管方面。 首先,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能夠顯著推動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增長 (艾華等,2021)。 一方面,數字經濟的普惠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生產者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精準識別消費者偏好進行生產,更高效地滿足消費者需求。 與此同時,移動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行交易,提高交易頻率以及交易規模 (楊志安和胡博,2022),增加企業營業收入,進而起到涵養稅源、擴大稅基的作用。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賦能于傳統產業,加快對傳統產業的改造,還可以通過數字產業化催生出新型產業以及商業模式,從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馬曉君等,2022)和經濟效率提升,有利于推動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和涵養高質量財源。
其次,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加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 (段丁強等,2022),提高主體稅種占比,優化稅收結構。 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大了數字平臺在經濟活動中的應用,能夠拓寬勞務以及貨物的交易范圍,直接帶動其交易規模的提升,進而推動增值稅稅基的增長,增加增值稅稅收收入。 數字經濟在推動企業轉型升級以及拉動企業進行實體投資的同時, 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企業所得稅以及個人所得稅稅基增長,擴展所得稅稅收收入增長空間(谷成等,2022)。
最后, 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提高稅收的征管水平。就納稅方而言,稅收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充分運用強化了稅源管控, 可以顯著地提高稅務部門稅務稽查的準確性, 加大避稅行為被發現與被處罰的概率(徐捍軍,2021),進而有效抑制偷稅漏稅行為。 就征稅方而言,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推動了政府征管的數字化轉型(宋寶琳等,2022),例如金稅工程的不斷升級以及掌上軟件的普遍應用, 可以有效地簡化辦事流程,提高征稅效率,節約征稅成本,同時能夠推動稅收優惠政策的推廣與落實, 有利于提高社會納稅遵從度。
(二)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間接影響機制
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財政支出、政府債務等方面。就財政支出方面而言, 數字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等方式緩解財政支出壓力(張偉亮和宋麗穎,2023)。首先,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有效帶動經濟的增長。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本身及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再加上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改變就業方式,例如居家辦公和在線接單的實現, 使更多的就業者可以突破工作地點與時間的限制, 這為居民就業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有利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進而促進居民自我保障能力的提升,緩解政府社保、醫療以及扶貧等剛性支出壓力(鄧達等,2021)。 此外,整體宏觀經濟環境的優化也有利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轉化為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公共產品與服務, 提高單位財政支出的效率。
其次, 數字經濟快速崛起的背后正是高新技術產業的飛速發展, 現代信息技術使得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平臺來處理公共財政的信息及數據, 實現政府不同部門之間數據信息的快速共享, 方便部門之間的相互交流與溝通, 有助于緩解政府決策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 更好地了解社會公眾對公共產品的需求與偏好, 為政府財政支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精準有效的依據; 同時隨著數字財政和電子政務的不斷發展,政府財政信息的獲得更加容易,政府財政資金的使用過程也變得更加透明 (宋寶琳等,2022),特別是將數字技術融入到我國全面預算績效管理之中,有利于我國構建全方位的財政監督體系,強化財政監督,減少財政資金的浪費,進而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張偉亮和宋麗穎,2023)。
就政府債務而言, 數字經濟發展主要通過縮小政府債務規模和提高債務融資效率兩個方面降低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首先,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 尤其是抑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擴張(朱冠平等,2022)。過去我國實體經濟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等融資約束問題, 地方政府只能通過大量發行城投債的方式來推動地方經濟增長, 導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日益增加。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許多新型金融業務與新型融資模式的誕生,例如網銀支付、線上購物和銀行信貸等,突破傳統融資局限,提升金融資產配置效率,使得企業較為容易獲得相應的融資資金和金融服務, 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袁鯤和曾德濤,2020; 郭峰等,2020),降低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城投債以及增加隱性擔保等方式來干預經濟的成本, 此時區域經濟也可以得到高質量發展, 不需要地方政府通過大規模地擴大債務規模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提高了財政資金透明度, 便于對地方政府發行隱性債務的監督管理, 可以有效抑制隱性債務的發行。另外,現有數字技術在金融體系的運用可以使得企業以及政府部門加大對國內外投融資交易的監控, 加上線上網絡交易活動的過程全程留痕,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活動的可追蹤性,可有效抑制金融洗錢以及偷漏稅行為, 有助于增加地方稅收收入, 而稅收收入增長將減少地方隱性債務的發生(梁曉琴,2020)。
其次, 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效率(侯世英和宋良榮,2020)。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容易受到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 數字經濟發展帶動了數字金融的發展, 可以進一步豐富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渠道,實現更多可配置資金的吸收與整合。與此同時由于數字金融技術的不斷發展可以有效提高地方政府財務信息和負債信息的透明度, 進而提高融資市場上政府債券信用評級(潘俊等,2016),再加上數字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 可以增強地方債務承受及償還能力, 有助于增加政府信用并進行債務融資,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違約概率以及借貸成本,提高地方政府融資效率,從而縮小地方政府的借債規模。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和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三種機制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相應影響機制如圖1 所示。 在此基礎上,提出研究假設H1 和假設H2:

圖1 數字經濟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機制
H1: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H2: 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和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進而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三)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空間溢出效應
在數字經濟發展新時代,各地區之間經濟活動的邊界性正在不斷被弱化,社會經濟資源以及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更加迅速,與此同時,數字技術以及數字要素的誕生更是使數字經濟的發展突破了時空上的限制。 然而由于數字經濟發展處于初級階段,該領域仍存在“贏者通吃”現象(鄧達等,2021), 數字經濟發展規模越大越容易吸引其他省份的技術、資本以及人才等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生產要素流入本省,很有可能形成明星經濟體而導致壟斷市場,搶占中小城市的市場份額,在損害競爭的同時不利于其他省份的經濟發展以及稅收增長,擴大地區間的稅收收入差距, 進而造成稅收領域的“馬太效應”(谷成等,2022)。
從區域發展和優惠政策來看,由于廣東、江蘇以及浙江這些地方自身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無論是科技創新水平、人才儲備還是基礎設施等都具有先發優勢。 為抓住數字經濟發展機遇,這些省份制定了大量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以吸引數字經濟要素的流入,而憑借自身的優勢,再加上各省份之間存在的“數字鴻溝”問題,其優惠政策與其他省份相比自然更具有吸引力(曹靜韜和張思聰,2022),從長期來看會對其他省份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產生不利影響。 因此,數字經濟在促進本地區財政可持續能力提升的同時,在數字經濟“虹吸效應”的作用下,其對周邊地區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會產生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劉建民等,2021)。 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H3:
H3: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具有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樣本數據為2011—2021 年全國30 個省份(不包括西藏)的面板數據。 除特別說明,數據來源于《中國財政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EPS 數據庫、Wind 數據庫等。 為了提高數據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對樣本數據做如下處理:部分年份的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和各省份的年均增長率予以補齊;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水平上進行縮尾處理。 經過上述處理,最終得到330 條面板數據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地方財政可持續性(sustain):根據財政可持續性的內涵,同時借鑒劉建民等(2021)的部分衡量指標,從財政運行穩健性、財政風險可控性及財政體制科學性三方面綜合衡量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具體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測度指標體系
(1)財政運行穩健性。 選取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收入可持續性和財政支出穩定性三個指標衡量地區財政運行穩健性。 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實際GDP度量。 將財政收入可持續性細化為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增速、財政收入結構和土地財政依存度四個三級指標,其中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反映出當地人均貢獻財政收入的程度,可以體現當地財政收入狀況以及可利用財力的多少;一般公共預算增速反映了地區財政收入增長潛力;財政收入結構可以較好地衡量地方財政收入的質量,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越高, 地方自有財源越穩定,財政收入質量也就越高;土地財政依存度反映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 其依賴度過高會威脅到地方財政的穩定性。 財政支出穩定性用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度量, 主要因為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地方財政支出壓力。
(2)財政風險可控性。 選取財政自給率和地方債務風險兩個指標衡量風險可控性。 財政自給率用財政收支缺口度量。 財政收支缺口是衡量地方政府支出職能和收入能力之間結構性失衡的重要指標,當財政收入可以滿足所承擔的事權所需要的支出時,財政收支缺口較小。 地方債務風險用政府負債率度量。 政府負債率反映出當前的經濟規模對地方債務的承擔能力,是衡量政府債務規模的相對值指標。
(3)財政體制科學性。 選取財政分權度和預算偏離度兩個指標衡量財政體制科學性。 財政分權度用收入分權度量。 收入分權能夠反映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的稅收權, 代表地方政府分享國家財政收入的能力。預算偏離度用收入預決算偏離度度量。收入預決算偏離度能夠反映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執行情況,代表地方財政管理水平的高低。
2.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借鑒曹靜韜和張思聰(2022)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該體系內容涵蓋數字經濟應具備的“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兩大典型特征。 這也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所提出的數字經濟核心內涵相一致。 為消除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在權重處理上,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各變量的數據進行處理, 將多個具有很強相關關系的變量轉化為較少的綜合變量(即主成分變量)。 與此同時,為方便比較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采用最大最小歸一化的方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 各細分指標的具體定義如表2 所示。 標準化公式如下所示:

表2 地方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測度指標的年份,ordigitali,t為主成分分析法處理之后直接得到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ordigitalmax和ordigitalmin分別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最大值與最小值,digitali,t為標準化后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由此進行標準化處理后,所有指標值均介于0—1 之間,指標數據越大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
3.機制變量。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rev):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來度量。 為統一比較標準,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進行標準化處理。
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efe):借鑒龐偉和孫玉棟(2018)的做法,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 模型) 測算出的技術效率值作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其中輸入指標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輸出指標包括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地區生產總值,這兩個指標分別代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地方政府債務規模(debt)。 采用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度量。
4.控制變量。 參考已有相關研究文獻,選取一系列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可能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各省份人均生產總值度量,同時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標準化處理;金融發展水平(fina),用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度量;工業化程度(indus),用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度量;技術創新能力(inov),用科學技術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來度量;對外開放程度(fdi),用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度量。 所使用的變量及其定義詳見表3。

表3 變量定義表
(三)模型構建
基于研究假設H1, 為考察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 同時經過Hausman 檢驗后,設定如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sustaini,t表示省份i在第t 年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digitali,t為核心解釋變量, 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Σ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μi控制個體固定效應;λt控制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α1衡量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當α1顯著為正時,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假設H1 將得到驗證。
為進一步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參照Dell(2010)和江艇(2022)等學者的做法,對“數字經濟發展→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數字經濟發展→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和“數字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這三種作用機制進行實證檢驗。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作為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因素, 其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已得到普遍驗證。 因此,分別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rev)、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efe)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debt)作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revi,t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efei,t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debti,t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如果式(3)、(4)和(5)中的系數α1、β1和δ1在統計上顯著且方向符合預期,則表明作用機制存在,即“數字經濟發展會通過改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 進而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假設H2 將成立。
最后, 為進一步探討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空間溢出效應, 設定空間計量模型進行檢驗。為確定具體的估計形式,首先進行了LM 檢驗,初步確定建立空間杜賓模型; 其次,Hausman 檢驗和LR 檢驗結果證實要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再者,進一步進行Wald 檢驗, 結果表明SDM 模型不會退化為SAR 和SEM 模型。 綜合以上檢驗結果,設定如下空間杜賓模型:
其中,ρ 表示空間自回歸系數,Wi,t為空間權重矩陣,使用0—1 鄰接矩陣進行回歸估計。 β1為解釋變量digitali,t的回歸系數;β2為自變量空間滯后項系數,代表解釋變量digitali,t的空間溢出效應對被解釋變量sustaini,t的影響;ρ 反映被解釋變量sustaini,t的空間溢出效應對sustaini,t的影響。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4 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結果表明,地方財政可持續性(sustain)的均值為0.351,最小值為0.217,最大值為0.806,兩者相差較大,表明不同省份之間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差距懸殊。 樣本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的均值為0.290,最小值為0.014,最大值為0.997,同樣表明不同省份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顯著差異, 與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現狀相一致。 其余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與已有文獻基本保持一致,說明數據特征均處于合理范圍之內。

表4 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基準回歸分析
表5 報告了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5 的第(1)列只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第(2)至(6)列依次加入控制變量。 回歸結果可見,隨著控制變量的加入,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的估計系數有所下降,但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從總體上而言, 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在前文理論分析部分已經指出,數字經濟的發展在促進社會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 可以緩解財政收支矛盾,改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進而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因此,研究假設H1 得到驗證。
(三)作用機制分析
表6 報告了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如表6 第(1)列所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rev)的回歸系數為0.459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經濟的高質量增長,涵養高質量財源、擴大稅基和優化稅收結構, 同時還可以提高稅收的征管水平和效率,從而促進財政收入的增加。 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進而直接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表6 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檢驗
財政支出效率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如表6 第(2)列所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與財政支出效率(efe) 的回歸系數為0.414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優化財政資源配置,有利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轉化為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公共產品與服務, 提高單位財政支出的效率。 與此同時, 數字經濟發展還有助于政府了解社會公眾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進而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財政支出政策, 從而通過提高地方財政支出效率間接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類似地, 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如表6 第(3)列所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對地方政府債務規模(debt)的估計系數為-0.252 且在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這與前文作用機制分析相一致, 即數字經濟發展可以有效提高債務融資效率和減少地方政府債務余額, 進一步縮小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緩解政府債務壓力,進而間接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綜合列(1)、(2)和(3)可知,研究假設H2 得到驗證, 即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和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進而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四)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在進行空間計量回歸分析之前, 采用Moran’I指數法對被解釋變量地方財政可持續性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見表7。 從表7 可以看出,2011—2021 年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在鄰接矩陣下的Moran’I 指數均達1%的顯著性水平, 且均為正值,說明2011—2021 年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可能存在正的空間自相關性(即空間依賴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使用空間計量模型來進行空間效應的估計是適宜的。

表7 2011—2021 年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全局Moran’I
表8 前三列報告了在鄰接矩陣下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空間回歸模型的結果。 為提高估計的穩健性,進一步列出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的回歸結果。 從中可以看出,不同模型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 與研究假設H1 結果相一致。 為了更好地揭示數字經濟發展對本地和周邊地區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 使用偏微分方法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效應進一步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分解結果見表8。 直接效應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直接帶動本地區地方財政可持續能力的提升; 空間溢出效應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具有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本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對鄰近省份的財政可持續性具有負向影響。 由于數字經濟發展在各省份間負向的溢出效應部分抵消了在各省份間正向的直接效應, 所以數字經濟發展對各省份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總效應并不顯著。 這些實證結果印證了數字經濟在其發展前期階段, 各省份之間的交流合作體系尚未形成, 各地區在制定本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策略時缺少統籌規劃與分工合作,難以實現資源共享,導致地區間相互爭奪技術、 資本以及人才等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生產要素, 由此本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反而不利于鄰近地區財政可持續能力的提升, 研究假設H3 得到驗證。

表8 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空間溢出效應
(五)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我國地區間資源稟賦以及發展階段存在較大差異,各地區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財政可持續水平都有著明顯的異質性,為考察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分別對東部地區、 中部地區以及西部地區進行分組回歸,具體結果如表9 所示。 可以發現,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回歸系數為0.092,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而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該作用并不顯著,表明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促進效果更強。 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雖然東部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更高,但是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可能已經得到充分釋放,其影響效益會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數字經濟發展進一步提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有限。 對于西部地區而言,雖然數字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數字經濟發展較晚,但是其發展紅利正在逐漸釋放,加上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支持,可以更大強度地增強當地財政可持續性。

表9 數字經濟發展影響財政可持續性的區域異質性檢驗
(六)穩健性檢驗
1.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借鑒楊慧梅和江璐(2021)的做法, 重新構建指標體系來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對其進行重新回歸。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指標體系后的估計結果如表10 第(1)列所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回歸系數為0.062,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有效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起到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的效果,這與前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說明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表10 穩健性檢驗結果
2.變更時間區間。為了排除樣本區間設定的特殊性,將模型(2)、(3)、(4)的樣本時間區間依次設定為2011—2015 年、2013—2020 年、2016—2021 年,回歸結果如表10 列(2)、(3)、(4)所示。 在新的樣本區間下,數字經濟發展(digital)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sustain) 的回歸系數至少在10%的水平上正向顯著,這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顯著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與前文結論基本一致,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3.工具變量法。由前文基準回歸結果可知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但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越高的省份, 地方政府也具有更多的財力支持其數字經濟建設, 進而帶動當地數字經濟發展,因此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
為緩解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借鑒黃群慧等(2019)的設置方法,其構造各省份1984 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量與上一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時間有關) 的交互項作為當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 理論上看,固定電話等通信方式的普及往往預示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而數字經濟的發展與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息息相關, 所以固定電話等通信方式會從技術水平和基礎設施等方面影響著數字經濟的發展, 這樣固定電話普及率越高的地區極有可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 選取固定電話數量作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的要求。 同時固定電話作為通信基礎設施,主要是通信運營商出于商業目的為人民提供通信服務, 并不會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產生直接影響, 滿足外生性的要求。此外,考慮到研究樣本為面板數據,借鑒Nunn &Qian (2014)的做法,在工具變量中引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滯后項(與時間有關) 來構造面板工具變量。
回歸結果如表11 第(1)列與(2)列所示,列(1)中的第一階段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選取的工具變量通過了相關性檢驗,F 值大于10 表明通過了弱工具變量檢驗, 以上檢驗共同印證了所選取工具變量的合理性。 列(2)表明,在第二階段的回歸中,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回歸系數為0.667,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能力的提升作用依然存在,基準回歸分析的結論仍成立。

表11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 借助信息與通信技術,在推進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也給不同地區的財政可持續性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基于2011—2021 年我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在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水平的基礎上,通過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及影響效應。 主要研究結果如下:第一,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第二,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和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進而增強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第三,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具有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本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鄰近地區財政可持續性具有負向影響。 第四,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地方財政可持續能力的提升效應更明顯。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 我國地方政府要緊抓數字經濟轉型機遇,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為地方財政擴大稅基和培養稅源, 同時將數字化變革性力量融入財政工作當中, 從而賦能財政可持續能力提升。 一方面要加快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新基建”水平,加大對數字核心技術攻關的投入,為數字經濟發展奠定必要的平臺與技術基礎。另一方面, 要引導數字信息技術深度融入實體經濟與產業發展當中, 借助數字技術不斷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激發傳統產業活力,積極引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 從而帶動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 在此過程中,政府部門還要制定有關的政策措施來引導數字經濟發展, 例如可以出臺財稅優惠以及金融激勵等措施, 從而讓企業敢于加大對數字化以及信息化的投入,切實解決企業的后顧之憂,提高其綜合效益。 此外,要加快推動財政數字化轉型。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 擴展大數據在財政資金領域應用的深度與廣度,建立跨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以及業務協同處理的新模式, 進一步構建服務智能化數字型政府,利用數字技術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并改進宏觀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果。
第二,各省份在推動本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合作,進行錯位競爭,構建區域財政協同發展網絡體系, 以弱化空間溢出效應的抑制效應。 在國家層面,首先,要健全數字經濟治理的框架體系,圍繞數字經濟產權確定、信息安全以及稅收征管方面的問題, 完善有關的治理體系, 堅決杜絕各省份之間為爭奪數字經濟發展機遇而進行技術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現象的發生;其次,要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與應用, 發揮數字經濟的擴散和示范效應,引導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支持數字經濟發展,加快區域之間的協同發展, 使其他更多地區從中受益;最后,還要鼓勵和引導地區間加大在數字經濟以及地方財政可持續領域的合作與交流, 加速數字要素在區域之間的流動,優化區域資源配置,實現資源共享。 在地方政府層面,各省份在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時,要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在發揮地方資源稟賦優勢的同時, 進行區域之間的生產分工與貿易合作,搭建云計算、電子商務以及大數據平臺,彌補生產要素區域分布不均,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數字經濟市場, 有效發揮數字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 從而使數字經濟在提升本地區財政可持續水平的同時, 也可以帶動鄰近地區的財政可持續發展。
第三,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提高地方財政可持續性需要保持戰略定力,深化財稅管理體制改革,合理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緩解財政縱向失衡程度。 首先,要將數字化信息技術充分運用到財政資金預算管理當中, 推動各級政府預算的陽光化, 從而建立全面規范和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 其次,合理劃分數字經濟背景下各級政府間稅收收益,完善現有的稅收治理體制機制,積極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稅收制度體系。 再次,要建立責任清單制度以科學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進一步明確各級地方政府職責權限,構建權責清晰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從而有利于推進各級政府分工協作, 為地方財政可持續能力的提升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最后,中央政府要提高對經濟發展水平較弱以及稅源薄弱地區財政狀況的關注度,完善現有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切實分析當地數字經濟對地方財政的影響, 因地制宜地加大對財政困難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以緩解數字經濟發展給地方財政帶來的風險。
第四, 地方政府在維持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在“開源、節流、增效”上做好文章,防范地方債務風險,兜牢財政平穩發展的底線,助推中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首先,“開源”是指要拓寬收入增加渠道。 地方政府要以數字經濟轉型為機遇,積極發揮數字經濟對宏觀經濟總量提升以及宏觀經濟結構優化的作用, 利用數字技術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經營模式改革等,改善企業營商環境,開辟更多的資金流入渠道。 與此同時,適度合理提高地方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上繳財政的比例, 擴充政府財政收入來源。 此外,還需要推動財政收入征管方式的數字化轉型,切實抓好金稅工程的建設工作,加大對稅源的管控,提高稅務工作的質效,提升企業以及個人涉稅信息的透明度,從而抑制尋租行為的發生,確保相關收入應收盡收,切實保障地方財政收入的穩定。 其次,“節流、增效”是指要合理縮減財政支出規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率。 地方政府可以將數字技術融入到政府支出管理當中, 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透明度,盤活存量財政資金,在保障重點項目以及民生項目的基礎上,嚴格控制培訓費、“三公”經費和會議費等支出,減少不必要的費用支出。 最后,還需要充分利用數字化信息技術強化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新增規模,提高地方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率,以有效控制債務資金沉淀,防范地方債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