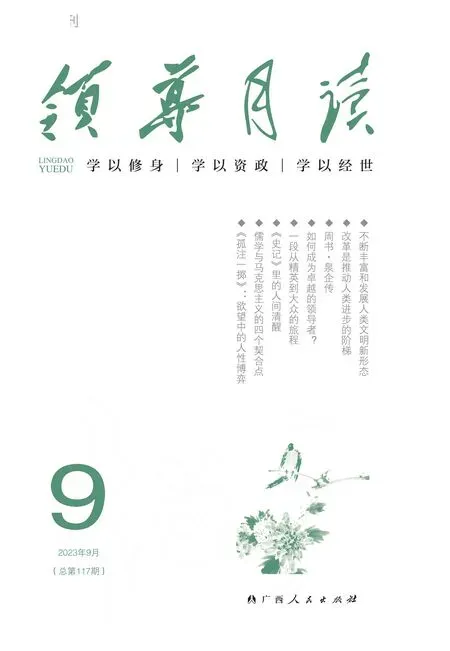交游之間 尤當審擇
劉 敏
古人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與什么樣的人交往,久而久之必然會受其影響,與之同化。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這是朱熹家訓《與長子受之》中的一句話,意在告誡后代:對交往的朋友,尤其要謹慎選擇。關于這一點,曾國藩家書中有類似論述:“擇友乃人生第一要義。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謹慎而交、擇善而友自古即為交友之道。哪些人能交,哪些人不能交,當分良莠、辨真偽、有判斷。
交益友,不交損友。《論語·季氏篇》有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在孔子看來,與正直的人、誠信的人、知識廣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與諂媚逢迎的人、表面奉承背后誹謗的人、善于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與益友交游,在其熏陶下能長知識、增才干,涵養正直守信的品格,受益終身。元稹與白居易詩詞唱和三十余年,往來詩篇千首,相互學習勸勉,共同進步,世稱“元白”。而損友人品堪憂,與其交游則染其墨、受其害,古人有云:“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污。”
交諍友,不交昵友。諍友也稱畏友,“道義相砥,過失相規”,諍友見對方有失,敢直指其過。韓愈和柳宗元志同道合,在推動文學進步中結下深厚友誼。當柳宗元從書信中得知韓愈畏懼刑禍不愿為史時,便寫了一篇《與韓愈論史官書》,一面直言不諱地批評韓愈“不直、不得中道”,一面推心置腹地鼓勵韓愈要忠于職守,做一個剛直不阿的好史官。字里行間力陳其弊、坦誠相見,盡顯諍友風范。而昵友“甘言如飴,游戲征逐”,看到缺點不說,碰到問題不指,與人多是阿諛之詞,又稱“諛友”。碰到這種“好”人,當離則離,當斷則斷。
交摯友,不交賊友。朋友相交,貴在真誠。不分貧富貴賤、不論身份地位,只要志同道合,交往中就能做到肝膽相照、患難與共。這種純潔的、心心相印的友誼,即為摯友。焦裕祿生前愛交四類朋友:熱愛勞動的人、有一技之長的人、生活困難的人、人窮志不短的人。這四類朋友無關權勢利益,焦裕祿卻與他們心貼心、實打實,親密無間。賊友則是勢利之交,“利則相攘,患則相傾”。當有利可圖時,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一旦“勢傾”“利窮”,馬上作鳥獸散,甚至落井下石。這種無品無義之人,自當遠離。
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數。這個“數”就是判斷力,誰是益友、諍友、摯友,誰是損友、昵友、賊友,“尤當審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