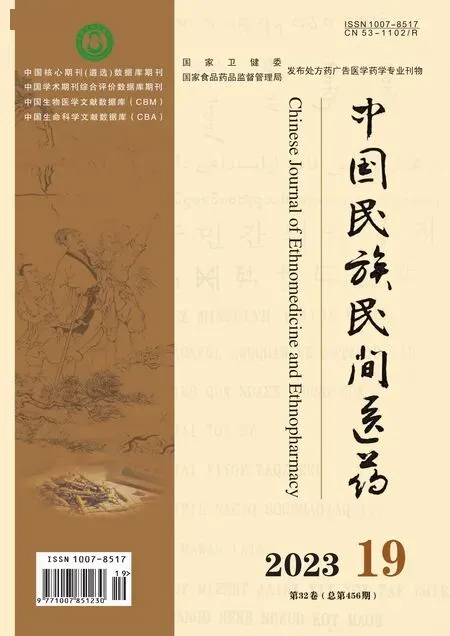基于氣機升降理論探討升陷湯加減治療經行頭痛臨證經驗
李 貴 李晉宏 陳 沫
1.天津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1617;2.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天津 300150
經行頭痛是婦科臨床常見疾病,指每逢經期或行經前后,出現以頭痛為主要臨床表現,經后輒止為特點的癥狀[1]。中醫認為此病為“月經前后諸證”之一,歸屬于“內傷頭痛”范疇。西醫將其歸于“經前期綜合征”范疇。研究[2-3]表明經行頭痛的發生率占經前期綜合征的73.63%,占女性偏頭痛的65%,已嚴重影響女性的正常學習,工作和生活。目前,西醫對經行頭痛的發病機制還不清楚[4]。有研究[5]表明,其病因可能與精神社會因素、卵巢激素水平、泌乳素、5-羥色胺、β-內啡肽、前列腺素因素有關。中醫認為本病的病位涉及肝、腎、脾三臟[6],病機為肝郁、腎虛、脾虛、氣血虛弱、瘀血阻滯、痰濕蘊結等[5-7]。現代醫家們分別采用疏肝解郁[8]、補腎填精[9]、補益氣血[10]、活血化瘀[11]、祛濕化痰[12]等法治療。然,筆者在跟師學習中發現,經行頭痛與氣機升降失調亦存在相關性,臨床運用升陷湯加減治療因氣機升降失調引起的經行頭痛有確切療效。
1 基于氣機升降理論探討經行頭痛的病機
1.1 氣機升降理論 《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地升降相因,形氣交感,則人體陰平陽秘,臟腑和調。若人體氣機升降失常,則百病由生。《素問·舉痛論》稱“百病生于氣”。《讀醫隨筆·升降出入論》認為升降出入者,“百病之綱領”“內傷之疾,多病于升降”。
中醫學認為人體中,心居上焦,腎居下焦,心火下達使腎水不寒;腎水上濟使心火不亢,二者升降有序,水火既濟。肺居上焦,肝居下焦,《素問·刺禁論》中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臨證指南醫案》載“肝從左而升,肺從右而降”,故肝升肺降,二者相反相成,升降協調。脾胃同居中央,且“脾以升為健,胃以降為和”,二者升降相因,納運相得。在此三對氣機升降關系中,以脾胃氣機升降為核心。正如《四圣心源·勞傷解中氣》云“脾為己土,以太陰而主升;胃為戊土,以陽明而主降。升降之權,則在陰陽之交,是謂中氣”,故人體氣機以中氣為樞軸,太陰脾土自左而升,“脾升則腎肝亦升”;陽明胃土自右而降,“胃降則心肺亦降”[13],升降有序,環流不息。
1.2 經行頭痛與氣機升降失調的相關性 《醫宗金鑒·婦科心法要訣》引李時珍言:“女子,陰類也,以血為主,其血上應太陰,下應海潮。”天地陰陽升降,形成自然變化,人稟天地之氣而生,與四時萬物相應,女子月經來潮與潮汐漲落、月之盈虧相應,人體十二經脈之氣血流注盛衰亦如潮汐,呈現周期性運動[14]。而頭為諸陽之會,五臟精華之血,六腑清陽之氣皆上榮于頭,足厥陰肝經會于巔,肝為藏血之臟,經行時氣血下注沖任,而為月經[1]。《雜病廣要·諸血病》認為血為氣母,氣為血帥,“養臟之血”需要氣的溫煦,“灌注之血”需要氣的推動[15],故氣血下注沖任形成月經的整個過程,是在氣推動下行即氣機下降的條件下完成的。《素問·六微旨大論》中言“升已而降”,“降已而升”,《醫碥·五臟生克說》中提及“氣有降則有升,無降則無升”,故人體十二經脈之氣血下注沖任,胞宮滿溢,月經來潮,同時伴隨著五臟六腑之氣血上榮于頭,清竅得養。在整個過程中,人體氣機升降有序,五臟六腑之氣血和暢,上下內外之氣機通達。
《明醫雜著》曰:“胃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也。”脾胃為氣機升降的樞軸,若因飲食勞倦等各種內因、外因損傷脾胃功能,致脾不能升,胃不能降,中焦樞機不利,則不能協調心肺肝腎之升降,全身氣機升降障礙,氣機升降失常,升降同病;血運失調,氣血水同病。如《素問·調經論》說:“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生理狀況下,女子行經期間氣血下注,同時清氣上榮于頭,則氣血和暢,若因中焦脾胃樞機不利,致機體氣機升降失常,清氣不能上榮于頭,清竅失養則發為頭痛,正如《靈樞·口問》言:“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故氣機升降失調亦為引起經行頭痛之病機。
2 升陷湯治療經行頭痛理論探討及方義闡述
近現代著名醫家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云“大氣者,原以元氣為根本,以水谷之氣為養料,以胸中之地為宅窟者也”,誠如張錫純所言,大氣之組成,部分來源于脾胃所化水谷之氣。氣機升降理論也認為中氣即所謂太陰脾土和陽明胃土相交產生,而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軸。故胸中大氣不足或下陷,可見機體氣機升降失調,氣機不能上升,則清竅失養,發為頭痛。與《醫學衷中參西錄》中“其神昏健忘者,大氣因下陷,不能上達于腦,而腦髓神經無所憑借也”亦為同理。
《讀醫隨筆·升降出入論》曰:“病在升降,舉之、抑之。”故氣機升降失常,可用升陷之法或下氣之法治之。張錫純所創升陷湯為治療胸中大氣下陷者,原文:“治胸中大氣下陷,氣短不足以息,……或神昏健忘,種種病狀誠難悉數。其脈象沉遲微弱,關前尤甚。其劇者,或六脈不全,或參伍不調。”原方:生箭芪六錢,知母三錢,柴胡一錢五分,桔梗一錢五分,升麻一錢。《本草綱目》時珍引元素曰:“黃芪氣薄味厚,可升可降,陰中陽也,益元氣,壯脾胃。”故以既善補氣,又善升氣的黃芪為主者。因黃芪性熱,故以苦寒之知母涼潤之。黃元御《長沙藥解》云:“柴胡降膽胃之逆,升肝脾之陷。”故以柴胡引大氣之陷者自左上升。《本草綱目》時珍引元素曰:“升麻手足陽明引經之藥,升陽氣于至陰之下,治陽明頭痛。”故以升麻引大氣之陷者自右上升。葉天士《本草經解》:“桔梗稟天初春稚陽之木氣,入足少陽,手太陽經,氣味俱升。”故以桔梗載諸藥上達胸中之力,用之為向導。故諸藥合用使下陷之氣上升,則氣機樞軸得利,升降得調,清氣上榮,清竅得養,頭痛自可緩解。
3 驗案舉隅
患者孫某,女,29歲,2022年2月15日初診。主訴月經期頭痛2年。患者訴于2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月經期頭痛,疼痛劇烈,需服止痛藥方能緩解。平素月經規律,周期28天,經期6天,經量偏多,經色偏暗夾有血塊。刻下癥見:患者體型偏瘦,面色淡白,月經期第3天,頭痛劇烈,周身乏力,倦怠嗜臥,納可,寐欠安,小便正常,大便3~4日一行,舌淡,苔薄白,三部脈沉弱,寸脈尤甚。既往輕度貧血病史。西醫診斷:經前期綜合征。中醫診斷:經行頭痛(氣虛血瘀證)。治療原則:益氣活血,調理氣機。處方:升陷湯加減。藥物組成:黃芪30 g,升麻6 g,柴胡6 g,知母10 g,桔梗6 g,炒白術6 g,當歸10 g,白芍10 g,阿膠珠5 g(烊化),仙鶴草30 g。共3 劑,水煎服,日1劑。另囑其避風寒,節飲食,暢情志。
2022年2月18日二診。患者訴服用上方后頭痛明顯減輕,周身乏力及倦怠嗜臥癥狀好轉,余癥同前。考慮患者病程日久,且平素飲食不規律,中焦脾胃功能虛弱,故于初診方基礎上加茯苓 15 g,太子參10 g以增強益氣健脾之功;又患者貧血且月經量偏多予蒲黃炭10 g,益母草15 g以加強活血、祛瘀、止血、調經之力。繼服7劑,方法同前。
2022年2月25日三診。患者訴服用二診方后,無頭痛癥狀,乏力倦怠明顯好轉,三部脈較前有力,效不更方,繼服二診方7劑以鞏固療效。隨診兩個月,患者次月月經來潮時無頭痛發生,周身乏力及倦怠嗜臥癥狀近無。
按:根據患者所述,結合患者舌脈,四診和參,辨為經行頭痛,氣虛血瘀證。病機歸為脾胃氣虛,氣機樞軸不利,升降失調。因經血為水谷之精氣所化,隨著月經來潮,氣血下注,由于患者素體虧虛,脾胃之氣機樞軸不利,升清降濁失調,清氣不升,腦竅失養發為頭痛,濁氣不降則大便秘結;氣不化精則周身乏力,倦怠嗜臥;氣不行血則生瘀血故經色偏暗夾有血塊。故治療應以調理氣機升降為主,氣機升降得宜則諸癥皆消。故以黃芪、升麻、柴胡、知母、桔梗之升陷湯為底方總理氣機;酌加白術健脾益氣;當歸補血和血,兼調經止痛、潤腸通便;白芍養血調經;阿膠珠補血潤燥;仙鶴草止血兼補虛。服用此方后,療效顯著。根據患者癥狀變化,二診酌加茯苓、太子參、蒲黃炭、益母草。三診時患者諸癥皆有好轉,效不更方,隨診兩個月,患者總體療效肯定。
4 小結
對于經行頭痛的患者,臨床中并不少見,中醫常以疏肝解郁、補益氣血、活血化瘀等治法為主。升陷湯治療由于氣機升降失調所引起的以三部脈沉弱,寸脈尤甚的病證,療效確切,而經行頭痛患者群中確有病機為氣機升降失調者,故運用升陷湯治療此類患者得到較為理想的療效。因此,對于臨床中遇到的病機為氣機升降失調的疾病,臨床表現不必悉具,符合升陷湯之證候或脈象,運用升陷湯加減治療或也可獲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