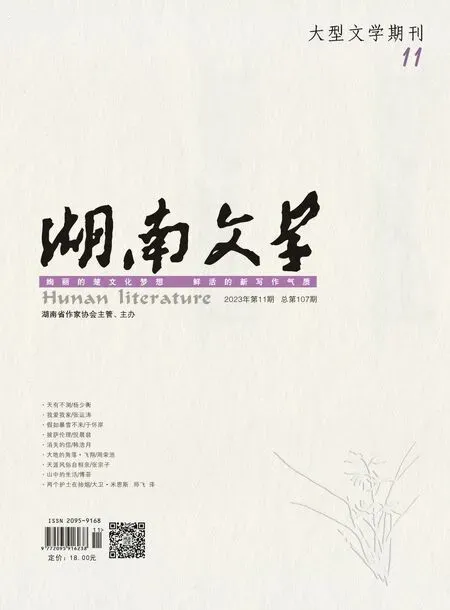假如暴雪不來
于懷岸
起床遲了些。七點時鬧鐘響過一次,魯道夫迷糊中順手劃了下手機屏幕,又睡了過去。現在已是八點四十分,必須得馬上起床。魯道夫很不情愿地從暖烘烘的被窩里拱出赤裸的半個身子,慢騰騰地套上內衣和厚毛線衣,然后再抽出細瘦光溜的雙腿,穿上秋褲和外褲。天色早已大亮,魯道夫下了床,披上大衣后拉開窗簾,眼前依舊是一成不變的景象,遠處寒山瘦水,近處樹木蕭瑟,整個世界一片暗淡,就像剛剛起床的他那樣困倦、頹廢。這是持續了兩個多月之久的寒冬景象,魯道夫知道它還將一成不變地再持續下去很長一段時間。不知為何,第一眼望出去時,魯道夫心里升騰起一股濃重的失落感,小區大院里的樹木、草坪,以及汽車頂上都沒有白晃晃耀人眼目的白雪,遠處的山峰上也沒有。前幾天市氣象臺發布了黃色暴雪預警,昨天一天都是陰暗天,北風倒是有,可連一張紙屑也吹不上天,更甭說見到一片雪花。
今天會下暴雪嗎?
大概率不會吧!
開窗時,魯道夫沒有感覺涼颼颼的冷風迎面撲進來,他的身子更沒有凍得哆嗦顫抖,今天的氣溫并不比昨天低,風倒還沒有昨天的大,魯道夫心想即使下雪也要挨到晚上吧。刷完牙,魯道夫整個人清醒多了,但一直盤桓在他心頭上的那種失落感依舊揮之不去,像被堵住的下水道只差要冒出沼氣泡泡了。這種感覺憋得他心里慌慌的,漱口時手一抖,牙刷掉進盥洗盆里,咣的一聲脆響,嚇了自己一大跳。肯定不是因為好幾年沒看到過大雪了,魯道夫心想,都快四十歲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見到雪就歡呼雀躍,沒見到就心情沮喪,他沒那么矯情,更不會那么幼稚;當然也不是對氣象臺預警不準的不滿。酉北的天氣預報從來都是同事朋友們無聊時打賭的主兒,誰不知道呢?這是一種他說不出來的失落感,這感覺是突如其來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像很多年前,他跟前妻辦好離婚證從民政局大門出來時那樣,本來應該興高采烈歡呼雀躍高歌一曲,但他不僅沒有高興起來,也是倏地就被一股突如其來的莫名的失落感緊緊地攫住全身,差一點他就失聲大哭起來。
五六年過去了,那時的感覺魯道夫至今記憶猶新。
再不能賴床的原因是魯道夫九點前得去烏嘎山參加一個葬禮,十一點前他得從葬禮上撤出,趕回市中心湘聚樓赴一個飯局。烏嘎山是烏嘎山殯儀館的簡稱,也可以說是代指,酉北人不知為了避忌還是為了方便,說起那兒一般都不叫殯儀館,更不叫火葬場,就叫烏嘎山。誰說去烏嘎山,別人就曉得那是要去參加葬禮,就像誰說去西合溝,人家就心知肚明,曉得你有家人或親戚在吃“公糧”,是要去探監。烏嘎山遠離市區,周邊也沒有村子和房屋,更不通公交車,來回不便,魯道夫自己不會開車,他得預留充裕的時間。葬禮是局長的岳父去世,不得不去。飯局是魯道夫自己訂的,更是必須得到。本來去烏嘎山,單位租了輛中巴車,大家統一從單位門口出發,定的時間是九點一十,魯道夫洗完臉刷好牙就到九點過五分了,從他家小區酉水新苑到單位大樓酉北群藝館,就是打的,最快也得十五分鐘以上,等他趕到單位門口,那車早走了。
出門前,魯道夫一直糾結到底怎么去烏嘎山,走大環城約有十二公里,沒有公交車,打的一趟得需三十塊錢,不走大環城,從護佑路轉北門路到城郊,穿過北溪村后再爬一段山路,最多五公里路程,但走這條線,不好打的,的士司機都不愿意去,北溪村沒有主干道,全是小巷子,只要對面來輛小四輪就會堵住。
來到大街上,魯道夫也沒有拿定主意走哪條路線。早餐肯定來不及吃了,魯道夫望著平時經常去吃,現在離他不到五米遠的那家津市牛肉粉館門口鑌鐵大鍋冒出來的白煙,一邊往喉嚨里吞咽口水,一邊腦子里不停地告誡自己,他首先得攔住一輛的士,而不是去吃一碗牛肉面。他極力忍住從粉館里飄過來的熱氣騰騰的誘惑,扭過頭,挺了挺腰板,表情嚴肅地盯著馬路前方。魯道夫右手不由自主地握拳,松掌,叉開五指,擺出一副只要看到出租車就能馬上招手的架勢。今天運氣挺不錯,沒等兩分鐘,對面過來了一輛出租車,魯道夫傾身向前,一腳邁出馬路牙子,高舉右手使勁揮舞。司機注意到了他,只往前開出十來米遠,又掉頭轉回來,停在他面前。
魯道夫上了車,坐上副駕駛座說,往前走。
司機問,去哪?
魯道夫沒有立即回答往哪走,而是思索了兩秒鐘。他想以最快的速度到達烏嘎山,走大環城要過三個紅綠燈,還要經過汽車站,那里是個丁字路口,經常會堵車,就是不堵車,那條長達三公里的老街道進站出站的大型客車和中巴車特別多,一路也得走走停停,到烏嘎山最快得二三十分鐘;走北溪村的話,打的到城鄉結合部,一路都是主干道,只有一個紅綠燈,三公里路程大概率暢通無阻,最多七分鐘能到,若是司機不肯進村,再從北溪村步行二公里,到烏嘎山再花十五分鐘足夠矣。魯道夫覺得這個路線比走大環城更快,既省時也省錢,何樂而不為呢!于是他大聲地說,到北門口,好又來廣場。
司機戴著帽子,聲音沙啞,魯道夫以為他是個年輕小伙子,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才發現是個女司機。這時她的手機剛好來了電話,她接通了,開的是免提,對方的聲音是個雄渾的男中音,老婆,等下你別去鄉下送人。
女司機問,為啥?
天氣預報說今天有暴雪。
這天氣有暴雪,女司機笑著說,你有病它也不會有雪。
萬一要是下了呢?
假如暴雪不來呢?女司機反問道,我就是干這活兒的,有活兒不干,西北風能喝嗎?
說完,她就掛了電話,抬頭專注地看著即將到來的紅燈轉綠。兩秒后,她松開剎車,車子啟動,繼續載著魯道夫往北門口奔去。
出租車快到廣場時,魯道夫看到北門路與北溪村連接的那座水泥預制板搭建的小橋上空蕩蕩的,沒有一輛過往的車子,他本想問問女司機過不過橋拉他去烏嘎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想女司機既然要去鄉下,開口也是白搭。魯道夫付了車費,下車后朝橋頭走去。
過了橋,魯道夫一頭扎進了北溪村。
此前,魯道夫從未專門來過北溪村,他家住城南,這邊既沒有同事,也沒有親戚朋友,但他曾經路過這里兩次。兩次都是從烏嘎山參加葬禮步行回城的,第一次是一年前他跟一個朋友一起,算是那個朋友帶的路,第二次是三個月前他獨自一人準確無誤地穿過整個村莊里的小巷子,一步未錯地到達了北門路口。這也是他今天有把握從北溪村步行到烏嘎山的底氣,否則他就不敢選擇這條線路了。過了小橋,魯道夫沿著小溪河堤往前走。他記得往前走約三百米左拐進一條小巷子,沿這條小巷再走四五百米,就是一片開闊的菜地。菜地大約有幾十上百畝,穿過菜地,往前二三十米,走上一段小斜坡后就能看到烏嘎山半山上的大環城線。那條環城線,是高速公路出口到酉北城區的連接線,一條標準的二級公路,殯儀館就在烏嘎山隧道一和隧道二之間的路段內側,它藏在兩道陡坡夾角的深溝里,從北溪村的任何位置都很難看到它。
走在小溪河堤上,魯道夫感覺身上有些冷,下意識地裹緊羽絨衣,快步行走。雖然身上冷,魯道夫的臉頰卻熱乎乎的,一點也不冷。河堤上靜悄悄的,沒有一絲風兒帶來的聲響,也許是剛從開有暖空調的出租車里出來,體表有些不適應環境,也許是村子里比市內人少車少廢氣少,溫度要低幾度吧?這么一想,魯道夫心里就釋然了。這釋然剛剛落地不到幾秒鐘,魯道夫感覺到鼻尖上一涼,像什么東西輕輕地在他鼻尖上點了一下,剛觸到他的皮膚馬上又收了回去,接著魯道夫的耳根上也涼了一下,跟鼻尖上的感覺差不多,就像有個小孩子在跟他調皮搗蛋,動作卻很輕柔,善意的,也是怯生生的。接連被戳了三四下,魯道夫不由地轉身往后看了看,身后空蕩蕩的,既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一只貓狗。魯道夫這才意識到了什么,抬起頭望向天空,這一瞧著實讓他吃驚不小,天空中在下雪呢!雪花不大,細細密密,鋪天蓋地,整個天空中撒滿了飄移著白色的細點,很壯觀。魯道夫仰頭看了兩秒鐘不到就趕緊低下頭來,他有輕微的密集恐懼癥,譬如看到溪溝里一團團游弋的千年魚兒他就會緊張,繼而就惡心,頭昏腦漲。平時看到白皚皚的雪景魯道夫會覺得賞心悅目,輕松愉悅,但看到漫天飛舞的雪花就不行,他會心慌,頭暈,盯著看久了更會全身冒冷汗。哦,對了,就像暈車的那種感覺。魯道夫小時候暈車,上車后幾分鐘內就會渾身冒冷汗,二十歲之后他不再暈車了,小時候他也并沒有密集恐懼癥,這癥他自己也不曉得是啥時候找上他的,好像就是這幾年才有的事情。記得十年前有一次他從駐村的寨子趕回市內,獨自一人在漫天大雪里跋涉了整整四個小時,他既沒心慌,也沒頭暈,更沒有跌倒或摔進山溝溝里。魯道夫低下頭,加快腳步,他想雪要是下得再大一些,他很有可能會暈雪,他得趕在暴雪來臨前從烏嘎山回到市區里來,中午十二點的那個飯局對他太重要了,他是萬萬不能遲到的。
不僅不能遲到,他至少得提前十分鐘到達,以示對客人的尊敬和重視。
雪越下越大,也越來越密集,雪花落在魯道夫羽絨大衣上,他的衣袖和胳膊上積了很多片雪花,黑色面料的羽絨服很快就花了,斑駁起來。雪落在他身上,也落到他頭上和臉上,一會兒后,魯道夫滿身都是一塊一塊的白斑,但他自己看不到。魯道夫一直低著頭急匆匆地趕路,就像北溪村某個從城里收工回家的粉刷匠一樣,目不斜視,自顧自地往小巷深處疾行。
魯道夫在巷子里穿行了十分鐘,還沒看到那塊菜地。他記得從河堤拐進小巷不遠有棟二層的歐式小洋樓,紅頂白墻,大門是對著巷子開的,方位是坐西朝東,跟這條巷子里其他坐北朝南的房子都不同。魯道夫回憶了下,想起來這棟小洋樓剛才穿行時他并沒有看到,心想壞了,一定是走錯了巷子。要不要退回去再找那個巷口?猶豫了幾秒,魯道夫又想,北溪村就屁大個地方,所有巷子肯定是相通的,即使走錯了,方向也不會錯,也許再往前走一截路就會到達那個斜坡。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二三百米,還是沒有看到那塊寬闊的菜地,更別說能看到環城線的那道斜坡,他的兩邊依舊是房子。也就是說,已經走了不下一刻鐘,至少走了兩千多米,魯道夫依然沒有走出北溪村,還在小巷子里打轉。魯道夫有點著急起來,抬頭望了望天空,雪花依舊在下,紛紛揚揚,滿天空飄蕩著細細密密的白點,每個小白點都在快速地漂移,不停地變換位置,就像滿溪溝里奮力游弋的小蝌蚪們一樣四處亂竄。這只是小雪,還算不上大雪,更不是暴雪,雪花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并沒有積起來,魯道夫想當務之急趕緊退回去找到那棟坐西朝東的小洋樓,順著那條巷子直走,很快就能走出北溪村。
魯道夫在巷子里又轉了十多分鐘,他已經走得渾身發熱,氣喘吁吁,不僅沒有找到那棟小洋樓,也沒有退出北溪村找到那條小溪河堤。這么冷的天,這么大的雪,村巷里沒有一個人,家家都關門鎖院,問個路也問不到。這等于說魯道夫想按重啟鍵,退回到北溪村河堤上再找到那個坐西朝東小洋樓的巷口的努力也白費了。手機上的時鐘顯示九點五十三分。著急是有點著急,魯道夫依然頭腦清醒,他知道時間還是寬裕的,現在路面一不積雪二不結冰,只要順利找到河堤,再找到那個巷口,步行十五分鐘到達烏嘎山仍舊綽綽有余。他想,到了那,隨個禮記個賬,就可以返回。說是參加葬禮,其實就是送份子錢而已,至于見沒見到局長,說不說句“節哀順變”,對于魯道夫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局長既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局長,即使見了面握了手說了話,估計局長也記不住他。即便局長記得住他,他也記不住局長,下次見面時魯道夫依然跟他是個陌生人,最多只會有點面熟的感覺而已。
魯道夫不僅有密集恐怖癥,他還有臉盲癥。
當然魯道夫也不奢望局長能記住他。
今天真正對魯道夫重要無比的是湘聚樓的飯局,這才是一個既有可能改變他的命運又能影響到他后半生生活的大事!魯道夫寧可錯過前者,也不能錯失后者。魯道夫現在還不想放棄前者,畢竟還有寬裕的時間,退一萬步講,即使他十一點趕到烏嘎山,隨個禮記個賬,哪怕跟局長兩口子寒暄幾分鐘,他只要在十一點半前撤出殯儀館,步行回湘聚樓,最多二十分鐘。當然前提是不像現在這樣穿錯巷子。魯道夫覺得自己又不是傻子,已經錯了一次,還會再錯第二次嗎?想到這,魯道夫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之前那兩次他都是從烏嘎山回來穿過北溪村回市區的,這次是反向而行,視角完全不同,所以才會走錯了巷子。若是現在找對了路,回來時更不會錯。再說回來時,說不準有便車搭或能在環城線上攔到出租車呢。
魯道夫再一次往回走,邊走邊注意巷子兩旁的房子。這時他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規律,北溪村高大漂亮的小洋樓都是坐南朝北的,從小巷這頭望去,沒看到不按規律排列的房子,就是說沒有那棟坐西朝東的小洋樓,他就不進這條巷子。北溪村畢竟不大,雖然巷子錯綜復雜,但都不長,一眼望得到頭。功夫不負有心人,五分鐘后魯道夫找到那棟小洋樓,認真地審視了一番,它確實坐西朝東,紅頂白墻,歐式拱形鐵柵欄大門。不會錯的!魯道夫松了一口氣,步伐堅定,大步流星地再一次扎進北溪村小巷深處。
十分鐘后,魯道夫一屁股坐在一塊已經被雪花浸濕卻沒有積雪的石頭上,使勁地抽動著鼻子。他感覺鼻竇里又酸又麻,還很癢,不是感冒鼻塞,而是他想哭了!他的眼睛紅通通的,臉上像針戳過似的灼痛。鬼打墻呀!魯道夫這次又沒有找到那塊菜地,他又來到了二十分鐘前坐過的那個地方,他的周圍還是房子,他還是沒有走出北溪村巷子。這十分鐘,他走得很快,起碼走了一千多米,要是沒走錯的話不僅早就走過了那塊菜地,還應該翻過了那道斜坡看到烏嘎山的環城線了。魯道夫喘著粗氣,努力忍住不讓眼淚掉下來。他是真的想哭出聲來,但他是一個大男人,不管有沒有人看到,都不能哭啊!天空中的雪花稀疏了許多,不再密密麻麻地飛舞,而是東一片西一片,像池塘里的浮萍一樣在風中旋轉,氣溫一直在下降,天氣比剛進村時冷了很多,魯道夫喘氣時口里冒出大團大團的白煙,他屁股下的石頭也一片沖涼,他也懶得站起來。他覺得需要坐著思考一會兒,他得先把想哭的沖動驅趕走。
為什么要去烏嘎山吊唁一個陌生人呢?
魯道夫首先思考的是這個問題。這是他第二次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第一次是昨晚睡覺前。局長岳父的訃告是昨天中午局長本人發到微信群里的,單位的人都回復了,魯道夫裝著沒看到,下午四點時,館里的微信群也發了租車統一去吊唁的通知,他還是裝著沒看到。說實話,魯道夫不想去,局長是從鄉鎮剛調來不到一周的新局長,魯道夫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魯道夫,可以說是素昧平生的兩個人,誰也不欠誰人情。再說,局長的岳父是誰,是個什么人,是個好人或者壞人,魯道夫也無從知曉。去吊唁一個既不知道他是誰,更不曉得他是個好人還是個壞人的人,就跟你在大街或小巷里碰到任何一戶人家在辦喪事,你就跑進去對著靈柩磕頭作揖一樣,魯道夫覺得既荒唐又滑稽。即便他的女婿是你的局長,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再何況,魯道夫任職的酉北美術館只是局里的二級機構,局長也不是他的直屬上司。尤其令魯道夫反感的是這種群發訃告,純粹就是厚顏無恥的撿錢方式。中國人講究的是禮尚往來,隨份子更是如此,但絕大多數官兒是不會遵守這個規則的,在任時他們也許會抹不開面子不得不應酬一下,若是升遷或調走后,這份人情禮魯道夫是不可能收回來的。酉北這些年來隨禮越來越大,一般同事間往來最少也得二百,好朋友得四五百才拿得出手,上司的話,最低也得隨五百吧。憑啥平白無故,也是有去無回地掏五百塊錢給他呀?想歸這么想,昨晚熊館長打電話來時,魯道夫卻不敢這么說,只得老實承認看到訃告了,告訴館長他明天盡量趕單位的車一起去烏嘎山。掛了館長的電話他才想到,明天曉蘭要回酉北,前天他就在湘聚樓訂了包廂,宴請她一家人。訂餐的二百塊押金都交了。
想到曉蘭,出門前魯道夫給她打過電話,那時她也還沒起床,捂在被子里說十點左右出門。從州城到酉北自己開車要兩個小時,下高速后到市區也要差不多半小時,也就是說,他們一家人最快要十二點半左右才趕得到湘聚樓。開餐時間定的是十二點二十,一切都在計劃中。魯道夫拿出手機,想給曉蘭打個電話,問她州城那邊下雪嗎,她走高速還是走國道。轉念一想,她現在正在開車,接聽電話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于是他把手機揣進了褲兜里。
魯道夫跟曉蘭認識五年了,戀愛也有兩年多了。曉蘭是個女詩人,一般人的觀念里女詩人開放、前衛和新潮,但曉蘭恰恰跟大多數女詩人相反,她是一個思想保守觀念傳統性格也很內向靦腆的女孩子。哦,在魯道夫的眼里,曉蘭就是一個女孩子,她比他小了近十歲,今年還不到三十歲。魯道夫已經想不起他是怎么認識曉蘭的,在什么場合認識的,他只記得認識她的時間是他跟前妻離婚后那年秋天,好像是曉蘭來酉北開會,也有可能是他去州城出差,反正不記得了。他印象里似乎是某一晚在大排檔攤上跟一幫朋友們喝酒,曉蘭也是其中一個,他記得那桌七八個人只有曉蘭堅決不喝酒,魯道夫自己沒喝醉,其他人都喝得東倒西歪,回去時他架著男性朋友小蘭扶著女性朋友,把他們一個個塞進出租車里送回賓館。之后他們又見過好幾次面,都是一眾朋友一起吃飯,聊天,但魯道夫從沒深入了解過她,似乎她對魯道夫也一樣,見面時半生不熟地打招呼,“拜拜”后也從不聯系對方。大前年夏天某晚十點后,魯道夫收到曉蘭的微信,大哥,在干嗎?
魯道夫回,沒干嗎。
曉蘭說,離婚了,想喝酒,不曉得找誰。
魯道夫愣了那么幾秒鐘,回她,你不是從不喝酒嗎?
大哥,可我今天想喝呀!
可我不在州城呀。
我在酉北呀。
原來曉蘭和前夫的戶口都在酉北,他們下午才在酉北民政局窗口辦好證。既然人家在酉北,魯道夫只好披衣起床,出門請她吃夜宵。魯道夫記得很清楚,那晚曉蘭并沒有喝酒,他也只喝了兩瓶啤酒,然后他送曉蘭回父母家。這也是魯道夫第一次知道曉蘭的父母居住在酉北城銅鑼巷里的一棟自建房。幸好那晚曉蘭沒有喝酒,自己也沒有喝醉,魯道夫送曉蘭進銅鑼巷一百米左右時,曉蘭的父母迎面來接她了。很顯然,他們平素對女兒管教很嚴苛。
父親見到曉蘭時劈頭蓋腦地問了句,喝多酒了?
曉蘭說,沒喝酒呢。
母親問曉蘭,那男的是誰?
曉蘭說,一個朋友。
她又著重解釋了下,普通朋友呢。
曉蘭的父親和母親臉色都不好看,他們沒跟魯道夫打招呼,更沒說句謝謝的話,魯道夫很無趣,轉身走了。后來魯道夫才聽曉蘭說她父母都是中學教師,是那種特別古板刻薄的人,既不討學生喜歡,更不討兒女喜歡。曉蘭有個哥哥叫曉天,自從大學畢業在廣州工作后,七八年了從沒回過一次家,不僅因為父母對他管教太嚴,而且他們曾經嚴重地干涉過他的私生活,大四畢業那年他帶女友回家遭到父母堅決反對,不歡而散。聽曉蘭說,反對的烈度之強令人咋舌,父親逼著哥哥寫斷絕父子關系的聲明,母親喝百草枯送進了醫院洗胃。后來曉天在廣州結婚生子,都沒通知他父母。他家住在廣州天河區,什么路什么小區他連曉蘭都不告訴,生怕曉蘭告訴父母后他們找上門去。有一年曉蘭去廣州,哥哥嫂嫂也不帶她去家里,而是給她開了家賓館住。
從去年春天開始,魯道夫跟曉蘭正式確立戀愛關系。自然是倆人私底下確認的關系,曉蘭并沒有告訴她的父母,她說她不想征詢他們的意見,因為根本不需要征詢,一旦征詢必然只會遭到他們的反對。魯道夫比她大了近十歲,這在她父母的觀念里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曉蘭說她離婚后父母一直在替她物色對象,催她相親,那些對象都是跟她差不多年紀的,而且都是未婚的童男兒。在父母的觀念里曉蘭雖是離異,但沒有孩子,也就等于未婚。他們不會考慮離異的男子的,更不會考慮魯道夫這樣的農村進城的男人。
這兩年來,每次曉蘭回酉北,他們都是偷偷摸摸地約會,小心翼翼地開房睡覺,像做地下工作一樣提心吊膽,用曉蘭自嘲的話說,他們就像是一對偷情的狗男女。酉北是座小城,曉蘭父母在城里生活了半個多世紀,教了上千個學生,全城每個角落都有他們的耳目,稍一大意就會傳到他們耳朵里去。
更多的都是魯道夫往州城跑。
現在,已經到了瞞不下去的地步了。曉蘭的肚子日益鼓脹,開始顯山露水。這對于魯道夫來說,當然是欣喜若狂的,也是揚眉吐氣的大好事兒。當年魯道夫與前妻離婚的真正原因,其實并不是離婚協議書中所填的感情不和,而是另有隱情。一句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結婚后一直沒有小孩。去醫院檢查過,兩人都沒有問題,但就是懷不上。一開始魯道夫對有沒有小孩也抱無所謂態度,都什么年代了,現在丁克的家庭多的是,但前妻可不那么想,她一直想要一個孩子。魯道夫提議過做試管嬰兒。前妻馬上否決了,說她不想做那么多檢查,說那種檢查在醫生面前隱私全無,太沒尊嚴。離婚后,前妻到處跟人說他那方面不行,也沒有生育能力,話都傳到魯道夫的耳里來了,有那么大半年里,弄得他很沒面子,上班只敢待在自己的畫室里,不敢到別的辦公室去閑聊,生怕撞上女同事們正在八卦他。前妻離婚后很快就再婚了,直到現在也沒懷上孩子。現在曉蘭懷上了,無疑會給那些八卦他的人們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懷孕對曉蘭來說,可就不是喜而是憂了。她已經有差不多一年沒回家了,臘月底必須得回家過年,那時父母就會發現她的肚子挺了,這個年就會過得雞飛狗跳,不得安寧。曉蘭一直想把這個孩子做掉,魯道夫哄了她幾個月,她才堅定決心保下了孩子。
三天前,曉蘭給魯道夫說她決定跟父母攤牌,攤牌后就按酉北的風俗,雙方先訂親,爭取過完春節就扯證辦酒宴。她叫魯道夫訂一個高檔點的酒樓,請她父母和大舅一家一起吃頓飯,借此把魯道夫隆重地推向前臺,在父母和親戚面前亮相。曉蘭說他父母愛面子,有大舅和大舅媽在,他們不會當場發火,至少不會當場發飆踢凳子掀桌子。
中午湘聚樓酒樓魯道夫必須得趕到,準女婿去見丈母娘最講究第一印象,不能遲到,更不能缺席。這個魯道夫比誰都懂。
魯道夫再一次掏出手機看時間,十點三十九分。若是沒有走錯路,這個時間他已經從烏嘎山撤出來打道回市內,說不準此時正走在北溪村的這條巷子里呢!魯道夫面部肌肉抽搐起來,苦笑一聲,又一連做了三次深呼吸。冰涼的冷空氣灌滿他的口腔,然后沿著喉嚨和氣管直達肺部,他感覺胸腔里依舊沉悶無比。他再一次打望山勢,烏嘎山就在眼前幾百米的地方,影影綽綽,隔著漫天飛舞的雪花和大霧一般無處不在的濕氣,幾乎伸手可觸。魯道夫不打算再退回去找到那棟歐式小洋樓,然后再穿小巷子到那個斜坡,那樣可能還會走錯,他想北溪村雖然巷子眾多,可它畢竟只是個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村子,只要方向沒錯,他即便沒找到那塊菜地,只要走出村子,就能夠看到環城線,上了環城線,還怕找不到殯儀館嗎?
這次魯道夫往前只走了幾十米,就出了北溪村,看到了一片寬闊的菜地。菜地上已經有了一層積雪,青色的大白菜、菠菜、包菜戴上了一頂頂小白帽,菜地中的一些小樹木,穿上了白衣白褲,很難看到本來的顏色了。溝壟里的泥土也被白雪覆蓋,但看上去還有一些拳頭大小的黑色窟窿,就像一張白畫布上粘了很多黑色的顏料,無序,混亂,但也不讓人有那種骯臟的感覺。這就是他要找的那片菜地。魯道夫也看到了環城線,在他正前方三百米遠處的山坡上,正有一輛大貨車飛馳而過,接著又有一輛顯眼的紅色小汽車開了過去。魯道夫松了一口氣,這時他的腦子全然忘記了要找到那道斜坡,翻過那道斜坡再上一個一二十米的小土坎,就能到達只隔條高速連接線的殯儀館大門口。
魯道夫看到正前方環城線下面的斜坡,直接往那奔赴過去,他想登上斜坡上到環城線再說,哪怕殯儀館不在正對面,最多不過就是一二百米位差而已。這點錯不了的,魯道夫很自信。很快,他就到了斜坡下面。這里有兩棟鐵皮房,應該是菜農的雜物房。兩棟小屋之間夾著一條小路,小路盡頭是登上環城線的臺階。坡度很高很陡,臺階應該有幾十級之多,看上去好像是垂直下來的。臺階上也有雪。蓬蓬松松的雪,一腳踩上去吱嘎一聲響,提起腳后留下一個非常清晰的大皮鞋鞋底印。魯道夫剛登上第三級臺階,褲兜里的手機響了,是曉蘭打來的。
親愛的,你起床了嗎?
早起了呢,曉蘭不曉得魯道夫今天要去烏嘎山,魯道夫也不想給她說。
曉蘭問,胡子刮了沒?出門收拾利索點喲!
這個曉得呀!
魯道夫出門前沒有刮胡子,他想從烏嘎山回市里來時間綽綽有余,完全可以洗個澡,換身衣褲,至于刮不刮胡子,倒真無所謂。魯道夫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個德國佬,但他既不是絡腮胡,也不留八字須,刮不刮都普普通通,不另類,更不扎眼。當然,現在看來,澡是洗不成了,衣也換不了了。
你到哪了?
魯道夫心想,曉蘭不會這么快就下高速了吧。
才到酉南服務區,曉蘭說,十一點五十你在湘聚樓對面步行街廣場門口等我,我把車停在那,然后我們一起進去。
沒問題,保證準時到!
魯道夫信心滿滿地答應道。
這不還有一個多小時嘛,魯道夫掛了電話,心里舒了一口氣,但腳卻提得更賣力了。他飛快地爬上一個個臺階,一口氣上了三十多階臺階,來到了一個小平臺上。這個平臺是水泥平臺,右側是一條很深的水溝,應該是上方環城線的排水溝。溝渠四周做了護坡,全是光滑的水泥坡面,坡面很陡,一直向上延伸,魯道夫盡力地抬頭尋找臺階在哪兒,但他沒有找到。盡管他把頭仰得很高很高,仰得腦殼幾乎跟地面成平行線,他也看不到上面的環城線,只能看到正上方很高遠的地方有一個巨大的正方形的黑森森的洞口。那是環城線排水涵洞口。洞口冒著騰騰白氣,但卻聽不到水響,也看不到水流。小平臺左側是長滿樹木和荊棘的荒坡,除了一條雜草叢生的荒蕪的小徑,并沒有向上的臺階。哪怕是腳窩子大小的坑坑也沒有一個。
這怎么上去呢?
魯道夫腦子一下子蒙了。
退回菜地的那棟小屋,再尋找其他的路徑顯然時間來不及,魯道夫想既然有臺階上到這個平臺,那么一定會有通到環城線的路,否則建造這些臺階就毫無意義。誰會去做一些費力費錢卻又毫無意義的事呢?就像自己現在出現在這里,也不是毫無意義的盲目的舉動,先不論他對自己此次行為有多么地否定,至少他內心里承認他不想成為領導和同事們眼里的另類。這就是意義所在。魯道夫顧不上多想,轉身沿著小徑往樹林里走去。他是山里長大的孩子,他知道像這樣的陡坡,一般都會是繞彎的“之”字形路徑,也就是說,他最多在樹林中多繞幾十米就能到達環城線上。樹林并不大,只有幾十株高大的杉木,穿過樹林,魯道夫上了一道小土坎,眼前出現一片菜地。菜地的周圍是圍欄,一眼望去,這塊小菜地沒有一個豁口,圍欄外是濃密的閻王刺、野月季、金剛藤和土薔薇等灌木緊緊相纏的牢不可破的荊棘叢,那是不可能穿過去的。魯道夫無奈地原路返回到小平臺上,察看水溝右邊有沒有通往環城線的路徑。右邊也是一片樹林,樹林緊貼著水溝護坡。溝渠倒是不寬,一腳就可以跨過去,但問題是那邊護坡斜度很大,又是積了雪的水泥地,根本無法落腳,腳掌一著地必然整個身子會失去重心而滑下溝底,溝底一米多深,滑下去就別想再上來。魯道夫往下退回,他想從菜地到小平臺這段路途中必定有岔路,否則誰會專為那個他剛到過的那幾分地的菜地修這么多級臺階?
下了兩級臺階,魯道夫感覺身子有點搖晃,小腿也有點打顫,簌簌發抖,絕不是因為他害怕滑倒,臺階上的積雪跟他上來時沒有多大變化,依然蓬蓬松松的,一踩一個坑,一提腳一個清晰的鞋底印。他還感覺到身上冷冷的,就像冷風從褲管,從袖口,從后頸上往里灌似的,冷得他一陣陣地驚顫。當然不是風在往身子里灌,魯道夫穿的是高幫大皮靴,厚厚的羽絨服袖口有緊松布,后頸上有帶毛的連衣帽,而是魯道夫身體的反應。他感覺這是要犯密集恐懼癥的前兆,否則他就不會是感覺身上冷,而是熱才對。畢竟爬了這么長一段坡,每一步都要使很大的力氣,不說渾身冒汗,至少也應該全身發熱了。記得小時候犯暈車時,就是全身發冷,繼而就會惡心、嘔吐,從發冷到嘔吐間隔最多兩三分鐘時間。魯道夫不敢抬頭看天空上的雪花,但眼前的雪花仍在飄舞,似乎比以前更大更密,一朵朵的雪花就像是一大群亂竄的魚兒在他身邊游蕩。這是真正的暴雪來啦。
魯道夫不確定他是否要犯密集恐懼癥了,他屏住呼吸,耷拉著眼皮,專心地下臺階。每下一級,他還得往左邊望一望,看有沒有分岔的臺階或小徑。下了十多級臺階,他依然沒有看到分岔小徑。魯道夫這時感覺身上更冷了,胸腔里也很悶,惡心和嘔吐的感覺要上來了。臺階太陡,又窄,魯道夫怕犯暈栽倒下去,只好又往上走,退回到小平臺上。
剛上小平臺,手機響了。魯道夫心想曉蘭就下高速了嗎?拿出手機,屏幕上顯示是熊館長,一接通,熊館就大聲質問他,你在哪呀,怎么沒見到你?
魯道夫說,我還在路上呢。
熊館長說,快點吧,局長都兩次問到咋沒見到大家畫?
魯道夫嘴上“哦哦”地應著,心里想的卻是路都還沒找到,來個屁呀!剛掛了熊館長的電話,手機還沒放進褲兜里,又亮屏了。
親愛的,我下高速了,你也準備出門吧。
啊,就下高速了?
魯道夫簡直不相信那是曉蘭的聲音。這才多大會兒工夫,就從酉南服務區到了酉北高速出口?這段路魯道夫走過無數次,七十公里,高速限速每小時八十公里,怎么樣也得五十分鐘。魯道夫看了手機屏幕,果然是十一點四十七分。天哪!自己竟然在小平臺上轉悠了近一個小時!看來殯儀館是去不成了,去他媽的局長,去他媽的局長的岳父大人!現在得趕緊下去,回市內,如果能順利地在好又多超市門口打到的士,時間更是充裕的,打不到的就得跑步過去,也不會晚點。魯道夫決定不去殯儀館了,他得馬上下去返回市區。他對曉蘭說,我這就出門,我在步行街廣場門口等你喲。
掛了電話,魯道夫準備下去時,突然渾身一個激靈,接著屁股“撲嗤”一響,放了一個響屁,但惡心和嘔吐的感覺卻并沒上來,魯道夫反而感到肚子傳來一陣絞痛,可見這不是暈雪,而是在鬧肚子!就像有時剛開手機時信息一條條不停地進來,從魯道夫意識到鬧肚子開始下腹里的絞痛就一陣一陣不斷襲來,已經到了非得去解手不可的地步。小平臺是平的,沒有一塊墊腳石,不好蹲,魯道夫只好沿著那條小徑往菜地跑去,那里有一壟壟的菜畦,有隆起的土堆和凹進去的土溝。
魯道夫來到菜地最里面的一個角落,正準備蹲下大解的時候,突然發現這里有個豁口。這個口子很隱蔽,被一些干樹枝遮蓋著,老遠看上去就像菜園主人扎的籬笆墻。魯道夫頓時便意全無,快步奔過去,搬開干樹枝,鉆進一個灌木叢拱成的小孔洞,又往前鉆了十幾米遠,他一眼就看到了環城線公路外邊深綠色的防護欄桿。魯道夫一陣欣喜,顧不上再去大解,往前奔去,翻過防護欄,他就站在環城線上了。
魯道夫斜對面三十米遠處就是殯儀館。他認真地看了又看,不錯,那個圓拱形的大門就是殯儀館的山門,魯道夫第一次注意到山門上的那幾個大字,原來不叫烏嘎山殯儀館,而是烏嘎山殯葬生態園。再往前走了二十來米,魯道夫看到那幾個鐵藝大字上還纏繞著一粒粒雞心形的深紫色的彩燈。絕對是彩燈,沒通電時是深紫色的,魯道夫的視力很好,他對顏色更加敏感,這不可能看錯。魯道夫想要是晚上經過這里,四周黢黑,這些彩燈一閃一閃,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他感覺頭皮一麻,剛要蹦出“恐怖”兩個字時,大腿上傳來了一陣更大的酥麻,震得他股外側肌不由自主地抖動起來。他的手機又響了。
我們到湘聚樓啦,你在哪兒?曉蘭的聲音有些急切。
魯道夫感覺自己的頭皮瞬間由麻變熱,驚訝地問曉蘭,就到了呀?
幾樓?
古城詩意包廂。
我問的是幾樓?
二樓,左拐第三間。
魯道夫想告訴曉蘭他還得等一會兒才能到,話沒出口曉蘭已掛了電話。魯道夫能想象到此刻曉蘭正在侍者的帶領下挽著父母穿過湘聚樓的前臺往旋轉的大樓梯上走去。曉蘭肯定以為他等在包廂里,正要出來迎接他們。魯道夫劃亮手機屏幕,想給曉蘭解釋一下,他有點事情剛處理完,讓她跟二老聊聊天,他這就馬上趕過來。曉蘭的號沒撥完,熊館長的電話號碼猛不丁地竄了出來,清晰無比地顯示在手機屏幕上,魯道夫不得不先接通這個電話。
你到底到哪兒了,來沒來?熊館長語氣很沖。
魯道夫壓著嗓門說,到門口了,就到了,就到了。
快去記個賬,熊館長的語氣溫柔下來,我們到餐廳了,給你占了座,到時好好敬敬局長。
魯道夫嘴里正“嗯嗯”時,舉在耳旁的手機震動起來,拿到眼前,看到曉蘭又打電話來了,他果斷地掛掉了熊館長的電話,切換成了曉蘭的聲音。
親愛的,你在哪兒?
聽到這話,魯道夫知道曉蘭是在包廂外打的電話,她不可能當著父母和親戚的面叫得這么親昵。定了定神,魯道夫說,曉蘭,你再等我二十分鐘行嗎,我現在有事走不開。
親愛的,你沒開玩笑吧?
我……我……現在真到不了。
那你到底啥時候能到?
你們再等我半個小時行嗎?半個小時,我一定能趕到。
他媽的魯道夫,你是啥子意思?曉蘭突然爆了粗口,不是講好你提前到的,怎么還要半小時才能到,魯道夫,我告訴你,要是十分鐘內見不到你人的話,我媽媽保準會掀桌子的,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魯道夫能理解電話那頭曉蘭的焦急,也能理解她的憤怒,心虛地解釋說,假如暴雪不來,我早就提前半小時到了……
曉蘭顯然沒有聽他解釋,大聲吼叫起來,魯道夫,你聽著,十分鐘內你要是趕不到,我媽肯定會拉我到人民醫院去做人流。
曉蘭的電話掛斷了。
魯道夫腦殼里像鉆進了一群蜜蜂似的嗡嗡直響,他被曉蘭最后的通牒震驚蒙了。他弄不清曉蘭剛才是說氣話,還是她媽媽真的看出了她有身孕了——這種可能性很大。魯道夫知道他必須得趕過去,立即、馬上趕過去!曉蘭媽媽的性格,不不不,而是曉蘭父母的性情,魯道夫已經聽聞不止百次千次,他們一氣之下拉著曉蘭去醫院做人流不是做不出來,而是絕對會做的,撒潑放賴也要做到的。除非曉蘭有與她斷絕母女關系的勇氣。魯道夫也知道曉蘭沒有這個勇氣,因為曉蘭不是她哥哥曉天。
魯道夫站在環城線內側,胯部貼著冰冷的鐵皮圍欄,表情癡呆地望著斜對面拱門上烏嘎山殯葬生態園那幾個鐵藝字,一時不知所措。暴雪已經停了,公路上濕漉漉的,很多地方積了一層薄雪,反射出一道道冷冽的青光,公路兩頭沒有一輛車子。搭不到便車,別說十分鐘,就是半小時內,魯道夫也難以趕到湘聚樓。
手機又響了,魯道夫點開接聽。
我馬上跑過來行不行,爭取二十分鐘內趕到好不好?
他以為是曉蘭打過來的,手機里傳來的卻是熊館長嘶啞的男低音,你到底到哪里了?
熊館長的語氣很嚴厲,等你半天啦,你他媽的哪時候變成滿口胡咧咧的扯謊鬼了。
魯道夫愣怔了兩秒鐘,隨后他深吸了一口涼氣,冷冽的空氣也壓不住他內心的暴躁,他把手機從耳邊拿下來,屏幕對著嘴巴,大聲地對熊館長爆了粗口,他媽的催啥子催嘛,你告訴局長,老子不來啦!
熊館長聽出魯道夫不對勁,語氣軟和下來,咋啦,你不是到門口啦,不進來了你要去哪?
魯道夫一字一頓地說,老子要去拉泡屎!
沒等手機那頭熊館長回過神來,他就摁斷了電話。
說什么真就來什么,魯道夫感覺早先憋回去的便意又上來了,下腹脹脹的,屁眼也癢癢的,到了需要馬上清理體內的穢物了。魯道夫環顧四周,搜尋去哪兒可以方便,他看到左側有一條砂石路通向環城線外的小山包,那里是一片茂密的小樹林。這個小山包應該就是十分鐘前他經過的那塊菜地的背面,魯道夫感覺他快不行了,捂著肚弓著腰往那條小路跑去。
雪已停了。十分鐘前紛紛揚揚密密麻麻布滿天空的雪花,仿佛被一陣大風吹得無影無蹤了,事實上此時還真沒有一絲風。天空依舊低垂,黑云流動,在魯道夫的正前方,懸掛著一團巨大的黑色云團,從那團黑云空隙里漏下一柱金色的光芒,這片光芒正好灑在遠處蜿蜒曲折的酉水河面上,河道兩岸的山頭上積滿了厚厚的白雪,高聳入云,熠熠生輝,好一幅可以入畫的壯麗的山河圖!魯道夫感慨道。只要沒有密集的雪花飛舞,魯道夫就不暈雪,他就能欣賞到眼前的美景,這也正是他期盼已久的雪景。終于下雪啦,魯道夫覺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開朗了。解開皮帶扣時,手機又響起來,魯道夫不知是曉蘭打來的,還是熊館長的電話,伸手去褲兜里掏,右手手指剛觸到褲兜口邊沿,他又停了下來,他不想接電話了。說來奇怪,這時魯道夫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句電影的臺詞,這哪是手機呀,這是手雷!他不想被這個電話破壞現在的好心情。
魯道夫想,管他誰的電話,老子先痛痛快快地拉泡屎再說!
老子邊拉屎邊欣賞下這幅壯麗的山河圖,它不香嗎?
說不準回去后還可以畫一幅大畫呢!
魯道夫選好地方,褪下褲子,光著屁股蹲了下去,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爽從魯道夫的體內噴薄而出,仿佛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脈,七竅皆通,全身通暢,魯道夫感到他那張被冷風和暴雪吹打得麻木僵硬的臉上滾過兩道熱流,他知道自己的眼淚下來了。
再也憋不住了,魯道夫干脆一屁股坐下了地,號啕大哭起來,哭聲震得周圍樹枝上的積雪簌簌地往下掉,既像配合魯道夫,也像在安慰魯道夫,陪著他一起哭……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