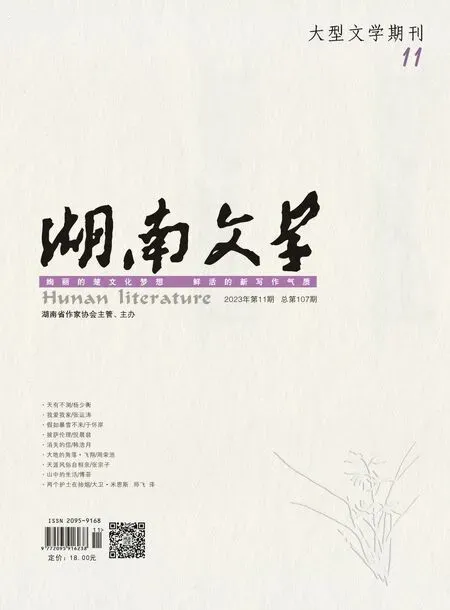靈魂隨水遠行
陳甲元
旺強在坐北朝南的廳屋里指揮滿臉絡腮胡的姐夫和瘦高的在家務農的弟弟搬東西。橘黃的太陽自東方山岡的樹杈上方升起,陽光被墨綠色的廳屋木門切開,灑落在廳屋的深灰水泥地上,也撫慰著廳屋門前不遠處幾叢青綠的萬年青。脫掉都市流行服裝的旺強,穿上幾年前黃舊的,前面披領、身后開叉的老式西裝,看上去,就與故鄉(xiāng)的山水真正地融為了一體。他囑咐姐夫將堆在廳屋南北角的幾麻袋稻谷背往雜屋,又指揮弟弟將松木椅凳移往放電視機的左側客廳,好騰出廳屋一大塊空地來。接著,旺強又轉身進入緊挨客廳的灶屋。灶屋里熱氣騰騰、白霧蒙蒙,像年節(jié)里喜慶的霧影。姐姐和母親都系著暗紅色的圍裙忙碌著。姐姐蹲在角落里用清水細細地洗菜,通紅的蘿卜和紫色莖葉的菜苔已洗了一大堆,躺在身旁鐵桶的篾箕上滴著水;母親在砧板上用力剁著排骨,排骨已剁了一小堆,紅白粘連、骨髓外涌的排骨丟盔棄甲,在母親身前的砧板上已碎了一攤,像極電影電視里拼殺后混亂慘烈的戰(zhàn)場。旺強揚起西服袖口抹了抹發(fā)汗的額頭,穩(wěn)了穩(wěn)心神,重點看了看母親,他第一次發(fā)現(xiàn),母親剁排骨的神情很特別,她每剁一刀,在旺強看來,都像是剁在她自己身上,那種鈍痛的表情可以用“硬”和“猙獰”形容。旺強又一次看了看廚房蒸汽鍋往上升騰著的白霧,緩著語調,對灶屋的兩人輕聲說:飯菜做好后,多燒幾鍋開水吧,寬面我買好了,晚上要給三只雞脫毛,灶里莫停火,到時候,煮點雞湯面做個宵夜。
從灶房里出來,穿過走廊,到廳屋門前,旺強看見了沿著屋門口斜坡緩緩而上朝廳屋走來的楊法師。楊法師穿著中長式樣青色呢子服,背著個青黑布袋,布袋鼓鼓凸凸,里面放了不少物器。可能物器有些重量,也許是斜坡有些角度,旺強覺得楊法師有些氣喘。但楊法師的臉色卻依然平靜如水,和旺強往日在村路旁和小賣部見到的楊伯伯有所不同。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今天的楊法師都像有另外一層物質附了體。與往日和藹的、農人裝束的他判若兩人。旺強突然一激靈,醒悟到今天的楊法師跟往日的楊伯伯是有區(qū)別的,往日的楊伯伯,是父親的朋友,可親可愛的長輩,是樸實的農人。今日的楊伯伯,更多的是法師的身份,今日他背負了祖師的重要使命,在陳氏家人的要求下,來到陳家,是來除妖降魔、治病救人,來渡盡苦厄、救濟凡人的。想到這一層,旺強對楊法師也就生了更多一層的敬慕和尊重。往日望著的楊伯伯只有三層樓那么高,今日的楊伯伯在他眼里就有了七層甚至更高的身影。他謙恭、熱情地招呼楊法師坐下,早就清潔一身、穿戴整齊的祖父見楊法師進來,立即站起來恭敬地雙手作揖、敬煙,行旺強從來沒見他對哪位親友和鄉(xiāng)鄰行過的大禮。行大禮的時候,祖父老化僵硬的脊背努力地朝著楊法師彎下去,蒼老的眼窩里似有液體要滾落下來、這讓旺強看著祖父后背那張“彎弓”很是心疼,生怕祖父的脊椎骨突然咔嚓一聲,瞬間斷成兩截,那就真是要命的事情。楊法師接過煙,再接過姐姐奉上的茶后,緩慢地將茶舉起在唇邊比畫著畫了幾個小橢圓,吹涼吹散熱霧后,舌不出唇地、莊重地抿了一口,轉向旺強輕聲問道:最后的診斷結果出來了?旺強平靜地回答:出來了。是肺癌晚期?是的。還有其他癥狀嗎?前期有些間歇性疼痛,近期有所好轉,只是吃得少,吐得多,身子越來越虛弱。楊法師再不說什么,脧一眼緊挨廳屋的房間,房間的木板門框漆成棕黃,地板的瓷磚是前些年村里流行的大眾的米黃,席夢思是十年前新房建成后鄰鎮(zhèn)街集專業(yè)做床的老師傅做的,床上蓋著綠色枝葉、紅色月季花圖案的棉被,棉被下的父親躺在床上睡著了,可能還要個把小時才得醒。楊法師收回瞟向棉被的眼神,寡淡的臉色就越來越繃緊了。
三個人就這樣安靜地坐著,沒有話,客廳的電視里正放著一部濫情的電視劇,一個妖嬈性感的小三正和一個凈水器公司老總在床上調情,被老總的老婆帶人抓個正著,瞬間,酒店的房間里酒杯碎裂,桌椅打翻,照相機、手機的拍照燈一陣亂閃,狗吠人叫,一屋子的人亂成一片。劇情狗血,庸俗搗亂,很不好看。倒是和客廳一角小方桌上不時續(xù)換的熱氣騰騰的煙茶一起,給房里添了熱鬧與暖和的氛圍。坐了一會,楊法師抬眼,透過綠色木窗框住的毛白玻璃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已是黃昏。屋外的山頭、田土和村道上暮色已起,天地的界限像奇大蚌殼的蚌貝將要慢慢合攏,仿佛要將眾人都閉合在混沌和迷霧中,封鎖在一季冬寒里。楊法師輕聲說了句,開始吧!爺爺和旺強就都得令般地站了起來,門口察言觀色一直待令的姐夫和弟弟聽見響動也走了進來,等著分配他們的活計。放神仙牌位的高腳桌、長凳、香爐、香、燭、錢紙、鞭炮、蓋有天地銀行印章的冥幣,旺強早兩天就準備好了,姐夫和弟弟也早已將它們搬到了適當?shù)奈恢谩罘◣熣f,都到廳屋去吧,晚飯之前把神請了,晚上放船!接著,他不緊不慢,先從凹凸布袋里翻出青色白邊的法衣,雙手高舉抖動著穿上,再去廚房水缸里舀清水凈手,凈手回來后,他又不聲不響地自布袋里抽出一塊紅布,然后將師尊的牌位自布袋緩緩請出,恭敬地供奉在廳屋正中。牌位下面是香爐,將香燭點燃,錢紙碼齊疊放好,擺放好相關法器,再緊緊法衣,請神的儀式就算正式開始了。鞠幾個躬,燒幾頁錢紙,聽楊法師喃喃自語,時而柔和,時而興奮,看通紅的燭光搖曳,再看錢紙在風的作用下詭異地沿地奔跑或飛旋在空中,凝望火紅燭光映襯下峨冠博帶似要開口說話的祖師爺,旺強相信楊法師能進入到一層虛空、幽冥的境界。旺強甚至越來越相信,在凡塵的世界之外,還另外有一個虛體的世界存在著,另一個世界,住了很多很多的神仙、幽靈、魔獸。他們屬于宇宙的另一個體系,他們能看見我們凡俗的生活。而我們,只能從偶爾的縫隙里窺到他們一點點的微光。
當旺強那天傍晚進山沖找到楊法師的時候,楊法師正在豬圈房頂忙著俗世的活,凜冬快來了,豬圈頂棚上的茅草被初冬的冷風吹漏了一個大洞,楊法師正同幾個鄉(xiāng)親認真地補著那個窟窿:釘木板,換茅草,堵石塊。像是修補著這些年他們倥傯而忙亂的時光。冬霧,豬圈,茅草,農人和山村的剪影很古老,加上旺強悲愁的思緒,讓旺強有時日恍惚的感受,感覺自己仿佛穿越了幾千年,一瞬間被拉回到了刀耕火種的先民時代。旺強甚至驚奇地覺得,今日傍晚自家彌漫的通紅燭光和前幾日傍晚楊法師家周邊緩慢墜地的光亮,有著相通的質地和色彩。
父親醒了,醒了的父親第一件事就是掙扎著要起來跟楊法師打招呼,旺強和弟弟見父親很堅決,就幫父親穿好棉大衣,再裹好保暖的毛毯,一人扛一只肩膀,一人一只手在父親手下做成手椅,牢固地托住他的身軀,幫他到楊法師身前簡單說話。父親已經很單瘦了,原來一百四十幾斤的身子現(xiàn)在估計只有九十幾斤,兄弟倆托著他僵硬的髖骨都覺得有些硌手。父親求生的欲望是強烈的,即使虛弱,他說也一定要到祖師爺跟前燒紙,祈求祖師爺保佑。
晚飯后,楊法師開始“做船”,將一張加厚的白紙對折幾次,再橫折幾次,再從內里旋形抽出,船的雛形就出來了,船艙內載著一些做工粗陋的黃色馬蹄印紙錢和花花綠綠的天地銀行的冥幣,船的正中間,是象征著父親靈魂的用紅紙剪好的小紙人,用一根竹簽穩(wěn)穩(wěn)地插在船中。這個旺強也見識過,旺強從小在橫村長大,看過楊法師多次做法事時將船做好,鄭重地雙手托著,在金色銅鑼砰砰捶響聲、牛皮鼓咚咚敲響聲中,在鞭炮噼啪炸響聲中,在煙熏火燎的迷煙中,在鄉(xiāng)鄰踴躍的簇擁和“哼哼”“吼吼”的奇怪囈語中,來到村莊低處的河流,將紙船放走。沒有人統(tǒng)計過楊法師在橫村的河流中究竟放走過多少紙船,扶助過多少病民。也沒有人質疑過祖師爺?shù)耐`和楊法師的法力,很多年了,村民們形成了一個共識:船順利地漂走了,病情好轉了,是吉兆,是祖師爺顯靈,是某家的福氣,是病主的造化;突然有風,水流突然奔涌,以致船翻了,沉了,那是祖上無福,病人命中注定,不關楊法師和祖師爺?shù)氖拢鎺煚斠呀洷M力了。
楊法師在前頭引路,他身軀高大,虎虎的后背上插著畫有古老符咒的三角形旗幡,雙手托著輕輕的紙船,恍如托著幾十斤重物事般莊重。精神似乎也在祖師爺?shù)耐`下煥發(fā)了新鮮的活力。旺強亦步亦趨地跟在楊法師身后,緊跟旺強的,是敲著銅鑼的鄰居老丁,再往后就是打著火把的姐夫、弟弟和鄰居老羅以及其他擁護的鄉(xiāng)鄰。到河灘有好幾里路,一行人炸著鞭炮,敲著鑼鼓,打著火把,秩序井然。旺強呼吸著夜色里帶草木氣息的空氣,心無旁騖地腦子里滿是祖師爺凝神的樣子,祖父在他去請楊法師前曾鄭重告誡他,只有內心專注,在做法事的時候,病人和病人的直系家屬眼前只有祖師爺,才能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于是,旺強所有的意念就有意識地朝著祖師爺靠攏,到河灘中央時,旺強覺得他在祖師爺?shù)臓恳拢踔劣辛诵碌陌l(fā)現(xiàn),蹚在河灘齊腰深的茅草中,他覺得,這一路放船的行程,像極了人生的旅程,人生很多時候是需要點起火把照路的。
楊法師在河邊站定,放大聲音,請了幾路師尊后,迅疾果斷地將點燃的紙船放入流淌的河流,冬季水流不大,火船順著楊法師和眾人的心意越燒越旺,順著流水緩緩漂向遠方,平穩(wěn)而夢幻地朝著下游駛去,沒有突然而至的風將船吹動、刮翻,火船流動的速度跟流水的節(jié)奏天然地契合,這是個好的征兆,說明父親的靈魂平安順暢,沒有任何波瀾。楊法師又激動地高聲吟哦,唱詞古老,大意應該是感謝師祖,一切順利,護佑黎民,我?guī)煵蝗琛1娙擞铸R敲鑼鼓,以示敬仰。旺強再次跪倒在河灘拜謝祖師爺顯靈。放船回來后,旺強要姐夫把剛祭船的雞提到廚房加火快燉,放幾片老姜,加點面條做宵夜。楊法師面帶喜色地來到父親床前,跟躺在床上等消息的父親說船行平穩(wěn),情況不錯,比較順利。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心情就好了很多,臉上就添了淺笑和欣慰。夜宵后,照例是謝祖師、敬酒、鳴炮。楊法師推辭了幾次,但臨走時旺強還是霸蠻將紅包放到了他的法衣里。楊法師再次要將紅包從法衣里拿出來,旺強就用力抓住楊法師的手,楊法師的手掌在旺強的大手里魚尾般柔弱地擺動了幾下,就溫馴地偃旗息鼓了。
送走楊法師后,家里有了短暫的安靜。旺強坐在電視房里靠著火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父親的鼻息均勻,已經在祖師爺?shù)谋幼o下沉沉睡去了,可見他的心靈已得到撫慰。姐姐說,今晚她睡父親腳下,照顧父親,如父親半夜驚醒,要水喝,哪里不舒服要揉揉的時候,被子掉了的時候,她可以及時跟上。說這是她做女兒應盡的孝心。聽姐姐這樣說,旺強就來到了樓上自己的臥室。外面依然安靜,偶爾聽得到幾聲犬吠,那是旺強自小就熟悉了的橫村夜晚的聲響。夜已經很深了。想著這一年多,父親被確診為晚期癌癥患者以來的種種經歷,想著前幾天楊法師家門前彌漫的冬霧和慢慢落地的微光,他始終沒有睡意。
寒夜的冷風又起了。它起于蒼茫,歸于蒼茫,如大手般自橫村上空吹拂而過。突然響起了篤篤的敲門聲,聲音里夾雜著大姐呼喚他的聲音。打開門,只見大姐手里拿著一對像兩只小手掌一樣的淺灰色的竹卦站在門口,說是剛才打掃衛(wèi)生時在廳屋角落里發(fā)現(xiàn)的,應該是楊法師留下的。旺強熟悉這用竹蔸制成的卦,這種卦在村廟里和楊法師那樣的私壇,是弟子們用來領會菩薩和祖師意圖的必備工具。而且旺強知道,方圓幾十里,像楊法師那樣的私壇弟子都有個規(guī)矩,就是所有的法器、道具都不能留在主人家過夜,否則,當晚的做法效果將大打折扣,對做法事的人家來講,這也是不祥之兆。于是,旺強下樓,在雜物間里找到一個墨綠色的小布袋,將竹卦放在布袋里,披一件厚外套,轉身就出了門。
出了門的旺強驚奇地發(fā)現(xiàn),這個季節(jié),午夜后的夜色并不如大多數(shù)人想象的那般漆黑和凝重,他甚至不用打開手電筒都能分辨出路的拐彎和坑洼,他想,這也許得益于他少年時求學的艱苦經歷。讀初中時,因為家居山地,路途遙遠,他經常要起早摸黑。所謂起早,就是經常要在凌晨五點左右起床,在家里啃過母親熱在灶窩里的玉米或紅薯后,趕幾十里路去上學。所謂摸黑,就是傍晚放學后,走十幾里平坦的村莊路,然后趁夜色走十幾里山路趕回家。這可能也鍛煉了他夜晚走路的“火眼金睛”。小時候,旺強跟著父親走遍了橫村的橫沖豎沖,走過亂墳打堆的楊梅崗,走過梯田層疊的木家灣,也沒少走過去往楊法師家的山間路,現(xiàn)在,當年引領他走路的父親已病入膏肓,許久不見的楊法師也頗現(xiàn)老態(tài)。想到這一層,旺強突然想起有一年父親和楊法師說的話,那時的旺強年紀尚小,父親和楊法師也正值壯年,旺強跟著父親去楊法師家做客。好像是暮春與初夏相接時節(jié),父親和楊法師先是在屋內聊了一些農事,然后轉身出來,一人端一碗農家自制的煙茶眺望屋門前遠近的青山,當日陽光晶亮,草木深綠,逶迤秀麗的青山在太陽的照耀下綠得耀眼,似要滴出水來。突然一陣山風吹過,搖動對面山嶺上茂盛的樹木,像一陣風吹皺深沉的水。當水波再次隨風起伏翻涌的那一刻,父親若有所思、語調平靜地對著楊法師說道:老楊,看眼前這景象,我想起了很多,還真是只有青山守人,沒有人守青山的道理啊。
楊法師的家近了。遠遠望去,他家家用的、瓦數(shù)不高的照明燈點亮在寒夜里,散發(fā)微弱的光芒,和今晚點亮在旺強家祖師爺像前的燭光有異曲同工之妙,有強烈的飄搖和夢幻感。旺強往上提了提手里的綠布袋,不由地加快了腳步。
“吱呀”一聲,旺強發(fā)現(xiàn)前面不遠處楊法師家的木門突然打開了。緊隨打開的木門走出屋外的是一個頭扎紅布、腰掛手電、手捧竹籃的人。寂靜的寒夜里,旺強被這刺耳的聲響和這個人詭異的裝扮嚇到了,雖然他立馬反應過來,這個人應該是和他剛分開不久的楊法師。他條件反射般地順勢跳到緊鄰坡路的一條水溝里,差點弄丟了手里的小布袋。好在冬季是枯水季,山間水溝本沒有多少積水,旺強在水溝底先是觸著一層軟泥,再踩牢硬處后,身軀就緊貼著溝墻以躲避楊法師,待感覺楊法師踩著滯重的步子,步步走遠后,他一翻身跨上山路,好奇地跟在了楊法師身后,保持著不被他發(fā)覺的距離。夜晚的山風又起了,走在旺強前面的楊法師禁不住打了一個寒顫,讓旺強誤以為楊法師發(fā)現(xiàn)了自己,正想開口招呼并將布袋交給他,但楊法師在顫抖過后,卻緩了緩神,依然心無旁騖地捧著他胸前的竹籃向村河方向走去,仿佛那平常的竹籃,已被注入了神秘和沉重的分量。
到了河邊的平坦地后,眼前的楊法師開始了今天第二次“做船”的儀式,他確實是累了,沒有鑼鼓,沒有鄉(xiāng)鄰陪伴,沒有雞牲,孤單的楊法師,在對著浩渺的夜空請了幾遍清風祖師、山神土地、各路神仙后,從竹籃里拿出一只瓷碗,到河邊舀了半碗清水,將頭上的紅布解下來,蓋在瓷碗上。接著,他又從竹籃里拿出一張白紙,找到附近一塊大點的方石,將一張加厚的白紙放在石板上橫豎對折幾次,再從內里旋形抽出,船的雛形就出來了。往船艙內放上一疊紙錢和幾張?zhí)斓劂y行紙幣,將紅通通異常醒目的小紙人,用一根竹簽插牢在船中后,他站起身,干了紅布下的半碗清水,從褲兜里摸出了打火機。
前幾天傍晚,楊法師從豬圈屋頂爬下來,神情疲憊地領著旺強進了自己的小法屋,到私壇前向祖師爺“報備”,旺強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楊法師在聽到父親的病情后,神情是相當慌亂的,近距離的旺強甚至在低矮的小法屋里,看到了楊法師額頭滲出的細密汗珠。說也奇怪,那天楊法師在祖師爺面前點燃香燭,焚紙祈告后,怎么也找不到旺強今日布袋里手提的竹卦。一老一小急忙慌亂著找尋,直到楊法師摸索著打開壁柜中間加了一把醒目銅鎖的屜子后,才發(fā)現(xiàn)抽屜里安靜地躲在病歷本下面的一對“小手掌”。雖然楊法師極力遮掩,但眼尖的旺強還是掃到病歷本上患者的姓名是楊法師。楊法師名字上方,印章蓋上去的淡藍色的“腫瘤科”三個大字,和父親病歷本上的三個字,又是多么的一致!
夜空比之前更加明亮了,卻又始終無法掙脫夜的黑。“我祖不負,顯應通靈”的唱詞又一次在夜空唱響。遠處,腳下的小船越漂越遠了。年輕的旺強,使勁踮起腳尖,也無法追逐到小船更遠的身影。
責任編輯: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