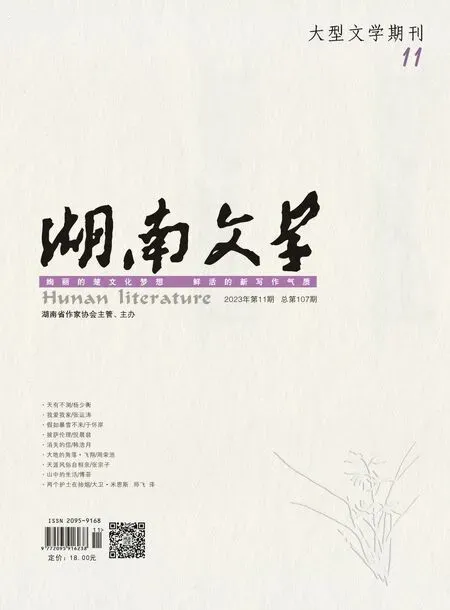消失的信
韓浩月
一
二〇〇四年前后,某個秋天的傍晚,家中,我把一疊大約十枚左右的嶄新信封整理好,踩著椅子,取下書架上的一個紙盒,把它們放了進去,其中的一個信封,裝有搭配這些信封使用的十張郵票,為了方便找到那枚藏了郵票的信封,還特意把它放在了最上面。默默做這些的時候,內心里想:這些信封,不會再也用不上了吧。
一語成讖,果然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沒有寄過任何一封信。閑極無聊的時候,想要把那疊信封找出來——不是需要用到,也不是想把它們送人(也無人可送),就是想翻翻,看看它們還在不在。我在尋找一件東西死活都找不到的時候,會沮喪,這是小時候養成的壞毛病。找了數次,那個盒子還在,只是信封沒了,我坐在書架下面的玻璃鋼桌子旁生悶氣,直到十幾分鐘之后,情緒才緩和下來。
那一疊信封,它們不知被我“寄”往了哪里。信封常見的顏色,只有黃色和白色,黃色通常是牛皮紙做的,白色則是厚一些的雙膠紙印制而成。而那些遍尋不見的信封,在我腦海里莫名其妙變成了黑色,它們或許趁著一個黑夜偷偷溜走,展開翅膀飛了,那十枚郵票是它們的“盤纏”。我找不到它們,感到悶悶不樂,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那信封里面空空如也,封面上的方格子里沒有填寫郵政編碼,橫線上也沒有寫出收信人地址,你們要逃向哪里,為何要舍我而去?
再過些天,就要到二〇二四年了,那些信封已經丟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人的一生,會弄丟很多東西,錢包、身份證、手機等等,哪一種都比信封重要。我每次出門旅行,總會把一件東西忘記在酒店里,白襯衣、充電器、刮胡刀等等。有時我想,如果把這幾十年來我丟掉的東西辦一個“失物展覽欄”,那將會是件有趣的事情,這個“失物展覽欄”是萬萬不可缺少那些信封的,失去了那些信封,這個展覽將辦得毫無意義。
以往在家里找不到東西,經常會問問妻子看見了沒有,但我從未問她那些信封是否出現在她視線里,我本能地認為它們屬于極度私人化的物品,它們的隱私程度相當于一個人內心深處的黑點,你會將內心的黑點展示出來給人看,或者請人幫你尋找它所在的位置嗎?肯定不會吧。
這些年我習慣了在旅行之后給酒店打電話,請前臺服務員把我遺忘在房間里的物品快遞回來,不是不舍得那些東西,而是不愿意與自己有關的它們,從此永別,不知流落何方。可當那些物品貼著寫我名字的標簽寄到家中時,我又是無動于衷的,它們物歸原主,理所當然,它們本來就不應該丟失。我撕掉那些寫著我名字的標簽,將物品回歸原位,心里想著,以后再也不要輕易弄丟東西了。
可有些事物,的確是丟了之后,不好去尋找的,要么是它們的價值,并不值得打一個電話,并且快遞回來,要么一旦失去就是徹底地失去,尋找只是徒增煩惱。于是,沉默便成為遺忘最好的情感匹配,就像夜色是黑夜不易覺察的外衣一樣。沉默是黑色的,不是令人壓抑的濃黑,而是如云如絮般柔軟的淡黑、淺黑、輕黑,但這黑如果寫到了白紙之上,就會永久留存,不會泛黃或消失……但凡我在那些信封上留下一兩個字呢,哪怕在信封中裝進一頁折疊好的白紙呢,想必那樣的話,丟失的可能性就會有所降低吧——在無數個瞬間,我心里涌現出這樣的念頭。
二
不會丟棄任何一封信。不管那些信來自何方,信封里所裝的紙頁上寫著或者印刷著什么,它們會在信封被打開的那一瞬間,大白于陽光或者燈光之下。閱讀是一件令人顫抖的事情,尤其是來自于書信上的閱讀,它帶有一種不可拒絕的闖入感,一封書信如同驛馬闖出了驛站,它使命必達,無可阻擋,它靜靜地佇立在郵件筐當中,等待它真正的主人到來,在等待的過程中,充滿著隨時丟失的風險。
一九九三年前后,我在街道所辦的一處焊條廠當工人時,每周總有一天下午會悄無聲息地失蹤一個小時。那是午飯休息之后的工作時間,我把機器調到最佳的自動工作狀態,出絲口切出的焊條絲,有秩序地一根根被切割出來,又直又亮,有著圓潤的切口,但如果不一直看管的話,切刀一旦出現斷裂或其他問題,長長的焊條絲便會蛇一樣在車間里躥騰,直到車間主任臉紅脖子粗地找到機床位子上來,怒吼著罵人。
但我還是要離開。我要去距離工廠三四公里外的居委會取一些寄給我的信,有的時候騎自行車,沒有自行車的時候就步行。在離開機床之前,我會默默在機器邊站一會兒,尋找到機器切割的節奏,然后帶著這節奏出發,仿佛這樣可以通過意念感受到機器會不會出問題。即便出問題,我也不會在半路受到心靈感應的支配,狂奔回車間,比起車間主任梗著脖子罵人,我取回那些信更值得重視——那些信仿佛裝著咒語,帶有魔力,我可以無足輕重,但它們至關重要。
但有的人不這么認為,比如門房里的那個老人,他大約六十歲上下的樣子,面孔還算和善。他還有一位同齡的老婆,臉色總是陰沉著。如果推開門房的門,看見是老頭兒,心里會放松不少,如果看到的是他的老婆,則會異常緊張……到后來,那個和善的老頭,面孔越來越像他老婆,我在郵件筐里翻撿信件的時候,他們都會用同樣的眼神看著我。他們像是黑森林的大樹越長越高,而我則像丟盔棄甲誤闖入的敗軍之將。有時候我會覺察到有汗不自覺地順著后脖頸流了下來,背上癢癢的,但手不會停止翻動那些信件,直到把屬于自己的信全找到帶走為止。
后來知道,那個門房老人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按輩分我可能要稱呼他一句“舅姥爺”之類,但我從未如此稱呼過他。雖無言語交流,但我們之間仿佛仇深似海,他不明白為什么每周都會有這樣一個面相看上去郁郁寡歡的青年,把一個郵件筐翻了一遍又一遍,有時候帶走一捆,有時候兩手空空。
有一段時間,他看上去表情有些不太自然,那段時間我一封信都沒有收到,我懷疑他偷偷藏起了我的信。我的疑心開始日益加重。終于有一次,他被門外的汽車喇叭催促出去開大門的時候,我掀開了他在門房的床鋪,檢查了他的枕頭底和床墊下,結果找出了十多個寫有我名字的信封,那些信封有的已經被拆開了,有的完好無損,我拿著那些信封站在房間的陰影里,看見他推門進來,他和陽光一起照射進我的瞳孔,我想他肯定看見瞳孔里閃爍的憤怒與仇恨,他嘴里尷尬地咕噥了一句什么,我什么話也沒有說,把那些信在他臉前晃了晃,揚長而去。
在離開縣城后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我總會做一個噩夢,夢見我在門房里,用手翻一沓沓的信封,翻著翻著,我的手指和手掌慢慢變成了黑色,而那個眼神一會兒和善一會兒陰沉的老人,坐在不遠處的床邊冷冷地看著我。正是因為他隱匿信件的事被戳破之后,他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他用挑釁般的眼神看著我,仿佛告訴我有我的信正被壓在他的床鋪之下,被他坐在屁股之下……在夢中,我與他廝打起來,這是在現實中未發生過的,如果在現實中發生過,或許此后近十年我就不會做那樣的噩夢了。
我知道他的名字,那個老頭,我的遠房親戚,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信是匿名的,為了不讓他發現,信封上的字,我使用了左手,在信封里面,還有一個信封,那是用一張好不容易尋到的黑色紙張折疊的,在黑色信封里面,裝著一張白紙,紙上只有一個用鋼筆墨水畫出來的濃濃的“X”號,那是一種警告。老頭收到這樣一封匿名信之后嚇壞了,他知道有90%的可能是我寄的,但他找不到證據。從此之后,我可以帶著夏天下午陽光的溫熱或者冬天寒風附著的冷氣,大大咧咧地跨進門房,隨意翻撿那些信,把屬于我的都帶走,和他則一個招呼也不打。
三
一個兄弟來看我,身上披著月光,眼里帶著悲傷,他抓起桌子上的蘋果輕輕咬了一口,然后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個信封——在一首歌詞的開頭,作者描述了這樣的一個場景。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仿佛聽見蘋果被咬下時發出的那“咔嚓”聲,我覺得自己的秘密如同被散彈射擊的靶子,散落一地,原來在如此廣袤的世界,在同樣的夜晚與月光下,發生過如此之多雷同的故事。
我離開職高輟學在家的時候,經常有一個兄弟來看我,他的名字叫顧維云,他敲開我家的門,上衣口袋里裝著一封或兩封寄到學校寄給我的信。我的桌子上沒有招待他的蘋果,他也沒有馬上把那些信給我,我們心不在焉地聊著一些天,語速很慢,具體說了些什么都忘記了。到了告別的時候,他才像突然想起了某件重要的事情,把信從口袋里掏出來,有時候他會用手撫平那信封上的皺褶,他那鄭重的表情和態度,仿佛交給我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份委任狀。
顧維云離開之后,我把門關上,讀那些來信,一些陌生人,在紙張上訴說著一些屬于朋友間的親近話語,這制造出一種張力,它讓人感覺到現實生活是如此虛假,紙上建造的“城堡”才是現實理想的樣子。在很多年之后,互聯網聊天室流行的時候,類似的狀況再一次大面積上演,人們總是對陌生人掏心掏肺,對身邊熟悉的人卻保持距離……現實是一條河,這條河水流緩慢,每天最大的事件,也不過是一片落葉飛落到河面上,激起幾圈漣漪,而虛擬與想象搭造出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它可以使人成為草原上的奔馬,撒開韁繩,一去不回頭。
還有一位初中時的同學,他有一段時間掌握了初中畢業后同學們之間的通聯,那些告別時彼此之間忘記(或者刻意沒有)留下聯系方式的同學,依然會把信寄到學校,寄希望于收信人還有百分之幾的可能性收到。對于十幾歲的少年來說,這個年齡段的信,往往左右著他們往后的人生走向:是選擇遠走他鄉,是從他鄉星夜趕回,是再等幾年參加部隊驗兵成為一名戰士,還是在街道一隅開個不起眼的小賣鋪;是在村莊的小路拐彎處等待一個人身影的出現,還是在城市租住的潮濕地下室輾轉難眠……那位同學給我送過十幾封信,但我確信,也有些信,遺失在風中。
我后來在一所職業中專當臨時代課老師的時候,因為與學校產生一點矛盾要離職,學校辦公室扣留了我用學校地址與外界的所有通信(當時并未意識到他們這么做是違法行為),從財務室拿回最后一份薪水經過辦公室的時候,我看見那些信放在一個大約一米長的匣子里,我知道那個匣子里裝的信的信封上,無一例外每一封寫的都是我的名字,我在辦公室門口猶豫了幾秒,我可以選擇沖進去不顧一切地抱起那個匣子就走,也可以選擇徹底放棄,永遠不知曉那些信里裝載了多少人的愿望、期待、等待……我選擇了后者,從此我在這個世界,成為幾十人、上百人心目中的“失蹤者”,在一個用書信編織的“空中電臺”里,我的聲音戛然而止。
四
整個八九十年代,是一個信件滿天飛舞的年代,據說最多的一年,有七十億件信件被寄出,人均九封,哪怕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都有可能在某天接到郵差隔著一條街扔過來的信件——那里面裝的內容千奇百怪,用后來電子郵件時代通行的說法是,那是標準的“垃圾郵件”。
最“垃圾”的郵件當屬詛咒信件,在打開它之前,你并不知道里面裝著什么內容,人在拆信時往往像現在拆快遞那樣帶著新奇與期待的心情,而有一種信件會讓你的心情直接降至冰點——那是一封詛咒信,收到這樣的信,就仿佛看見一只黑蝴蝶從信封中飛出來,只有怔怔地看著它,不知該如何是好。那封詛咒信要求你抄寫十份或者更多份寄出去,否則厄運便會降臨,很多人抵抗不住這份恐懼,紛紛加入了抄信大軍,那些人為制造的垃圾郵件除了讓郵遞員更忙碌之外,并沒有給正常社會運轉造成多大的阻礙,無論相信或不不相信那些詛咒信件,日子總像滾動的車輪一樣向前向前,日子碾壓一切,包括那些不必要的擔憂。人們很快忘記了那些“不速之客”,與火熱的生活相比,那一點點的陰影根本不算什么。
我的一位忘年交老友,在他的回憶錄寫到,他在鄉村的家庭地址,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寄來的“致富信息”,于是在長達五六年的時間里,他受到那些信件的指使,奔波到多個陌生之地去考察,每次都帶上了自己所有的存款,甚至從親戚朋友那里湊來的一筆“巨款”,而那些黑色信件,每一個都像是吞金獸,把他的錢款全部吞沒之后,一個子兒也沒有給他回吐。
他寫到他與自己的侄兒在某天黃昏坐著火車上路,去很遠的一個城市購買了一批血鱔,在回來的路上,那批血鱔已經死了大半,回到家把它們放進提前就挖好的池塘里,結果第二天全部的血鱔死得干干凈凈,這已經是他七八次“創業”被騙,他已經再無退路,絕望之下他想到,既然如此,何不效仿之,于是他跑到市里的報社,花錢做了一條中縫廣告,沒幾天各種咨詢的信件雪片一樣飛來,在信件的指引下,那些陌生人紛紛上門購買——他讓侄兒從街上的魚市買來了普通的鱔魚當作珍貴的魚苗銷售,當然價格翻了幾倍之多,理所當然地,那些“魚苗”或死在了路上,或死在了買家新挖好的小池塘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賺回了自己損失的錢,便毅然決定了不再繼續這么干下去……
讀到這段回憶錄我沉吟良久,不是為了這件事的荒誕,而是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懺悔意識,這是一個有口皆碑的好人,在眾人的評價中,他一生沒有做過壞事,如果不是他把自己賣“假魚苗”的事情主動公之于眾并記錄在案,恐怕已經沒有人記得這件事情。他在寫這份回憶錄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的生命所余不多,他仿佛已經看見一扇黑色的大門在朝他打開,所以他回首往事,想要把屬于自己的那枚黑色信封掏空,并緊緊地把封口粘上,不讓這個秘密被帶入墳墓。
我在成年后不同的年齡階段,分期分批燒掉了所有屬于我的信,這不屬于告別也不屬于懺悔,我燒那些信的動機在于想讓自己徹底與過去作別,但直到多年之后才知道如此做法的幼稚,一個人是沒法與自己作完全的切割的,越是刻意地想要涂抹掉一段經歷或一份記憶,它們就越會頑強地存在。時間自然有其涂抹一切的方式方法,而人為地干涉就是與時間作對,往往在你覺得自己贏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敗得一塌糊涂。
我想如果萬一能找到消失的那十枚信封的話,我要仔細斟酌,從通訊錄里找九個人出來,分別給他們寫一封信。在信里,我要像那位已經告別人世的老友那樣,認認真真地回憶過往,坦率真誠地承認過失與錯誤。當然我不會用很直白的方式說出一切,時間已經教會我如何既把話說明白又不會傷到自己或別人。剩下的那枚信封,我要裝上寫給自己的信,不需要寫太多的話語,言簡意賅就好。
每個人都會有一封寫給自己但自己卻收不到的信,它以文字或意念的形式存在,且日日撰寫,很少停歇。這封信無須寄出,因為它早已歸檔,宛若一雙無形之手,把一個人的榮辱對錯,分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且碑刻一樣不會消失。
責任編輯: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