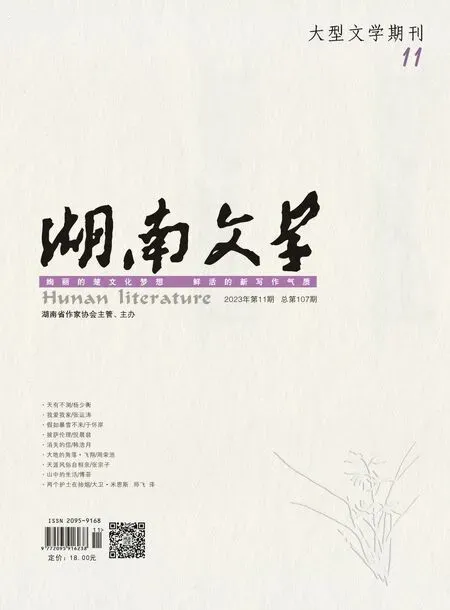一只鷹在天空盤旋
周實
一
在小學同學的聚會上,我和他又見面了,半個世紀沒見過了。他問我有什么感覺,我說仿佛一眨眼又變成了小學生,傻乎乎地為那些已經逝去的日子,還有童年的回憶,而興奮,而歡笑。不管分開的幾十年里,我們變得多么陌生,多么隔膜和疏遠,我們仍然擁有某種難以忘懷的共同記憶。這是我們的終身紐帶。
我們居然還能記起校園生活的很多細節,多半是某個人一提起,很多人就來補充,七嘴八舌,搶著說。大家的記憶被喚醒了。那時,我們說說笑笑,打打鬧鬧,聯合又分裂,密謀又告密,結仇又和好,擁立山頭又另立山頭……我們哪里是在念書?我們是在小試牛刀,練習如何混社會啊,這些才是令我們想忘也終生難忘的。
你說我們那時候真的就這么復雜了?他感嘆著對我說,那個階段應該還是一顆赤子之心啊!
赤子之心?我笑道,說幼兒園還差不多。
二
他會吹口哨,吹得非常好,尤其是吹《啊!朋友》時。
他的口哨讓我想起讀小學的某堂課上,我把嘴巴噘著,噘著,一不留神,噓的一聲,竟讓哨音溜了出來。
老師指了指教室門口,我乖乖地走了出去,走出校門,來到街上。
那真的是美妙的一天!
我閑逛著,打發時間。腳下,黃葉,沙沙作響。頭上,藍天,白云裊裊。現在回想,仍想了又想。
于是,我打斷了他的口哨,對他說起我的口哨。
三
他告訴我他想起了他小時候把撿來的避孕套當作氣球吹的事。他說不曉得怎么回事,當他正在炫耀著時,卻被大人一聲吼,把那氣球搶走了,還被罵著去洗手,去漱口。啊,他感嘆,那時我曾收集了多少我不懂的東西。
我說我也是一樣,可能比他還要多。
他又說起小時候因為說謊總挨打。
我說那是你不想平庸。
他說是,說老實話沒意思,一點味道都沒有。謊言就是他的想象,是他所希望的那樣,不像真的事實那樣。他想自己不同尋常,不料卻是一敗涂地,想象總被現實粉碎。
我笑他不實事求是。
他還說起他的爺爺。說他曾經回去看他。最后那一次,爺爺對他說:上次你回來看我時,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再過十年,你想見我,恐怕你也見不到了。然后,他就上了火車。人人都在揮手告別。但是,火車只管往前,因為它已別無選擇,它不愛看人們道別。
我靜靜地聽他說著,看到了他的回鄉之路。那路回去很長很長,那路離開也是很長。
四
小時候,他住過幼兒園,我也住過幼兒園。最記得生病時,幼兒園有面條吃。或者你想吃面條,那你就得裝生病。那時,面條很金貴。再就是周末接回家,周一又要送回去。每次,再去幼兒園,我都摳在門框邊上,號叫著,不松手。父母一邊哄著我,一邊試著想扳開我那摳住門框的手,我就號得更厲害。要不,就鉆到床底下,怎么喚都不出來。
他說他可不是這樣,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樂意去幼兒園,幼兒園里多好玩。
這就是人的差別了。人的差別是巨大的。
多巨大?
有人說簡直是人與猿的差別一樣。
那——我們兩個誰是猿呢?
從身胚和模樣看,老實講,公平說,沒有貶低你的意思,我覺得你更像些。
好吧,就照你說的。沒想到他很大度,竟然一點不計較。
一個人,一只猿,之間有何公平可言?
只是一個比方嘛。只是想要說明一下人之間的差別呀!人之間即使有差別,也是平等的,也應平等相待的。
差別這么大,還能平等相待嗎?
平等相待并非說人之間就沒有差別。平等相待是一種教養,是即使知道人的差別,也對差別視而不見。這也就是所謂禮數,也就是平等待人了。
無論怎么說,都是你有理,你應改名:常有理。
五
說起上學時的午睡,我們兩個都有同感。
他怕,我也怕,趴在那張課桌上。
怕什么?睡不著!怎么睡都睡不著,想睡著也睡不著。
還有老師,不聲不響,坐在那個教室門口,看著有誰還沒睡著,可我偏偏就睡不著。
睡神,教室里面游蕩,硬不停在我的身上。
我想去游泳!能去游泳該多好呀!可我沒有那個膽量!
我將額頭伏在臂上,眼睛看著課桌下面。于是,地面波動起來,成了一個起伏的水塘。水面上有好多泡沫,一個破了,又是一個。泡沫上有水鳥滑過,伸出爪子,撕破水面,鳥嘴張著,叫著饑餓。它們似要攻擊我,似要啄破我的皮膚。它們叫著,嘲笑我,罵我是個膽小鬼。我的前面還有蛇,一條又瘦又長的黑蛇,它的身子左扭右擺,攪起一圈圈的波紋。它那平而尖細的腦袋翹著露在水的上面,回過頭來緊盯著我。
六
我和他在街頭溜達,來到廣場的噴泉旁邊。水池邊上好多孩子正在池邊玩著小船。水池中央,水柱落下,形成一道道的圓環。圓環一波又一波地把小船又推回池邊。見此情景,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兒時的情景。時間像是停頓下來。
他也隨之感嘆道:孩童時代的任何地方都是好玩的樂園呀!可是,人一長大了,就要自己打造了,雖然想要打造快樂,卻不一定好玩了。
我問為何這樣說?
他說他又想起了前幾日的同學聚會。
同學聚會,沒有其他,就是四字:想起童年。而童年,他覺得,其實就是一個謎。
一個什么謎?我又繼續問。
想起它時,它在眼前;時間變了,它也不變。然而,某日,你會發現,突然之間,它就走了,成了一片墨黑的虛空,就像你的某個器官活生生地被摘除了。
你又多愁善感了。我打斷了他的話。
他說是是是,他不該這樣,他又滔滔地說了起來,說起他的永遠的童年。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總是有點搖擺不定,觀點也是隨時變化,比如此刻,他就說,而且幾乎說服我: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本來就是件簡單的事情,如果你抓住此時此刻,幸福就會像草一樣滋滋滋地生長出來。
七
聽著兒歌《小蜜蜂》,他說他小時候曾被一只蜜蜂追過。后來,他跳進一條河里,在水下憋了好一陣,結果還是被蜇了,那蜜蜂竟哼著在水面上候著他。所以,他說這兒歌唱得根本就不對。什么小蜜蜂,嗡嗡嗡,大家一起來做工,來匆匆,去匆匆,別做懶惰蟲!它們并沒有那么忙。它們有的是時間。它們能等候。那些關于蜜蜂勤勞,如何忙忙碌碌的說法,都是錯的,是個謬論。
我說之所以會這樣,是他妨礙了人家做工。
他說那次只是路過。難道路過都不行嗎?
當然不行。你從蜂的地盤路過,就得遵守蜂的規矩。如果你是蹦蹦跳跳,手之舞之,嚇壞了它,它以為你是入侵者,不拼死搏斗那才怪。你要知道,它蜇了你,它的性命也沒了的。你雖無意殺死它,它卻因為你而死!
我被它蜇了一個包,痛了整整一星期!
你夠走運了,只有一只蜂,若是一群蜂,你就完蛋了!
那就沒有今天了。
那倒不見得。其實,只要尊重它們,也就能夠和諧相處。看過“蜂人”嗎?
顯然沒看過,只能搖搖頭。
那可真的是奇觀。養蜂人的渾身上下密密麻麻爬滿蜜蜂,像是穿了一件蜂衣。蜜蜂們都簇擁著他,信賴他,喜歡他,他也慈愛地看著它們,任它們在自己身上,還有臉上和頭上,爬上爬下,嗡嗡嗡嗡。
為什么會這樣呢?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把那窩蜂的蜂王放在了他的胸口上。
是母親的召喚啊!
八
說起母親,想起媽媽,有次下班回家的時候,帶給他一根棒棒糖,還有一把小雨傘。于是,在一個有風的日子,他就打開傘,從高墻上跳下去,相信自己能飛起來,結果掉在水泥路上,把腳踝都摔傷了。我曾經也這樣想過,幸虧我膽小,沒有去體驗。
你還膽小啊?那個時候誰不知道你打起架來不要命啊!
我不要命嗎?應該不是吧?我可是把我的命看得非常要緊的。我是生怕自己死的。但為什么別的人都那樣地看我呢?
回想小時候,打架的時候,我一進入那種場合,全身就充滿了恐懼感。總是覺得對方會一下要了我的命。于是,我就拼死一搏,就像蜇他的那只蜜蜂,好似要將我的性命置之死地而后生。果然,我的這種瘋狂總是壓倒了別人。一般來說,我都是——每打必勝,不勝不行,不勝我就決不收兵。
那你到底是膽子大還是確實膽子小呢?
我的膽子大,是我認定了一件事,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我的膽子小,是我天生敏感多疑,覺得世界上,時時有危險,處處是陷阱,我必須謹慎。現在,我老了,膽子更小了。
九
他不同意我的結論。他說他記得非常清楚,每個學期結束的時候,老師給我的評語中都會寫上這么一句:敢于與壞人壞事作斗爭!
我說是,是這樣。
他說,不過,我認為,你自己也明白,你斗爭的多數時候,只是為了你自己。
那當然,我承認,不過,你也要看到,當我為我自己斗時,僅僅只是為個人嗎?不,我同時也為了許多和我一樣的人。
也許吧。你的正義感很強,個性也激烈,你的眼睛太容易看到壞人壞事了。我與你不同,我小時候平和安靜,好像沒有看到過什么壞人壞事啊。
怎么會沒有?有人在班上稱王稱霸,欺負人,我就不服!
哦,我若遇到那樣的人,不跟他玩就是了,好像也沒人找事欺負我。
難怪老師給你的評語總是五個字:不關心集體!
是呀,每個學期都這樣講,但我不知道怎樣去關心,我看不出什么事需要我去關心。一切都很正常啊。
人跟人不同,人眼中的這個世界自然也就大不相同,人看世界的方式方法,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
我們相約去湖邊,又路過了那棵樹,那棵大樟樹。
那是我的樹!我轉頭對他說,小時候我常在樹下玩。現在它已老朽了。部分的樹干也枯空了,人用水泥填了起來。枝干也被柱子撐著,要不就會垮下來。看來它真的快死了!
你也多愁善感了。他打斷了我的話。所有的東西到最后都是會死的。它還算是運氣好的,沒有被人弄走砍掉,還一直活在它的原地。
它是樹中之豪杰啊!你想想,它這一生幾百年,見過多少風雨呀,庇護了多少生靈呀,它是有功的。當然,它就是再偉大,再豪杰,也是要死的,就像人一樣。一個人即使再偉大也是要死的,我們這些普通人那就更不用說了。
怎么又扯到人身上了?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幾年真的是經歷了太多人的死亡了。看著他們的肉身消失。他們生前用過的物品也被毀掉和丟棄。他們生前的音容笑貌也在漸漸變得模糊。雖然他們留下的相冊,有時還在被翻閱,但是隨著他們的同一代人的逝去,他們終將被遺忘。
有點兔死狐悲呀!
你不也是嗎?
是啊,是啊,我也是,誰最終都這樣。不過,你也可以想想,也許過了好多年,或許過了好多代,你的基因又會在某個子孫身上顯現,那個世上又會出現一個酷似你的人,又是一個新的人生。
那與我有什么關系?你信生死輪回嗎?
那你還想怎么樣?人都只有一輩子。這輩子足夠你活的了。
十一
站在湖邊,他問我,還打水漂嗎?他彎腰撿起了一塊不大不小的石子,在手指間轉了轉。然后,又彎腰,稍稍瞄了瞄,揚起手臂甩出去。石子碰到水面后,受驚似的彈起來,一連跳了好多次。石子在沉下去前,在水面上舞蹈著。
我沒動聲色,也彎下了腰,選了一塊扁平的,放矮身子,甩出去,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數著:一、二、三、四、五!呵呵,比他多一個,嘴上卻說著:不行了,不行了,真老了。
老夫聊發少年狂呀!想不到你身手還是這樣地有感覺!
我的心里想:這算什么呀!小時候什么不會玩呀,拍洋菩薩,抽陀螺,打彈彈。打出的彈子那個準,真的可說穩準狠。至今我都聽得到那些被我打中的彈子所碰出的清脆聲。那時,一群小伙伴,只要有人叫,就溜出去了。玩起來也真是瘋啊,簡直就是廢寢忘食,不知被媽媽罵了多少次。
小時候的最大幸福,不是別的,就是玩!
是呀,我們這代人,童年以后就沒有半點時間再玩了。哪里能像現在的人,三十好幾了,還在玩電游,而且那趨勢,會要一直玩到老。
電游這東西大概更加吸引人吧?
那當然,還用說?不然,哪里還會有這么龐大的游戲產業?現在的玩家很多是以此為終身職業的。這是個好玩又有錢還能出名的好職業。他們都被稱為“家”了,游戲家!知道嗎?國際游戲的大會上,他們也大出風頭的!
唉,聽你說,我感覺,我們這輩子,真的沒玩夠!
你還可以繼續玩嘛。你難道就沒看到好多好多的銀發一族都在抓緊時間玩?玩是人的天性呀!
十二
還想起釣魚,說起挖蚯蚓,把蚯蚓穿到釣鉤上。那時,從來就沒想過蚯蚓也是活著的,也是活潑潑的生命,它是否也會痛。
這說明你真老了。
而且還弱了。人只有在老弱時才會想到細小的生命也同樣是生命吧。
我可沒有你這么老人般的多愁善感。他說他小時候有段時間在鄉下,成日里在樹林中跑過來又跑過去。那些小動物,那些小昆蟲,就是他的好伙伴。它們的生,它們的死,他是見得太多了。
一條青綠色的大肉蟲,叭的一聲,掉在地下,很快就被無數的螞蟻包圍撕咬和纏住,無論它是如何蠕動,如何拼著命地翻滾,最終還是被蟻群浩浩蕩蕩地抬往蟻穴,成了它們的美餐。
一只鷹在天空盤旋,禾場上的雞呀鴨呀頓時嚇得四處逃竄,人們使勁地喊呀跳呀,使勁地哐哐敲著面盆,那老鷹卻置若罔聞,一個俯沖,閃電般,眨眼就叼走了一只雞。那只雞的好朋友,另外一只蘆花雞,從此也就嚇破了膽,病懨懨的,長不大了。
還有貓,母貓下完崽,口渴難耐時,竟吃剛剛生下的兒女。他眼睜睜地看著它吃,想要去搶救,那只平時溫順的母貓卻發出了嗚嗚聲,眼里射出兩道兇光。
動物界的那些事情,不是我們人能管的。但是,我們也知道,動物是人可利用的。
我們在山溝的小溪里,翻開石頭捉小蝦,捉小蟹,拿回家,先是放在盆里玩,玩夠了就烤著吃。蝦蟹烤紅了,又香又新鮮,對于那時肚子里沒有什么油水的孩子,真的實在是太需要了。
那時,我們也養蚯蚓。埋一堆剩菜葉在屋外的垃圾里,天天澆些米潲水,不久就會生養出好多好多的大蚯蚓,用來喂雞鴨,雞鴨特肯長。
雞鴨長大了,自然殺了吃。那時的伢子十多歲,不管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就會殺雞了。殺雞就是家常便飯,你不學幾手,以后怎么能持家?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天生就很殘忍啊?
沒有,沒有,怎么會?那時的你是自然人。
那么,現在的我和你又是什么人?我們與自然已經隔離了?
我不知道如何說才好。現在已經有人在說:人類正在大步跨入機器人的新時代。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