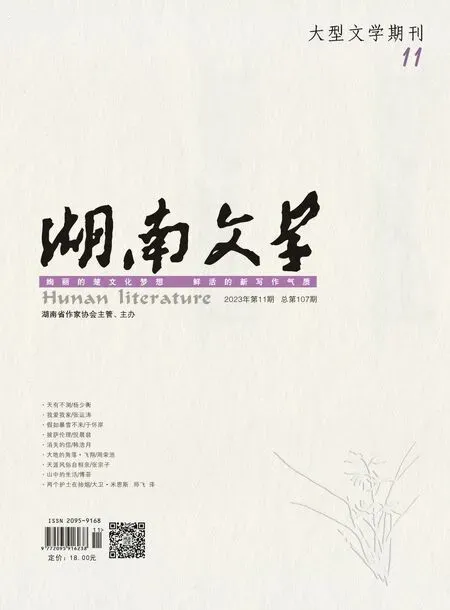大地的角落·飛翔
周榮池
我常常覺得雞鴨鵝是村莊里的鳥兒。它們只是被眼前的生活所圍困,就像死守的人們失去遠走高飛的夢想。哪天有個孩子考學或者當兵走了,人們也說是“雞窩里飛出了金鳳凰”。人們總是有一種認命的態度。這種認命多數又是有些腳踏實地的。如果村莊和土地消失了,很多事實都會消失。至于天空,如果沒有土地,就只能更加地空洞。
人們的口頭也非常實際,把羽族統稱為雞鵝鴨鳥。遙不可及的天空和村莊似乎沒有關系,如果能成為鍋里的一口湯倒才是令人滿意的。此外,沒有人關注飛翔。
一
母親有一只黃土壺,外觀的云紋非常精致。她在里面點了些碎草,像雞窩一樣堆著撿回來的蛋。雛雞是自家的母雞孵的。母雞一旦“靡”了,大概就是母愛泛濫起來了。父親就把蛋放在窩里任它去孵。也有人家不愿意這么麻煩,就把“靡”的雞塞進冷水逼醒,并用一根雞毛穿過它的鼻息,不知道這是什么古怪的方法。孵雞要二十一天的時間。這一點父親很有些經驗。他過幾日就把蛋拿到燈光下照。他能判斷出能不能出小雞。有些不能出殼的蛋被稱為“壞蛋”。他也不舍得扔,殼里面有了成形的“雞喜子”,用韭菜炒著吃,要放大量的胡椒粉才能掩蓋那種肉身怪異的氣息。他的這種吃法是從一位上河的舅舅那學來的。這位舅舅有一條很大的船,在里下河平原的河流里四處游蕩,尋找一些屬于他的生機。他是販蛋的——把各家散落的鴨蛋收回來賣給炕房。(我后來去徐州的丈人家,蘇北人說“嬎蛋”音同“販蛋”,是雞鴨下蛋的意思,這讓我想起這位表情古怪的舅舅。)他在炕房的日子比在家還多。他的船到鄉里炕房的時候,就央人帶信給父親去喝酒。父親不喜歡他船上的味道。人們總是嫌棄船上的人吃喝拉撒都在河里。但他燒的“雞喜子”好吃,我有一次吃了小半碗,肚子里仿佛能聽到雞叫。這位舅舅也把炕房里的雛禽販賣到各個村落里。父親說他過的是雞鴨鵝屁股里的日子。又說他這個“瞎子”是精明的——他總是戴著厚厚的眼鏡,又把東西湊在眼前去看,所以人們就叫他瞎子。他也從來不生氣,心里敞亮得很,腰包里也是鼓鼓的。
父親關于侍弄雞鴨鵝的本事好多是從他那學來的。每次要請教的時候,父親總是擠著笑容說:“你看我們子舅之間還有什么好隱瞞的?”這位舅舅確實有點本事,雛鴨經他手一捏,又湊到眼鏡下,聞了聞那淡淡的腥味,就能辨別出公母來。他的船在平原上的河水里來來去去,也像是一只漂泊的鴨子。他的漂泊給了沿途的村莊很多生機,所以人們都盼望著他的船常來。
母親黃土壺里的雞蛋是不賣給他的。村莊里也有專門來收蛋的人。他們抓著蛋看一下,只要是“頂磅”的就不稱,按個數給錢。十枚雞蛋一斤就是頂磅。其實也并不十分計較,大多都是毛估估。這筆收入非常重要。“雞生大蛋”這個詞是春節之前就寫在春聯上的禱祝。而對養鴨的父親來說,“鴨上滿欄”是更重要的事情。
他養了一群粗魯的鴨子。為了教育我以后不要成為“鴨司令”,他把手上的“舞把”塞在我的手里命我去放鴨。這是一件非常寂寞又常令人暴躁的事情。那些被稱為“鴨溜子”的畜生們,在河水里還算是老實的,一旦登陸進了秧田簡直就像到了天堂一樣歡快,一眨眼就無影無蹤。我只能坐著聽它們若隱若現的啾鳴,才能大概確定它們的位置。等到日落西山的時候要趕鴨子上來,那是天底下最揪心和落魄的事情!你明明聽著那些聲音在稻田響起,可當人到達的時候,它們卻突然沒有了影子。站在稻田中央,我就像是稻草人一樣尷尬。等著再循聲而去,它們早又轉向另一個方向。秧田里的泥水松軟膠黏,腳就像被咬住一樣行走艱難。拼命地吆喝著一群活物到了田邊,似乎身后又還有零星的叫聲。轉身再去尋找,前面的又炸開來。父親說鴨群散了叫“炸了”。他和這些生靈斗了一輩子也沒有十足的把握。等把掉隊的殘兵敗將找回來,我用竹篙狠狠地抽打它們,可只是激起一點憤怒而無奈的水花。
最為可恨的是,一身狼狽的我像掉隊的鴨子一樣赤腳奔跑,還沒有緩過神來就聽到對岸父親的呵斥。他的憤怒有時候是無端的,好像村莊沒有了他扯著嗓子的叫罵,就沒有其他內容可以關注一樣。我倔強地站在河邊不回去,就像與他周旋的鴨子。我也默默地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令人跳腳的爛泥地。但父親是熱愛他的鴨子的,不然他不會一輩子都和這些聒噪的牲畜周旋。鴨子長大了,他就背著手看看。那些莽撞的鴨子被他訓練得很有些規矩,每天早出晚歸在村莊的河流里覓食。他常常酒后在河岸邊的草地里睡去,醒來了看看那些淘食或者休息的牲畜,臉上都是滿意。
他后來又學會了用黃泥腌鴨蛋。這個很是受城里人歡迎。但他仍然很少去城里賣,他一貫覺得精明的人難打交道。人們就只好上門來問。他把自己的號碼用油漆寫在墻上,其他并不做任何的說明,也不會因為收入多寡而或喜或怨。這倒是很有些意思——也許是他和這些鴨子斗了一輩子,最后終于沒有任何怨氣。脾氣好的那是鵝。鵝踱著步子在門口轉悠。它們并不愿意去很遠的地方。鴨子是要雜食的,鵝卻有些認命地只愿意追逐樸素的青草,是個沉著而樸實的素食主義者。但村里人好像也并不怎么養鵝,難得聽到一兩聲尖銳而驕傲的叫喊。它們還頗有些介懷陌生的人,會伸出嘴來表現出一點兇猛而狹隘的性情。
殺鵝在村子里是一件大事,之前全家要好好地合計一下,并且吆回要好的親戚朋友來。我們這樣的人家是沒有大事的,所以也并不會去殺鵝——它們也沒有飛走。
二
天上自有鳥雀飛過,就像云彩一樣來去,似與村莊并沒有任何瓜葛。它們有時候落下來,找到幾顆種子又或是休息片刻,也許仍然不會記得某個村莊。這種來去有點悲涼的意味——有些離開就是永遠不再回來。
有一次三叔抓住一只“瓦灰”。這只鴿子大概是乏了,懸在半空往村莊來,一走神撞進了屋子里。三叔逮住它放進養雛雞的籠子,一時非常得意。他當過兵受過集體的熏陶,一生總有一種退不去的自豪表情,似笑非笑的臉上卻有著明確的意思。這只鴿子從哪里來呢?只有它自己知道。現在它不再能信守承諾了,被圈禁在陌生的村莊里。我去看過幾次,突然起了一種古怪的情緒——有些舍不得它又或者有點妒忌的意味,想悄悄地放了它。可不幸的是,我以為自己悄悄松動了一點那破落的門能救了它——我又不敢承擔直接放走它的罪責。最終人們并沒有放過它。它變成了一鍋湯。他們不知道哪里學來的方法,把鴿子悶進水里致死。傳說鴿子不能見血,它們的同類可以辨認血跡。我不知道這種慈悲有什么意義。大家都流著口水說,隔著窗戶都能聞到香味。村莊似乎容忍不了什么好的事物被流于空洞——比如讓它飛走——只有吃到肚子里才是安心的。
父親有些不以為然地說:“吃一年不過長一歲。”他是連野鴿子都不愿意吃的,認為“沒肉”。人們對于禽鳥的判斷是以肉多少計的,而父親覺得肉有肥白才算是正經。他們不在乎什么飛翔或者好看的問題。所以沒有人去贊美它們的叫聲,甚至都不愿意叫它們的名字,只以“雀子”統稱。人們認為這些大抵都是些無用的東西,就像生活里多余的情緒。這倒讓鳥雀們自在起來。萬物生長自有道理,有些無用本事也很要緊。我們小時候從書上學過做那種笨拙的“機關”去捉鳥,可費了一些糧食卻總沒有收獲。父親怒罵著我們浪費的口糧。他有些殘暴地把米拌上農藥撒在門口,把那些歡快的野鴿子毒死了一片。他把那些僵硬的尸體埋到地里,又冷漠地對我們說:“這些雀子性子野,養不‘家的。”家就是馴服的意思,家確實也馴服了人們。這是他們要的馴服,鳥雀們何嘗要把村莊當家了呢?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而村莊某種程度上又是靠著自私、煢煢孑立而風雨不倒的。
村莊里也有人養鴿子。這是要有些閑情和手段的事。我的姨父就養了很多的鴿子。父親總有些不以為然。姨父過去家里是地主——人們說這話的時候總有一種古怪的情緒。所以他養的鴿子似乎也被人們所不屑。但那些鴿子并不知道這些,顧自無憂無慮地飛到天上去,好像要集體逃脫一樣。但是看到夕陽疲憊落幕的時候,它們又飛回來落在屋脊上。它們的羽毛比瓦片的顏色鮮亮一點。那些瓦據說還是“地主”在的時候置的家業,已經蒼老了。到夜色完全降臨,它們就回到自己的格子里。那間屋子里的味道很不好,與鳥雀在天空飛翔的美感聯系不起來。美到底是天上虛幻的事情。
外婆會把鴿子蛋帶給我吃。那時候我瘦弱得像家境一樣令人焦慮。她多一個雞蛋也要走好遠的路帶給我。鴿子蛋像鵪鶉蛋一樣,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滋味。至于營養,對于緊缺的身體來說,也是杯水車薪的事情。鵪鶉蛋平時也吃不到,它只會出現在酒席的雜燴碗里。農人們對肥厚的肉皮更感興趣,零星的幾枚鵪鶉蛋都給孩子。我總覺得鵪鶉蛋是一種含有悲情的食物。集市上有人去兜售鵪鶉。它們被裝在一個破舊的籃子里瑟瑟發抖。這些鵪鶉買回去都是剝了皮毛吃肉的。它們的內心敏感而卑怯,受了驚之后便不能下蛋。人們又嫌棄它的瘦弱,固執地覺得不如野鳥的味道。事實上這只是人們囊中羞澀的辯詞。人們和鵪鶉一樣也內心卑怯。
村頭通往城市的大路邊有人養鵪鶉。那個人家是處單頭厙子。鵪鶉是受不得煙火人間的熱鬧的。村莊也嫌棄那種工廠一樣養殖所帶來的壞味。所以它們只能孤零零地遠離村莊。這處屋舍就像村莊老舊的衣服上一塊扎眼的補丁。但幾十年過去了一直還在,人們也就原諒了這種隔膜。屋子里主人的古怪性情也被理解了。我少時外出求學總要經過這處房子,心里總想著去看看那些瑟瑟發抖的禽鳥。汽車并不理會我的雜念,總是果斷地奔馳而去。后來我有機會回鄉工作,竟然安排我去動員這一戶搬遷。新的鄉村建設對這一塊補丁忍無可忍。而我卻有些浪漫主義地認為這戶人家已經有了獨特的意境。我沒有把這話說出來。我知道人們不會理解我的天真。但我帶著一種微妙的情緒和那性格古怪的主人談話,我也聽得出他的戀戀不舍。那些鵪鶉在籠子中啾鳴。主人說平素生人都見不得的,若是要搬遷它們就要全部被淘汰。一種禽鳥無路可走竟然比人無家可歸還要悲情。最后我說服大家保留它們的立錐之地。我覺得沒有什么比失去家園更悲情。
后來那處房舍依舊安放在由來已久的光陰里。每次經過時我都會想起自己曾經做過一個非常深情的決定。回到村莊我總是有這種留戀的情緒,害怕古舊無用的屋舍慢慢地消失,就像那些野鳥飛過虛空難以覓得身影。
三
土地上原來有很多野意的叫聲,總是遙遠得有點虛無,但又是那么確切與分明。野雞的叫聲像頑固的方言般古怪,這是無從改變的遺傳。不知道它們究竟躲在哪里——那平坦的田野分明就是空無一物的。過去平原上有打獵的人來。他們扛著土制的火槍,人們對朝下的槍口敬而遠之。他們也不與人說話,只豎著耳朵尋找那些野外的聲響。突然間田野里起了一聲殘忍的巨響,隨即又像消散的硝煙一樣安靜下來。同行的獵人發現了野雞的尸體,默默地撿起放進開槍者身后的簍子里。那種竹制的簍子里是滴著血的,有些血沾在竹片上,有些滴到了泥土上,這些都沒有人去關注。村里人會和獵人要一兩根漂亮的大翅,插在家里的燒香的大柜上。許多年后,羽毛上沾了塵灰,色彩卻依舊奪目。
聽父親講野雞總是在墳頭的,這讓人有些莫名的懼怕。不知道它們吃的種子是不是和墳地有什么古怪的關聯。人們好像只是任由它在野地里鳴叫,很少去主動干擾它們,盡管聽說它也是一口好湯。“春不撿雞,冬不撿兔”,即便是輕而易舉地碰見死了的野雞,也一律無人問津的。人們害怕把不安帶進村子里讓家禽遭殃。對于意外的收獲,村莊一直是很警惕的。野雞對于日常來說還有一種非常怪異的隱喻,是日常所不能容忍的。“不怕墳頭野雞叫,就怕屋后蛤蟆跳”就是其中一種土氣的理論。墳頭的號哭是死去的舊事,屋后面的蛤蟆是活人的念頭。人們對于外情是忌憚的,這倒是一種非常迷人的規矩。
喜鵲在村莊里是受歡迎的。黑白相間的它們被附著了美好的情緒。只要喜鵲登上枝頭,人們就會念叨有好事來了。這是村莊的一種勢利。一種同樣是喜鵲的鳥,因為灰土色的羽毛而不被待見。人們叫它“三蠻子”。大概人們覺得它的口音也是不佳的。村里人對外來者也有這種狹隘。因為口音不好——實只是和自己口音不一樣——南邊人被叫作蠻子,北地來的叫作侉子。人們覺得自己的村莊就是中心。三蠻子也很怪異。它只要叫起來,母親就會陰著臉說:“又有蛇來了。”蛇神出鬼沒地到來,和貓狗爭執起來,三蠻子就在樹梢拼命地叫。不知道它是助威還是看笑話。它還有一種劣跡,就是喜歡偷食曬在門口的咸肉。有些人家用舊的漁網罩起來防備它。其實我們有時候也偷偷地用刀割肉,用樹枝挑著烤了吃。鄰居們知道我們的這些詭計,笑話窮人家孩子的頑劣。奶奶總是不以為然地說:“是三蠻子偷的,和孩子有什么關系?”我們那時候活得不如一只鳥。
麻雀也是不省心的家伙。它們就像檐口邊無數的省略號般多余。它們看起來和日常很友好,總是在眼睛邊跳動,像親朋一樣熟絡。它們細小的肚里卻詭計多端,一陣陣地往返于莊稼地里,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公認的危害。等到它們洗白了身份成為被保護的動物,人們依舊對其保持著警惕。下秧的時候會有一件很無聊的事情——看鳥。那時候學校逢了耕種收割的時候就放忙假,因為先生們也要務農的。浸過的種子有了鮮嫩的芽頭,撒在水田的壟子上育秧。那幾日麻雀們一陣陣地趕來。生產隊里安排每戶輪流去看鳥。發給一具銅鑼,一遍遍地在田邊敲響。后來各家自掃門前雪,孩子們就被安排到田邊敲盆,就像插在田壟間分界的樹樁一樣孤獨。看鳥,說起來是一件很輕省的事情,但有著無比的寂寞。那些敲打聲此起彼伏響徹田野,沒有嚇唬到鳥雀的飛翔,卻讓童年縈繞著揮之不去的雜音。
也有人家扎了稻草人在地頭站著。那種草人頭上還戴了一頂破舊的草帽,目無表情的矗立顯得異常古怪。鳥雀遠遠地看了先是有些恐懼,久了之后竟然飛過來站在草人肩膀上休憩。秋后麥子播撒到地里,它們同樣也去泥土縫隙里找——這不是挑釁,饑餓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鳥雀和人一樣只能鋌而走險。聽說過去饑荒時,人們實在絕望了就去薅稻穗塞在嘴里,或者偷挖埋下去的蠶豆種子。這都是走投無路的事情,地上的人或者天上的鳥都會面對絕境。我在地里看鳥的時候,經常想這些古怪的問題。我見它們偷嘴吃飽了之后,列隊站在電線上,像是逍遙法外的罪人。它們實也是村莊的居民,和人們一樣多有無奈。它們的面孔也是一樣的,就像平原上無數表情相像的人們。
有一個傍晚,我見過一只鷹落在電線上。不知道它從哪里來,也不知道要去向哪里。它和村莊里的鳥不一樣,只是獨行在自己的世界里,和這個村莊毫無牽連。它更不會像雞鴨鵝那樣落地成為實用,就靠獨自的飛翔驕傲地活著。那一天我真的為了一只鳥掉下了眼淚。村莊里的生活太過艱難,我們都想著能夠飛離這里,奔走已經是太緩慢的辦法。我們是要逃亡一樣離開村莊,離開早就已經爛熟于胸的事實。人們不懂得這種飛翔的意味,當然對這一只陌生的鳥也毫無興趣。但它的來去讓我心里升起了一種激動,好像我陡然長出了一對倔強的翅膀。
我一直看著它,直到天完全黑透。我在漫長的深夜里睡去后,還記得這只鳥與我并無瓜葛的飛翔。
責任編輯: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