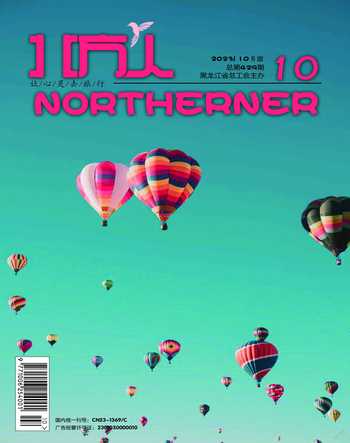死與生的吻別
梁衡
上飛機前還有一小時的機動時間,我堅持要去看看莫斯科的公墓,看看那個特殊的文化角落。
去得匆匆,竟連大門口是什么樣子也未及細看,只記得是一條很寬的街,高大的門,門對面好大一片樹林,綠濤翻滾著,無鬧市的喧囂,有郊野的清風,氣氛是一種淡淡的寂靜。一進門,甬道兩旁分列著一排排的常青松柏,松柏下是死者整整齊齊的眠床。這里沒有中國公墓常見的土堆,也無供骨灰的靈堂,只有綠樹護著青石,青石襯著鮮花,猛一看像一個清凈的公園或誰家的庭院。
我向一個靠近路邊的墓地走去。墓蓋是一面極光潔的花崗石板,石板中央伸出兩只大手,也是花崗石雕成,粗壯的腕部,有力的骨節,立時叫人起一種堅實的聯想。這兩只手輕輕地合攏著,捧著一塊三角形的大紅寶石。我一時不解了,這組頗具匠心的雕塑,就算是墓碑嗎?那么這下面安息著一個怎樣特殊的人呢?我在墓前肅立良久,細細揣度著,那雙手從石中沖出時的強勁與合攏時的輕柔,那花崗石的純黑與寶石的鮮紅,幻化成一種多層復合的美,將人引向一個深邃的意境。向導過來告訴我,這里安眠著的是一位著名的心臟外科專家,他一生用自己靈巧而有力的手拯救過無數人的生命。
噢,我一下明白了,用這種含蓄的手法來表達死者的生平與事業,表達生者對死者的紀念。最哀切的事情卻用最藝術的手法來做,這是一種多么平靜、超脫而又理智的舉動啊!我們說長歌當哭,他們卻更祭以藝術。
我慢慢地往里去,一股強勁的藝術魅力如磁石般吸引著我。這哪是什么墓地,簡直是畫廊,所不同的是這里的每一件藝術品下還有一個曾是活潑潑的人,那是這件藝術的根,是它的主題。墓碑全部是清一色的黑花崗石,打磨得極光亮,熠熠照人如一面銀鏡。有的只簡單地在這石面上刻出死者的頭像,輕輕的又淡淡的如一幅隨意素描。說是清淡,那不過是藝術的質感,這石與錘造就的作品自然是風雨不去、歷久如新的。有的鑿成浮雕,死者的形象微微突起在石板、石塊或石柱上,若隱若現,好像在天國那邊透過云霧回望人間,更多的則是半身胸像和各種含義深刻的組合雕塑。但這偌大的墓地無兩塊相同式樣的墓碑,生者不肯抹殺死者的個性,也決計要表現出自己的匠心。
一位叫依留申的飛機設計師的墓碑是一個圓柱形與凹面的組合,圓柱上雕有他的胸像,胸前有三枚醒目的大勛章。那塊凹面石塊立襯在石柱后面,表示無垠的天穹,天穹上還有些飛機的航行軌跡。看著這一組近在咫尺、盈縮如許的石雕,我頓然如馳騁藍天,并感到一種凌云的壯志。有一位海軍將領,他的墓蓋上只有一只大鐵錨,黑錨金鏈,屹然挺立,風打浪涌,不動絲紋。有一組更特殊的墓碑,石柱上橫著一個大箭頭,上面浮雕著6個人的頭像,這只箭頭正穿云過霧急急飛行,原來這6個人是一個派到國外的救援小組,不幸同機遇難。
松柏中有一組男女雕像吸引了我。不用說這是一個合葬墓了,令人吃驚的是,兩人全是裸體。男子略向前俯身,依在一石上,右臂彎回,手中握著一柄鐵錘;女子偎在他的身后,手執一條輕紗,款款地飄在身后。兩人都目視前方,但我切實地感到他們的心是那樣的相連相通,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最純真大方的愛是用不得一點遮掩的。
原來這對夫妻,男的是雕刻家,女的是一位芭蕾舞演員,都是搞藝術的。我想這組作為墓碑的石雕一定是他們生前設計好,叮囑后人這樣創作的。試想以我們的傳統觀念誰愿在自己的墓前留一個裸體像呢?又有誰敢將自己的親友雕成一個裸體立于墓上呢?但藝術家自有藝術家的思考。世間雖有山水的磅礴,花草的艷麗,但哪一種美能比得上人體蘊藏的靈感呢?而這種人類的共性之美,并不是隨便哪一個形象都可以表達的,只有那些個別的、極富外美條件的人體,才可充分表現這種內蘊的美感。
這兩位藝術家,一個人是終生為人們塑造這種能表達內蘊之美的外形,另一個則所幸天地鐘秀其身,就矢志以自己美的外形去表現人類美的靈魂。總之,他們一生都沉浸在對人體美的追求、創造中。正當他們的事業處于頂峰之時,突然上帝要召他們而去,這是多大的遺憾啊!我好像聽見他們彌留之際請求上帝答應他們再給世上留下點東西,上帝說只許留一件,這就是墓碑。于是他們就將自己的一生濃縮在這塊石頭上。他們要將自己美麗的軀體展示在這里,用這力、這柔、這情,留給后人永恒的美。什么才能久而不朽呢?石頭。什么才能跨越生命的“代溝”,無言地表達感情與思想呢?藝術。于是這石頭的藝術便成了死者與生者在墓前吻別的信物。
(摘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生誰能無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