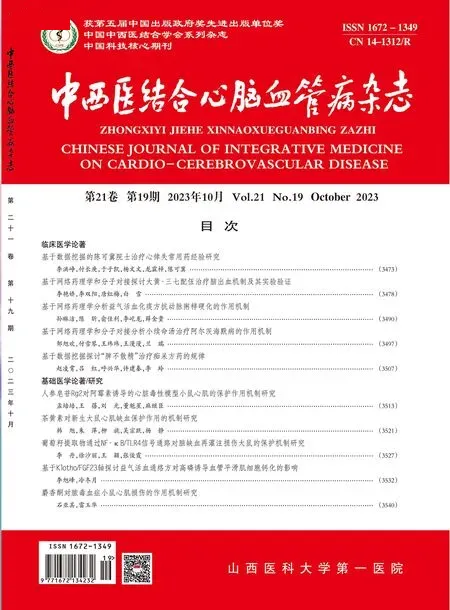中西醫結合治療高血壓亞急癥的實踐與思考
甄曉敏,張 騰,2
高血壓亞急癥(HU)是指收縮壓(SBP)≥180 mmHg和/或舒張壓(DBP)≥110 mmHg,需接受治療但無急性血壓升高引起的靶器官損傷發生,但病人可有血壓明顯升高造成的眩暈、頭痛、胸悶、鼻出血、煩躁不安、急躁易怒等癥狀[1]。1%~2%的高血壓病人存在急性血壓升高,需要緊急藥物治療,其中75%屬于高血壓亞急癥[2-3]。
血壓的急性升高可能與體液縮血管物質的流入有關。全身血管阻力升高后,血管壁應力的增加和相關的內皮損傷導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激活以及纖維蛋白沉積,如果這種狀態持續存在,將導致血管纖維素樣壞死和組織缺血的發生。同時,壓力性利鈉和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的激活將引起容量耗竭和進一步的血管收縮,造成重要器官供血減少,甚至出現靶器官損傷的不良預后[4]。引起高血壓亞急癥發生的病因主要涉及肥胖、女性、心血管病史、糖尿病、吸煙等,其主要原因是降壓藥物治療的依從性差,這給高血壓亞急癥的治療帶來巨大挑戰[5]。研究顯示,高血壓亞急癥病人在降壓藥常規治療1個月后仍有80%以上的病人血壓控制未達標(<140/90 mmHg),即便治療達到6個月仍然有超過60%的病人血壓控制未達標或者增加了口服降壓藥種類[6];其全因死亡率仍然很高,1年與3年的全因死亡率分別達6.8%和12.1%[7]。
1 中醫學對高血壓的認識
中醫學中并無高血壓的病名,高血壓是現代醫學的病名,臨床以眩暈、頭痛為主癥,常伴有失眠多夢,急躁易怒,心悸、耳鳴、夜尿頻、腰酸等癥狀,中醫根據其臨床癥狀多將其歸屬于“眩暈”“頭痛”等范疇,亦有學者提出將“脈脹”作為高血壓的中醫病名。然目前高血壓臨床治療指南中均未提及中醫藥在高血壓亞急癥治療中的應用[1,8-10],但中醫藥治療急危重癥方面具有悠久的歷史,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中病機十九條,就已經記載了“熱、瞀、瘛、厥、固、泄、禁、慄、痙”等多種急癥的發病機制。之后,在中醫學家對急危重癥治療的探索過程中,尤其是在熱病及瘟疫方面,涌現出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及學說,例如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首次提出六經辨證治療各種傷寒急癥;晉代葛洪《肘后備急方》記述了治療各種急危重癥的單方驗方;清代溫病學派提出衛氣營血及三焦辨證治療瘟疫急癥等。高血壓亞急癥發病急、危害大,中西醫結合策略、方案亟待發掘探索,意義重大。
2 高血壓亞急癥的中醫特點
張騰教授課題組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發現高血壓亞急癥病人具有獨特的臨床特點,風火上越證(包含肝火亢盛、陰虛陽亢兩型)是其主導證型。高血壓亞急癥病人多是長期患高血壓的老年人,常合并多種慢性病,其肝腎精血素有不足,經脈絡道多有痰瘀,遇煩勞、季節變化等因素刺激,易肝陽暴亢,相火挾風上越,阻遏蒙蔽腦竅清陽,發為頭暈、頭痛、頭脹等為主要表現的高血壓亞急癥,若清陽不展,氣機郁滯日久,還易形成風火痰瘀阻塞腦脈的中風重癥等。基于其獨特的病機特點,張騰教授提出治療高血壓亞急癥當以清肝為君,益腎為臣,祛風通陽為佐使的治療法則。精芩平脈方(原名清肝益腎祛風方)組方:炒黃芩15 g,夏枯草30 g,石決明20 g,黃連6 g,柴胡15 g,川芎15 g,羌活15 g,防風15 g,黃精15 g,懷牛膝15 g,桑寄生15 g。方中炒黃芩、夏枯草、石決明、黃連味苦性寒,清瀉相火為君;黃精、懷牛膝、桑寄生酸苦甘寒,滋水涵木為臣;柴胡、川芎、羌活、防風辛散輕盈,祛風通陽為佐使。全方使腦竅清陽伸展,氣機迅速恢復流通,相火內風得以清平,肝腎精血得以滋養,標本兼顧,是以治療高血壓亞急癥效果顯著[11-20]。
3 高血壓亞急癥的中醫臨床觀察
2021年11月—2022年3月,張騰教授課題組連續觀察了就診于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急診的高血壓亞急癥病人30例,年齡(70.44±5.88)歲,其中,女25例,約占83.3%。30例高血壓亞急癥病人中,未服降壓藥物1例(3.3%),單純口服鈣離子通道阻滯劑(CCB)類降壓藥物4例(13.3%),單純口服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ARB)類降壓藥物6例(20.0%),口服2種降壓藥物聯合治療10例(33.3%),口服3種及以上降壓藥物聯合治療9例(30.0%)。聯合用藥多是CCB、ARB、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利尿劑、β受體阻斷劑、α1受體阻斷劑等的組合。
所有病人均于就診當天給予尼卡地平注射液緊急降壓,使血壓控制在160/100 mmHg左右。次日,在原降壓藥物治療基礎上,給予精芩平脈方煎劑400 mL,早晚分服,治療2周,并隨訪病人1、2周時的血壓情況。血壓療效評價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1],分為顯效、有效、無效。顯效:DBP降低>10 mmHg,并達到正常范圍;DBP雖未下降至正常,但已降低≥20 mmHg。有效:DBP降低<10 mmHg,但已達到正常范圍;DBP較治療前降低10~19 mmHg,但未達到正常范圍;收縮壓(SBP)較治療前下降>30 mmHg。無效:未達到以上標準者。
結果顯示,1)在不增加其他口服降壓藥物或不增加原口服降壓藥物使用量及使用次數的前提下,30例高血壓亞急癥病人使用精芩平脈方干預1、2周后,頭暈、頭痛、頭脹、腰酸、膝軟等主要癥狀顯著改善。2)入組時SBP為(188.5±10.23)mmHg,干預1周時為(149.5±8.10)mmHg,干預2周時為(139.4±9.70)mmHg;入組時DBP為(93.93±11.99)mmHg,干預1周時為(84.87±8.44)mmHg,干預2周時為(82.30±8.58)mmHg,血壓較入組時明顯降低且干預2周時收縮壓較干預1周時進一步下降(P<0.001)。3)干預1周時,30例高血壓亞急癥病人中顯效7例(23.3%),有效23例(76.7%),無效0例,總有效率100%;干預2周后顯效16例(53.3%),有效14例(46.7%),無效0例,總有效率100%。
4 驗案舉隅
病例1,病人,女,73歲,2021年11月28日初診。主訴:突發頭脹痛2 d。近來家屬患病,內心焦急,夜不能寐,平素性情偏急躁,睡中易醒,舌淡紅苔薄白,脈弦。急診室血壓200/100 mmHg。既往高血壓病史10余年,腔隙性腦梗死病史5年,平素口服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絡活喜)5 mg,每日1次;奧美沙坦酯氫氯噻嗪片20.0/12.5 mg,每日1次;阿司匹林100 mg,每日1次。急診給予尼卡地平緊急降壓后,處方精芩平脈方,7劑,水煎,早晚分服。
二診,2021年12月5日就診。頭脹痛及失眠改善,舌淡紅苔薄白,脈弦。診室血壓135/80 mmHg。繼續服用原方,7劑,水煎服,早晚分服。1周后隨訪,頭脹痛未發,睡眠顯著改善,服中藥過程中絡活喜自行減半,血壓仍維持在130/80 mmHg左右。
病例2,病人,女,73歲,2022年1月22日初診。主訴:頭暈頭脹2周加重1 d。近2周來,病人因家事煩惱失眠,后出現頭暈、頭脹時作,素有腰酸、耳鳴,舌暗紅少苔,脈弦細。急診室血壓180/108 mmHg。既往類風濕性關節炎20余年,高血壓史10余年,長期口服硝苯地平控釋片30 mg,每日1次;替米沙坦氫氯噻嗪片80.0 mg/12.5 mg,每日1次;鹽酸阿羅洛爾10 mg,每日1次;甲氨蝶呤7.5 mg,每周1次;潑尼松5 mg,每日1次。急診予尼卡地平緊急降壓后,處方精芩平脈方,7劑,水煎,早晚分服。
二診,2022年1月29日就診。頭暈、頭脹、失眠均明顯改善,舌暗紅薄白苔,脈弦細,診室血壓144/82 mmHg。繼續服用原方,7劑,水煎服,早晚分服。
1周后隨訪,病人訴頭暈、頭脹癥狀消失,失眠顯著改善,自測血壓維持在135/80 mmHg左右。
按:以上兩則病例,均為老年女性,既往長期高血壓病史且合并其他慢性病。病人年老多病,在本為肝腎虧虛,肝陽偏亢,在標有痰瘀阻絡,故臨床常見性格急躁、腰酸、耳鳴、失眠等癥,偶逢境遇不遂、家事煩擾、季節變換等,使亢陽乖張,化火生風,上擾腦竅,清陽被遏,血壓急劇升高。因此,精芩平脈方中重用黃芩、夏枯草、石決明、黃連以清火平肝為君,黃精、懷牛膝、桑寄生以固本求源,助君藥滋水涵木為臣,更佐以羌活、防風、柴胡、川芎祛風通陽,全方使清竅之郁陽得伸,上擾之相火得清,在本之精血得滋。此外,方中祛風藥物尚具有引經報使作用,引清熱藥物上行頭目,使陽伸火滅,不僅無風火相煽之虞,反是遣方用藥精華所在。在臨床中觀察到精神壓力、失眠、勞累等煩勞因素及季節變化也是高血壓亞急癥發生的重要誘因,其根本上是這些誘因導致高血壓病人肝陽暴亢,風火上越而引起高血壓亞急癥發生。
5 高血壓亞急癥辨證實踐與思考
高血壓亞急癥病人多是久病高血壓的老年人,常合并多種慢性病,在腎虛肝亢的基礎上,遇精神壓力、失眠、勞累等可使亢陽乖張,引起血壓急劇升高,正如《黃帝內經》所言:“陽氣者,煩勞則張”。近來,煩勞因素與高血壓之間的相關性受到廣泛關注[22-24]。研究表明,焦慮、失眠等可以加劇血壓的變異性,增加高血壓亞急癥發生的風險[25-26]。老年女性更易受到煩勞因素影響,其焦慮程度普遍高于男性,該性別特征可能是高血壓亞急癥病人以老年女性為主的原因[27]。季節變化,尤其是遇到寒冷的季節,可誘發血壓升高。研究表明,高血壓病人冬季血壓普遍升高,老年高血壓病人尤甚[28-29]。冬主藏,陽氣潛伏于體內,對于肝腎虧虛的老年高血壓病人而言,陰不制陽的病理改變尤為突出,更容易導致風火上越,上擾清竅的發生。因此,冬季老年高血壓病人高血壓亞急癥發病率升高,同煩勞因素的致病機制類似,仍然責之內風,并非由風寒外感所致。從另一角度來看,外感風寒的傷寒證鮮見其血壓突然急劇升高的情形。
臨證中高血壓亞急癥的中醫病機多由煩勞、季節變化等因素誘發老年高血壓病人肝之陽氣升動無制,亢而化風,肝中內寄相火不安其位,上擾腦竅,郁遏蒙蔽清陽所致。《內經》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生理情況下,相火安于其位,具有溫養臟腑百骸,推動人體生機的作用。五臟皆有相火,其實為人之元氣,張介賓《景岳全書·傳忠錄·君火相火論》曰:“然以予之見,則見君相之義,無藏不有……此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臟各有位,則五臟亦各有相,相強則君強,此相道之關系,從可知矣。”若相火離位,則為賊有害。肝為剛臟,主動主升,發病最易動風,故內經言“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而肝陽上亢,風氣內動,相火離位,風火相挾上擾則發為高血壓亞急癥。
現代醫學認為高血壓發病機制復雜,Irvine Page博士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高血壓馬賽克理論”,認為高血壓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導致血壓升高和末端器官損傷的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更多的致病因素被囊括其中,包括腎臟機制、血管/內皮功能障礙、鈉攝入/儲存量、氧化還原/應激改變、先天和適應性免疫、遺傳、交感神經激活、微生物組等,這些因素之間又相互影響,形成復雜的促血壓升高網絡[30]。近年來,新近的高血壓的腦-腸軸理論備受矚目,該理論認為血管緊張素Ⅱ、鹽、醛固酮、系統炎癥、情緒或環境刺激等多種原因均可引起中樞神經炎癥,尤其是大腦自主神經調控中心下丘腦室旁核(paraventricular hypothalamic nucleus,PVN)區小膠質細胞被激活,導致交感神經興奮性輸出增加,促進血壓升高;與此同時,交感神經興奮性增強可引起腸道屏障破壞及微生態紊亂,形成“腸漏”,促進系統性慢性低度炎癥狀態的形成,繼而增強PVN區小膠質細胞激活,構成血壓升高的惡性循環,而阻斷腦腸軸中任一環節,均有益于血壓的控制[21,31-33]。這種由多因素誘發,以中樞炎癥為核心的血壓升高機制亦可以理解為從現代醫學角度對高血壓亞急癥風火上越,腦竅清陽郁遏病機的佐證。由于高血壓現代病機的復雜性,當高血壓病人受煩勞因素或季節變換等刺激時,單靶點降壓藥物往往難以保持療效,導致高血壓亞急癥發生。高血壓亞急癥的急診治療多采用緊急降壓,但次日血壓往往再次回升,甚至超過緊急降壓前的水平。為了使病人達到目標血壓,急診高血壓指南要求通過持續的降壓藥物調整,使血壓數周內降至正常目標值,這里的調整,往往是增加口服降壓藥物種類,或者原有降壓藥物服用頻次的增加[8]。在臨床觀察中,30%的高血壓亞急癥病人已經是3種及3種以上降壓藥物聯合服用,這種調整無疑增加高血壓亞急癥病人的心理負擔,降低了藥物的依從性。而短期內服用精芩平脈方治療,病人依從性高,能夠在不增加額外口服降壓藥,甚至口服降壓藥物減量前提下達到預期治療目標。究其緣由,從中醫學角度,精芩平脈方,以清肝為君,清瀉上行相火,使相火歸于其位,變賊為用;以益腎為臣,滋水涵木,平息內風。明代醫家李中梓《醫宗必讀》中有“乙癸同源,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即所以補肝”的論述,即通過益腎的方法以養肝體,制其風動;以祛風通陽為佐使。辛散郁遏之陽,使氣機流暢,絡脈得通,至此,由肝腎虧虛,肝陽暴亢,風火上越引起的諸癥可解,即便年老素有痰瘀絡阻者,其血壓可平,之后當隨癥辨證調理,以期無虞。
從現代醫學角度,精芩平脈方作為中藥復方,其化學成分復雜,天然具有多靶點干預優勢。本課題組前期臨床觀察及藥效學實驗研究結果表明,精芩平脈方具有顯著的降壓作用,同時對心、腦、腎、胸腺、腸道等靶器官具有良好的保護作用[11,12,14-19]。其發揮降壓效應的途徑是多方面的,就傳統的高血壓致病因素而言,精芩平脈方具有如下效應:拮抗血管緊張素Ⅱ的生物學效應[18-19];降低高血壓模型動物內皮素-1與醛固酮水平[34];抑制腎臟、心臟等靶器官氧化應激及炎癥反應[13,15];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內Ca2+的含量[34],發揮舒張血管作用等。另一方面,從腦腸軸理論而言,精芩平脈方具有抑制自主神經中樞(PVN區)神經炎癥,降低交感神經興奮性輸出[18],糾正“腸漏”、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物紊亂,阻斷腦-腸軸功能異常等作用[20,33,35]。因此,對于高血壓亞急癥的治療,本課題組提倡急診緊急降壓處理后,在原有口服降壓方案基礎上給予精芩平脈方治療,實施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案凸顯中醫學的優勢,讓病人最大程度受益。
精芩平脈方干預高血壓亞急癥是基于對高血壓亞急癥病機的精準把握,其中腦竅清陽被遏機制是張騰教授治療高血壓的獨到見解。該病機及對應治法,受李東垣治療火熱病的啟發頗深,例如:治療陽氣郁遏于脾,肌膚灼熱,或骨蒸潮熱,捫之烙手的升陽散火湯;治療風熱疫毒上攻,諸陽之會被遏,頭面紅腫焮痛,目不能開,咽喉不利等大頭瘟病的普濟消毒飲;治療風濕熱上壅腦竅,目損、腦痛的清空膏等,都寓有“火郁發之”“伸展清陽”之意。張騰教授結合多年臨床觀察,厘清高血壓亞急癥癥結所在,守正創新,在清空膏及近代“黃精四草湯”基礎上創立了精芩平脈方,用于高血壓亞急癥的治療可謂正中肯綮。祛風通陽法雖為該方佐使,但其使諸陽之會的清陽之府得以平和,這是張騰教授治療高血壓亞急癥的核心創新觀點,也是能夠迅速發揮降壓效應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