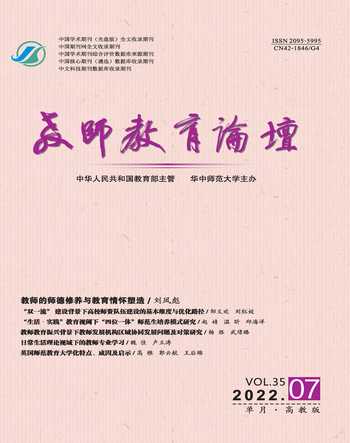教師學科理解的基本特征及其結構優化
摘要:理解是個體在已有經驗基礎之上通過一系列的認識活動對理解對象所形成的本質認識,學科理解則是以學科本質、學科知識與學科價值為認識對象,所建構起的系統化、結構化的學科理性認知,是教師對學科與知識、學科與人的發展之基本關系的整體性認識。教師學科理解內在地具備特殊性與遷移性、內隱性和外顯性、歷史性與創造性、一維性與整體性相統一的特征。然而,現實中教師學科理解往往停留在單維學科知識理解,因而拓寬學科理解的內容向度,深化教師在學科本質、學科知識、學科思維和學科思想層面的理解是優化教師學科理解結構的關鍵之舉。
關鍵詞:學科理解;學科本質;教學推理;教師專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995(2022)07-0050-05
學科教育活動是學科經驗傳遞的過程,經過“教師化”和“學生化”完成學科經驗的傳遞、理解和改造,教師理解和把握學科經驗的過程即是學科經驗的教師化,并直接關乎學科經驗傳遞的效果。教師如何理解具體學科,理解具體學科的內容結構、具體學科與學生發展之間的關系,成為了育人目標轉化為學生素養培育的關鍵。現實中教師的學科理解往往受到學科概念知識的禁錮,局限于學科符號認識的單維理解,缺乏對學科整體內容的完整把握。因此,教育教學改革應以教師深度的學科理解助力學生的深度知識理解,即從教師學科理解的本質和特征切入,探索拓展學科理解內容維度,助力系統化、結構化教師學科理解的建立。
一、理解與教師學科理解
理解是形成對事物本質認識的基礎,任何知識與素養的發展都必須經歷理解的過程。當理解進駐到教育領域,則開始從認識論到方法論再到本體論的轉變,聚焦于理解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和特征,以獲得意義拓展和價值生成為旨歸。“理解的本質是作為此在的人對存在的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1]。學科理解是理解在學科境域中的存在本身,一方面意味著從片面的學科理解過渡到清晰的學科理解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指向教學實踐中理解主體在教學境遇中的真實存在。以往教育領域中的理解問題研究大多聚焦于教師課程理解和學生知識理解,缺乏對教師之于具體學科理解的研究。要知道,教師的課程理解失去了教師對學科這一內容憑借的深化理解會導致虛無,而在教學場域中學生知識理解也需要實現從教師學科理解到學生學科理解的跨越,由此確立教師學科理解在學科教學過程中的價值。
學科理解是教師對學科體系的事實性認知和發展性認識。即教師不僅僅要關注學科知識的概念、原理、思想方法與價值觀念等內容,還需著眼于學科之于個體發展價值的理解。而現實教學中教師學科理解又往往禁錮于知識理解,其本質是在點狀的、片面化的教學思維下對學科的實體性理解,是對學科理解目的把握不清所導致的學科窄化,缺乏對學科知識背后蘊含的學科本質、思維方法與思想價值體系的探知,且難以從學科育人的高度建構對具體學科的整體認知。此外,學科理解聚焦教師內部的知識理解和教學轉化,其根植于教師對學科知識和學科育人價值的認識,內隱于教師的知識理解和知識處理過程,并外顯于教學方案和教學活動設計的教學實踐中。基于教師理解與轉化的緘默性,這意味著表征和外顯這一思維過程變得非常困難,因而要試圖透過教師的教學方案和教學實踐的分析來把握教師教學處理的邏輯與設想。綜上所述,教師學科理解是脫胎于初始的學科知識理解,逐步走向穩定的系統化、結構化的有關學科本質、學科知識體系與學科價值的理性認知,是教師對學科與知識、學科與人的發展的基本關系的整體性認識。
二、教師學科理解的基本特征
(一)特殊與遷移的統一
“學科是指人類千百年來形成的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的、分門別類的認識成果或科學知識體系”[2],通過推演學科發展史可以清楚地發現,現代學科的分野是建立在科學知識體系分化的基礎之上,從而實現從學術學科到教育學科的跨越,自此確立了學校的教育學科的性質。與此同時,“學科分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由比較單一的初級綜合學科向多門許可分化,而多門學科分化到一定時候又產生了比較高一級的綜合學科”[3],因而學科呈現出學科壁壘界限下的互動發展態勢,學科之間存在著類活動的思維過程和思維方式,也包含著個體活動的思維理解的共性。學科理解也同樣表現出了學科特性和學科共性,特性與共性在教師學科認知中實現了特殊性與遷移性的統一。學科理解是教師對具體學科的知識體系與研究方法的把握,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基本問題與學科范式的差異導致了學科所涉獵的知識領域與思維方式都有所不同。然而學科理解的特殊性不等于封閉性,學科本身存在的開放性給予了教師學科理解的遷移能力,基于對多個學科之間共性特征的把握,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嘗試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以學科間共性的學科思維為主線,將其相互關聯,串點成線,以建立更加系統的學科理解。
(二)內隱與外顯的統一
理解是一種內在的思維過程和思維認知水平,其必須依托于一定的載體而體現。同樣的,教師學科理解通常是不能夠直接被他人所感知,且往往不被教師自己所反應,只能經由教師的教學行為及其教學活動來表現。這也就意味著教師學科理解集內隱與外顯于一身;一方面,教師學科理解內隱于教師對于學科的看法、內隱于教師對學科育人特殊價值的教育理念、內隱于教師的知識處理和教學方式之中,是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過程中自動化的一種思維方式;另一方面,教師學科理解又外顯于教師的一系列教學行為和教學活動,通過對教師的教學方案、教學活動設計和教學行為表現的分析可以表征教師學科理解水平,或通過教師自述的方式來探知教師的學科理解層次。聚焦教師學科理解發展的完整歷程,發現深化理解要經歷內隱—外顯—內隱的循環發展過程,外顯行為是對內隱內容進行反思與優化的靶點,其中知識處理作為溝通學科理解與教學行為的橋梁,通過對教師教學目標、教學設計與教學行為中內涵的知識處理反推教師學科理解中存在的問題,能夠更真切地表現教師的理解水平。此外,學科理解是在具體的教學情境中得以表現,通過在教學實踐情境中實現學科誤解的消除和學科正解的確認是深化教師學科理解的關鍵,并在實踐和理論的反復驗證與激活的過程中實現螺旋式深化。
(三)歷史與創造的統一
理解是主體客體化的過程,教師在理解學科的過程中深化自身對學科的理性認知,學科理解伴隨著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對學科本質及其知識體系的理解和應用而得以發展。教師對學科的認知從來都不是“從零開始”,也并非是“從頭再來”,而是個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進行內化和自我加工的過程,進而建立和深化自身的學科認知,這其中新手教師往往還會借鑒和模仿專家教師的知識處理和教學方式,在模仿過程中深入思考學科特質和學科知識育人價值。通過學習前人和他人的發展經驗,可以幫助教師突破個體經驗的局限,力圖實現學科理解繼承性和累積性的發展。與之相對的是,繼承和累積的發展根植于教師對他人經驗的批判性學習和創新,也就是說,單純的吸收他人經驗是難以實現個體學科認知思維和學科認知水平的提升,其關鍵還在于教師在前人基礎上的自我突破。依托于教師自身理解水平、學科經驗和學科敏感性,建基于對學科專家內涵的學科邏輯和教學心理邏輯的把握之上,實現對學科內容和教學資源進行接納、學習和創造。因此實現歷史與創造統一的學科理解意味著要立足于他人優秀學科經驗基礎,嘗試復演學科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實現從學科專家到教師層面的學科轉化,而這一過程必然是創造性的。
(四)一維與整體的統一
“存在的本性就是引起一切生成的潛能,過程就是經驗的生成”[4],過程屬性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屬性,教師學科理解也同樣具備內在的過程性和發展性。學科理解存在于每位學科教師的思維認知體系之中,伴隨著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對學科及其知識體系的認知和理解程度的加深而處于不斷深化和發展之中,并在教師學科經驗的生成和發展中得以優化。學科理解聚焦于教師學科理解從生發到深化的完整歷程,關注學科理解生發的一維性,注重學科理解發展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才能助力完整學科理解價值的發揮。學科理解的生發往往聚焦于一維學科知識理解,是教師在初始狀態下對學科的淺層次認知,這并不意味著學科理解止步于此,而是基于教師對學科知識這一單一維度的理解基礎,拓展教師對學科內容的理解向度,嘗試思考學科知識背后的知識結構、思維過程和學科思想,以及學科知識與人的發展等多個維度問題,以期建立教師對這一學科的自我認知和思維方式。學科理解從一維向整體發展的過程本身就隱含著階段性和程度差異,這也就意味著存在著學科理解的單維和立體之分、理解水平的深淺之分。從單一維度的學科知識理解階段到立體的整體性學科理解范式,同時指向知識背后的科學機制、文化內涵、社會屬性等整體性理解,以及知識發生學、學科價值論、學科思維方法的多維認知,以形成系統化學科理解體系。
三、教師學科理解的結構優化
理解本身需要依托內容憑借,單一維度的知識理解導致教師學科理解存在結構不平衡的問題,要求立足于學科本質,通達對學科知識載體的理解,并挖掘學科思維中隱含的認識事物的思維方法,最終以學科思想統括學科價值體系,融會學科育人的發展性價值。
(一)以認識學科本質為前提
“學科本質表現為知識建構過程,問題是,從知識存在到學科建構的過程又經歷了怎樣的篩選和排除過程。”[5]從人類知識到學科分界,其經歷了人類知識—學術學科—教育學科的學科生態譜系過程,這其中實現了學科向教育規訓學科的轉化。即以學科研究對象及其基本問題為參照劃分學科邊界,實現對人類知識的分化與重組。學科之間往往存在著不可滲透的邊界和壁壘。從學科邊界的視角去把握學科特性,厘清學科探究對象和學科思維方式,有助于教師更好地理解具體學科之于個體發展的價值,為具體學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奠定基礎。而缺乏對學科本質的本源性理解,教師在后續的學科理解和學科知識處理過程中容易出現偏差,僅限于學科知識的理解會嚴重限制教師對學科深度理解的視野。
學科本質關涉學科研究對象及其基本問題的探究,隱含在學科問題探究中的認識過程和思維方式中,這也就意味著對學科本質的把握要著眼于學科研究對象、學科基本問題以及學科認識論層面,不可置否的是,學科知識本身蘊含著對學科本質的確認。一方面,從具體學科知識出發,探究知識所揭示的具體事物的本質及其關系,理解知識確認背后的邏輯思維方式和形象思維方式,能夠幫助教師更精準地把握學科知識背后蘊含的學科本質。也就是說,教師可以嘗試以學科最本質基元:學科知識作為學科大廈的點,由點成線,由線及面,挖掘學科知識和學科體系搭建的學科思維邏輯梁,形成對學科本質的微觀層面的認知和理解。另一方面,教師可以著眼于學科史的發展過程建立宏觀層面的學科認知。學科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現象,即學科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蘊含在學科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中。嘗試挖掘學科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從知識發生學視角理解學科有助于厘清學科知識的邏輯系統和學科發展的歷史系統。
(二)以理解學科知識為基礎
學科知識是學科理解的內容憑借。從教師學科理解的原始樣態來看,其大多生發于教師對學科知識的理解,而自發狀態下的知識理解往往會呈現出片面化、淺層次的理解樣態,因而實現教師知識理解的深化成為了建構理性學科理解的關鍵。要知道,任何一門學科大廈都是以學科概念為基礎搭建而成,對學科概念背后的有關事物質的規定性和事物本質規律的關注是對教育科學生命的關懷;但其不能僅僅停留在自身對學科知識內涵的科學把握,更要著眼于學生知識理解的視角解構學科知識的內部構成要素及其基本關系,架構學科概念到學科結構體系的思維橋梁,跨越學科知識理解到學科知識應用之間的溝通,以關系思維、轉化思維和實踐思維引導教師深化知識的理解之維。教師的教學思維與知識理解兩者存在反哺價值,教師的知識理解往往受到教學思維的影響,反之,知識處理的深化也會促進教師教學思維的轉變。
以轉化思維助力教師深化知識理解和知識處理是至關重要的。知識的轉化必然建立在教師對學科知識理解的基礎之上,其不僅要求關照學科概念的科學理解,更要實現對學科知識多重屬性的把握。“知識的內在結構是由符號表征、邏輯形式和意義系統所組成”[6]。這也就意味著在知識概念的科學理解過程中要把握學科知識形成的邏輯思維過程和思維方式,再深入挖掘內隱于知識符號背后的規律系統和價值系統,實現對具體學科知識理解的深化。與此同時,學科知識理解要求橫向把握知識的多維屬性,從知識發生和發展過程的文化、社會、歷史依存性著手,即跨越符號理解走向知識背后的本質理解、意義理解和文化理解。知識從理解到轉化的過程大多在知識運用的情境中實現,知識應用其本質在于對個體知識理解的準確性、知識問題情境的適應性的檢驗,教師可以變換學科知識內部構成要素、形成條件及其應用情境,來探究知識所揭示的內在規律及其變化,以更深刻的形成對知識本質規定的認識。
(三)以復演學科思維為牽引
“學科思維是在學科本質理解的基礎上對學科知識背后過程性、邏輯性和演繹性學科特質的揭示,是一種動態的思維過程”[7]。從學科思維的過程、邏輯與演繹中能夠更加深刻地形成本學科的獨特思維方式,從而完成對一般宏觀意義上的思維方法的超越,形成具備學科特質的思維邏輯體系。這種學科思維邏輯體系有助于學科核心素養的培育,也就是說,將學科知識轉換為學科素養的中介要求經歷學科思維的建構過程,這其中對學科思想和學科規律的過程性推演最為關鍵。與此同時,學科思維本質上是人類經驗思維,是在種族經驗中所派生出來的學科思維方法,再經歷學科專家對學科知識、結構和體系的編排與建構。這意味著教師要試圖把握學科思維這一牽引力,就必須要復演學科知識形成的論證過程和實踐邏輯,探索學科知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所內隱的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最終實現學科思維與學生學習心理規律的結合。
教師應立足于學科知識體系,把握不同教材撰寫的學科思路,以學科知識關涉的學科思想為核心勾勒出知識結構框架,并對教材中的核心概念及其關系進行反復的追問,探知核心概念所揭示的事物發展規律及其認識方法。此外,要讓學生經歷學科知識和學科思想的生發過程,這意味著讓學科史進入到學科教學過程,現實學科教學往往呈現出歷史的結構性沉默,陷入了歷史虛無的困境當中。要知道,學科發展的歷史也是學科建構的思維史,學科史的融入能夠更好地實現知識學習的深度、廣度和關聯度,從知識生發和發展的過程、學科體系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學科體系中關鍵事件、人物和節點的學科歷史故事拓寬學科理解的維度。最后,學科體系的建構遵循學科專家進行學科編排所運用的思維邏輯,其主要考量的是學科知識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深淺程度和關聯程度,挖掘學科知識的橫向關聯線索與縱向思維線索,是教師細化學科理解內容,尋找教學切入點的關鍵。
(四)以領悟學科思想為提升
科學知識體系大多以知識為基、思維為線、思想為核來建構整個科學學科框架,教育學科作為學科生態譜系中的最后環節,也繼承了科學知識體系中的這一特征。“學科思想是建立在學科事物感性認識基礎之上進行分析、綜合、辯證等思維活動的產物”[8],這也就意味著學科思想是內隱于零散學科知識背后的知識獲取過程、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之中,是類主體學科經驗中派生的思維方法在學科實踐中的不斷驗證和升華的結果。學科思想不僅僅是學科知識內核中學科深層結構的一般性思想觀念,更是學科思維的導航器,即學科思維過程中更上層的策略、法則和思想上的引導,是學科學習過程中形成的對學科本質、學科特征和學科價值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思維方法。
學科理解的內核就是教師對學科思想的深度理解,也就意味著要以學科思維助推從學科知識到學科方法再到學科思想的建立,實現從符號解碼、思想建立、意義建構的逐層深化的理解過程。對于一門學科特定內容中所蘊含的思想方法必須從具體的學科知識之中提煉出來,學科思想內隱于學科概念、法則、定律等基本知識的形成過程,也內隱于學科知識形成的不同階段。一方面,教師可選擇自下而上以微觀視野理解學科知識結構內涵的學科思想,從學科核心概念的本質出發,探究核心概念中的本質關系、核心概念對其他概念的統攝邏輯,基于學科邏輯思維的類同性構建學科知識結構。另一方面,教師可選擇自上而下以宏觀視野把握學科思想統攝下的學科知識教學,以學科思想為憑借串聯學科概念背后的規律、思維方式、方法和價值觀體系,關聯學科概念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文化、思想和社會等要素,深入理解學科概念、學科知識和學科原理形成過程的思維過程和思維方法,反向助力教師學科經驗的生長。
參考文獻:[1]馬勇.論理解性教學[D].廣西師范大學,2004.
[2]郭元祥.論學科育人的邏輯起點、內在條件與實踐訴求[J].教育研究,2020(04):4-15.
[3]孫綿濤.學科論[J].教育研究,2004(6):49-55.
[4]懷特海著,李步樓譯.過程與實在[M].北京:商務出版社,2012:247.
[5]申天恩.論學科本質及其三態表現形式[J].中國高教研究,2013(10):68-71.
[6]郭元祥.知識的性質、結構與深度教學[J].課程·教材·教法,2009(11):17-24.
[7]魏宜貿.論基于學科思維邏輯建構的中學化學教學[J].中學化學教學參考,2019(1):7-15.
[8]陳娜,郭元祥.學科課程思想的內涵、特征及其對教學的觀照[J].課程·教材·教法,2017(8):11-16.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Teacher's 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Liu Yan
(College of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is the essen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 of understanding formed by individuals through a series of cognitive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isting experience, while 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is the object of understanding with disciplinary natur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disciplinary value as its cognitive object, the systematic and structured disciplinary rational cognition i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e and knowledge, and between disciplin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ularity and migration, implicitness and explicitness, historicity and creativity, one-dimensionality and integrity. However, in reality, teachers'?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ten stays in the one-dimensional disciplinary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us broadening the content dimension of subject understanding. Thus, what is critical to do is building a three-dimensional discipline understanding framework horizontally which based on discipline knowledge, discipline thinking, discipline concept and discipline essence.
Keywords: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Discipline essence;Discipline thinking;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基金項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創新資助項目)“指向課程核心素養發展的學科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22CXZZ05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劉艷,女,江西吉安人,教育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