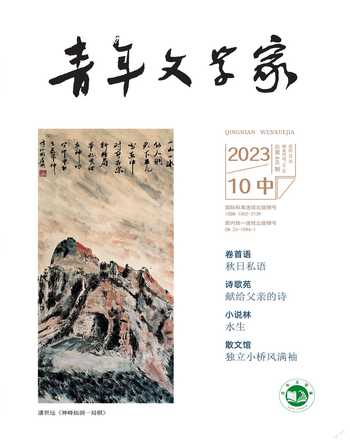逝去的親人們(外一首)
2023-11-27 08:54:28陸定漁
青年文學家 2023年30期
陸定漁
父親? 母親? 哥哥? 姐姐? 嫂子
居住在只有如腳趾? 手指甲般大小的一隅
或者? 只是一個臉龐大小的角落
而今? 他們如枯萎的小草般黏附在一撮泥土上
他們當然不知道遠方有海? 草原
草原? 大海? 天空還互相比拼
只是隨著太陽的升起
而咳嗽? 蹣跚? 躑躅
腳板撞擊著路表? 地球
在蕓蕓眾生中咳嗽
這是反饋給蕓蕓眾生無止境的信號
而蕓蕓眾生收割莊稼就像節日宰殺豬羊
對他們而言
千萬條道路? 巷陌只是一條
親人的病痛帶來了我的病痛
連電燈? 床鋪? 窗欞也抖動
即便一條路的方向變成幾百條路的方向
一個字符分裂成幾百本書籍
我們都夢見天庭? 夢見車水馬龍
夢見遠方的城市? 這種時刻
我的一個字符? 一本書竟然變幻莫測
如腳印? 眼瞼的精神? 這是大風
它是光天化日地背叛自己的初衷? 來歷
我不能背叛自己? 在水中央? 沙漠? 草原
我只能不停地禱告? 祈福
逝去的親人們? 你們可曾知道
我是用血液觸及每個白天? 夜晚的姿態
紅臉人
意識里一只瞳孔不停地克隆空間的紅
但是? 一萬年的文字已經沉淀
我們緊攥光線的手像光線一樣顫抖
活著是為了更好地活著
潛意識里發現一個全身通紅的人
他是把雙腳置換成凌亂? 七彩的車輪
甚至置換成雙手? 桅桿? 樓門
我知道
他是把歷史的一天置換成未來的一天
他還把自己? 魚群安置在水中央
心理學家知道? 他內心
總是處于不安? 悸動之中
我的邏輯? 跟心理學家完全一致
黃河的車燈是用石頭? 血液充電嗎
舉著刺鼻的楊樹枝在路上揮舞
還把車門像地球一樣旋轉
但是? 我們天天在床上奔跑
紅臉人用腳板測量兒童的道路
已經變成一個成人? 道路只有一米
一米的道路困囿著我
走不動三十年前? 難于走到三十年后
愛情會把文化焚毀? 呈白? 呈黃
紅臉人辭世那天
夜晚必然變成白晝
他妻子還有愛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