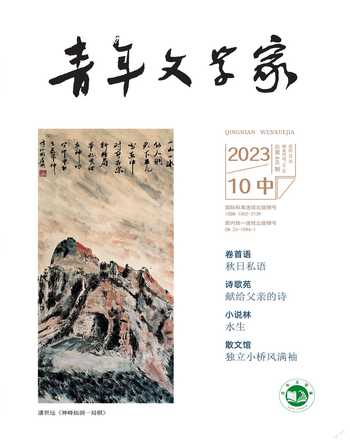馴化與被馴化后的重構愿望
向芷萱
韓少功以細膩生動、質樸平實的筆調描繪了一個獨特的文化世界—馬橋,而《馬橋詞典》中的《三毛》也在這個傳統儒家與巫楚文化滋養的封閉文明中,通過“我”這個敘述者,也即一個“知青”的視角,一個“外來者”的視角,向我們展示了主人公身份認同轉變的過程,揭示了小說悲劇背后所代表的精神價值。小說前半部分清新明麗,后半部分沉郁悲慨,將時代變遷中人物的身份認同意識藏于文本細節中,最后的悲劇結局也指向了作者對民族傳統文化重構的決心。
一、對鄉土文明的身份認同與超越—從“巖石”里蹦出來的三毛
(一)獨特的生命活力—難以被馴化的三毛
小說開篇便提醒了讀者—三毛并不是一頭普通的牛。它不僅有自己的名字,且馬橋的人們認為它“不是牛婆生下來的,是從巖石里蹦出來的,就像《西游記》里的孫猴子,不是什么牛”;它極通人性,會抓住機會捉弄“我”,會在志煌殺它前流露出悲傷的神情;它的個性也不同于傳統的牛那樣勤懇老實,而是飛揚的、狂放的。在雷雨交加的天氣里,它“有一種獲得解放的激動,以勢不可擋的萬鈞之力向嶺上呼嘯而去,不時出現步法混亂的扭擺和跳躍,折騰著從來未有過的快活”。
因此,三毛是難以被馴化的,就像文中的“我”被它逗,志煌有時也喊不住它。但在村民眼里,它又是理所當然地要被馴化的:“煌寶是巖匠,管住這塊巖頭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種說法被人們普遍地接受。”馴化它的方式也不同,只有志煌能馴化它,用的也是巖匠的常用語—“溜”。
于是,這頭與眾不同的牛加深了馬橋巫楚民俗空間的封閉和神秘色彩,也說明了三毛因其旺盛的生命力是難以被馴化的,開拓了“三毛”這個形象的象征意義。
(二)純粹的情感超越—馴化他者的三毛
除了被馴化,三毛的形象作為一種文明精神的象征,也馴化著志煌。
志煌與三毛的合作是出神入化的:“他犁過的田里,翻卷的黑泥就如一頁頁的書,光滑發亮,細膩柔潤,均勻整齊,溫氣蒸騰,給人一氣呵成、行云流水、收放自如、神形兼備的感覺。”
志煌也把三毛當作自己的家人:“他不大信賴貪玩的看牛崽,總是要親自放牛,到遠遠的地方,尋找干凈水和合口味的草,安頓了牛以后再來打發自己。”
志煌不愿意賣牛,殺牛之后是一整晚的失落和沉默。
在三毛與志煌之間的相互馴化中,三毛的形象越發溫情,小說的最后三毛的悲劇色彩也越發動人。作者用二者產生的情感羈絆加深了小說的張力,三毛的形象也就更加豐滿起來,它在此角度上超越了傳統的牛作為生產力工具的意義,也超越了傳統鄉土文明,更多指向一種傳統文化中的純粹情感與原始本能。
而文中的這句“沒有牛鈴鐺的聲音,馬橋是不可想象的,黃昏是不可想象的”,也證明了在這種鄉土世界、民俗空間里,“三毛”代表的傳統文化底色是難以割舍的。
二、身份認同的偏移和價值悖論—“不賣牛”和“殺牛”的志煌
文中的志煌,從“不賣牛”的選擇,到“殺牛”的抉擇,并不是外界所迫,而是出于身份認同來源的偏移。
第一次被馬橋的人們要求賣牛時,志煌的道理有些“怪”,他否認了集體身份認同,認為“哪個種田,田就歸哪個,未必不是這個理?”—牛也一樣,因此他認為即使是從隊上買來的,但自己養大的三毛是屬于個人的。除了急于保住三毛的強詞奪理,志煌的這種認識其實暗含著此時的他出于個人身份認同即對“農民”這個身份的認同,身為農民,牛是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里不可缺少的生產力工具和財產。
而當三毛第二次撞人時,文中志煌因為之前有“這畜生要是往后還傷人,他親手劈了他”的承諾,下定決心要“殺牛”。此時,志煌不再只是為了一個承諾,而是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已經發生了偏移—轉換成了一種集體身份認同,是作為一個人類社會中的“村民”對長久穩定的道德倫理和民間秩序的維護。
韓少功書寫志煌的兩次抉擇,闡述志煌身份認同的偏移,凸顯了鄉土文明和現代文明的沖突,在沖突中進行著精神尋根。韓少功用一頭牛瘋狂的生和殘酷的死,來展現這種時代變遷下文明之間的巨大沖突。
但構成悖論的是,當志煌殺了牛,表面上維護了鄉土文明中的道德與秩序時,卻是深層次地對鄉土文明中的純粹情感和原始力量進行了一次“閹割”、一次“滅活”。鄉土世界時刻受著時代沖擊,“殺牛”這一現象也在大地上普遍發生。同時,第二天早上仍會有雞鳴,時間仍在不斷向前。于是在精神尋根之后,韓少功進行的是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解構和重建。
三、兩個必然—“我”與“看客”的身份選擇與啟示
文中“我”的形象的參與,是從一個“外來者”眼中,強調那些“奇特”之處,展示馬橋封閉之下各式各樣的風土人情。
(一)知青身份認同困境下的必然
這里的身份認同困境指向“我”作為現代知青面臨的身份認同困境,必然指向傳統文化重構的必然選擇與如何重構的必然導向。
文中,“我”和三毛的相處過程中,三毛會“抓住機會捉弄我。越是遠離電線的時候,它越跑得歡,讓我拉也拉不住。越是走到電線下面,它倒越走得慢,又是屙尿,又是吃田邊的草,一個幸災樂禍的樣子。最后,它干脆不走了”。
極通人性的三毛,在面對作為“外來者”的“我”時,不再是一個“被困者”,而是在“我的柳鞭抽毛了,斷得越來越短”時,朝岸上狂奔,帶走了犁耙。三毛“救”了“我”,三毛對自然的感知顯然比“我”敏感,三毛也掙脫了這種“被困”的境遇,它朝山嶺上毫不猶豫地飛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活。
三毛對自然的敏感、“救我”于瞬息、面對雷電的奔放,同樣彰顯著三毛的純粹情感與原始生命力,這也與“我”作為一個現代知青的身份形成了對比。
知青經驗是尋根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尋根文學的興起就是知青作家推動發展的。作家將知青經驗轉化為尋根文學的文化尋根意味,也豐富了尋根文學的主題。
現代知青的身份是特殊的,雖然尋根文學主要想從民族傳統文化中挖掘精神與美,但一方面,知青經驗也不可避免地展現了落后蒙昧的文化心理與習俗,揭露了封建文化的劣根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們的知青經驗導致他們并非完全如同現代科學般全知全能,他們無法解決自身的文化困境,他們對后續的文化選擇有著時代必然的迷茫。
正如三毛面對自然的閃電,是瘋狂的,即使被犁擊傷,它仍舊飛奔過泥地,在韓少功筆下仿佛是對野性生命力的贊嘆;但作為知青的“我”的反應是糾結的、恐懼的,“裸線剛好橫跨我正在犁著的一塊田,凌駕在我必須來回經過的地方,使我提心吊膽。一旦接近它,走到它的下面,忍不住腿軟,一次次屏住呼吸扭著頸根朝上方警戒,看空中搖來蕩去的命運之線潑下一把把火花,擔心它引來劈頭蓋臉的震天一擊。看到其他人還在別的田里頂著雨挖溝,我不好意思擅自進屋,不想顯得自己太怕死”。恐懼是生物的本能反應,此處表現的是知識分子的無所適從,也暗示著一種文化困境,一種身份認同的困境。
對于這些知青作家來說,保守貧困的鄉村和現代科學的城市都不是他們精神的皈依所在,他們游離在城市文明和鄉村文化之間,也解釋了他們擁有的對尋根的熱情。因此,雷電的場景與“我”作為現代知青身份的心理描述,并不是無關緊要的。
韓少功用這樣一種喻體再現了尋根文學的困境,對傳統文化的肯定之中暗含著批判與否定,也對尋根之路的導向懷有迷茫無措;但這種探尋不是全無價值,它確定了重構傳統文化的必然選擇與必然導向,同時對應了上文“殺牛”的選擇與象征意義。
(二)看客身份認同局限下的必然
文中“我”的形象的身份認同帶有明顯的現代色彩,與看客的身份認同形成了一種對比。
文中“我”的態度是科學理性的。“我”害怕雷電,害怕雷電天氣下的電線。在三毛第一次“傷物”的時候,“我”也支持將它賣掉,此時的“我”并不是為了維護馬橋的傳統秩序,而是一種現代文明中對自我權利的保障意識—它差點兒傷害了“我”并傷害到了村莊的財產,理應被賣掉,這是一個來源于現代文明的選擇。
如果說“我”是沒有介入到這種馴化與被馴化中的,那么馬橋的看客們則是完全介入于此的。因為他們認為三毛作為一頭牛理應被馴化,這是因為鄉土農耕文明馴化著看客。
在殺牛前,看客們認為,在撞傷別的牛、差點兒撞傷小孩兒的污點中,最可氣的是三毛作為一頭牛沒有接受馴化—“最氣人的是另一回,你黃豆也吃了,雞蛋也吃了,還是懶,不肯背犁套,就算背上了,四五個人打你你也不走半步,只差沒拿轎子來抬你,招人嫌么”。此外,關于犁套,看客們說,“你沒看見洪老板比你苦得多,死的時候犁套都沒有解哩”。“最氣人”的行為暗含看客們消解了三毛這頭獨特的牛的意義,在他們眼里,牛就是生產的工具;“洪老板比你苦得多”則暗含了看客對生死輪回意識的虔誠,對話語力量的信奉。但這二者都揭示了馬橋人貧困保守的生存狀態,對生活困苦的嘆息無奈。
同時,看客還表達出一種同情—復查他娘讓志煌喊一喊三毛。當志煌喊“三毛”時,“牛的目光一顫”“牛眼中有幸福的一閃”,這里的歉意和無奈將情感推向高潮。最后,失落悲痛的志煌一言不發地坐了一整晚。這種呼喚是無力的、無奈的,同時表現著民族傳統文化一些部分被消解的必然。
也只有如此在看客眼里消解三毛的意義,三毛的逝去、三毛的旺盛生命張力與動人的情感,就越發濃烈悲壯。
“牛的腦袋炸開了一條血溝,接著是第二條,第三條……當血霧噴得尺多高的時候,牛還是沒有反抗,甚至沒有叫喊,仍然是跪著的姿態。最后,它晃了一下,向一側偏倒,終于沉沉地垮下去,如泥墻委地。它的腳盡力地伸了幾下,整個身子直挺挺地橫躺在地,比平時顯得拉長了許多。平時不大容易看到的淺灰色肚皮完全暴露。血紅的腦袋一陣陣劇烈地抽搐,黑亮亮的眼睛一直睜大著盯住人們,盯著一身鮮血的志煌。”
三毛殘酷悲痛的逝去過程延續了韓少功一直以來的寫作傳統,即一種對傳統鄉村文化魂靈的祭奠與禮贊。尋求重構道路是必然,但三毛沒有反抗、沒有叫喊的長跪,與韓少功在《怒目金剛》中玉和感天動地的一跪,都寄托了韓少功對民族傳統文化美好部分的眷戀與感佩,但歸根結底,他仍然是在積極探討重構民族傳統文化。
四、“馴化與被馴化”中的精神尋根
與重構
從以上四種形象,多層關系的分析中,不難看出韓少功在《三毛》這篇小說中有著悲天憫人、敬畏生命的生命意識,有著對農耕文明趨向沒落的歷史性悲劇的呈現,有著時代變遷之下身份認同混亂的深度思考,還有著對如同“三毛”一般的精神的“尋根”。可見,《三毛》是韓少功“尋根”思考之延續。它承續的是自《爸爸爸》《馬橋詞典》一路而來的主題,即“鄉村”和它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的意義。
尋根文學在發掘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對民族文化予以現代再審視。一方面,它表現了傳統文化的魅力和美,比如三毛的旺盛生命力,與志煌的勞動默契描寫宛如藝術,從而表達一種直接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原生智慧,以期喚醒國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關注和熱愛。而另一方面,它對封建文化的劣根性予以批評,同時對現代文明帶來的沖擊予以審視。可以看出,在《三毛》這個故事中,當不同形象作出選擇時,馬橋的人們用這些選擇來維護著民族傳統文化和社會穩定的同時,也在象征意義上抑制了人的生命力、創造力,挫傷了人性中的純粹情感。
但韓少功并非僅是表現對于這種純粹情感沒落的無奈,更多的是在“殺牛”一般“否定之否定”的困境中,重新找尋“三毛”所代表的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價值,重新審視現代文明沖擊下的精神尋根,從而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重構。
的確,或許此時“重構”的最終指向是迷茫的,因為實際上在縱向的時間維度上,尋根文學所提出的對現代文明的質疑和對傳統文化的重構,是沒有答案的。
尋根文學在文學史發展歷程上仿佛是轉瞬即逝,也確有其局限性,但尋根文學以發掘民族傳統文化為本,將文學中的文化書寫從邊緣地位拉到中心地位。作為一種文學啟蒙,無論是對于當時文化荒蕪的20世紀80年代初,還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建構,甚至中國當代社會的思想重構,都具有深刻意義。
僅從《三毛》來看也是如此,小說對三毛、志煌、“我”,以及看客的形象進行了不同身份認同下的價值演繹,雖并未告知讀者最后的答案,但為讀者提供了深入認識與反思傳統文化的又一途徑,也展現了以韓少功為代表的尋根文學作家對于民族傳統文化重構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