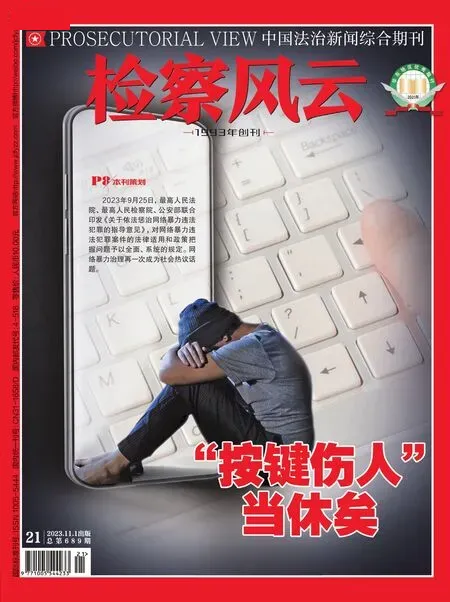洛倫茲·斯坦恩:軍事教養院里最著名的學生
文/馬嵐熙
維也納大學附近的瑪麗亞-特蕾西街9號是一座宏偉的舊建筑。這座大樓共四層,外墻呈淺棕色,每一層的窗戶上方都懸有不同的浮雕。其中,二層的窗欞上方更是點綴著尖頂與羅馬式的檐廊。在這條以古建筑著稱的大街上,這座建筑也顯得雋秀精美。直到1887年,這座大樓里的一間小公寓里,仍住著一位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法學教授:洛倫茲·斯坦恩。
畢業后要當教授,不想當一名軍人
1815年11月15日,斯坦恩出生于艾肯佛德(現屬于德國北部,當時為丹麥國王統治區域),卒于1890年,與俾斯麥是同時代人。他的家鄉在歷史上一直是個充滿爭議的地區。斯坦恩從出生就在經歷著戰爭與糾紛。據張道義教授考證,斯坦恩為非婚生子女。他的母親名為安娜·斯坦恩。單親家庭的背景使他幼年時受到不少困擾。6歲時,他進入一所軍事教養院——克里斯蒂安教養院學習。該教養院以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的名字命名,由其父親腓特烈五世于1765年在哥本哈根設立,最初是接收那些無法服役的年老貧困的士兵,以及士兵的遺孀和孤兒的機構。
教養院里最著名的學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斯坦恩,老軍營外部還有一座青銅浮雕紀念這位曾在此上學的少年。當他在此上學時,這里大約有200名男性、60名女性、80名男孩和40名女孩,所有人都必須穿著紅色丹麥陸軍制服,接受教官的監督,生活在嚴格的軍事紀律之下。就讀該校的學生可以免交學費,且有補助,但畢業后有擔任軍職的義務。斯坦恩在該校應有卓越的表現,因此1831年6月26日,丹麥國王腓特烈六世在巡視該校時,16歲的斯坦恩得以有機會當面報告國王:他知道自己的原始父姓為瓦斯默爾。他知道自己的生父應該是一名軍人,但是他自己畢業后要當教授,不想當軍人。這段對話源自斯坦恩家族流傳下來的逸聞,有點浪漫但真實性已不可考。

不論事實如何,丹麥國王事后不僅同意斯坦恩轉念拉丁文中學,并且給他批了3年的獎學金。1832年10月,斯坦恩轉往佛倫斯堡就讀中學,結束長達11年的軍事化生活。1835年他中學畢業后,于5月8日在基爾大學的法學與哲學系注冊。當時的基爾大學采取考試入學,斯坦恩以“Lorenz Jacob Stein”之名登記注冊,但是另以括號注明生父的姓氏。顯然直到大學時期,他仍堅持自己流著瓦斯默爾家的血。斯坦恩的入學考試科目有德文、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地理以及修辭學——在佛倫斯堡拉丁文中學的教育顯然幫上了忙。由于家境并不富裕,斯坦恩的大學生活似乎一開始就有經濟困難。為了維系學業與生活,申請獎學金是唯一的方法。除了向丹麥皇室申請,他也以中學時期在拉丁文學校的優異成績向佛倫斯堡市政府申請。他的母親為此還請家鄉的市政府出具貧困證明以便于獎學金的申請。幸運的是,這兩項申請都獲得批準,他共獲得了四年的獎助,得以順利完成學業。然而,這些艱難的時刻,那位被他寫在入學手冊上的軍官瓦斯默爾自始至終沒有露過面。
以斯坦恩這個姓氏受封皇家騎士爵位
在基爾大學念到第三學期時,1836年6月18日,斯坦恩的生母在家鄉過世。張道義教授這樣評述 道:“他分得若干的遺產,從此必須完全依賴自己。”斯坦恩的學習成績極好,還獲得了兩個學期的出國交換獎學金。1837年4月26日,斯坦恩前往耶拿大學登記入學,主攻哲學。1838年冬季,他又繼續回到基爾完成學業。1839年4月他以極優異的成績通過法學國家考試。
大學畢業后,斯坦恩并沒有直接開始學術生涯。他首先前往哥本哈根,以實習生的身份在政府部門工作。由于實習生的收入微薄,所以他開始在報刊撰寫文章與書評,以賺取生活費用。1839年8月,以哲學思辨著稱的《哈勒年刊》登載了他的第一篇書評。在哥本哈根政府部門實習的半年時間,行政工作的經驗反而使他下定決心以學術工作為業。
1840年4月26日,斯坦恩向實習單位提出辭呈。同時抓緊撰寫自己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主題雖然是丹麥的民事訴訟程序,但是他所提出的問題似乎已經為他未來的學術生涯勾勒出輪廓,那就是精神與法律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作用。在基爾大學完成博士學習后,他向丹麥皇室申請獎學金,擬出國游學。1840年7月11日,丹麥皇室批準基爾大學向他頒發法學博士學位。6天之后,皇室也核準他為期2年的出國游學獎學金。
經過三年在柏林與巴黎的游學,1843年冬天,斯坦恩返回母校基爾大學開始學術研究及教學。同年他以法國地方自治基本法制為題,完成教授資格論文。他以兼任講師的身份開設法國法制史以及德國國家法的課程。前者有3名學生選課,但是他們到了期中卻紛紛退選,后者則有12名學生選課,以當時的法學院規模來看已屬熱門課,因為法學院的學生總數也不過80人左右。據考,他的課平均約有5到12位學生選修。當時的兼任講師薪資是依選課人數而定,所以他的經濟狀況由此可知。
這一情況直至斯坦恩前往維也納任教方有所改善。1855年1月,維也納大學法學與國家學院進行三位被推薦人選的選聘,其中即有這一年40歲的斯坦恩。從此,他在維也納開始了長達30年的教學及研究工作,也就是這個時候,他購置了位于瑪麗亞-特蕾西街9號的公寓。在維也納大學,斯坦恩在夏季學期教《法哲學與財政學》,冬季學期教《國民經濟學》以及《行政理論》。他著作頗豐,1856年出版了《國家學體系》的第二冊《社會理論》;1858年,出版《國民經濟學》教科書;1860年,出版《財政學》教科書;1865年,出版《行政權理論》。學術上傲人的成就為他帶來了極高的榮譽:1868年8月14日斯坦恩獲頒奧地利皇室三等鐵十字勛章,同年11月5日奧地利皇帝授予其皇家騎士爵位。至此,斯坦恩終于以這個姓氏攜家族及后代登堂于奧地利皇室的貴族階層。
斯坦恩的東方讀者
據張道義教授概括,斯坦恩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在于,他整合了當時的社會理論、經濟理論(含財政理論)以及行政理論,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學說。他還提出,“人口統計與自然資源統計”應當作為國家學說的事實基礎。即便在今日,這也是相當重要的。
與此學術理念相應的是,斯坦恩呼吁理性社會改革,并支持以行政力量統合資源。他區分社會自由行政、社會急難行政以及社會發展行政三個領域,其中在社會發展行政中,提出社會保險制度。在其著作問世十一年后,與斯坦恩同年出生的俾斯麥開始推行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于1883年實施疾病保險、1884年實施意外保險、1889年實施退休保險。這一系列改革不僅僅在歐洲,即使在全世界,也是首度以國家力量系統推行的“社會發展行政”。盡管難以考證,俾斯麥推行的改革是否受益于斯坦恩,但有證可查的是,1872年7月27日,俾斯麥通過駐維也納大使館轉交信函,以感謝斯坦恩贈予的著作與啟發。
1890年9月23日,75歲的斯坦恩病逝于維也納附近的小鎮魏德臨高。據載,葬禮極盡哀榮,除了維也納大學以及奧地利官方的吊唁文件外,來自其他國家的代表,包括日本皇室都出席喪葬儀式。他死后遺留下相當豐富的著作,幾乎能裝滿一個小型的圖書館。其影響之深遠,在其去世百年后尤可見。1993年第1期的《日本研究》刊載了一篇名為《洛倫茲·斯坦恩的日本遺產》的文章,文中寫道:“約有一百封斯坦恩一家的信件,以及三百多張名片,這些名片主要來自斯坦恩的日本訪客和其子恩斯特在日本和中國期間見到的友人。這些信件往來是遺產中最有趣的部分之一,共包括近400封信件、便簽和邀請函。”那個曾在丹麥邊陲小鎮苦讀于軍事學校、在基爾入學時尤在括弧中寫明生父姓氏的少年,在16歲斬釘截鐵說“我不要當軍人,我要當一位教授”時,恐怕自己也難以想象,將與這個世界,與海洋另一端,有那樣奇妙的際遇與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