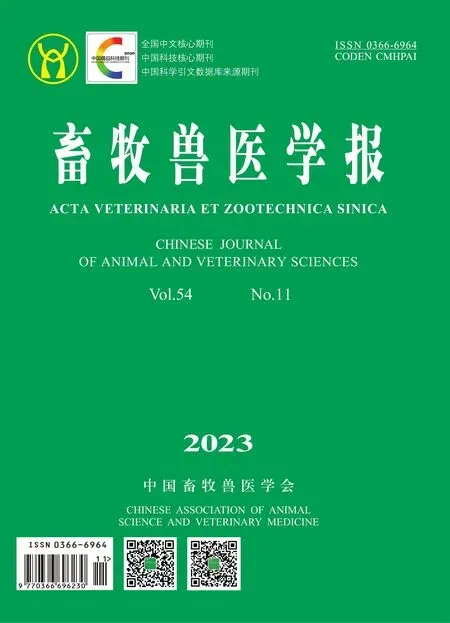鴿源鼠傷寒沙門菌的分離鑒定及致病性分析
楊夢林,鄭世奇,彭 凱,王 瑋,黃燕華,3*,彭 杰*
(1.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健康養殖創新研究院,廣州 510225;2.廣東省農業科學院動物科學研究所,廣東省畜禽 育種與營養研究重點實驗室,農業農村部華南動物營養與飼料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640; 3.嶺南現代農業科學與技術廣東省實驗室,廣州 510642)
沙門菌在全世界廣泛分布,自1885年沙門菌首次被分離后,截至目前為止,已發現的血清型已經超過2 600種[1]。鴿沙門菌病是肉鴿養殖業中常見的細菌病之一,主要病原菌為鼠傷寒沙門菌,通過消化道、呼吸道等途徑傳播,癥狀表現為精神狀態萎靡、羽毛凌亂、下痢、行為失常等。被感染的種鴿能夠通過垂直傳播將細菌傳遞給種蛋,引起種蛋壞死,降低孵化率,還能通過哺乳等方式感染乳鴿,引起乳鴿生長速度減慢甚至死亡[2]。此外,沙門菌作為人畜共患病原菌,能夠通過污染鴿的加工產品傳播給人類和動物,對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威脅。目前抗生素濫用情況較為嚴重,造成了細菌的耐藥性形成速度加快[3],因此了解沙門菌的耐藥性對于科學用藥有重要意義。
廣東某地區規模化肉鴿養殖場出現肉鴿下痢、消瘦、精神異常、關節腫大等癥狀,臨床觀察發現疑似感染鴿沙門菌。試驗采集病死鴿病變組織,進行細菌分離、純化、鑒定、耐藥性分析、耐藥基因和毒力基因檢測并建立感染嚙齒動物模型,分析沙門菌的毒力和致病性,以期為沙門菌病防治提供一定的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病料收集
從廣東某地區三個大規模肉鴿養殖場收集72只病死鴿,根據病鴿臨床癥狀在無菌條件下分別采集36份肝、23份脾、13份膝關節樣品,共計72份待檢測樣本。
1.2 試劑和培養基
麥康凱培養基、XLD瓊脂、SS瓊脂、LB培養基、生化鑒定管購自廣州環凱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產品;藥敏紙片購自杭州微生物試劑有限公司;2×F8 Master Mix購自艾德萊有限公司;DNA標準 DL2000,核酸染料E×Red(10 000×)購自北京莊盟國際生物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產品;沙門菌屬診斷血清試劑盒購自寧波天潤生物藥業有限公司。
1.3 病原菌分離與鑒定
在無菌條件下將72份病變組織進行研磨,先后接種于XLD瓊脂、麥康凱瓊脂和SS瓊脂培養基分離純化,記錄菌落形態和顏色并進行革蘭染色和鏡檢。對分離菌進行生化鑒定以及生長曲線觀察;采用沙門菌屬診斷血清,觀察分離菌與O價血清凝集情況;鼠傷寒沙門菌特異性STM4497基因PCR鑒定[4]及16S rRNA鑒定[5],擴增片段送往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測序,測序結果在NCBI數據庫中進行Blast序列相似性對比分析,并構建系統進化樹。
1.4 藥敏試驗
參照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委員會(NCCLS-2018) 描述的K-B法的標準,根據抑菌圈直徑進行判定分離菌株的耐藥情況。藥敏試驗用藥包括氨芐西林、阿莫西林等20種藥物。
1.5 耐藥基因和毒力基因檢測
試驗挑取單菌落溶解于裝有50 μL無菌水的EP管中,振蕩混勻后作DNA模板,檢測耐藥基因(tetA、tetB、sul-11、aphA3、aacC4、aadAF、aacC2、qnrA、qnrB、Aac(6′)-Ib、catI、floR、cmlA、blaTEM、blaSHV)[6-14]和毒力基因(mogA、sseL、mgtC、bcfA、araB、spvA、spvB、spvC、spvD、spvR、stn、fliC、fimA、avrA、invH、sopA、virK)[15-18]。
1.6 動物致病性試驗
將6周齡C57BL/6小鼠隨機分為5組,每組6只,選取攜帶毒力基因數量最多的致病菌分別以103、105、107、109CFU·mL-1濃度的攻毒劑量處理試驗組,每只灌服0.2 mL,設置陰性對照組,以PBS代替菌液,每只0.2 mL,僅第1日灌服,飼養期為6 d,試驗期結束后觀察小鼠器官病變。
2 結 果
2.1 分離菌分離鑒定
本研究在72份樣本共分離鑒定出12株病原菌,在XLD培養基均長出邊緣整齊、圓形粉紅色菌落,中心呈黑色(圖1A);在麥康凱培養基均長出表面光滑、圓形半透明灰白色菌落(圖1B);在SS瓊脂均長出無色半透明狀菌落,中心呈黑色(圖1C)。鏡檢觀察到兩端鈍圓、沒有芽胞和莢膜的革蘭陰性桿狀菌(圖1D)。生化鑒定結果均符合沙門菌特性,血清型鑒定結果顯示沙門菌A~F多價O血清和沙門菌O4單價血清因子與12株分離菌發生凝集反應,鼠傷寒沙門菌特異性序列STM4497經PCR擴增得到一條接近523 bp DNA目的條帶,并將16S rRNA測序結果在NCBI數據庫中進行Blast分析對比并建立系統進化樹(圖1E),綜上,說明12株分離菌均屬于鼠傷寒沙門菌。
2.2 分離菌耐藥性檢測
藥敏結果顯示,12株菌分離菌對恩諾沙星、甲氧芐啶、復方新諾明、氟苯尼考、氯霉素、氨芐西林、阿莫西林、頭孢噻吩、美羅培南、頭孢曲松耐藥率為0.0%,對卡那霉素、呋喃妥因、頭孢噻肟、丁胺卡那、環丙沙星、慶大霉素的耐藥率為8.3%~33.3%,對多西環素、米諾環素的耐藥率為58.3%~83.3%,對萘啶酸和利福平耐藥率為100.0%。
2.3 分離菌耐藥基因和毒力基因檢測
12株分離菌耐藥基因檢測結果顯示,tetA攜帶率為58.3%,sul-11攜帶率為41.7%,其他耐藥基因未檢出,結合“2.2”藥敏試驗結果發現,四環素類耐藥基因與其耐藥表型符合率100%,但磺胺類耐藥基因與耐藥表型符合率為0%。毒力基因檢測結果顯示,mgtC、bcfA、spvA、spvD、spvR、stn、avrA、invH、sopA攜帶率為100%,sseL、spvC、fliC攜帶率為91.7%,mogA、virK基因攜帶率為83.3%,araB為75.0%,spvB為66.7%,fimA為58.3%,說明該地區流行沙門菌毒力基因攜帶較多,詳見表1。
2.4 分離菌致病性研究
試驗隨機選取攜帶檢測毒力基因最多的1株分離菌進行攻毒小鼠試驗,結果顯示,隨著灌菌濃度增大,小鼠體重和采食量顯著下降(圖2A、B),脾、肝腫大,結腸長度縮減(圖2C、D、E)。觀察空腸HE切片發現鼠傷寒沙門菌引起絨毛長度與隱窩深度比值下降(圖2F),杯狀細胞逐漸減少(圖2G、I);觀察肝HE切片發現大量免疫細胞匯集肝,并且肝枯否細胞(Kupffer cell)數目逐漸增加(圖2H、圖3)。
3 討 論
本研究發現從樣本中分離出的12株致病菌均為鼠傷寒沙門菌,除本研究外,在多地報告中也指出鴿沙門菌病是由鼠傷寒沙門菌感染引起,這提示了鴿子對鼠傷寒沙門菌易感。細菌耐藥性形成與抗生素產生的環境壓力有著緊密聯系,細菌能夠通過整合子、質粒等從外界獲取抗性基因,同時還能夠通過質粒、轉座子等多種可移動原件發生水平傳播[3,19-20]。試驗檢測出5株菌具有磺胺類耐藥基因sul-11,但對磺胺類藥物卻保持高度敏感,與相關報道中磺胺類耐藥基因sul-11與磺胺異噁唑耐藥表型符合程度較高[21]具有差異性,這可能與本研究使用的藥物為甲氧芐啶和復方新諾明有關,不同的藥物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此外,sul-11基因能夠表達出具有磺胺類藥物抗性的二氫蝶酸合成酶,使細菌的生長不受磺胺類藥物影響。但在細菌內部由于sul-11基因存在多種類型的質粒中[22-24],其表達水平以及作用機制并不清晰,需要進一步探究。除此之外,部分菌種對氨基糖苷類和喹諾酮類具有耐藥性,但并未檢出氨基糖苷類和喹諾酮類耐藥基因,可能與本研究檢測耐藥基因種類不全有關,亦或者產生了新的耐藥基因。
細菌是通過多個毒力因子之間的協同作用對機體器官造成炎性損傷的,因此檢測毒力基因攜帶量有利于評估沙門菌致病能力。本研究發現,毒力島基因ssel、mogA、mgtC、bcfA、araB檢出率高于75.0%,毒力質粒基因、腸毒素毒力基因、鞭毛基因以及其他毒力基因檢出率均高于66.0%,其中11株菌含有sseL毒力基因,在諸多研究中發現,攜帶毒力島基因sseL的沙門菌毒性更強,沙門菌分泌的sseL蛋白能夠抑制機體炎癥反應,并且還能損傷吞噬細胞,有利于沙門菌逃逸[25-26]。除此之外,還有magtC、avrA、spvB、spvC、sopA等主要毒力因子[27],在本試驗分離菌中攜帶率也較高,說明該地區沙門菌的致病性較強。

在動物致病性試驗結果中發現灌服致病菌濃度高于105CFU·mL-1時,小鼠空腸絨隱比及杯狀細胞數目隨著灌菌濃度升高逐漸下降。杯狀細胞分泌的黏蛋白是腸道機械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沙門菌定植于腸道后,毒力島SPI-1和SPI-2向腸上皮細胞輸送效應蛋白,引起腸上皮細胞損傷,破壞腸道屏障的完整性[28-31],研究結果說明沙門菌對腸道吸收功能和屏障功能具有負面影響。除此之外,研究發現隨著灌服致病菌濃度升高,肝臟中枯否細胞數量逐漸增多,有研究指出革蘭陰性菌細胞壁組分脂多糖能夠活化枯否細胞,使其炎癥因子分泌增加,引起其他免疫細胞向肝臟聚集,共同清除血液中的細菌[32],然而這個過程是否有枯否細胞前體細胞募集進入肝臟發生分化增殖這一機制并不清晰,本研究枯否細胞數量增加可能與上述過程有關,此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4 結 論
成功分離出12株鼠傷寒沙門菌,通過藥敏測試、耐藥和毒力基因檢測以及6周齡小鼠致病性研究發現分離菌均出現多重耐藥,并且毒力基因攜帶量較高,致病性強,建議在該地區治療鴿沙門菌病中使用甲氧芐啶、復方新諾明等高敏感藥物,同時要提高公共衛生安全意識,注重食品安全,避免向人群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