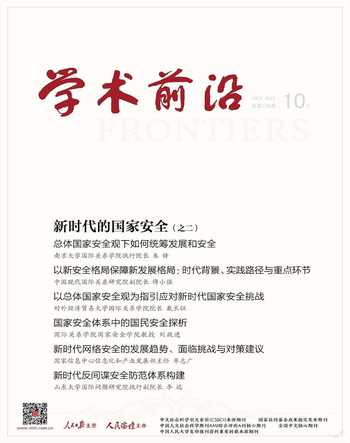新時代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構建
李遠
【摘要】推動構建新時代的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對于以高水平安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為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提供法律規范和保障,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進入了現代化、規范化、制度化的發展階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反間諜斗爭也面臨更加復雜緊張的嚴峻態勢。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切實加強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關鍵詞】反間諜? 國家安全? 安全防范體系? 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
【中圖分類號】 D631?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0.006
間諜活動是一種為境外敵對勢力竊取情報的行為,具有隱秘性高、滲透力強等特點,會對國家安全造成極大危害。為了適應國家安全的需要,世界各國高度重視嚴查防范和打擊一切間諜活動,并將間諜罪普遍規定為一種可以被判處最嚴厲刑罰的嚴重犯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1]當前我國反間諜斗爭形勢極為嚴峻,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各類間諜情報活動的主體更加復雜、領域更加廣泛、目標更加多元、手法更加隱蔽。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推動構建新時代的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對于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我國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建設的歷史進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維護政權和軍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與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激烈斗爭,抓獲了大批帝國主義國家及國民黨殘余勢力安插、派遣的間諜特務組織,維護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初見雛形。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之后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初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等文件,對間諜犯罪的行為作出了司法解釋并規定了相應的量刑標準,形成了當時的反間諜法律體系。這一時期對間諜行為的判罰具有“處罰重”“規制范圍廣”等特點。[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隨著人員、技術、資本的跨國流動性增強,境外間諜機構進一步擴大在我國的活動空間與行動范圍,活動重點目標由傳統的政治顛覆轉向破壞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境外間諜情報機構借機加大對我國社會的破壞力度,采取了包括政治滲透、分裂顛覆、情報竊密、反動拉攏、刺探收買、圍堵打壓等多項破壞行動,我國的反間防諜工作也由此進入新的階段。[3]
面對新的歷史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不斷提升反間防諜工作能力,對間諜犯罪的規制范圍和刑罰力度進行適時調整,以促進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相統一。1979年7月,我國頒布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去掉了諸如“里通外國”的描述,明確納入間諜罪條款,并將間諜罪處罰的一般量刑由“無期徒刑或死刑”降低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1983年,我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反間諜工作,保障國家安全;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改稿)》明晰了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為敵人竊取、刺探、提供情報”的“敵人”含義,不再統指“外國政府、機構”;1993年2月,我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彼時安全工作的重心更強調反對外部滲透和內部叛亂的政治安全;1997年3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特務罪、反革命罪及間諜罪修訂為資敵罪、泄密罪和間諜罪,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求。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信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愈發凸顯,我國開展國家安全和反間諜工作面臨的環境日益復雜。同時,隨著信息革命的到來,境外間諜機構針對我國的工業技術、科技機密等間諜犯罪活動明顯增加。為了應對新形勢下的間諜威脅,我國于2000年建立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負責國家安全領域工作的議事協調和決策。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4],由此非傳統安全威脅逐步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關注點。面對與日俱增的境外遠程網絡攻擊事件,我國完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等文件,還組織了64家國家級和198家省級工作單位共享網絡安全信息,有效處理了一大批網絡攻擊事件。[5]這一時期,國家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不再局限于傳統安全領域的政治和國防安全問題,而更多集中于經濟安全和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然而,彼時我國尚未單獨制定反間諜工作相關法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協調各類國家機關開展反間諜工作的多領域、多層次合作。有學者認為,反間諜不僅僅是偵查問題,還包括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宣傳教育等方面問題,應當單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推動我國今后的反間諜工作順利有效開展。[6]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內外安全形勢日益嚴峻復雜,國家安全面臨的可預見和不可預見風險明顯增多,我國的反間諜工作進入發展轉型關鍵期。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對新時代大安全格局下的國家安全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高瞻遠矚的重大決策部署,開創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新時代做好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我國建立并發展國家安全工作體制機制的進程也隨之加快。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規劃國家安全戰略政策,統籌國家安全工作藍圖方針。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指出必須始終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7]黨的十九大把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并寫入黨章。[8]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統籌發展和安全納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9]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作出專章論述和戰略部署,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重大要求。[10]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完成了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工作的理論構建與體系建設,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開創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嶄新局面。
隨著新時代加快構建大安全格局,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國家安全法律法規來為反間諜工作提供法律規范和保障,推動我國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進入了現代化、規范化、制度化的新發展階段。2014年11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作為維護國家安全領域的專門性法律。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確立了新時代加強國家安全的法治體系建設部署和依法開展國家安全工作的體制機制。此外,我國還于2016年4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于2016年11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于2020年6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等,切實增強了維護與塑造國家安全的法律基礎。
2023年4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下文簡稱《反間諜法》)。作為黨的二十大召開后國家安全領域的首部專門立法,該法的修訂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視,對深化新時代新征程反間諜斗爭、筑牢國家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反間諜法》的修訂是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貫徹落實。在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閾下,“國家安全”的客體范疇得到極大拓展,延伸了反間諜工作的內涵及外延。修訂后的《反間諜法》更加明晰完善了間諜行為邊界,提升了反間諜工作的精準性與全面性,拓展了反間諜安全防護鏈條和安全治理空間,有效維護和保障了重點安全領域和總體安全格局。其次,《反間諜法》的修訂適應了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鞏固了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堅持中央統一領導”為基本原則,強調建立健全更加科學規范的反間諜工作協調機制、執法程序和工作路線,堅持以系統性的安全治理手段和科學統籌的根本方法推動構建大安全格局,以制度優勢保障國家安全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再次,修訂后的《反間諜法》規定了國家安全機關行使職權必須嚴格規范執法活動,強化了反間諜工作監督,以法治建設保障新形勢下的反間諜工作;同時,加強了與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強制法、行政處罰法、地方性法規、工作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協同。最后,《反間諜法》的修訂充分體現了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筑牢了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反間諜法》強調反間諜工作路線要堅持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協助反間諜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與警覺性,強調積極開展反間諜安全防范宣傳教育,筑牢國家安全的堅固防線與社會基礎。
我國反間諜工作面臨的風險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下,我國國家安全得到了全面加強,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與考驗,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證,國家安全取得歷史性成就。然而,雖然我國國家安全總體向好、有序可控,但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和外部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我國國家安全仍將長期處于高風險期、高承壓期,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我國反間諜工作也面臨更加復雜緊張的嚴峻態勢。
首先,隨著信息技術的變革,各類間諜情報活動的主體更加復雜、領域更加廣泛、目標更加多元、手法更加隱蔽。間諜因為其特殊的工作性質,需要以保證自身長期處于隱蔽狀態為前提,為情報機構提供所需信息。在以往的反間諜斗爭環境中,國家安全人員更多面對的是“沒有案底、證件齊全、行為低調”的國內外人員和組織。在新時期的反間諜斗爭環境中,反間工作隨著科學技術革命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人工智能與網絡信息技術使得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權責邊界模糊化,賦予了后者操縱間諜行動、施加政治影響力的權力。間諜行動主體和目標更加多元,間諜活動領域從傳統的軍事、政治領域逐步拓展至經濟、科技和商業領域。同時,間諜行動平臺更加虛擬化,間諜手段更加隱蔽,間諜行為主體更加難以“追根溯源”,間諜犯罪的破壞性日益嚴重。例如,1992年的“米開朗琪羅”電腦病毒引發了第一次大眾電子恐慌,2011年的“盜空一切”病毒構成了對國家工業系統的顛覆和間諜活動,但這些網絡襲擊始作俑者的身份和動機卻一直未知。[11]美國智庫蘭德公司曾在報告中指出,“工業時代主要是核戰爭,而信息時代主要是網絡戰”。[12]2022年,美國使用40余種不同的專屬網絡攻擊武器對西北工業大學進行竊密攻擊。[13]此外,美國還利用“棱鏡”計劃對美國境內外公民實施多年的網絡監聽,甚至對日本、墨西哥、法國等“盟友”也進行大規模網絡攻擊滲透。[14]
近年來,網絡空間成為境外勢力和情報機構對我國開展間諜行為、實施破壞活動的新領域,我國應高度重視網絡空間范圍內的反間諜安全防范部署。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布的《網絡安全信息與動態周報》與《國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臺(CNVD)周報》顯示,針對我國的常見網絡攻擊和情報搜集手段包括利用漏洞、篡改網站、設置惡意程序和植入后門程序。截至2023年9月上旬,每周涉及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事件型漏洞總數平均約為12865個,范圍涵蓋銀行、保險、能源、城市軌道交通等重要行業單位、基礎電信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系統以及部委單位及其直屬單位,目標直指黨政軍要害部門和重要信息系統。[15]除此之外,互聯網為境內外間諜組織及個人實施滲透策反行動提供了新的活動場域。特別是互聯網的開放性、聯動性消除了傳統間諜行動的地域和人員限制,境外間諜機構可以通過網絡空間在我國境內建立代理人體系,進行常規性網絡攻擊和常態化情報搜集。2022年,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公布的典型間諜案例顯示,有兩例案件的當事人就是在使用某知名網絡交友軟件時被境外間諜情報機構實施了網絡勾連。[16]
其次,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逐步加大與全球各國在貿易、科技、人文等領域的合作往來,在為國家發展帶來巨大成果的同時,也增加了境外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的輸入性風險。在我國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中,外部敵對勢力的干預滲透愈加激烈,針對我國的間諜活動愈發頻繁。[17]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不少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價值觀領域的滲透與顛覆日益加劇。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一節中專門增加了“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側面反映出國家高度重視當今敵對勢力的干預滲透活動。[18]
從近年來國家安全部公布的間諜典型案件來看,一方面,外部敵對勢力常通過金錢、利益、美色等方式實施誘惑。例如,2003~2009年,澳籍華人胡士泰等四名澳大利亞鐵礦石企業力拓公司員工在高額酬勞引誘下,從事經濟間諜活動致使我國鋼鐵企業在近乎訛詐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上多付出7000多億元人民幣;[19]趙學軍作為中國航天領域的科研人員,向境外間諜組織提供大量涉密資料并收受間諜經費,于2022年8月被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20]2023年8月,國家安全部披露多起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案,涉案嫌疑人包括國家部委干部郝某、某軍工集團重要涉密人員曾某某等,經調查均與美國CIA人員有巨額報酬和間諜經費往來。[21]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對外交往活動日益頻繁,社會大眾對間諜活動的警惕性仍有待提高。長期以來,因反間諜工作政治性強、保密性高,我國反間諜安全防范實踐極少進行對外公開與宣傳,普通群眾缺少識別間諜行為的敏感性與警覺性,缺乏制止間諜活動、防范間諜滲透的能力儲備。境外間諜機構逐漸將行動目標擴展至我國普通民眾,如勞務輸出人員、留學生、駐外機構等。例如,在國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件中,多位犯罪嫌疑人系在外留學、進修、工作期間被境外反華勢力及情報機構策反收買并簽署參諜協議,并在其系統培訓指導下竊取國家安全機密。[22]
再次,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國際輿論層面集中對我國進行攻擊,頻頻以“國家安全”為名炒作“中國威脅”,我國反間諜工作面臨的來自個別境外媒體的污蔑和輿論壓力不斷增加。針對間諜行為進行防治防范和規范立法,防止國家秘密泄露和維護國家安全是世界各國通行的措施。美國于1917年通過《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 of 1917),于1996年通過《經濟間諜法》(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 1996),以保護兩極格局結束后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領先地位。英國的《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于2023年7月正式生效,聲稱將決心阻止、偵查和瓦解那些通過間諜活動竊取敏感信息、商業秘密,損害英國國家利益、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組織和個人,并增加了獲取或披露受保護的信息,泄露敏感的商業、貿易或經濟信息,協助外國情報機構三項罪名。[23]然而,《反間諜法》頒布后,卻被個別境外媒體以“侵犯人權”的噱頭進行了負面報道和惡意抹黑,渲染其會影響投資營商環境,上演了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中國威脅論”戲碼,進一步反映出部分西方國家一以貫之的“雙重標準”。
切實加強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構建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上,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切實加強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堅持黨對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的全面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黨中央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根本保證。面對新形勢、新挑戰,需要加強黨對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黨在反間諜實踐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推動各級黨委(黨組)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主體責任,為新時代反間諜安全防范體系構建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以法治建設加強和保障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維護國家安全,既需要有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也需要有專業系統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要進一步把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反間諜法律制度體系,充實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法律工具箱,貫徹落實新修訂的《反間諜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武器加強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斗爭。
以科技賦能推動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的能力現代化。科技創新是保障和塑造國家安全的關鍵,也是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任務。面對間諜活動形式和威脅不斷演變升級,需要加強反間防諜工作的關鍵技術攻關,掌握高級加密、入侵檢測、風險識別等核心技術,以科技賦能推動建設系統化的反間諜技術工具箱,掌握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的主動權。
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加強反間防諜人民防線建設。堅持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反間諜工作不是國家安全部門的“單打獨斗”,而是需要人人參與、全民共擔,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同防范,進而筑牢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對此,要組織開展反間諜安全防范宣傳教育,增強人民憂患意識和安全防范意識。一方面,要暢通舉報渠道,以方便公民向國家安全機關舉報間諜行為或線索,形成守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另一方面,要對舉報人提供必要的保護措施,對故意捏造、誣告陷害他人等也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統籌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反間諜安全防范。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統籌開放與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24]。在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需要處理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沒有高水平對外開放就很難有高質量發展,沒有堅實的安全保障就很難有良好的對外開放環境。在新征程上,只有切實做好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基礎,才能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抓住機遇、化解挑戰,確保中國這艘巨輪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加強國際傳播效能,提升國際話語權。面對西方部分國家炒作“中國威脅”,動員力量遏制中國的不利形勢,我們需要保持戰略定力,發揚斗爭精神,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上,全面提升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
(本文系2022年度山東省外事研究與發展智庫課題“山東省與英國的交流合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VHQ005)
注釋
[1]《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董為:《我國間諜罪立法問題檢視與修正——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視角》,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9期。
[3]謝貴平:《我國反間防諜的歷史經驗》,《人民論壇》,2023第16期。
[4]《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上所作報告全文》,2002年11月18日,http://rs.china-embassy.gov.cn/xwdt/200211/t20021118_3324298.htm。
[5]《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中國是黑客攻擊的最大受害國》,2010年1月25日,http://www.scio.gov.cn/ztk/hlwxx/02/02/Document/533531/533531.htm。
[6]劉躍進:《國家安全法的名與實——關于修訂我國〈國家安全法〉的一點建議》,《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人民日報》,2015年1月24日,第1版。
[8]《深刻把握新時代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意義》,《人民日報》,2018年4月16日,第12版。
[9]《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10月30日,第1版。
[10]《習近平強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2022年10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16/content_5718828.htm。
[11]阿蘭·柯林斯:《當代安全研究》,高望來、王榮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第531~546頁。
[12]J. M. Mazarr et al., "Disrupting Deterrenc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es on Strategic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14 April 2022,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595-1.html; R. S. Cohen et al., "The Future of Warfare in 2030: Project Overview and Conclusions," 11 May 202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800/RR2849z1/RAND_RR2849z1.pdf.
[13]《西北工業大學遭美網絡攻擊——揭開“黑客帝國”虛偽面紗》,2022年9月6日,https://www.jasjj.gov.cn/read.asp?xwid=12420。
[14]蘇凱:《從“棱鏡門”事件分析信息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及對策》,《網絡安全技術與應用》,2022年第10期。
[15]《網絡安全信息與動態周報》,2023年9月15日,https://www.cert.org.cn/publish/main/upload/File/Weekly%20Report%20of%20CNCERT-Issue%2037%202023.pdf。
[16]《國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臺(CNVD)周報》,2023年9月13日,https://www.cert.org.cn/publish/main/upload/File/CNVD202336.pdf。
[17]曹夏天:《大國競爭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的域外適用》,《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2021年第1期。
[18]《國家安全機關公布多起典型案例》,2022年4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16/content_5685561.htm。
[19]周九常:《新形勢下我國企業情報保護體系的基本架構》,《情報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11期。
[20]《國家安全機關發布典型案例提醒廣大群眾——共同筑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固屏障》,《人民日報》,2023年4月19日,第11版。
[21]《“80后”部委干部竟是美國間諜,國家安全部本月公布多起間諜案》,2023年8月21日,http://news.china.com.cn/2023-08/21/content_105838062.shtml。
[22]《國家安全機關公布4起危害國家安全典型案例》,2021年4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4/15/c_1127331422.htm。
[23]UK government, "National Security Bill–Factsheet," 11 May 2022, https://homeofficemedia.blog.gov.uk/2022/05/11/national-security-bill-factsheet/.
[24]《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2020年10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14/c_1126611290.htm。
責 編∕楊 柳(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