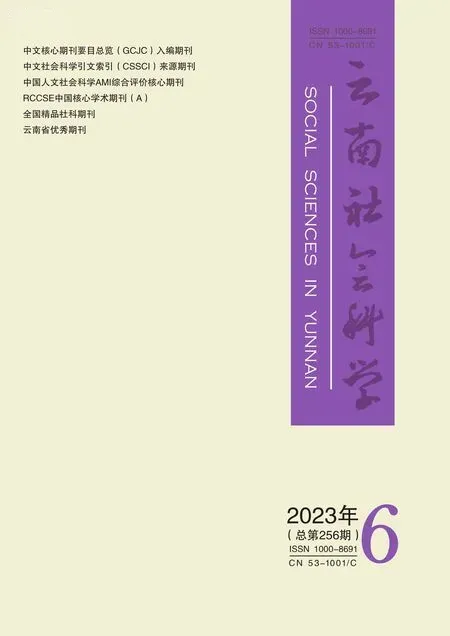互動數字敘事視域下非遺的開發框架與實踐方略
劉 芮
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被各社區、群體以及個人視為其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①UNESCO,《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2003 年10 月17 號。,是地方文化根脈滋養孕育的活態文化②郭永平、賈璐璐:《全球在地化到地方全球化:互聯網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2 期。,也是影響地方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中國高度重視非遺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工作,自2003 年起相繼頒布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等政策,并將其融入文化數字化、文旅融合、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之中。作為提升用戶參與度和推廣歷史研究逐步深入的有效方法③Holloway-Attaway L,Vipsj? L.(2020).Using Augmented Reality,Gaming Technologies,and Transmedial Storytelling to Develop and Co-design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s,Visual Computing for Cultural Heritage,Cham:Springer,177-204.,互動數字敘事被視為博物館等具有文化意義的地方的一種解釋工具,便于公眾了解物質遺存、非物質習俗和地方傳統的故事,實現地方與全球以及跨文化的過去的相遇④Chrysanthi A,Katifori A,Vayanou M,Antoniou A.(2021).Place-Based Digital Storytelling.The Interplay Between Narrative Forms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Space,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useums and Heritage Sites.RISE IMET 2021,Cham:Springer,127-138.。
目前,互動數字敘事應用于非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1)實踐的多元化。工具開發層面,國外基于不同的敘事類型和應用場景開發了故事化工具。譬如,有學者開發了基于互聯網的敘事編輯器(Narrative Storyboard Editor)和移動敘事播放器(Narrative Mobile Player)等工具①Vrettakis E,Kourtis V,Katifori A,et al.(2019).Narralive-Creating and Experiencing Mobile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Cultural Heritage,Digital Applications i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15:1-9.,使用推薦系統和數字敘事技術分析背景信息,改善用戶體驗②Mario C,Massimo D S,Marco L,et al.(2021).Recommender Systems and Digital Storytelling To Enhance Tourism Experience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Computing,323-328.。實踐應用層面,國內外通過敘事性游戲、互動小說等方式講述非遺故事,增強互動性、參與性與沉浸感。如蘇州中國絲綢檔案館開發了國內第一款檔案解謎游戲“第七檔案室——漳緞疑云”。該游戲將檔案知識融入在沉浸式書本、H5 頁面小游戲以及線下實景解謎中,通過游戲化敘事、沉浸式體驗和情景化探索,寓教于樂。(2)主體的協同性。互動數字敘事強調多元主體的積極參與。特別是圖書館③牟曉青、于志濤:《交互式數字敘事:加拿大 Writing New Body Worlds 閱讀治療新探索》,《圖書館論壇》,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30224.1834.008.html.、博物館與檔案館④張斌、李子林:《圖檔博機構“數字敘事驅動型”館藏利用模型》,《圖書館論壇》2021 年第3 期。等文化機構具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責任,也共同承擔保護歷史、傳播知識、教育大眾的社會功能。如何構建多元主體參與機制,促進圖博檔的融合發展以滿足日益多元的社會文化需求和國家文化可持續發展是當務之急。相較而言,中國互動數字敘事理論發展時間較晚,理論成熟度有待提升。如何扎根于本土化和民族性是互動數字敘事理念應用于非遺領域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有鑒于此,本文立足于互動數字敘事理論和地方的雙重視域,關注“人—媒介—地方”互動過程中所創造的非遺實踐圖式,從故事化表達和地方性書寫兩個維度構建基于地方特色的非遺開發的互動數字敘事框架。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框架
(一)互動數字敘事
敘事在交流和知識轉移以及個人和社會意義的形成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人們將新的傳播技術用于敘事,利用其潛力擴大敘事表達的空間。⑤Koenitz H.(2023).Understanding 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 Immersive Expressions for a Complex Time,New York:Routledge,1.新媒體技術催生了新的文本形式和敘事形式,互動數字敘事(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IDN)即是數字媒介技術發展的時代產物。IDN 的萌芽肇始于19 世紀60年代后期,互動小說、超文本小說、敘事性電子游戲等敘事類型的出現使得互動敘事理論和實踐研究漸熾。目前學界對于互動數字敘事的定義及其特征尚未形成共識。國內,李媛認為IDN 是用戶通過角色扮演、人機對話等方式參與敘事,改變敘事進程或結果,以增強用戶參與體驗的一種敘事方式。⑥李媛:《主題出版中的互動數字敘事策略》,《科技與出版》2018 年第11 期。章萌提出IDN 的核心在于構建數字敘事系統,讓用戶在虛擬的敘事體驗中激活腳本認知來理解故事世界,按照規則對情景產生參與式反應完成敘事行為。⑦章萌:《互動數字敘事產品的價值評價體系初探》,《出版科學》2020 年第6 期。國外,瑪麗-勞爾?瑞安(Marie-Laure Ryan)認為IDN 強調在程序化和參與式的環境中,利用引人入勝的故事元素,譬如冒險游戲或交互性敘事等方式,激發參與者的能動性。⑧Murray J H.(2018).Research into 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 A Kaleidoscopic View,Cham:Springer,3-17.哈姆特?寇安尼茲(Hartmut Koenitz)將IDN 定義為一種多種形式的敘事表達,以多模態計算系統的形式實現,并帶有可選的模擬元素,通過參與式過程增強用戶體驗。其中互動者對進度、視角、內容、結果有非同小可的影響,敘事被理解為心理投射世界的靈活認知框架。同時,其將系統(System)、過程(Process)和產品(Product)作為IDN 的核心要素,構建了SPP 模型并對其不斷完善(詳見下頁圖1)。其中,原生故事是系統的核心要素,包括程序組件、資產、用戶界面和敘事設計四個要素(詳見下頁圖2)。程序組件是指實現敘事設計的各種軟硬件工具。資產主要包括IDN 作品中使用的所有元素,包括2D 圖像、人物、景觀和建筑的3D 模型、文本、視頻、聲音等數據資源。敘事設計是指如何通過用戶界面對敘事元素、程序組件以及敘事邏輯等的架構。①Koenitz H.(2023).Understanding 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 Immersive Expressions for a Complex Time,New York:Routledge,71-78.綜合考量理論的成熟度和應用方式,本文主要采用哈姆特?寇安尼茲對于IDN 的定義及SPP 模型作為理論基礎。

圖1 SPP 模型的演化過程

圖2 原生故事元素示意圖
(二)本文研究框架
“地方”的含義并非單一固化的,而是充滿模糊性與多義性,且在不斷拓展自身的邊界,兼具實在與虛擬的生成性概念。②張娜、高小康:《后全球化時代空間與地方的關系演進及其內在理路——兼論一種地方美學的構建》,《探索與爭鳴》2020 年第7 期。一方面,數字媒介技術使“地方”得以掙脫地理位置的束縛,以擬態的形式存在于賽博空間之中。③郭崢、張濤甫:《媒介與空間視域下的賽博“地方”——兼論B 站地方性》,《編輯之友》2023 年第5 期。另一方面,非遺所界定的信仰、觀點、工藝和儀式等傳統實踐深刻地根植于本土社區的歷史當中④Kirshenblatt-Gimblett B.(2014).Intangible Heritage as Metacultural production,Museum International,66(1-4): 163-174.,是地方文化的結晶。因此,多元主體通過互聯網和計算機等媒介的參與式書寫實踐在非遺研究領域形成了“主體—媒介—地方”的三維互動場域(詳見圖3),通過互動數字敘事的方式推動用戶參與、講述數字故事、實現空間表達,旨在達到凝聚地方認同和文化認同的目標。從當前非遺開發的權利話語體系來看,主要是官方話語、高等院校、文化機構以及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博弈的結果。媒介技術強化了社會公眾的深度參與,制造出“人人皆可數字敘事”的文化圖景。從互動數字敘事的模型及其構成元素而言,數據資源體系是互動數字敘事應用于非遺領域的基礎。敘事工具為非遺故事化開發提供了多元化的方法。敘事設計影響了非遺故事化開發的邏輯與結構。從地方的空間形態而言,媒介化社會中,地方性的再生產過程越來越屈從于媒介邏輯和傳播形態。人們經由媒介所提供的參與過程與認同方式,可以形成全新的、超越時空的地方體驗。⑤袁星潔:《“再造地方性”:媒介化理論視角下地方媒體的傳播創新》,《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 年第6 期。地方的空間形態逐漸由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擴展到虛擬空間。虛擬空間既拓展了互動數字敘事的邊界,也為非遺的故事化開發提供了新的可能。

圖3 “主體—媒介—地方”三維互動圖示
二、非遺開發的故事化表達
(一)基礎:數據資源的聚合與集成
數據資源是非遺故事化開發的基礎。2022 年頒布的《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2022 年5 月22 日。不難看出,非遺數據已然成為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非遺保護多為建立“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級—縣級”四級遺產保護名錄和確立非遺傳承人兩種方式。因而,非遺的傳承和保護以地方為依托,以人為核心,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主要方式,其“活態流變”的特性影響了數據資源聚合與集成的方式和范圍。云計算、數據關聯、數據孿生等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資源的聚合與集成提供了新的途徑。因此,非遺數據資源的聚合多運用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方式,立足于“人—時間—事件”的三元框架,根據非遺資源傳承和演變的時間序列收集傳承人、非遺作品、地方歷史等類型的多元異構數據。盡管,中國針對民俗建立了數字化保護、數字資源采集和著錄的標準,但是針對其他類型的非遺尚未設計通用型標準和元數據核心元素集,且多參考國際標準依據其核心元數據體系對采集的非遺數據進行結構化處理。這種方式既沒有體現出非遺的特點和地方特色,也不利于搭建非遺數據平臺,打通數據壁壘和數據共享的“主動脈”,實現開放共享。
(二)核心:文化符號的提煉與轉化
文化符號是理解地方、重塑地方的關鍵性力量。非遺開發的關鍵在于借助空間的自然地貌和人文環境,形成一套清晰、連貫且頗具可讀性的符號文本,彰顯歷史風貌與地方個性。②劉海:《城市景觀:基于一種視覺認知的空間旅行》,《蘭州學刊》2014 年第6 期。地方作為媒介傳播信息的對象,在媒介的作用下會產生各種地方意象。③邵培仁:《地方的體溫:媒介地理要素的社會建構與文化記憶》,《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5 期。一方面,針對地方文化符號中最具代表性、辨識度和表現力的文化符號,如人物形象、地標性建筑、特色作品等方面進行提煉。同時,在充分結合地域文化、現代藝術設計與數字媒介技術的基礎上,將其轉化為文化符號。譬如,意大利外交部和游戲開發商Infinity Reply合作開發了文化遺產游戲APP“奇跡之地”(Italy.Land of Wonders)。該游戲聚合了自然、美食、藝術、演出和設計五個領域的文化遺產數據資源,設計了五名遺產衛士游戲角色,利用地圖指引玩家去探索意大利的文化遺產,完成意大利地標的100 個拼圖游戲。④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taly.Land of Wonders,Retrieved on 9th Dct.2023,from: https://ilow.esteri.it/#characters.另一方面,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加速了文化符號的移植與復制。動漫游戲、網絡文學、數字藝術、創意設計等方式推動了文化符號的衍生,為文化IP 全產業鏈發展聯動提供機遇,培育和塑造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原創IP,提升IP 的生命力。如故宮通過與騰訊攜手打造“數字故宮”微信小程序、開發《胤禛美人圖》《繪真?妙筆千山》互動游戲等方式實現非遺的創新性轉化和現代化表達,形成故宮文化IP 譜系,引發了持續不斷的“故宮熱”。
(三)方法:敘事工具的運用與開發
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豐富了故事的表現手段,隨著區塊鏈、AR/VR、虛擬引擎、3D 投影等技術日臻成熟,數字媒介技術在故事之中融入聲音、圖片、文字、動畫、影視等多種元素,并逐漸與非遺的開發場景深度融合,催生出“非遺+數字博物館”“非遺+線上旅游”“非遺+電子游戲”等新型業態。譬如,韓國文化遺產廳、SK 電訊與谷歌韓國共同開發了“昌德阿里郎(ARirang)”應用程序幫助公眾瀏覽昌德宮。看守宮殿的神獸獬豸以AR 的方式全程陪伴參觀者游覽,沿途還會提供12 個特殊景點以及歷史典故的詳細信息。公眾可以利用360 度VR 觀看限制觀眾進入的后院,在樂善齋內院可通過AR 欣賞宮廷舞蹈《春鶯舞》。用戶還可以通過AR 技術與王和王后一起拍攝AR 照、進行AR 射箭以及AR 放風箏等活動。①東亞日報,“傳說中的獬豸將引領我們進入3D 昌德宮”,https://www.donga.com/cn/article/all/20200728/2133694/1,2020年7 月28 日。此外,部分機構還根據具體的應用場景和不同類型的用戶需求積極研發數字敘事工具,強化數字敘事工具應用與推廣,鼓勵不同主體創造和分享故事。例如,CHESS 項目為博物館及其用戶開發了通用型故事創作工具——CHESS。該工具仿照電影的制作流程,基于劇本創作、舞臺設計、制作和編輯四個流程進行故事設計,利用腳本圖、分期圖和編輯圖三種圖形構建故事模型圖,形成信息內容與故事元素交織在一個連貫情節中的分支敘事。②Katifori A,Karvounis M,Kourtis V,et al.(2014).CHESS: Personalized Storytelling Experiences in Museums,In Mitchell A,Fernandez-Vara C,Thue D.(Eds.),Interactive Storytelling,ICIDS 2014,Cham:Springer,232-235.
(四)規則:敘事結構的邏輯與設計
敘事結構意指故事講述和情節鋪陳的方式,是數字故事的骨架。以技術為驅動力的數字媒介生態逐漸改變故事的形態、生產和創作邏輯。盡管線性敘事按照一定的時間或空間順序鋪陳故事文本,但是在互動數字敘事中,敘事文本不再是線性的、單一的和固定的,而是結構動態交織的超文本③蘇曉珍:《數字敘事交流結構淺析》,《出版科學》2017 年第4 期。,敘事結構也逐漸由線性敘事向非線性敘事結構轉變。非線性敘事結構打破了非遺故事中時空的統一性和敘事的連貫性,通過分叉敘事、回環敘事、復調敘事等設計方式搭建非線性的、多支線式的敘事結構,增強了非遺故事的趣味性和公眾的參與感。而且,互動要素的引入意味著向讀者讓渡部分故事操控權,使得素材在事件序列中的排布不同程度上脫離線性模式而呈現出更加復雜的結構。④陸文婕:《互動敘事中的敘事支點研究:結構、權重與語境》,《出版科學》2019 年第5 期。這意味著公眾采用不同的路徑選擇就會出現不同的敘事結構,構建出多元化故事序列。如2016 年11 月啟動的EMOTIVE 項目提出以情節為基礎,創作非線性、個性化、適應性更強的持續性故事。該項目以雅典古城阿高拉(The Ancient Agora of Athens)為空間原型,選取歷史學家德西普斯、曾生活在此地兒童等不同敘述視角,利用在線故事原型工具將故事相關的音頻、視頻、文本和圖像編譯成一個多分支故事。⑤Roussou M,Ripanti F,Servi K.(2017).Engaging Visitor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Through “Emotive” Storytelling Experiences:a Pilot at the Ancient Agora of Athens,Archeologia e Calcolatori,405-420.
(五)主體:多元主體的協同與合作
數字媒介的技術賦權激發了政府、高校、文化機構、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參與非遺開發的積極性,有助于全面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合作機制,形成非遺保護與開發共同體。作為非遺保護與開發的主導力量,政府機構不斷完善政策體系,建立專項資金,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培育公眾文化自覺。高等院校和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進行非遺研究、合作交流的重要陣地,延續歷史文脈、穩步推進非遺數字化保護與開發是其重要職責。公共文化機構通過館藏資源資源數字化、資源共享等方式建立協同合作機制。公眾參與是遺產包容性保護的重要環節,不僅體現在生態和經濟層面,更影響著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⑥管永康、祁天嬌:《作為新主體的“網絡公眾”——荷蘭城市遺產保護中的在線參與機制》,《旅游科學》,https://doi.org/10.16323/j.cnki.lykx.20230626.001.數字媒介使得公眾在非遺開發利用中的角色逐漸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參與者,提供了公眾與非遺深度交互的多元化渠道。譬如,芬蘭西普市政府與來自阿爾托大學的研究人員皮爾維?努米(Pilvi Nummi)合作開展Nikkil? Memories 數字記憶地圖繪制項目。該項目通過Instragram、Twitter 賬戶以及發放問卷的方式,鼓勵人們講述、分享和轉發他們的回憶并添加相關的圖片,以收集當地人對老建筑的故事、記憶、經驗等地方性知識。同時,通過GIS 的方式將故事與地點和建筑相關聯,構筑故事地圖,增強當地居民的地方感。⑦Nummi P.(2018).Crowdsourcing Local Knowledge with PPGIS and Social Media for Urban Planning to Reve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Urban Planning,3(1),100-115.
(六)結果:數字故事的樣態與呈現
媒介融合語境下,數字故事的類型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主要包括超文本小說、互動小說、敘事性電子游戲、互動電影、數字平臺以及實驗藝術裝置等多種樣態。多元化的數字故事類型有助于展現非遺的文化背景和蘊含其中的生動地方故事,助力非遺守正創新。如倫敦國王學院數字實驗室(King’s Digital Lab)和互動故事領域的先驅To Play For 共同發起的互動數字敘事項目——人工智能與故事敘述(AI&Storytelling)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進軍英國、發生憲法危機的歷史背景,以戲劇For King and Country 為故事原型,借助Charisma AI 互動媒體平臺,創作故事腳本、人物角色和敘事結構,讓公眾獲得最佳的敘事效果和沉浸體驗。①King’s Digital Lab.AI &Storytelling,Retriered on 9th Oct.2023 from: https://aiandstorytelling.com/.與此同時,數字媒介也豐富了非遺數字故事的呈現方式,以媒介矩陣的方式推動非遺傳播,形成非遺IP 宇宙。即面對需求日益分化的公眾,根據不同數字媒介的特性展開敘事和表達內核,呈現數字故事的內容,實現數字故事跨媒介傳播。故宮即是中華文化在地化開發、講好非遺故事的典型。藉由《穿越故宮來看你》H5 頁面、數字故宮小程序、《上新了?故宮》等多種數字故事類型,故宮通過微信、微博、網頁等多媒介平臺實現協同敘事,調動公眾對現有IP 的參與度。
三、非遺故事化開發的地方性書寫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媒介刺激了虛擬空間的誕生與擴展,地方演化為“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虛擬空間”的三元形態。流動性的網絡空間實現了地方文本的脫嵌與重寫,為非遺的傳承發展營造出新的空間場域與展演情境。②郭永平、賈璐璐:《全球在地化到地方全球化:互聯網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數字敘事被用作激發、構建和分享關于地點的新知識的一種解釋工具。基于特定地點的數字敘事突出了移動設備等媒介和場所之間的聯系,讓公眾以即時和定位的方式與空間和主題產生共鳴。③Grandison T,Flint T,Jamieson K.(2023).Participatory Polyvocal Performative and Playful Interpreting Resnik’s 4 for creative placemaking with digital tools.In Giglitto D,Ciolfi L,Lockley E,Kaldeli E(Eds.),Digital Approaches to In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Insights from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Europe,New York: Routledge,114-140.地方不僅包括客觀空間的尺度,也以人文主義視野彰顯了主體的實踐、生活、身份、符號等文化意義,④裴萱:《“地方感”與空間美學的意義結構表達》,《云南社會科學》2023 年第1 期。強調以敘事為紐帶實現公眾的自我定位與群體歸屬,從而在特定社會結構中回應“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如何不同于他們”等身份認同與他者劃定問題。⑤Schiffrin D.(1996).Narrative as Self-portrait: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Language in Society,25(2):167-203.因此,作為塑造地方和地方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遺的故事化開發必須考慮其空間形態和應用場景。
(一)物理空間:嵌入應用場景
物理空間是非遺形成和存續的物質基礎。遺址、博物館、檔案館、文化館等是非遺保存和展示、喚醒集體記憶、生成文化認同的重要場所。物理空間如博物館作為承載敘事信息的載體,不應僅僅是一個客觀的展示容器,更應是一個有意義的、充滿敘事性矛盾的場域,是“事件”的發生地,是可敘事的動態審美過程。⑥[英]萊恩?勞森:《空間的語言》,楊青娟、韓效、盧芳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3 年,第135 頁.在此過程中,公眾對于空間的感知由靜態向動態轉變。由此,互動數字敘事理念可以作為一種選擇方法引入文化機構物理空間的設計之中,為公眾營造一個交互式沉浸感知空間。國家典籍博物館、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與字節跳動公益合作、依托“同心護珍寶 聚力續華章——‘字節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金’成果展”推出的沉浸式互動解謎游戲“故紙修復師?碎丹青”即是一個良好探索。公眾以“古籍修復工作者”的視角切入游戲,使用手機端互動平臺和沉浸式互動道具等互動裝置,根據互動終端給予的邏輯劇情,通過推理、修復古籍,在遍布謎題線索的展陳空間,獲得游戲線索,不僅可以通過該游戲了解古籍背后的歷史,更有機會通過手機端互動平臺親身體驗古籍修復,寓學于樂,趣味無窮。⑦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沉浸式互動解謎游戲“故紙修復師?碎丹青”在國家典籍博物館開放體驗》,http://www.nlc.cn/pcab/zx/xw/202306/t20230601_216142.htm,2023 年6 月1 號。
(二)社會空間:強化社會互動
“場所”的內涵在空間呈現形式的應用中得到擴展,人們以身體為主體的整體性感知方式也為空間交互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①湯子馨:《數字人文視野下基于空間交互的場所營造》,《室內設計與裝修》2021 年第1 期。數字媒介極大地改變了公眾與社會空間交互的方式,公眾可通過“技術具身”的方式進入社會空間,通過感官共振、互動儀式、角色交互等方式強化社會互動,產生情感共鳴與文化認同。首先,印刷媒介和數字媒介的融合帶來了新的感官體驗和審美變化,通過聲光電等技術媒介或可穿戴式設備的刺激,營造多感官沉浸的空間臨場感。其次,非遺是一種程序化、儀式化的社會活動,可以通過線上文化展演、虛擬互動裝置、技藝學習體驗等方式傳播非遺知識。最后,基于應用場景設計不同類型的人物角色供公眾選擇,通過文本輸入、設備控制等方式實時控制場景內角色的行為。譬如,由國家文物局指導、敦煌研究院與騰訊聯合打造的全球首個超時空參與式博物館“數字藏經洞”,以4K 影視級畫質、中國風現代工筆畫美術場景與交互模式,讓公眾通過人物角色扮演的方式“穿越”到4 個不同的歷史時段,與洪辯法師等8 位歷史人物互動,逐步揭開藏經洞出土文獻敦研001《歸義軍衙府酒破歷》的面紗。②敦煌研究院:《全球首個超時空參與式博物館“數字藏經洞”今日正式上線》,https://mp.weixin.qq.com/s/59wkcL7MLBXI79keg7f3-g,2023 年4 月18 日。
(三)虛擬空間:重構現實場景
盡管網絡空間是一種虛擬場所,其依然能夠作為地方被感知,并和物理層面的地方建立聯系而延伸地方感。③白曉晴、張藝璇:《文旅直播與跨媒介地方的生成》,《南京社會科學》2022 年第9 期。一方面,非遺的保護與開發可以通過3D 建模、數字孿生等數字技術形成現實空間的鏡像世界,實現空間復原。地方擺脫了物理空間的限制,成為數字地圖上可以自由移動的錨點。例如,Etruscanning 3D 項目通過數據收集、數據清洗、地形采集、數字修復等途徑完成了兩個伊特魯里亞古墓的虛擬重建工作,并開發了應用程序。公眾站在博物館的投影墳墓虛擬環境的屏幕前,使用有Kinect 運動傳感器基于手勢的交互界面與應用程序進行交互。④Pietroni E,Adami A.(2014).Interacting with Virtual Reconstructions in Museums: The Etruscanning Project,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7(2):1-29.另一方面,非遺的保護與開發通過模擬現實世界中的人、建筑等元素,重構非遺在時空維度上的聯系,并對其進行改造和變形,嵌入到虛擬空間之中,實現空間再造。虛擬博物館跨國網絡(V-MUST.NET)曾舉辦過一個名為“羅馬鑰匙(K2R)”的互動展覽。該展覽以奧古斯都皇帝統治時期的羅馬文化為主題,鼓勵公眾通過尋寶游戲的形式,利用Admotum 應用程序從羅馬、亞歷山大、阿姆斯特丹和薩拉熱窩4 個地方的博物館中尋找展品。在找到其中一個地點的所有物品后,公眾可解鎖其余3 個地點的虛擬空間尋找展品,了解展品的歷史和故事。⑤Pagano A,Armone G,Sanctis E D.(2015).Virtual Museums and Audience Studies: The case of “Keys to Rome” Exhibition,IEEE,373-376.
四、非遺故事化開發的實踐性方略
(一)面向全數據采集,破除共享壁壘
數據是非遺故事化的基礎性資源,全數據采集可以獲取更加準確、全面、實時的數據。就采集標準而言,依據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制定適用于地方的非遺元數據互操作通用型標準和集成框架,對數據進行規范化描述。在此基礎上,結合非遺的特點和歷史因素,拓展互操作框架的核心要素,建設具有兼容性、互操作性和地方非遺特色的數據采集標準體系。就采集內容而言,多元化、規范化、流程化的數據形式便于后續通過互動數字敘事的方式對數字資源進行解構和重構。梳理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種類和數量,建立數據采集目錄或表單,對非遺進行分級分類采集和管理,從“人—時—地—物—事”5 個方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多源數據采集。就采集方式而言,可以采用影像記錄、3D 掃描、數據庫、API 接口、傳感器等多種采集方式,獲取不同來源、多元格式的元數據,實現非遺數據的多端采集和有效集成。就共享方式而言,可建立人物、事件等類型的專題數據庫和非遺數據共享平臺,在保證數據安全的前提下面向其他類型的用戶提供數據共享接口。
(二)打造本土故事IP,形成敘事風格
本土故事IP 是互動數字敘事理論關照下推動非遺可持續開發、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文脈。一方面,挖掘非遺中蘊含的人物、建筑、事件等故事原型,從價值觀念、文化表征、體驗內容三個方面構筑非遺故事的符號系統。價值觀念是非遺故事的情感基調,故事的價值觀既要適用于人類永恒的價值,也要與時俱進,凸顯時代精神。文化表征是識別非遺故事特色的關鍵,文化表征既要體現地方特色,也要便于轉化和提煉成文化符號,讓受眾從審美認知、藝術體驗自然地過渡到文化理解和價值認同。①史春林、宿程晴:《講好中國故事要用好文化符號》,《光明日報》2023 年3 月22 日。文化體驗是非遺開發的核心,通過主題體驗館、民俗文化游、實景游戲、VR 游戲等方式為公眾帶來沉浸式體驗。另一方面,建立媒介矩陣,形成敘事風格,打造故事IP 鏈。通過跨媒介的方式,圍繞統一的故事世界觀,實現非遺故事在不同媒介平臺上的傳播和故事IP 的互文敘事,建構邏輯高度關聯的敘事文本和故事宇宙,并逐漸延伸到文創產品開發等周邊實體文旅產業,實現非遺故事從“破圈”到“常青”的跨越式轉變。
(三)整合故事化工具,注重應用場景
故事化工具可以集成聲音、圖片、文字、動畫、影視等多種媒介元素,規范數字故事的生產步驟和操作流程,支持數字故事的協同創作和高效傳播。一方面,利用通用故事化工具設計非遺故事。時任美國新媒體聯盟副主席的艾倫?萊文(Alan Levine)于2007 年創建了一個名為“cogdogroo”數字故事網站,集成了具備數字故事創作功能的Web 2.0 工具。又于2013 年對網站進行改版,將通用故事化工具分為幻燈片放映、故事書、時間軸、地圖、漫畫、拼貼、設計、視頻、音頻9 種類型。網站也提供了移動應用程序工具列表以供公眾參考和選擇。②Alan Levine,All Tools A to Z.Retrieved on 9th Oct.2023 from:https://50ways.cogdogblog.com/Tools+A+to+Z.html.通用故事化工具簡便、快捷的操作方式也有助于專業機構和公眾積極參與非遺故事的創作以及激勵公眾的二次創作。另一方面,根據非遺的類型和地方特色設計和開發故事化工具。數字故事創作工具的開發應該考慮非遺“活態流變”的特性和地方的文化背景因素,既可以在原有工具的基礎上添加新的功能,亦可以重新開發新的工具。
(四)采用非線性敘事,創新表達方式
非線性敘事打破了線性敘事中固有的時空關系,通過多元化的敘事方式以及富有變化的敘事節奏豐富了非遺故事的敘述方式,降低了公眾出現審美和感官疲勞的機率。從時間維度而言,可以打亂非遺故事原型中原本的線性時間順序,并將其拆解成相應的敘事碎片,通過時間循環、多重時空、平行時間、時間回溯等不同的敘事時間呈現方式,來構建故事的文本,設置故事情節。時序上的變化會營造出諸如懸念、因果的強化等敘事趣味,③於水:《從非線性敘事電影到交互敘事電影》,《當代電影》2012 年第11 期。提升故事的趣味性,吸引公眾的注意力。從空間維度而言,既可以通過改變文本中空間的形態、位置及關系等方式以及空間折疊、空間切割、空間拼貼等方式設計非線性敘事空間,也可以通過物理空間中故事碎片或互動裝置的隨機嵌入設計物理空間的敘事方式。從公眾選擇而言,可以根據非遺故事的劇情,設計多個故事角色、多條分支結構或故事結局以供公眾選擇。在此基礎上,公眾可選擇不同的節點或采用遍歷敘事支點的方式體驗不同的故事,增強其與文本的交互性。④劉珂、劉芮:《游戲化敘事視域下數字人文的敘事表達、媒介呈現與實踐路徑》,《圖書情報知識》,https://kns.cnki.net/kcms2/detail/42.1085.G2.20230619.1458.002.html.
(五)多元化主體參與,構建協同機制
非遺故事化開發需要構建多元主體參與、協同聯動的合作機制。首先,政府、高校和公共文化機構應通過科研項目申報、舉辦會議、開展專業技術培訓等方式鼓勵多元主體積極參與非遺故事化開發,建立“合作—共享—創新”的非遺開發學術共同體,形成良好的非遺開發的學術生態。其次,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驅動力,建設面向非遺故事化開發的項目管理框架。通過項目管理的方式,建立跨學科項目小組,引入企業等社會力量,增強團隊的合作精神,合理安排項目的進度,有效控制節約項目成本。同時,依據項目管理流程,從規劃、籌備、實施、驗收、反饋、改進、推廣7 個維度推動項目的開展、項目成果宣傳和運用。最后,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建立公眾反饋渠道。除眾包模式外,引導公眾積極參與非遺故事的文本創作、敘事結構設置、角色形象設計等開發流程,讓公眾深度參與其中。同時,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征集地方特色故事,收集公眾對于非遺故事化開發的產品和服務的意見及評價,并及時改進。
(六)遵從空間化轉向,形成地方認同
非遺的產生與開發與空間形態和地域文化是一種和諧共生的狀態。一方面,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可以根據故事的主題、應用場景的不同以及場館的空間形態將聲音、圖片、視頻、音頻等敘事工具和互動裝置嵌入至其物理空間之中,實現內容型交互;也可以利用AR、VR 等技術穿戴設備,以及數字虛擬人等方式為公眾構建數字化身,擴展公眾的具身體驗和沉浸體驗,實現人際型交互。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主題并置、游戲敘事、環繞敘事等方式安排空間的布局和結構,讓公眾在體驗過程中了解非遺歷史,感悟非遺精神,進而促進地方意義的生產,增強文化自覺與自信。此外,數字媒介為空間敘事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利用3D 建模、全息投影等媒介技術賦能非遺故事的場景構建與復原,再現非遺的故事空間,幫助公眾實現更深層次的認知和理解,讓其產生情感共鳴和地方認同,還可以通過多個虛擬文化空間場景串聯或設置專題故事路線的方式,促進場館之間的聯動。
綜上所述,故事是人類學習知識、理解文化、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徑。立足于互動數字敘事視域,持續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故事化開發和地方性書寫是數字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應有之義。面對非遺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時代訴求和價值召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故事化開發關注“人—媒介—地方”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地方經驗和實踐范式,以數據資源為基礎,以文化符號為核心,以敘事工具為方法,設計敘事結構,鼓勵多元主體參與,構建多種形態的數字故事,并基于空間形態和應用場景的雙重考量,將非遺故事嵌入“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虛擬空間”三元空間形態,實現非遺敘事的當代表達。公眾則經由非遺敘事感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魅力,感悟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蘊含的時代精神,在潛移默化中構建起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