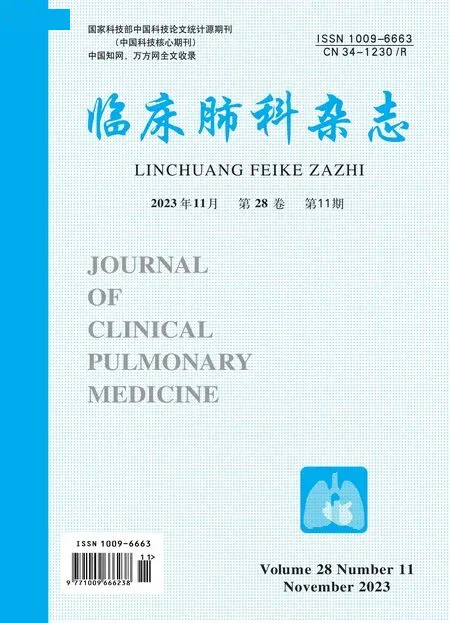B7-H3(CD276)在呼吸系統疾病中作用機制的研究進展
劉文潔 武帆
B7-H3分子也稱為CD276分子,是B7家族的成員之一,在人類組織中廣泛表達。近年研究顯示,B7-H3與肺癌、支氣管哮喘、感染性肺炎等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病及病情嚴重程度密切相關。早期研究發現B7-H3在人類多種器官組織靜息細胞表達低,但在各類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感染性疾病細胞中高表達,在外周血淋巴細胞中不表達[1]。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上述疾病血清可溶性B7-H3水平亦明顯高于正常人群。可溶性B7-H3在活化的T細胞、單核細胞以及樹突狀細胞中表達,并可在血清中用ELISA法檢測到。因此,本文對B7-H3的分子結構、表達形式、生物學活性及其在呼吸系統常見疾病中的作用機制、臨床特征等進行綜述,為指導臨床早期診斷及判斷預后提供幫助。
一、B7-H3的結構和表達形式
B7-H3是B7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員之一,屬于B7-CD28家族的免疫分子,最初從人類樹突狀細胞來源的cDNA文庫中克隆而來,位于人染色體15q24.1上,由4.1kb大小的mRNA所編碼[2],長度為951個堿基,由316個氨基酸組成,為Ⅰ型跨膜糖蛋白,在氨基酸端有一個信號肽,包括細胞外的免疫球蛋白樣可變區(IgV)、恒定區(IgC)、跨膜區和45個氨基酸的包漿區[1-3],相對分子質量在45 000~66 000之間[4]。人類B7-H3基因由于剪接差異形成兩種不同形式的剪切體:一種為2IgB7-H3又稱B7-H3a,由IgV-IgC 2個免疫球蛋白結構域組成;另一種為4IgB7-H3又稱B7-H3b,其分子胞外段由 IgV1 -IgC1 -IgV2 -IgC2 4個免疫球蛋白結構域組成[5]。基因序列研究發現,4IgB7-H3為 2IgB7-H3 串聯外顯子復制的結果,分子量為110KDa,4IgB7-H3在第一個C樣結構域末端存在“PQRSPT”6個保守性氨基酸,而2IgB7-H3則不存在該段序列[6]。B7-H3有膜型(mB7-H3)和可溶性(sB7-H3)兩種存在形式,mB7-H3存在于活化的T淋巴細胞、單核細胞、樹突狀細胞,可在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的切割下脫落,形成sB7-H3[7]。實驗證實[6],可溶性B7-H3僅來源于2IgB7-H3,而4IgB7-H3僅以膜型形式存在,保守性氨基酸PQRSPT的存在可能是導致4IgB7-H3不能被剪切成可溶性蛋白的原因。
二、B7-H3的免疫活性
B7-H3可作用于不同的T細胞亞群,影響宿主T細胞免疫應答過程。B7-H3最初被認為是共刺激分子,可刺激CD4+T、CD8+T細胞增殖,增強細胞毒性T細胞的誘導,在T細胞受體信號通路存在的情況下選擇性地刺激干擾素γ(Interferon-γ,IFN-γ)的產生,促使T細胞向Th1分化,對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白介素-8(Interleukin-8,IL-8)等也有上調作用[1,8]。然而另有學者證實,B7-H3也可通過抑制T細胞轉錄因子如激活蛋白-1(AP-1)、核因子Kappa-B(NF-κB)等的活性,抑制IFN-γ的分泌,因此被認為是共抑制分子[9-10]。目前的證據表明,B7-H3對T細胞產生兩種不同效應的機制與兩種不同的剪接體相關,2IgB7-H3促進T細胞的增殖和IFN-γ的產生,4IgB7-H3則抑制了T細胞的增殖及細胞因子的產生[6]。此外,B7-H3對NK細胞的活性也有抑制作用,在B7-H3基因缺陷小鼠體內NK細胞的百分比和絕對數量均增加[11],Liu等學者證實其機制與NK細胞表面CD16信號通路特異性激活有關[12],B7-H3的過表達降低了NK細胞的細胞毒性[13]。對于B7-H3的特異性受體目前尚無定論,研究發現B7-H3具有Toll樣受體2(Toll-like-receptor 2,TLR2)依賴性,提示TLR2可能為B7-H3的受體分子[14],另有學者發現,B7-H3能與細胞表面的白細胞介素-20受體α亞基(IL-20RA)結合,表明B7-H3與IL-20細胞因子家族之間存在著未知的聯系[15]。因此,B7-H3導致的機體的免疫功能紊亂、自穩態失衡及由此導致的免疫風暴可能是導致機體組織的炎性損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與呼吸系統疾病的關系
呼吸系統疾病是臨床最常見的一類疾病,國內外研究發現,B7-H3與呼吸系統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病情預后有關。
1 B7-H3與肺癌
根據全球癌癥最新統計報告顯示,2020年肺癌占所有癌癥新發病例的11.4%,占所有癌癥死亡病例的18.0%,肺癌依然是致死率第一的惡性腫瘤[16]。研究證實,B7-H3在肺癌尤其在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組織中高表達,其水平與患者的臨床預后成負相關[17],在肺腺癌患者血清中sB7-H3水平也高于健康人群。B7-H3通過PI3K/AKT、JAK2/STAT3和Raf/MEK/ERK1/2信號通路級聯反應觸發肺腺癌細胞中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促進肺腺癌的發生發展。目前已觀察到B7-H3可降低EGFR突變的肺腺癌細胞藥物治療的敏感性[18]。國內研究發現[19],在肺腺癌中B7-H3高表達患者對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靶向治療更容易耐藥,且耐藥的發生時間更短,由此推測B7-H3有望作為避免或延緩肺腺癌EGFR-TKI靶向治療發生耐藥的潛在靶點。目前,B7-H3靶向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已證實在小鼠和體外實驗可抑制NSCLC生長,尤其對伴有IFN-γ和IL-2分泌的NSCLC效果明顯[20-21],抗B7-H3單克隆抗體奧布爾他抗(8H9)已成功用于B7-H3(+)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免疫治療[22],并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
B7-H3與肺腺癌調節轉錄因子1(ets-like protein 1,ELK1)結合,激活上皮-間葉轉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途徑促進肺腺癌的轉移[23]。EMT使上皮細胞失去極性,并與周圍的上皮組織分離,轉化為具有游走能力的間質細胞。B7-H3可調控EMT相關因子的表達,通過PI3K/AKT通路上調SIRT1的表達,從而促進EMT與NSCLC轉移相關的激活[24]。綜上說明B7-H3在促進肺癌細胞增殖、侵襲和轉移方面,可作為獨立預測的指標。B7-H3靶向對肺癌的免疫治療具有一定的臨床指導意義。
2 B7-H3與支氣管哮喘
支氣管哮喘是臨床上最常見的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研究發現支氣管哮喘患兒血清B7-H3水平明顯升高,急性發作期升高更顯著,并與肺功能成負相關[25]。研究證實[10],B7-H3對Th2細胞存在正性調節作用,促使Th1/Th2平衡向Th2偏倚,在哮喘患者血清中sB7-H3與白介素-4(IL-4)水平呈正相關,IL-4是Th2細胞分泌的主要細胞因子,可趨化嗜酸性粒細胞聚集,誘導B細胞合成IgE抗體,引起喘息發作。Gu等[26]研究發現B7-H3融合蛋白通過上調Th2細胞GATA-3轉錄因子的表達而促進Th2細胞分化參與哮喘發展。此外,B7-H3在中性粒細胞哮喘對Th17/Treg細胞失衡發揮了重要作用,B7-H3可促進Th17細胞分化,并促進Th17細胞分化的關鍵受體維甲酸相關孤兒受體γt(RORγt)過表達,且對RORγt的作用存在劑量依賴性[27]。
哮喘患者存在微小RNA(miRNAs)異常表達,研究發現B7-H3與miR-29b成負相關,miR-29b表達上調后,肺組織B7-H3與信號轉導子和轉錄激活子3(STAT3)表達水平下降,B7-H3與STAT3協同作用進一步增強Th2型炎癥反應[28]。另有學者發現B7-H3對miR-29c也有相反的作用,B7-H3是miR-29c的直接靶基因,miR-29c通過與B7-H3-3'UTR位點結合,降解B7-H3 mRNA,使B7-H3表達降低,從而抑制哮喘發生[29]。因此sB7-H3有可能成為判斷哮喘嚴重度及預后的生物學指標。但B7-H3在哪種類型的哮喘中促進疾病進展或控制病情發作,需進一步研究。
3 B7-H3在感染性肺炎中的作用機制
(1)B7-H3與肺炎支原體肺炎 肺炎支原體(MP)是臨床上常見的一種呼吸道病原體,目前普遍認為肺炎支原體肺炎(MPP)的發病機制主要集中在免疫損害學說,自身免疫抗體與細胞因子相互誘導,造成機體免疫反應過度紊亂導致疾病的發生。當機體被MP感染后,血漿及肺泡灌洗液(BALF)中sB7-H3的水平異常升高,且與疾病嚴重程度成正相關[30]。sB7-H3是MP感染后發病的主要炎癥介質,sB7-H3通過參與TLR-4/NF-κB信號通路,促進Th2細胞因子IL-4、IL-10的分泌,加重肺部組織炎癥損傷[31]。TLR-4也可激活NLRP3炎癥小體,NLRP3炎癥小體和 NF-κB 信號級聯形成正反饋回路,與sB7-H3共同促進下游炎性因子IL-1β的分泌,導致細胞的程序化死亡[8,32]。另外在MP感染患者血清sB7-H3與IL-36水平成正相關,IL-36作為促炎因子可直接刺激初始CD4+T細胞增殖和促進IL-2的產生[33]。
在MPP中B7-H3水平同樣受miR-29c調節,miR-29c/B7-H3/Th17軸在重癥MPP中發揮重要作用,miR-29c水平降低,相應B7-H3水平升高,并與Th17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IL-17水平呈正相關[34]。MP感染后B7-H3通過與炎癥因子的相互作用及級聯反應參與組織細胞凋亡,導致肺組織及其他組織器官的炎癥損傷。然而MP感染后引起的免疫級聯反應中哪種細胞因子占主導地位尚未十分明確。
(2)B7-H3與膿毒癥及肺炎鏈球菌腦膜炎 B7-H3目前在細菌性肺炎的表達尚未見報道,但研究證實[35],細菌性膿毒癥患者血漿sB7-H3水平增高,其水平高低與感染程度正相關,且該水平與臨床結局和血漿TNF-α和IL-6水平相關,B7-H3通過TLR-4和TLR-2依賴機制放大了革蘭氏陰性和革蘭氏陽性細菌引發的炎癥反應。
在小鼠肺炎鏈球菌(SP)腦膜炎模型中發現[14,36],B7-H3通過TLR-2信號機制增強小鼠腦內TLR-2下游NF-κB p65和MAPK p38通路的激活,進一步介導腦內炎癥反應,同時B7-H3能夠促使趨化因子如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的表達增加,加劇腦損傷。B7-H3對腦損傷特異性標志物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及中樞神經特異性蛋白(S100b)的基因表達也發揮了上調作用,血清水平越高,腦損傷的程度越重[37]。關于B7-H3在細菌和病毒性肺炎中的作用機制及對病情影響的研究尚少,尚需要更多的動物實驗、體外實驗及臨床研究證實。
4 B7-H3與急性肺損傷
急性肺損傷(ALI)及其更嚴重的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是肺內過度的炎癥反應,肺泡-毛細血管屏障破壞和肺水腫導致的氣體交換嚴重受損。研究證實B7-H3通過抑制NF-κB p65的激活,并通過下調趨化因子配體2(CXCL2)的表達和釋放,減弱脂多糖誘導的肺多形核中性粒細胞(polymorphonuclear neutrophils,PMN)趨化和跨內皮遷移,降低肺多形核中性粒細胞浸潤及肺髓過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的活性,從而顯著減輕肺損傷[38]。
四、總結與展望
B7-H3作為B7家族新成員,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其分子結構及表達譜已經明確,但B7-H3的確切受體目前仍然未知。B7-H3的生物學功能復雜,其在免疫調節中可能存在共抑制和(或)共刺激作用,國內外研究發現,B7-H3與肺癌、支氣管哮喘、肺炎支原體肺炎、細菌感染以及急性肺損傷均存在相關性。然而對B7-H3未來能否作為呼吸系統疾病的治療靶點仍缺乏更多的臨床研究,需更多的臨床病例及多中心研究證實,特別是各種細菌及病毒所致的重癥肺部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