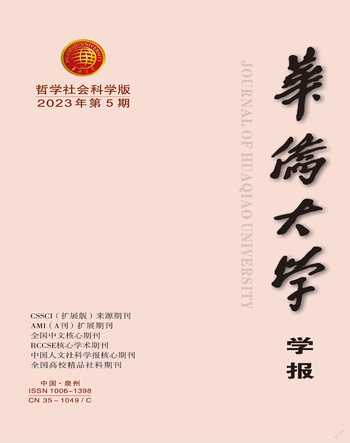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先天性及其認知神經基礎
王思敏 張沛
摘要:程序正義作為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原則之一,其實現路徑呈現出了“程序工具主義”和“程序本位主義”兩大陣營。兩陣營的爭論焦點在于:除了追求物質利益的工具性價值,程序正義本身是否具有可追求的獨立價值?發展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實證結果為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提供了依據。發展心理學發現:人類對程序正義具有先天趨向性,且隨著年齡和認知水平的增長,這種先天趨向會發生演變并逐漸成熟。認知神經科學則揭示了程序正義獨立作用的生理機制,功能性核磁共振的研究發現:(1)人腦表征程序獨立價值和工具價值的腦區不盡相同;(2)程序本身便可激發人腦的獎懲機制,這從先天傾向和認知神經視角說明了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基礎。
關鍵詞:程序正義;工具主義;本位主義;哲學心理學
作者簡介:王思敏,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學(E-mail:1309176251@qq.com;上海,200092)。張沛,廣東第二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學(廣東 廣州 510812)。
中圖分類號:D0;B0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5-0102-11
在法哲學領域,程序正義研究的核心問題是闡明程序正義何以可能。有關這一問題的探討,歷史上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程序工具主義”(后文簡稱“工具主義”)和“程序本位主義”(后文簡稱“本位主義”)。“工具主義”不承認程序具有獨立價值,認為衡量正義與否的唯一標準是結果正義的實現程度,程序本身只有作為手段和工具的作用。與之相反,“本位主義”認為程序除了具有工具價值外,還具有獨立價值,而真正的正義不應該只是結果正義,還應包括程序本身的正義,甚至認為只要堅持公正的程序,就可以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決或決定。現今,盡管大多數學者都已經承認了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但在程序正義獨立價值如何存在這一問題上,“本位主義”始終沒有給出一致且有力的證據。
有關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爭論促使人們必須深入思考正義問題,也為司法改革和國家治理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建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該爭論依然造成了許多難題。在國內,司法界長期以來忽視了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形成了“重結果,輕程序”的傳統,這一現象已經成為司法改革的重要阻礙;而國外情況則恰恰相反,由于羅爾斯的巨大影響力,以及“程序本位主義”在實踐中較強的可操作性,重視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或者說“重程序,輕結果”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的共識,但對程序的過度推崇卻可能導致本該增進社會正義的程序成為破壞正義的誘因。例如,1994年轟動美國的辛普森案中,檢察機關以程序不當為由否定了關鍵證據并宣布辛普森無罪,到導致大量民眾對司法程序的公正性產生質疑。這一系列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在于,學界和司法界對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機制始終模糊不清。
有關程序正義獨立價值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機制的研究應該包括兩個方面:(1)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是如何存在的?(2)這種獨立價值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科學的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一個長久以來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很難在原有的理論維度上得以解決。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爭議長期懸而未決的原因之一在于:“本位主義”陣營無法提供足夠堅實的事實證據,以致理論上的爭辯無法在實踐層面驗證。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心理學家也開始研究程序正義,在“程序正義獨立價值如何存在”這個問題上,對人類嬰兒的研究發現:既使最終結果相同,嬰兒也更愿意接受公平的程序。也就是說,程序正義不但具有獨立價值,對程序正義的趨向還是人類的本能,相關的動物實驗也佐證了該觀點。另外,對不同年齡段兒童的研究還發現,盡管追求程序正義是一種本能,但這種本能會隨著年齡和認知能力的增長逐步發展。在“獨立價值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上,認知神經科學通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發現,程序正義的確具有為結果利益服務的工具職能,但程序正義同時也具有獨立的職能,且人腦對兩種職能的加工過程是分離的;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認為程序正義具有獨立價值,是因為即使沒有物質利益的刺激,公平的程序本身也可以刺激主管獎勵機制的腦區,即程序正義具備某種“內在價值”。
然而,來自認知科學的證明并非無懈可擊,這些證明依然會面對來自對學科交叉這一方法和心理學內部的質疑。因此,未來的研究(1)仍需進一步發揮交叉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人們評估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神經機制;(2)同時值得關注的是,程序正義不是一個單數名詞,而是一個復數,因此需要在不同情境中對程序正義的標準進行細致劃分,以最大化地利用程序正義實現社會的善治。
一程序正義獨立價值問題的爭論
在程序正義何以存在的論證中,“工具主義”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邏輯起點,這種假設似乎是天然合理的,在現實生活中更符合人們的一般思維,而“本位主義”在承認程序的工具作用之外,還認為程序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此,論證“程序正義獨立價值如何存在”這一問題的責任主要需由“本位主義”一方承擔。
首先,對于程序正義的存在基礎,“工具主義”和“本位主義”有著不同的看法。“工具主義”認為人們完全是以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而進行經濟活動的主體,此時程序正義只作為人們爭取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存在。正如邊沁所說:“對于法的實體部分來說,惟一值得捍衛的對象或目的是社會最大多數成員的最大幸福……程序的有效性最終取決于實體法的有效性。”,使用程序的目的在于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種論證似乎是自明的。但“本位主義”對此進行了反駁,認為該觀點無法解釋人們在某些情境中寧可犧牲部分利益,也要選擇程序正義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不爭饅頭爭口氣”。“本位主義”對該現象的解釋是:程序正義本身就具有值得追求的價值,且這種價值獨立于物質利益,單純用物質利益來解釋人的選擇會忽略人的復雜性。
為了對抗“工具主義”的“經濟人”假設,“本位主義”需要為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尋找一種有同等論證效力的證據,并在某種自然主義的基礎上,進一步證明人類追求程序正義同追求物質利益一樣,都是人的自然需要。對此,“本位主義”主要采用了以下兩種論證策略。
“本位主義”的第一種論證策略認為程序正義具有某些獨特的,結果正義無法實現的作用。比如邁克爾·貝勒斯(Michael D.Bayles)認為法律程序可以讓當事雙方充分參與審判過程,令其明白裁決是如何做出的,從而使雙方更易接受裁決結果以化解矛盾,他將這種作用稱為“過程價值”( process values)。美國法學家羅伯特·薩默斯(Robert S.Summers)也持有相似觀點,他認為人們對結果正義的判斷在絕大多數時候是一種主觀的感知,并沒有客觀的標準,而程序正義可以使當事人得到公平、人道的對待, 并產生一種受尊重的感覺。同時充分且恰當的程序可以使當事人了解他們被如此對待的原因,可以提高當事人對審判過程和裁判者的認可度,從而促使當事人更愿接受審判結果。
但這種證據很容易被“工具主義”反駁。“工具主義”采用的是一種還原主義的路線,可以這樣反駁:人們之所以選擇尊重程序,是因為公正的程序從長期來看,是有利于個人利益的。這一論證是霍布斯式的,可以被稱為“長期利益”或“間接利益”論證,也就是說程序正義之所以具備這些作用,是人們權衡“長期利益”和“間接利益”的結果。比如當事人選擇接受判決,不是因為他認可了程序,而是他在衡量以后發現尊重程序可以帶來社會的穩定,而不遵守程序可能會造成周圍人對自己的敵意,在充分衡量長期和間接的利益后,他選擇接受判決。
“本位主義”的第二種論證方式是證明程序正義具有某些不可被還原為物質利益的價值。耶魯大學學者馬修(Jerry L .Mashaw)采用“永遠把人類——無論你親自所為還是代表他人——當作目的, 而絕不僅僅當作手段來對待”這一康德式的話語,認為人的權利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得到尊重,這是人的基本價值。比如人作為主體需要得到的尊重,不應為了結果正義而被剝奪。因此,人有權平等地參與關乎自己利益的審判過程,并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得到人道的對待,這種參與本身就是有價值的,且這種價值不同于結果帶來的價值。基于此,馬修認為程序正義中的“平等”“可預測性”“透明性”“理性”“參與”“隱私”是人的基本需要。然而,馬修的論證訴諸于一般的人類直覺,這種論證方式帶著直覺主義的基本弱點。“工具主義”可以反駁:這些所謂的需要沒有真正的證據,無法證明所有人都贊同自己有這些需要,而在事實上,每個人對程序正義價值的判斷也都不盡相同。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個世界存在著依靠叢林法則生存,從不顧及程序正義的人;或存在專鉆程序正義的空子并以此謀生的人。
此外,在“本位主義”內部,也存在人們對程序正義的趨向是否具有“先天性”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僅在廣義層面使用“先天性”這一概念,指人們天生就具有對程序正義的趨向;與之相對的觀點則認為,對程序正義的趨向是依賴后天教育形成的。一些學者認為,程序正義的某些原則是先天(并非依賴后天教育)存在的,它們透過漫長的歷史而鑲嵌在人類的本性中,這些原則構成了程序正義的存在基礎。羅爾斯認為,為了保證社會的正義和良序,人類通過“反思平衡”,可以自然建立一些普遍的、先天的和確定不移的社會觀念。羅爾斯認為這些標準包括平等、自由等,是可以被人們普遍認可并共同遵循的。羅爾斯之所以認為基于某些先天的觀念可以建立一套可確定的秩序,是在為程序正義尋找一個相對客觀的基礎。但這種看法卻遭到了哈貝馬斯的批評,哈貝馬斯認為羅爾斯主張的自由、平等原則是基于其抽象的理論。他認為并沒有什么先天的原則,人們之所以選擇程序正義,是因為人類在漫長歷史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普遍的規則,程序正義正是歷史交往的產物。人們對程序正義的偏好,以及程序正義的原則都是在后天逐漸形成的,即所謂“通過對話來獲得規范的有效性要求”。可以看出,哈貝馬斯是用到一套類似“文化相對主義”的論證,實際上這一論證已經動搖了“本位主義”的基礎。“工具主義”或可借此聲明,既然程序正義沒有先天性,那它可能只是人們為了滿足某些需要而采用的普遍流行的某種產物,如此,程序正義自然也會隨著需要的改變被歷史拋棄。
可見,盡管“本位主義”采用了很多論證方式,但這些方式并不能算成功。一方面,各種論證都可以被還原為某種形式的“工具主義”;另一方面,其內部也在獨立價值的來源問題上存在爭議。然而,“本位主義”論證方式存在的問題不止于此,一個理論如果是有效的,不僅要在理論上證明其正確性,還要具備更強的現實解釋力。也就是說,“本位主義”理論需要解釋人們在現實中是如何使用程序正義來行事的,對此,“工具主義”表現的依然更加優異。在“工具主義”看來,我們選擇尊重“程序正義”,是因為它可以帶來現實利益,同時我們可以通過計算遵守或違反程序正義而得到的收益大小,來做出遵守或違反的決定。這種計算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這取決于個人對所處環境的判斷。盡管“本位主義”可以提出很多例外現象,但是“工具主義”可以用更多的現實案例回應。比如他們可以合理地假設,平等不過是爭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證據是人們總是在因不平等而遭受利益損失時,才會要求平等;一旦在不平等中獲益,就很少以不平等為由而放棄利益。此外,對程序正義的要求完全可以成為換取實際物質利益的籌碼,例如以程序不公平為理由,要求他人進行經濟賠償或拒絕承擔賠償責任的情形。最后,對于無法明確看到利益回報,卻依然選擇程序正義的行為,“工具主義”依然可以合理地假設,這可能是出于某種未知的原因,而這種原因最終指向的是物質利益。比如,人們選擇程序正義是為了彰顯自己較好的合作資質,或者希望在更長期的時間線上得到對方的回饋。
可以看出,法哲學界的論證局面對“本位主義”非常不利。盡管如此,理論學家大都相信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畢竟一個人人自利,只把程序作為利益工具的社會不是我們愿意接受的。綜上,為了研究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方式,“本位主義”必須完成兩個任務:(1)證明即使排除利益回報的可能,人們依然會趨向選擇“程序正義”,同時為了排除這種趨向僅僅是后天形成的心理慣性,還必須證明該趨向具備一定的先天性,而并非完全由后天形成;(2)明確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作用機制,即如何不依賴于人們趨利避害的本能而發揮作用。
二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及其先天性——來自發展心理學的證據
要證明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存在及其先天性,現實中顯然不存在這樣的條件,畢竟現實中的選擇難免被各種因素所干擾,但發展心理學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方案。發展心理學主要致力于在新生兒到成年人的分階段研究中,揭示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情境對其心理及行為傾向變化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發展心理學通過設計縱向實驗,經過一定的時間跨度去采集人類某些行為傾向的變化,從而分析造成該變化的核心影響因素。例如,在嬰幼兒到青少年的時間跨度上,對人類程序公平性的感知變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發展心理學的研究發現:(1)在程序正義是工具還是本能需要的問題上,人類嬰兒已經具備了識別不公平程序的能力,并且具有選擇公平程序的趨向,即公平是一種本能需要,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了動物實驗的佐證,即選擇公平是高等動物的共同趨向;(2)在程序正義到底是先天還是后天的問題上,實驗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齡更大的兒童逐漸具備了識別復雜程序的能力,對程序公平呈現出更明顯的趨向。
(一)追逐程序正義是人的本能性需要:來自人類嬰幼兒和動物實驗的證據
嬰幼兒實驗是心理學中用于研究人類本能的重要方法,由于嬰幼兒不具備復雜的邏輯思維能力,而且尚未接受系統的社會教育,其行為往往是出于本能的,因此可以用來識別人類先天具備或者早期發育中的行為趨向。也就是說,參與實驗的嬰幼兒年齡越小,得出的結論就越能反映人類的本能傾向。此外,在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的研究中,心理學家認為,如果發現人類嬰幼兒的選擇是基于程序的公平與否,例如選擇程序公平下產生的相對較小的收益,則可以說明程序正義具有獨立的價值,即人類并非只是把程序作為獲取更好結果的工具,而是先天性的對程序正義具有一定的趨向。心理學研究發現,人類嬰幼兒先天具備識別程序公平與否的能力,同時可以對一些簡單的程序不公平事件做出拒絕性的反應。當然,由于嬰幼兒無法使用明確的語言表達其對程序公平喜歡或者討厭的能力,心理學家一般通過觀察嬰幼兒對公平或不公平分配程序的注視時間以及后續行為,從內隱認知層面推斷出他們對不公平分配程序的不滿和對公平分配程序的喜愛。
Sloane等人發現即使是19個月的幼兒也具有公平分配資源的期望,具體而言,如果兩個幼兒都完成了實驗者布置的任務,他們就會期待得到同樣的獎勵,但如果他們中只有一個完成了任務,而另一個只是在玩耍,那他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期待,說明此時的幼兒已經可以初步分辨出結果不公平的來源,即分配過程的不公平。此外,Surian 和 Margoni 發現20個月大的幼兒已然能辨別幫助程序中的一致和不一致。在實驗中,研究人員向20個月大的幼兒展示了一個主角對另外兩個接受者提供幫助的視頻。一種情況下,主角不偏不倚地同時幫助這兩個接受者;另一種情況下,主角有偏見地立即幫助其中一個接受者,而另一個接受者則等待較長時間后才得到幫助。盡管在這兩種場景中,每個接受者最終都得到了幫助,但結果卻發現,相比無偏見的幫助場景,幼兒對有偏見的幫助場景觀看時間更長。如果把年齡擴大到三歲,則會有更加明顯的實驗結果,Baumard發現在一個簡單的故事情境中,三歲的幼兒便可以根據每個人在任務里的貢獻量來分配獎勵。更重要的是,Kenward 和 Dahl發現,在資源分配游戲中,當三歲左右的幼兒不作為資源分配的受益者時,他們會更偏愛于與將資源在接受者之間等分。
心理學家通常會利用動物實驗來探索人類更為原始的本能,而來自動物實驗的結論也可佐證程序正義趨向的先天性。著名的動物心理學家Waal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兩只僧帽猴可以用鵝卵石向實驗者交換食物。一開始,兩只猴子得到的是同樣的食物(黃瓜),此時,兩只猴子交換食物的頻率基本相同。隨后,實驗者改變了規則,給一只猴子更美味的葡萄,另一只仍然是黃瓜,這時被給予黃瓜的猴子便不愿再次交換食物,甚至表現出憤怒的情緒,將鵝卵石和黃瓜拋出籠子。倭黑猩猩被認為是同人類親緣關系最近的物種之一,實驗發現它們同樣具有很強的公平意識,當一只倭黑猩猩被給予了好吃的食物后,它并不會馬上吃掉食物,而是不斷地給實驗者和同伴打手勢,直到實驗者給予同伴和它一樣食物時,它才愿意收下食物。甚至在非靈長類的動物中也發現了類似現象,灰鸚鵡在同伴獲得更多花椰菜時表示抗議,狗在執行任務后如果沒有得到與同伴一樣的獎賞則會拒絕執行后續指令。這一系列的動物實驗可以說明,追求公平在高等生物中是普遍存在的,并與平等、分享原則一起形成動物正義的行為簇。
上述嬰幼兒實驗和動物實驗主要說明了以下兩個問題,(1)“工具主義”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將程序正義作為獲得利益的工具,這在事實層面上存在漏洞。因為即使在不需要考慮結果收益,或者在當事者們擁有一致結果的情況下,嬰幼兒也會傾向于選擇程序公平。同時,嬰幼兒實驗還排除了“工具主義”的“長期利益”假設,即人們放棄利益選擇公平是為了得到長期利益。因為對嬰幼兒來說,選擇長期利益的認知能力尚未成熟。(2)上述實驗結果證實了人類對正義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先天性,因為無論是在程序還是結果上,嬰幼兒都更偏愛公平的選項,這佐證了羅爾斯的假設。
(二)程序正義趨向性伴隨人類認知發展逐步成熟
嬰幼兒對程序正義存在先天的偏好,是否意味著哈貝馬斯的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并非如此。哈貝馬斯認為程序正義的標準是在人類的社會交往中逐漸形成的。在他看來,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開展交往活動,在交往過程中,人們會逐漸形成程序正義的原則,同時,他將促進交往順利進行的認知能力,稱為當事人的“交往資質”。心理學中將不同年齡段孩子作為當事者的實驗,也可證實哈貝馬斯的這一假設。不同年齡段的實驗表明,人們使用程序正義的能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認知能力的提高不斷成熟,并逐漸發展出辨別復雜程序公平性的能力。人類對程序正義趨向的先天性并不是程序正義的充分條件,嬰幼兒表現出的對程序公平性的趨向也并不能說明人類對程序正義的偏好完全是先天的,畢竟程序正義的實現包含著一系列的規則,而對于這些規則的理解需要一定的認知能力。
研究者發現5~8歲的兒童可以處理較為復雜的程序正義問題。Grocke 等人使用均分和沒有均分的兩種轉盤,考察了5歲兒童對程序公平的認知水平,結果發現,有一半兒童會選擇均分的轉盤來分配多余的資源。同時,如果不均等的分配結果是由均分的轉盤做出的,他們便會普遍接受這樣的分配;相反,如果不均等的分配結果是由沒有均分的轉盤導致時,他們大多會拒絕這樣的結果。此外,研究者首先讓一名兒童作為分配者給兩名接受者分配物品,這個時候兒童一般會選擇公平分配,但在分配結束后實驗者多給出一個物品,這時他可以選擇扔掉物品或是進行不公平的分配。結果發現,6~8歲的兒童寧愿扔掉物品也不愿進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當兒童自己是接受者之一時,也依然會選擇扔掉物品。
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能夠發展出利用程序公平性進行其他判斷的能力。Fry和Corfifld研究了10歲左右兒童如何對權威進行評判,發現兒童在對權威人物進行評判時,程序公平起著更重要的作用。Fagan 和Tyler發現,當10~16歲兒童認為法律過于嚴酷或者執行者不能公平執法時,他們會降低對法律的合理性評價,并對法律報以嘲諷的態度。此外,Murphy還發現青少年更愿意與公平執法的警察展開交往。
除了從上述不同實驗中對比不同年齡段孩子對程序正義的判斷,也有研究在同一實驗中考察了兒童和青少年面對程序公平時的行為演變。Shaw 和Olson研究了5~8歲兒童如何使用公平程序或者不公平程序來分配獎品。結果表明,在所有年齡段的兒童中,選擇公平程序的人數均多于選擇不公平程序的人數,且7~8歲兒童使用公平程序的人數遠多于5~6歲兒童。如果讓兒童在扔掉物品和不公平程序之間進行選擇,相比年齡小的兒童,年長兒童則更多選擇寧愿扔掉獎品,也不選擇不公平程序。Damon利用4~8歲兒童在生活中遇到的兩難情境來對比他們對公平的認知,結果發現,4~5歲兒童的只能把個頭大小作為公平與否的標準;5~6歲兒童開始把公平和平等聯系在一起;6~7歲兒童開始按照貢獻來評價公平性;8歲兒童開始考慮到相對復雜的個人需要。Mills 和Grant的研究還發現,6~8歲的兒童開始質疑成年人的分配決定,他們能意識到成年人的選擇可能是不公平的,從而開始選擇用公平的程序來進行資源分配,而不是讓成年人直接分配。有關程序公平判斷的發展過程,Damon提出了公平的認知發展階段論模型,他認為兒童的公平推理水平與其數學和物理問題的推理水平高度相關,大多數兒童在這兩個領域(公平領域和認知發展領域)的發展體現出緊密同步的特點。
綜上,無論是嬰幼兒還是青少年,他們都具有追求程序正義的自然傾向,即使這種傾向有可能帶來物質利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自然傾向并不是追求程序公平的決定性原因,因為理解程序需要一系列復雜的理性加工,因此,人類追求程序正義的傾向雖然具有先天性但并非恒定的,而是會隨著認知能力的成熟逐步發展。
三認知神經的證據:程序正義獨立價值發揮作用的認知神經基礎
上述實驗即便證明了程序公平具備一定的獨立價值,但“工具主義”依然可以反駁:這并不能為解決現實問題帶來更多的幫助。因為我們不明白其獨立價值發揮作用的機制,因此即使它在理論上存在,在現實中依然是無意義的。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主要在于行為實驗揭示的結果依然存在于現象層面,而現象背后的內在機制對我們來說仍舊是一個“黑箱”,因此要想真正地解決問題,就必須打開黑箱,對其內在機制進行探索。
如果承認一切意識現象都依賴于物理性的載體,那么人類加工程序公平和結果時的大腦活動,無疑能直接證明程序公平是否具有相對于結果的獨立性。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術是20世紀90年代產生的,利用高能磁場對人類大腦活動進行觀測的技術,又被稱為“科學的讀心術”。具體而言,人體血液中含有氧合血紅蛋白和脫氧血紅蛋白,脫氧血紅蛋白具有比氧合血紅蛋白T2*短的特性,再者脫氧血紅蛋白較強的順磁性會破壞局部主磁場的均勻性,也使得局部腦組織的T2*縮短,這兩種效應的疊加結果便是降低局部磁共振信號強度。當腦區活動增強時,該區域脫氧血紅蛋白的相對含量降低,磁共振信號強度隨之增強,如此便獲得了相應腦區的激活圖像。2000年以后,隨著fMRI技術的廣泛使用,科學家開始用其研究人腦加工程序公平事件的神經機制,結果發現,人們加工程序公平事件的腦區和加工結果公平的腦區不盡相同,兩種公平的作用機制相互聯系,卻不相互隸屬。進一步的實驗則證明,人們選擇程序公平是因為其本身就具有價值,而不是它能帶來更高的物質價值。
(一)程序正義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的作用模式在神經層面的分離
Dulebohn在2009年首次使用fMRI技術探索了個體加工程序和結果的腦機制。在實驗中,兩位參與者被要求同時完成一道數學試卷,成績較好的一人會在隨后的分錢實驗中成為提議者(proposer),成績較差的一人則作為回應者(responder),只能被動選擇是否接受提議者的分配。然后,兩位參與者將通過顯示屏得知自己的試卷批改過程是否公平。例如,參與者通過顯示屏得知自己的試卷中只有一道題被批改,且其剛好答錯,而剩余題目都未參與計分,因此被安排為回應者角色,這種成績評定過程便是程序不公平的。最后,研究者以評定過程顯示屏和分配方案顯示屏,分別作為反應大腦加工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的記錄屏。腦成像的結果發現,在結果不公時,背外側前額葉、前扣帶皮層和前腦島激活更強。這些腦區也經常出現在最后通牒任務的分配結果不公時,主要負責情緒加工。而當程序不公平時,腹外側前額葉和顳上溝激活更強,這兩個腦區則是參與執行控制和規則反思的腦區,反映了理性加工。這就可以合理地推論,人們對結果公平與否的判斷更多基于一種直覺性的情緒反應,而對程序公平與否的判斷則是邏輯思維這一高級認知活動的結果。既然人們對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的判斷,在神經機制層面的表征并非不處于相似的腦區,那么二者依據的判斷標準自然也不盡相同。
2014年, Feng匯總了20篇有關公平行為的神經基礎研究,發現有兩個不同的加工系統參與了公平行為的策略決定:一個是快速的自動的直覺系統(intuitive system),包括前腦島、杏仁核和腹內側前額葉皮層,這一系統可以快速識別和評估違反公平準則的行為;另一個是與認知控制有關的深思熟慮系統(deliberate system),包括背側前扣帶回、背外側前額葉皮層、腹外側前額葉皮層和背內側前額葉皮層,這一系統則會整合追求公平準則和獲取自身利益之間的沖突,從而回應直覺系統的反應,并最終做出更為靈活的決策。也就是說,不公平的規則會被直覺系統直接識別出來,但是直覺系統并不負責選擇接受或者拒絕這樣的規則,最后的決策行為還需通過深思熟慮系統,對不公平規則引起的心理不適和可能的利益得失進行綜合評估后作出。
這兩個研究針對的都是程序正義發揮作用的機制,采用的兩種方法都證明了人腦對程序公平的加工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過程,有其專門負責的神經系統,而不是利益權衡的副產品。
(二)人類選擇程序正義的內在神經機制
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在絕大多數時候是聯系在一起的,很難單獨去探索各自的作用,因此二者的功能總是糾纏不清。為了說明在無關利益的情況下,人們為什么還愿意選擇公平的程序,心理學家設計了巧妙的實驗,排除了結果的影響,并分離出了程序公平的作用。
首先,心理學家發現,不公平的程序激活了消極情緒,同時會引起認知沖突。一般認為,前腦島的激活表征了個體的消極情緒狀態,尤其是憤怒和厭惡情緒(大量研究發現前腦島與疼痛、壓力、饑餓、口渴、憤怒和反感等負性情緒狀態有關)。2003年,Sanfey等人在《Science》上的一篇研究,證明了不公平的程序和前腦島的關系。在實驗中,2個參與者需要分配一筆固定數目的錢,其中1名參與者作為提議者向另外1個回應者提出如何分配這筆錢,回應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提議者的分配方案。若接受,就按提議者的方案分配;若拒絕,則2人都得不到錢。按照“經濟人”假設,回應者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應該接受任何提議,因為即便少得錢也比不得錢更好。如果提議者預測回應者會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他應該選擇分配盡可能少的錢給回應者,從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來自不同國家、采用不同分配金額和不同實驗設計的行為學實驗一致證實了:人們并非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相關的腦成像結果表明,回應者前腦島的激活強度在收到他人不公平分配時顯著大于其收到公平分配時,在其選擇拒絕時顯著大于選擇接受時。此外,隨著分配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回應者前腦島的激活程度也隨之增強,同時提高了其對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這說明,回應者之所以放棄利益也要維護公平,是因為不公平行為本身就會讓回應者產生了強烈的消極情緒,這種情緒甚至可以壓倒獲得利益的理性計算。Civai等人于2012年發表的研究擴展了這一結論,他們進一步發現,回應者不但在得到更少的錢時會激活前腦島,在得到更多的錢時也會激活該腦區。也就是說,即使回應者得到了比提議者更多的錢,依然會產生厭惡情緒,這說明,人們厭惡不公平,不僅是因為遭受了利益的損失,還有對不公平(包括優勢不公平和劣勢不公平)本身的厭惡。
與之相反,公平的程序則會激活人腦的獎賞機制。人們喜歡物質利益,也喜歡公平的程序,在大多數時候,兩種喜歡是聯動的,因此我們很難識別人們對公平程序的喜愛是出于對程序本身的偏向,還是把其當作追求物質利益的工具。為此,Tabibnia在2008年設計了一個實驗,實驗者在實驗中控制了總的收益量,也就是說,無論程序是否公平,實驗參與者最終獲得的收益量都是一樣的。結果發現,相比面對不公平的程序,參與者在面對公平程序時,報告了更高的幸福感,而且公平程序激活了與獎賞有關的腦區,如腹內側前額葉、腹側紋狀體和杏仁核。的一系列公平行為神經機制的研究也表明,當回應者面對提議者給出的公平提議時,雙側的腹內側前額葉和后側腦島、左側后扣帶、楔前葉以及右側顳下回有顯著激活,這些腦區也都是與積極情緒相關。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偏愛公平是因為公平選項本身對于人們來說是一種獎勵,進而激活了與獎賞有關的腦區。
事實上,心理學實驗已經證明了“工具主義”的“經濟人”假設存在嚴重問題,人們不但追求物質利益這一“外在利益”,還會追求程序正義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而且人類對程序正義“內在價值”的追求機制是一種生物本能。如此“本位主義”就獲得了同“工具主義”同樣效力的論證基礎。
四質疑和展望
2000年以來,用心理學解決哲學問題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方法,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甚至在歐美,“自然主義”或“唯物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顯學”。有學者指出“就目下的情況而言,也沒有什么別的不同體系性的本體論立場可與唯物論爭鋒。作為其結果,哲學與科學中的那些最具典型性的理論建樹,都以一種或隱或顯的方式受到唯物論所推出的諸種概念思想的制約。”。此外,學科交叉的方法在近年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比如,耶魯大學開創性的“偽善”實驗證明了道德偽善的存在,而“鏡像神經元”的發現揭示了同情心的生理基礎,這都證明了心理學和哲學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這并不代表心理學和哲學交叉研究的方法是沒有問題的,甚至可以說,這種方法取得的成果和它的爭議一樣多。下面將針對本研究可能引起的內部和外部爭議,進一步探討未來哲學和心理學交叉研究的可能方向。
(一)心理學論證的問題和有限性
本研究使用了學科交叉的方法來研究程序正義問題,但該方法本身就充滿爭議,其爭議的原因不僅在于這種方法本身,還在于這類研究的不成熟。然而,隨著近些年實驗哲學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質疑的聲音也在逐漸轉化為建設的聲音,即使是羅爾斯也在1995年就承認“必須以道德心理學去長久地支持一個合乎理性的正義之政治社會”,不過質疑依然需要被嚴肅對待。
第一種質疑是針對用心理學解決哲學問題這一方法本身的。心理學和哲學的交叉,或者說“實驗哲學”從一誕生就飽受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場哲學革命”,反對者則將其斥為“一個尷尬的概念”。這里簡單列舉幾種質疑:首先,心理學的論證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說心理學所提供的證據只是對事實的描述,無法為我們是否支持“本位主義”的觀點提供辯護,即便“本位主義”被證明是正確的,卻也是無用的;其次,這種方法預設了“基因決定論”或者“生物決定論”的觀點,忽略了人類社會歷史對人的塑造作用,而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一個具有主體意志的人會被消解掉,從而變成一個完全由物理規律支配的“哲學僵尸”(philosophical zombie);最后,人類復雜的行為和情感能否被還原為客觀的生理現象,這一點是存疑的。比如,以往的心理學研究認為某些腦區的激活代表著人的獎賞機制被激活,但此時人可能根本沒有感受到快樂。當然,對于這種方法的質疑遠不止這些,而對這一質疑的回答超出了作者的能力范圍。實際上,這個問題已被眾多國內外學者深入探討過。為了不偏離研究主題,本研究的目的只是在心理學的框架下,為程序正義獨立價值提供某些事實性的證據。
第二種質疑存在于心理學內部,即目前的證據是否構成對“本位主義”的充分證明。首先,對嬰幼兒的研究證據能否充分證明程序正義趨向的先天性,畢竟嬰幼兒只有簡單的行為指標可反應程序正義的趨向,而程序正義趨向的復雜性是隨著人類逐漸成長并發展出來的。人類成長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這就不能排除程序正義是一個社會“教化”的結果。其次,即便程序正義的趨向具有先天性,那這種先天性能否在后天被充分表達?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雖然人類對程序正義的趨向具有先天性,但在人類的理性充分發展后,先天性的作用會逐漸讓位于精密的理性計算。最后,認知科學和fMRI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是否成熟到能夠足以確定實驗結果的正確性?畢竟除了腦島,雙側的腹內側前額葉、左側后扣帶、楔前葉以及右側顳下回是否能作為表征獎賞機制的特異性腦區,在心理學內部還有爭議。而且當前研究只能證明程序正義會產生“內在獎勵”——但如何轉化為外在的程序正義趨向并不清楚,也就是說證據鏈條并不完整。
上述質疑可以進行如下回應,首先,先天性只能說明人的一種本能趨向,并不否認后天的作用,這種先天性只是讓程序正義的趨向在人類發展中成為一種更具優勢的發展方向。其次,人的行為趨向確實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結果,至于二者所占的比例如何尚未可知。不過,研究發現人類嬰幼兒時期的行為反映是一種更本能的行為傾向,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本能雖然會受到理性的制約,但也會成為人們行為的底色。這至少說明嬰幼兒對程序正義的趨向絕對不會被后天教化完全取代。最后,目前的研究已經構成了行為和神經反映的互證。在行為上,人們會表現出對程序正義本身的趨向,在fMRI的測量下,可以發現伴隨這些行為的是人腦“獎賞機制”的激活。然而當前的證據僅限于此,人腦的獎賞系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程序正義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方式對這一系統的激活也將有所差異。
(二)未來發展方向
程序正義是一個古老又現代的問題,羅爾斯、哈貝馬斯和哈耶克等也曾圍繞這一問題開展過針鋒相對的直接討論,長期的爭論證明了該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同時,程序正義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不能被無限制的爭論下去,其內在作用機制的模糊,將導致實踐過程中各種各樣的自相矛盾,甚至會加重糾紛。然而,程序正義涉及哲學、法學和心理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因此,未來對于程序正義問題的研究需要整合各學科的力量。
首先,需要完成研究框架的統一和研究問題的明確。盡管心理學界對程序正義的關注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也證明了程序正義在社會治理上的促進作用。然而遺憾的是,程序正義的作用機制、程序正義的內在標準這些關鍵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離真正掌握程序正義的規律還有很大的距離。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其中一個原因是,目前心理學的研究仍然缺乏統一的研究框架,導致目前的研究很分散,難以聚焦核心問題。此外,心理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應用層面,由于沒有合適的理論指導,心理學研究者無法設計出更為精細的實驗,以明確程序正義更為基礎的心理機制。上述兩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哲學和心理學的深度合作。哲學家擅長提出問題,并通過邏輯推論篩選出合適的理論方案,但很難驗證該方案的可靠性,而構建用于驗證理論難題的可行性方案,正是心理學家所擅長的。
哲學和心理學的深度合作需要一套可以兼容的問題框架,盡管程序正義問題在哲學界和心理學界分別具有相對固定的研究框架,但是兩套研究框架卻存在較大差異,關注焦點也不盡相同,如此一來便很難合力而為。因此,為了便于開展共同研究,至少要明確以下幾個問題:到底什么是程序正義?判斷程序正義與否的標準是什么?程序正義的目的是什么?程序正義與一般意義上的平等或者結果正義有何異同?
其次,未來研究要盡快從“單數的質性研究”轉入“復數的量化研究”。程序性正義是一個龐大的話題,即使是羅爾斯的觀點,也曾被哈貝馬斯指責是實質正義而非程序正義,而后來的學者也都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各自對程序正義的定義。心理學有關程序正義的定義也是五花八門,這種定義的混亂給后續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阻礙。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很多研究希望把“程序正義”作為一個單數名詞,并探索其發揮作用的機制,這種希望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因為哲學的學科特點就是尋找問題的共性。但是心理學的研究發現,人們對程序正義的定義是存在分歧的,而且程序正義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機制也不相同。比如同樣是在程序公平中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有的人選擇質疑程序的可靠性,有的人坦然接受了結果,這二者心理機制肯定是不一樣的,需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研究者需要將“程序正義”視為一個問題的集合,而不再把其視為一個單數名詞。在不同的情境中,針對不同的人,程序正義的作用機制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只能進行精確且具體的研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把研究陷入瑣碎,而是在不同位面開展研究的同時,盡快找出問題的共性。目前心理學界熱門的計算建模方法可以縮短這個進程。計算建模的方法可以將復雜的影響因素放在同一個心理模型中進行研究,并通過行為實驗和定量分析篩選出比較核心的因素,以確定行為背后的最為核心的加工機制。
Independent Valu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ts Cognitive Neural Basis
WANG Si-min, ZHANG Pei
Abstract: Procedural justice, a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presents two main camps in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procedural instrumentalism” and “proceduralism”.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camps lies in: whether procedural justice itself has independent value that can be pursued in addition to pursuing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material interes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independent value of procedural justi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has found that humans have an innate tendency towards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is tendency evolves and gradually matures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and cognitive leve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has revealed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independent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e research on functional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has found that (1) the independent value and instrumental value of human brain representation procedure differ in brain areas; (2) the procedure itself can stimulate the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of the human brain, which explains the existence of? independent value of procedur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ate tendencies and cognitive nerves.
Keywords: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ism; proceduralism;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責任編輯:龔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