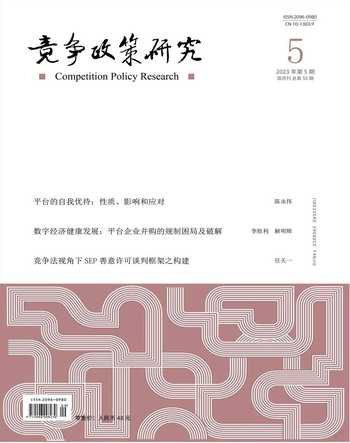Google、Facebook等公司:反壟斷法視域下的數據及算法力量
【德】托爾斯滕·科貝爾 丁庭威
摘要:在過去的30年里,互聯網的成功造就了眾多新的服務,并大幅增加了消費者福利,也為企業創造了許多新的機遇。然而,種種擔憂亦接踵而至,即一些大型數字公司及其使用的算法可能獲得過多的影響力。全球各國通過各種法律來解決這些問題。通過反壟斷法和監管法對潛在的競爭作出回應。在德國,立法者曾兩次(2017年和2021年)修訂《反限制競爭法》(GWB),以更好地涵蓋數字市場和商業模式。對此,當時的重點是改進對權力濫用的監督。在歐盟,立法者選擇通過《數字市場法》(DMA)對數字守門人進行監管,該法案自2023年5月2日起生效,并提列了眾多禁止條款。本文將德國的法規(特別是《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與《數字市場法》進行比較,并批判性地對這兩部法規進行評估。
關鍵詞:互聯網;算法;數字巨頭;守門人;競爭法;德國《反限制競爭法》;歐盟《數字市場法》
一、研究緣起
若看到諸如“算法的力量”此類講座標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想到幾家大型互聯網公司,例如Google(或Alphabet)、Amazon、Facebook(或Meta)、Apple和Microsoft,簡稱“GAFAM”。市場力量集中在商業模式中并不鮮見。早在19世紀80年代,美國就有人擔心鐵路和石油行業的市場力量集中,例如在重組標準石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時,就可能導致經濟和政治上無法控制的壟斷。為此,美國在1890年出臺了世界上第一部現代反壟斷法案——《謝爾曼法》,該法案至今仍存在,禁止卡特爾和反競爭手段的壟斷。如今,幾乎每個反壟斷法案中都可以找到規制卡特爾和濫用市場力量的規定,在過去的130年里,它們在保障市場良性競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22年6月,鑒于汽油和柴油價格高企,德國聯邦經濟與氣候保護部(BMWK)出臺了新的規定,企業拆分將不基于濫用行為并且將通過針對壟斷行為衍生利益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礦物油市場再次成為德國反壟斷辯論的焦點。
在數字經濟領域,市場力量集中也并非是新鮮事。即使互聯網只有30年的歷史,人們對Microsoft的市場霸權依然感到擔憂。在20世紀90年代末,人們擔心微軟會利用其在操作系統市場中的力量來主導其他市場,如網絡瀏覽器、媒體播放器和流媒體,并最終主導整個互聯網。而在2000年1月10日,媒體集團時代華納(Time Warner)和互聯網接入提供商美國在線(AOL)宣布其合并計劃時,有人便擔心這個新集團將可能掌控整個互聯網市場乃至重要的輿論市場。然而,現在我們知道這些擔憂都被證明是空穴來風。雖然微軟仍然是第二大市值的數字公司(僅次于蘋果)。但如今主導互聯網的是其他公司,在媒體播放器和流媒體領域,微軟更是無足輕重。具有話語權的其他公司是YouTube、Netflix或Spotify。而時代華納和美國在線的合并計劃也被證明是失敗的。早在2002年,時代華納就因此遭受了大約450億美元的虧損。美國在線在2009年被拆分,并在2015年以44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美國在線并沒有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成為互聯網壟斷者,而是同樣陷入了一種無足輕重的地位。
如今,人們的擔憂主要集中在Google、Amazon、Facebook以及Apple這幾家公司身上,有時也包括Microsoft,簡稱為GAFA或GAFAM,認為它們可能會主宰數字經濟、互聯網以及媒體領域。Google成立于1997年,其可能利用在搜索引擎市場的領先地位,以此作為籌碼來征服其他市場,如地圖市場(Google Maps)、視頻內容市場(YouTube)或比價市場(Google Shopping)。這已經引發了人們十多年的激烈辯論。此外,Google(或Alphabet)還掌握著安卓系統,它是目前最為成功的移動操作系統。Amazon成立于1994年,其從原先的互聯網書店已經成長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并且通過亞馬遜商城(Amazon Marketplace)運營著面向第三方賣家的最大銷售門戶之一,同時為其制定規則。Facebook(或Meta)成立于2004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網絡平臺,也是這個尊貴俱樂部(GAFAM)中最年輕的成員。除了對Facebook經濟權力集中的擔憂,人們還擔心其潛在的“媒體權力”。自從Facebook并購了WhatsApp和Instagram這兩個更為重要的社交平臺后,這一恐懼和隱憂便更為突出了。
就像在Microsoft案例中一樣,這些服務受到強大的網絡效應和規模效應的影響,即“自我強化效應”和其他因素,而這些效應尤其對數字平臺具有重要意義。詳細探討這一點已經超出了本講座的范圍。但是,德國的GWB(《反限制競爭法》)在第18條第3a款已列舉了(包括但不限于)適用于數字市場的相關因素。在此,僅舉兩個例子:第一,網絡效應與規模優勢(GWB第18條第3a款第1項和第3項);第二,獲得競爭性相關數據(GWB第18條第3款第3項和18條第3a款第4項)。
無論是操作系統、社交網絡還是即時通信服務,擁有越多的訂閱者并能與他們交換信息,就能運作得越好。另一方面,隨著用戶數量的增加,還會越受廣告客戶的青睞,這一進程被稱為“網絡效應”。任何曾考慮從WhatsApp轉移到其他服務的人就知道我們在談論什么。這使得新公司很難立足于市場。它們不僅要為硬件、服務器和程序進行大量的投資,而且還需要在用戶市場(如新的社交網絡)和廣告市場都贏得足夠數量的客戶,并最終說服他們從已經建立的“每個人”都在使用的服務中切換過來。然而,這并非不可能。Google曾經并非始終是領先的搜索引擎,Facebook過去也并非一直占據社交網絡的頭把交椅。兩者都“推翻(entthront)”了原先占主導地位的競爭對手。Microsoft在2011年并購Skype之后,曾短期占有90%以上的即時通信市場份額。然而現在,WhatsApp或Zoom等其他服務已主導了市場,雖然它們都具有網絡效應,但它們之所以成功,只是因為它們更好。
近些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GAFAM公司擁有的所謂“數據權力”。數據在任何行業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Google和Facebook這類互聯網服務公司來說尤為如此,因為它們向用戶免費提供服務,并通過廣告的多邊業務模式來融資。用戶數據被用來優化產品以及有針對性地、進而更成功地投放廣告。易言之,用戶數據是這些公司算法能夠良好運作的重要原材料,最終形成能夠控制產品和廣告的人工智能(AI)。但與其他材料或資金不同,數據是“非競爭性的(nicht rival)”,因為金錢花掉就沒有了,石油也會因燃燒或加工而消耗殆盡。換言之,金錢和石油只能被一方或另一方使用,這些消費品是具有“競爭性”的。但對于數據而言,情況往往截然不同。因為大多數據可以多次傳輸給不同的公司,所有公司可以同時或相繼使用這些數據。為了在競爭中保持抗衡能力,也并不必須擁有像Google和Facebook那樣多或甚至相同的數據。但肯定需要“充足(genug)”的數據來訓練人工智能(AI)。在此,我們談論的是“最低最佳的數據量(mindestoptimale Datenmenge)”的概念。而“數據網絡效應(Datennetzwerk effekte)”是否真的存在,還存有疑問。
鑒于這些因素和GAFAM的龐大規模,如今人們仍然擔心這些公司已經獲得了無法撼動的競爭優勢,而小型企業正變得落后,尤其是德國和歐洲的公司。例如,因為它們缺乏數據而難以跟上,或者因為GAFAM會以自身為優先。這種隱憂體現在德國《反限制競爭法》新的第19a條以及歐盟《數字市場法》(DMA)之中。還有人擔心,創新的初創企業將因GAFAM并購而被“吞噬(geschluckt)”,進而限制技術進步以及產品多樣性的發展。最終,人們普遍擔心作為市場參與者的我們無論是在資金方面抑或是數據方面都將被剝削。
二、反壟斷法
無論如何,一旦存在公司“過于龐大(zu gro?)”的危險且不再受到市場和競爭的充分控制時,反壟斷法便會像1890年那樣發揮作用。由于本講座的聽眾并非都是反壟斷法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們先簡要介紹反壟斷法能夠且打算做什么,以及它不能和不打算做什么。
反壟斷法旨在保護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作為一種有效互動的市場力量,有效競爭確保了供應受到需求的控制,有限的資源能夠在大眾經濟中得到最明智的利用。歷史告訴我們,市場參與者(包括私人和企業)由市場激活的“群體智慧(Schwarmintelligenz)”在實現這種協調方面遠比通常以假定知識為基礎的國家計劃更為出色。市場是一種“基層民主(basisdemokratischer)”的調控機制。同時,相對于大公司乃至(更大的)國家,競爭也是保障自由的一種手段。
當競爭發揮作用時,它會促進低價、產品多樣性以及創新。簡言之,它能提升消費者福利。有效的競爭會不斷迫使公司降低價格、改進產品和流程,否則它們將失去市場份額,甚至可能從市場上消失。正如自然界“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基本法則一樣。創新和高效的公司不斷成長,而其他缺乏創新和效率的公司則“倒閉(pleitegehen)”,這正是市場運作(Funktionieren)的體現,而非市場失靈。
為了確保競爭的運作和有效性,反壟斷法(Kartellrecht)顧名思義首先禁止的便是卡特爾(Kartelle),卡特爾即企業之間旨在限制競爭或施加影響的行為約定,如固定價格協議(Preisabsprachen)。
其次,反壟斷法嘗試防止由于違背競爭的企業并購(Unternehmenszusammenschlüsse)而導致的權力集中(Machtkonzentrationen)。這便是并購管制所關注的主題。例如,若某家GAFAM公司感覺受到一家創新初創公司的威脅,為了“擺脫”該競爭對手而干脆將其“吞并(schluckt)”,該行為可能會被禁止。當然,細節決定成敗,這樣的并購也有可能促進創新,并且也很可能是初創企業夢寐以求的。一家只有幾年歷史的初創企業,誰不夢想著能以數億甚至數十億的價格被收購呢,就如當初的WhatsApp一樣。這種前景可以成為創新和對創新投資的強大激勵,進而推動進步。因此,在實踐中并購(Fusionen)很少被禁止,這是合理的。
最后,這讓我們看到了該議題的本質,反壟斷法禁止濫用權力是為了防止占據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不受競爭的充分規制,從而濫用權力阻礙競爭對手或剝削市場伙伴。但在這里,我們必須做出仔細的區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競爭中取得成功會導致有些公司變得更大而其他公司失去市場份額。因此,反壟斷法并不禁止通過競爭獲得的市場力量。如若不然則意味著對成功的懲罰。一家公司之所以能夠取得主導地位,僅僅是因為它比競爭對手更具創新性、更有效率、更為“優秀”。在此情形下,市場力量本身甚至壟斷都是被允許的。因此,要解散這樣的公司,即使它沒有濫用市場力量,正如人們一再要求對GAFAM公司以及現在德國聯邦經濟與氣候保護部(BMWK)對礦物油公司的要求一樣,這是有悖于反壟斷法的一種錯誤做法(kartellrechtsfremder Irrweg)。美國和英國曾嘗試過這樣的拆分,但幾乎從未取得持久的成功。反壟斷法不能也不應與市場背道而馳,而只能為市場上的自由競爭設置“護欄(Leitplanken)”。因此,更有效的做法是,依據反壟斷法密切關注那些不再受到競爭充分規制的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公司,以識別、防止并懲罰這些公司濫用市場力量。只有在這些措施無效的情況下,才可以根據現行法律,在反壟斷法框架下對具有重復濫用行為的“嚴重違法者(kartellrechtlichen Intensivt?tern)”進行拆分。
三、 “務實主義的反壟斷法”和數字市場
反壟斷法是以一般條款為基礎的。這適用于禁止卡特爾(《反限制競爭法》第1條,《歐盟運行條約》第101條),也適用于禁止濫用行為(《反限制競爭法》第19和20條,《歐盟運行條約》第102條)。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針對技術現狀的特殊標準很快就會被實踐所取代。對數字市場來說,一般條款尤其適用,因為數字市場是非常動態的,因此,如果有一部專門的“數字反壟斷法(Digital-Kartellrecht)”很快就會變得過時并需要修訂。相反,反壟斷機構和法院可以根據實踐的發展靈活地適用一般條款。
然而,反壟斷法有關濫用權力的禁止條款存在一個“不健全之處(Pferdefu?)”:由反壟斷機構或法院執行必須以濫用權力行為已經發生為前提。易言之,禁令只能在事后適用。所以有觀點認為,現行反壟斷法做得“太少,太遲”,并且無法在數字經濟中跟上時代的步伐。當反壟斷法最終介入時,競爭已經陷入了困境,例如在涉及GAFAM公司的情況下。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Google Shopping訴訟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此案件中,從競爭對手Foundem在2009年11月3日投訴至歐盟委員會至2017年6月27日作出決定,已過去了近8年,然而該案件還未得到最終裁決。歐盟委員會于2021年11月10日在歐洲法院獲勝,但歐洲法院(EuGH)有最終裁定權。相較而言,最近德國聯邦卡特爾局(das Bundeskartellamt)只用了約9個月便完成了對Amazon的訴訟程序。這證明實際可以快很多。兩個案件都是在“舊”反壟斷法基礎上進行且都是針對數字公司的,但為什么第一個案件花費了如此長的時間,而第二個案件進展如此之快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2022年的歐盟委員會和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權力和能力比2009年強得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Google Shopping訴訟案中,政治干預阻礙了Google和歐盟委員會之間達成一致的協議(盡管雙方都愿意達成),并迫使歐盟委員會在爭端中作出決定,而在沒有政治干預的情況下,Amazon和德國聯邦卡特爾局能夠尋求并找到一致的解決方案,這自然無需進行冗長的法庭審理程序。這表明,政治獨立對于快速的競爭保護是十分重要的。
盡管如此,應用權力濫用規定的確非常復雜,需要全面的經濟和法律分析。而且濫用行為往往也難以證明。這也適用于數字市場并且可能更為明顯,因為數字市場往往更加復雜。在一個“普通”的市場中,供應商和需求方面對面交易(如汽車經銷商和買家),而在數字市場中,多個市場頁面往往跨平臺聯網。如,在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統中,就有五個相互影響的市場頁面。盡管如此,2019年和2020年為德國聯邦經濟與氣候保護部(BMWK)以及歐盟委員會準備的多份科學報告認為,對現有反壟斷法進行適度調整、數字化賦能和加速就已足夠。然而,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和歐盟委員會試圖擴展其能力,并且政策制定者尋求對美國公司進行更大的干預,以改進德國和歐洲公司的競爭機會。因此,德國和歐盟制定了法律,對大型數字公司或者被認定為守門人(Torw?chter)的企業進行事前監管。在德國層面,這樣一項規定在2021年1月19日的第十次《反限制競爭法》修正案中成為法律,以第19a條的形式規定。在歐盟層面,《數字市場法》的最終文本已于2022年10月12日在官方公報上發布,并將于2023年5月2日起實施。鑒于這些規定的復雜性,本文在最后一部分將對這兩套法規進行概述性和批判性的比較分析。
四、題外話:并非總需適用反壟斷法
必須強調的是,反壟斷法并非解決數字(或其他)市場問題的“萬能藥(Allheilmittel)”。通常來說,其不適用于此目的,或者至少不如其他法律更為適用。這一點可以從德國聯邦卡特爾局正在審理的Facebook案件中看出,該案件主要涉及不當的一般商業條款與條件(AGB)以及數據保護違規行為。問題在于相較于適用反壟斷法,應首先適用一般商業條款與條件以及數據保護法。因為公民在面對任何公司時都會受到保護,防止一般商業條款與條件被濫用以及違反數據保護規定,而不僅僅針對守門人企業。然而,在此案或其他案件中仍然經常訴諸反壟斷法,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強大的執法機構,而其他標準(如一般商業條款與條件法律)的執行只能通過訴訟來實施。另一方面是依據反壟斷法可以對處罰對象施以高額罰款,在歐盟委員會提起的三起Google訴訟中,罰款金額總計高達82.5億歐元。
因此,在數字化領域各種錯綜復雜的新規定中,反壟斷法的持續調整只是微小的一部分。例如,歐盟已經發布或“正在制定”大量的法規,這些法規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數字市場。僅舉最重要的幾項:2018年歐盟頒布了關于個人數據保護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其中第20條就涉及關于數據可移植性的規定。同樣在2018年,歐盟頒布了關于非個人數據跨境流動的第2018/1807號規定。2018年還頒布了《歐洲電子通訊法》2018/1972號指令,其中包含了諸如即時通信程序和互操作性的規定,最近已經在新的《電信法》2021年版中得以實施。隨后歐盟在2022年還出臺了旨在促進跨境數據共享并規范中介機構的《數據治理法》(2022/868號規定),以及針對在線平臺內容規則的《數據服務法》(2022/2065號規定,DSA),即根據平臺的規模進行分級,旨在打擊所謂的“仇恨言論”或通過所謂的“暗模式(即互聯網陷阱)”對用戶進行誤導,該法案將于2024年2月17日起生效。然而,最重要的是上文已經提到的《數字市場法》已于2022年完成,其目的是限制互聯網守門人的經濟權力,并以類似于反壟斷法的方式確保市場的競爭性和公平性,盡管它在第10條和第11條的介紹條款中強調自身并非反壟斷法。除此之外,處在立法過程中的還包括有關在互聯網上進行數據收集的《電子隱私條例》,該條例將取代現有的“Cookie指令”2002/58號規定。它原計劃于2018年與GDPR一起頒布,但一再推遲。同樣的情形也適用于《數據法》和《人工智能法》,前者旨在為歐盟的數據訪問和使用制定通用規則,以確保數據互操作性并實現數據交易,后者旨在監管和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以保護公民,特別是在產品安全、歧視和數據安全方面。
這些法規并非總是相互協調的,甚至與各國現行的法規也不始終一致。對于大型企業而言,這無疑是麻煩且代價高昂的,但又是可行的。而對于律師來說,這甚至是好事,因為它為未來的咨詢需求和法律爭議開辟了一個黃金時代。然而,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初創公司可能會因此不敢進入市場,或最終被迫退出市場或被并購。一言以蔽之,過多的調控,雖然初衷旨在促進競爭,但最終可能反而導致更強的企業集權,從而減少競爭。
五、依照《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和《數字市場法》對守門人的監管
《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和《數字市場法》的新規定旨在解決上述事后應用反壟斷法而被認為緩慢且復雜的問題。一方面,通過對特定的“大型數字公司”作出并非在濫用行為得到證明后才會生效的規定,而是事先(事前)對這些公司進行“束縛”;另一方面,通過減輕舉證責任來簡化反壟斷機構的執法工作并提高執法效率。與此同時,這些法律希望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提高小型競爭者的競爭機會,尤其是對德國和歐洲的競爭者而言。通過這種方式,旨在促進市場競爭和市場公平。原則上,對此并不存在什么反對意見。然而,細節乃成敗的關鍵。
(一)依照《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1款和《數字市場法》第3條規定的守門人決議
首先必須確定的是新的事前規定的適用對象。兩部法律都對此作出了特定的規定并且都要求當局作出決定。兩者都規定可以通過行政行為來宣布公司成為標準的適用對象。這是可取的,因為企業需要法律上的確定性。然而,在德國法律和歐盟的《數字市場法》中,這方面的標準極為不同。
二者使用的相應術語也有所不同。《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1款提到了“具有顯著跨市場競爭影響的公司”,縮寫為?MB公司,而在德國聯邦卡特爾局(BKartA)被縮寫為“?müB”。在這方面,也可以稱之為“數字守門人”(正如《數字市場法》所稱),因為根據說明備忘錄的規定,其所指就是“大型數字集團企業”或者說白了就是美國的GAFAM公司。易言之,這是對大型數字互聯網平臺進行監管。為了回答“誰”的問題(譯者注:即規定的適用對象),《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列出了一些定性因素,作為可能表明“顯著跨市場競爭影響力(überragende marktübergreifende Bedeutung)”的指標,包括市場支配地位、財務實力、一體化、數據獲取和平臺實力。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必須調查這些要素。最終作出自由裁量的決定并發布一項行政行為,將某個公司定性為?MB公司,初始期限為5年。不出所料,《反限制競爭法》生效后的第一年,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就對Google、Amazon、Facebook和Apple發起了四起訴訟程序。Google早在2021年12月、Facebook(Meta)在2022年5月以及Amazon在2022年7月分別被劃定為?MB公司。而針對Apple的訴訟程序仍在進行中。
此外,根據《數字市場法》,由“某個政府機關”即歐盟委員會來決定誰是守門人,該決定有效期為三年。不同于《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數字市場法》第2條列出的“守門人”僅適用于特定的互聯網服務,即所謂的“核心平臺服務(zentrale Plattformdienste)”。第2條列舉的“核心平臺服務”包含了許多服務,包括在線中介服務、在線搜索引擎、社交網絡、視頻分享平臺、即時通訊服務、操作系統、網絡瀏覽器、虛擬助手、云計算和在線廣告等。籠統地說,幾乎涵蓋了GAFAM公司的所有業務。歐盟委員會與德國聯邦卡特爾局不同的是,如果提供此類核心平臺服務,歐盟委員會不一定要對“顯著跨市場影響力”進行全面的定性評估。其可以依據《數字市場法》的第3條第2款的規定,即若某家公司超過一定的定量門檻,即三年內在歐盟范圍內的營業額至少為75億歐元,或者市值至少為750億歐元(第3條第2款第a項),并且過去三年在歐盟范圍內每月至少有4500萬活躍的終端用戶以及每年1萬個活躍的商業客戶(第3條第2款第b項和第c項),則可以推定其為守門人。理論上,雖然被推定的守門人可以證明自己即使滿足這些標準仍不是守門人,但實際上要求相當高,在實踐中幾乎無法成功。
乍看之下,《數字市場法》比《反限制競爭法》提供了更多的法律確定性,因為其列出了涉及的服務并且具有明確的定量門檻。特別是對于小型服務提供商來說,它們很容易就能確定自己并不受《數字市場法》的規制。但是,這些標準有些過于粗糙。第一,《數字市場法》混淆了公司規模和“守門(Gatekeeping)”的概念。一旦某家公司規模足夠大,即使沒有明確指定它所守護的門,也會被宣布為守門人。第二,這些門檻標準對所有服務都是相同的,盡管4500萬月活躍用戶對搜索引擎來說幾乎不算什么,但對其他服務來說可能是很多的。第三,這些定量門檻標準并沒有基于任何經濟上的合理事實。它們純粹是政治協商的結果,與2020年12月的《數字市場法》草案相比,這些門檻標準還被提高了,可能是為了盡量少地涵蓋歐洲公司。
(二)依照《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2款和《數字市場法》第5、6和7條對守門人的監管
如果某家公司被首批行政行為宣布為守門人,會發生什么?在此,這兩部法規也顯示出相似性和差異性。雖然禁止目錄相似,但執法程序的設計卻是不同的。與反壟斷法使用靈活的一般條款不同的是,《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2款和《數字市場法》中包含了全面且部分極為詳細的要求與禁止目錄。就《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2款而言,就列舉了七項,其中一些通過不同的衍生和規則示例可以進一步加以細化:自我優待(第1項)以及在準入和采購市場中阻擾競爭者(第2項),“席卷”市場(das “Aufrollen” von M?rkten),即基于擁有優越的資源而通過快速的內部增長占領市場(第3項),通過使用數據阻礙競爭對手(第4項),拒絕或阻礙產品或服務互操作性和數據可移植性(第5項),向其他公司提供不充分的關于自身績效的信息(第6項),以及向市場合作伙伴“揩油(Anzapfen)”,即要求不合理的好處( 折扣或數據使用權)(第7項)。《數字市場法》的第5、6和7條甚至包含了約30條非常復雜的要求和限制條款,這些條款在某種程度上與前述目錄類似,在此就不詳細列舉。若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目錄是反壟斷機構的一種“精選列表”或“愿望清單(wünsch dir was)”,因為它們反映了德國聯邦卡特爾局或歐盟委員會大部分仍在進行的反壟斷程序中的觀點。例如,第19a條第1款(自我優待)顯然是受到歐盟委員會的Google Shopping案的啟發,而第4款(數據使用)則是受到德國聯邦卡特爾局的Facebook訴訟的啟發。幾乎所有的禁令都可以追溯到類似的起源,在《數字市場法》的背景下,這一點顯得更為明顯,因為它聲稱自己并非反壟斷法,而僅是對反壟斷法的補充法規。
這兩項法規中列舉出來的行為規則將在未來用于禁止守門人,且并不需要事先費力地證明它們濫用權力。初步聽上去不錯,但實際上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僅舉幾個例子:首先,雖然禁止自我優待符合歐盟委員會在Google Shopping訴訟中的觀點,但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其他領域一直宣稱此類自我優待符合競爭法。第一,最重要的是我們并非始終明確什么是“自我優待(Selbstbevorzugung)”。若我想獨自使用自己的數據或自己的服務器,這是一種應被禁止的自我優待嗎?Google的搜索算法對結果的排名不同于Bing,這是一種自我優待嗎,還是說僅僅是搜索引擎之間的競爭呢?第二,類似的問題也適用于“數據濫用(Datenmissbrauch)”:若我使用合法獲得的數據而不與競爭對手分享,我是否阻礙了競爭對手?那么后果將是什么?我是否必須共享這些數據呢?或者,我自己也不再被允許使用這些數據,即使這意味著我對用戶的服務會變得更糟?第三,在對互操作性有要求的情況下(如WhatsApp之類的即時通信服務)這種不明確性并未減弱:即使像WhatsApp這樣的即時通信服務能夠與其他即時通信服務實現“互操作性(interoperabel)”并實現多宿主(Multi-Homing),這就真的符合用戶利益嗎?從競爭的角度來看,這是矛盾的,因為一方面它可能導致競爭對手通過遵循市場領導者的規范而非通過創新來與之競爭,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垃圾郵件、惡意郵件和安全漏洞的風險,因為各方在此可能有必要就“最低限度共同標準(kleinstengemeinsame Nenner)”達成一致,并且在問題出現時可能無法迅速作出反應。這并非意味著在這方面不存在競爭問題,但它確實表明,不能僅僅通過制定明確的規則和禁令就簡單地“完全界定(wegdefinieren)”數字世界的真正復雜性,并且“不帶附加條款(ohne Wenn und Aber)”地約束守門人。
特別是在執行要求和禁止條款的問題上,《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和《數字市場法》存在顯著差異。《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2款不包含任何根據法律直接有效的禁令。因為該標準只是一個授權基礎,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可根據這些禁止目錄通過進一步的行政行為對?MB公司發布要求或禁令。這使得德國聯邦卡特爾局有機會根據具體情況做出適當調整措施,以避免過度監管或監管不足。然而,與傳統反壟斷法不同的是,德國聯邦卡特爾局不必證明?MB公司的違規行為。?MB公司只要觸及了這些行為,就會被認為是濫用。因此,舉證責任是顛倒的。這里適用的是“有罪推定(gesetzliche Schuldvermutung)”,?MB公司必須證明自己的清白。從憲法的角度來看,鑒于上述許多要求和禁令在競爭上的模棱兩可,這種舉證責任倒置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里涉及國家干預的問題,而國家必須根據憲法的一般規則證明國家干預的正當性,而非反過來要公司或者公民來證明。但根據《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第2款第2項,這些公司至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客觀地為他們的行為正當性加以辯護。
《數字市場法》展示了還可以比德國立法者在《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中做得更糟糕的情況。與《數字市場法》相比,《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是審慎和權衡的典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數字市場法》已經使用了一種“一刀切(Holzhammer)”的方法來定義守門人的地位,因為守門人的屬性僅僅是基于規模推斷出來的,甚至都沒有定義其所守的是什么門。不幸的是,《數字市場法》在要求和禁令的執行方面也延續了這種方法。其為了盡快實施,認為這些要求和禁令應該直接依法適用,易言之,它們應該是“自動執行的(self-executing)”的,并根據“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的方法適用于所有市場和所有守門人。換言之:所有的守門人都被“混為一談”而不顧及不同的產品、商業模式、市場以及實際市場競爭情況。若一家公司被宣布為守門人,它必須在六個月內履行《數字市場法》第5、6和7條的所有義務,并加以證明(《數字市場法》第3條第10款)。雖然歐盟委員會可以通過行政行為更為詳細地界定《數字市場法》第6條和第7條的要求和禁令,但這并不是必須的(《數字市場法》第8條)。這些公司亦不具備客觀地為自身行為進行辯護的可能性,也無法證明例如若不履行這些要求和禁令并不會限制競爭、創新和消費者福利,反而可能會促進它們。在法律上就已將“開脫或無罪證明(ist gesetzlich ausgeschlossen)”排除在外。即便按照法律執行將明顯不利于促進競爭以及提升消費者福利,公司也必須遵守這些規則。不過在極為例外的情況下可能得到豁免(《數字市場法》第9條),但這也只能適用于保衛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數字市場法》第10條)。簡言之,法律適用速度優先于法律適用質量以及對基本程序性權利的保障。這與數字經濟的復雜性是不協調的,在現實中,它也不會比德國的方法更快地產生影響,因為它引發的法律糾紛可能會持續多年,就像Google Shopping訴訟那樣。
六、結論
當《數字市場法》于2023年生效時,數字化的西方有消亡的威脅嗎?當然不會!對于那些對數字化和反壟斷法感興趣的人來說,好消息是,通過《反限制競爭法》第19a條,尤其是通過《數字市場法》,肯定會帶來新的一輪法律咨詢和解決權利爭端的需求。反壟斷專家將繼續是一種非常稀缺的高薪職業。
《數字市場法》是否會促進競爭,數字冠軍會不會在德國和歐洲涌現呢?也不太可能!因為德國或歐洲的巨頭無法通過“監管(herbeiregulieren)”而產生,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歐洲之所以尚未出現這樣的巨頭絕不是因缺乏監管,原因可能恰恰相反。
守門人監管本身可能非常有意義,甚至在某些領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監管不應該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應該量體裁衣。德國法律在這方面明顯比《數字市場法》更好地滿足了這一要求。
整件事情讓人想起一段描述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之間心態差異的妙語,它誕生于反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中,其中一個版本是:當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集結在戰場上對抗拿破侖時,局勢不利,普魯士將軍讓他的同事報告說:“情況很嚴重,但并不是沒有希望(Die Lage ist ernst, aber nicht hoffnungslos)。”奧地利人回答:“情況是沒希望了,但并不是很嚴重(Die Lage ist hoffnungslos, aber nicht ernst)。”歐盟委員會以普魯士的方式,將形勢描述為嚴重但并非沒有希望,并試圖通過《數字市場法》來應對。但這種情況更接近于奧地利式的“無望但并不嚴重”:因為試圖通過“監管方式(wegregulieren)”消除GAFAM公司或削弱它們的霸權似乎是一項相對無望的努力,只要終端用戶仍然偏愛它們的產品。
但正因如此,局勢也并不像一些人擔心的那樣嚴重,因為被認為是“守門人(Gatekeeper)”的公司后來也被證明是Snapchat、TikTok或Zoom等公司的“敲門人(Gateopener)”。這些新興公司能夠克服經濟上的重重險阻、實踐中的逆境以及政治上的悲觀,僅僅是因為它們比那些勢不可擋的、看似堅不可摧的“巨頭(Platzhirsche)”及其產品都更好。這就是競爭的真正意義所在。也本就應該是這樣的!
Google, Facebook & Co: The Power of Data and Algorithms 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Law
Abstract: The triumph of the interne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has enabled numerous new services and brought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consumer welfare. It has also created many new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es. However, concerns have arisen that some major digital companies and the algorithms they use could gain too much influence. These issues are being addressed worldwide through various laws. Potential competition problems are being tackled through antitrust and regulatory law. In Germany, the legislature revised the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 (GWB) twice (in 2017 and 2021) to better address digital markets and business models, with a focus on improved abuse control. At the European Union level, the legislature has opted for the regulation of digital gatekeepers through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DMA), which has been in effect since May 2, 2023, and sets out numerous prohibition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German regulations, especially § 19a of the GWB, with the DMA and critically evaluates both regulations.
Keywords: Internet; Algorithms;Digital Incumbents; Gatekeepers; Competition Law;German Act Against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