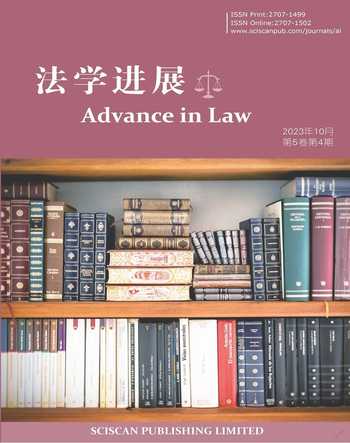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認定
滕媛媛?張貝貝
摘 要|2017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中正式確立了“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行政機關是否依法履行職責是行政公益訴訟中的爭執焦點。行政公益訴訟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認定標準,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分歧較大,需要建立認定標準,明確、整合。建立評判標準應當以我國司法實踐為基礎,要兼具靈活的特點,便于操作,便于判斷,便于鑒別,同時“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認定不能僅僅只從“行為論”或者“結果論”來考量,應當從更全面的角度綜合考量。
關鍵詞|公益訴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不依法履行職責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017年修訂的《行政訴訟法》中正式確立了“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第二十五條的第四款規定的內容中,對于行政機關的“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以及在檢察建議之后“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可見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階段分別存在于,一是行政機關本身在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情況下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這一階段的“不依法履行職責”;二是在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之后行政機關這一階段的“不依法履行職責”。
一、“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認定現狀
目前學者普遍認為“不依法履行職責”僅指第25條第四款的最后一句,也就是在提出“檢察建議”之后,行政機關的“不依法履行職責”,這一觀點是字面上的狹義解釋,筆者認為“不依法履行職責”這一表述應當作廣義解釋,即應當包括對于行政機關本身負有的監督管理職能不能夠依法履行的這一角度,也就是兩個階段抑或這一法律條文規定的全部過程都應適用這一表述。也有學者對于這一法條有兩個層面的理解,一是從行為角度分析,即只要“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有這一行為存在,就可以認定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二是從結果角度分析,因為該款表述了“致使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這一結果,所以認定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僅憑“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是不足夠的。但是結果角度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使得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
二、對“不依法履行職責”解讀的存疑之處
(一)“不依法履行職責”之“階段”
無論怎樣解讀,對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解讀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最初的法律文本。立法者的本意需要從文本出發來解讀,對于《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的構成要件需要做一定的分析。人民檢察院通過這一行為來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也即是對前文表述的“違法行使職權或不作為”進行的一種“糾正”,這一表述從邏輯上可見“依法履行職責”不僅僅說的是“檢察建議”之后的階段還包括了“檢察建議”之前的階段,因為在被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時。不難發現,其間是存在矛盾的,如果這一“不依法履行職責”解釋為“檢察建議”提出之前,在行政機關應當有所作為或者不作為時就做出嚴格限制,那么即是說檢察機關在存在“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時就可以判斷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那么第四款的結果要素又該當如何解釋?但如果將“不依法履行職責”解釋為“檢察建議”提出之后,那么檢察機關想要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去“糾正”行政機關的這種“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就存在著一種“滯后性”,這也令人懷疑是否為立法者的本意。
(二)“不依法履行職責”之“法”
對于“不依法履行職責”中的“法”也存在著一些爭議,有將其擴大解釋為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規章、上級命令等文件、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等,也有人將其解釋為僅限法律、法規。在行政機關的角度一定是希望最好將其做限縮解釋,不然行政機關面臨的被監督范圍會很廣。但是檢察機關的角度就更希望對其做擴大解釋,一方面可以全方位的保護生態環境,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在行使其職權時也更容易有更大的履職空間。其中擴大解釋中“法律”“法規”都是兩種解釋共同認可的,畢竟依法治國是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環境下最基本要遵循的原則,而對于規范性文件其中包括了一些內容行政機關可能為相對人設置了一些規范性內容,也即行政機關為自身的職責進行了細化,那么行政機關制定出來的合法的規范是具有一定法律約束力的,所以行政機關必須在規范有效期之內依照其設置的合法規范遵照執行。否則行政機關所作出的行政行為與其自身所做規范前后不一致,自己制定的標準自己卻不予以執行,難免會影響行政機關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筆者認為此處的“法”除了“法律”“法規”之外,還應當再向下有所延伸,比如“規章”,其中部門規章是國務院部門發布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對于地方行政權的規范重要性不言而喻,地方規章包括省政府和社區的市政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是地方政府為執行法律法規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制定的適用于本地方的規范性文件,約束與管理著整個省或市內,在省市層面規范的相關內容對于一個省一個市而言影響力較大,這一角度而言,即使是地方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各個行政相對人也應當按照規定執行,各個地方政府也必然應當依據自己制定的“規章”而嚴格執行。再比如其他規范性文件中的省市級制定的文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對行政相對人有一定的約束力,但是更低一級的區縣鄉鎮政府制定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便不適合列入該范圍,最低限度應當止步于此。所以筆者更傾向于將此處的“法”作一定程度的“擴大解釋”。這并非使行政權過于擴大,而相反這是擴大了檢察機關對行政機關履行監督管理職責的檢察機關監督權的擴大,這一層面上是有利于檢察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的,同時也利于地方行政機關嚴格執行相關規定。
(三)“不依法履行職責”之“結果”
環境的破壞不是一下子顯現出來的,是長久的不良破壞行為的堆積而最終爆發出來的,環境的修復也并非一下就能夠完成的,是長年累月的細心維護才能挽救回來的,甚至有些被破壞的環境面臨無法挽救的境地。所以,這里要討論的“損害結果”是一個無法明確或者無法估量的狀態,多數學者認為,有具體的事實損害才比較適合認定為“不履行法定職責”,但是筆者認為立法者關于任何“環境保護”的相關立法一定不僅僅站在事后的角度來考量,必定有著事前預防性的考量,因為自然環境的修復或者恢復不是說能修復就容易修復的,所以本文更傾向于該條法律條文在立法時對環境保護存在一定的“預防性”考量,而不僅僅是只站在“滯后性”的事后修復或恢復角度考慮的那么簡單。因此對于其構成要件的“結果”要素,還是不應當將其作為適用該條文的硬性要求。并且企業對于環境的破壞有可能有不符合標準的行為,但是這一行為未必立馬就能造成損害結果,結果也未必在行為作出之后就立馬產生,但是該行為確確實實是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的,這時也不可能單純地追求結果,用結果來說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不能等待結果發生時再采取行動,生態環境的修復并非一蹴而就,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其成本非常之高,代價非常之大。在我國風險社會防范階段的今天,一定是以預防為主的,所以本文更贊同從綜合角度來認定“不依法履行職責”。
三、《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4款的適用完善
認定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應當首先從正面考慮“依法履行職責”的行政機關是怎樣的依法履職情況。同時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正常行使職權是什么樣的情況,一個行政機關正常履行行政職責或者是順利履行行政職責需要有哪些方面的考量。其次再對照著正面從反面考慮“不依法履行職責”到底該如何判定。單一地從某個角度解讀《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4款的適用完善是容易出現許多漏洞的,甚至是邏輯上不能夠自洽出現問題。目前關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不依法履行職責”的判定還未有過較為明確的界定標準,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標準不一五花八門的認定,對于該款的具體適用與完善需要更深入全面的考量。
(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不同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有許多不同之處,前者是民告民的私人糾紛,后者是官告官客觀性的糾紛。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也因此要面臨著檢察權與行政權的碰撞,二者兩方的權利又必須把握好一定程度。否則,二者一旦失衡,如出現檢察機關的過于強勢的情形,很有可能會影響行政機關的“權威性”甚至行政機關今后在行使對社會的管理規范,所以檢方在這方面必須有所把握,一方面要履行監督職能,另一方面,檢察院在行使監督職能的過程中,還需要尊重行政權,否則行政機關在進行社會管理的時候,其權威性會大打折扣。檢察權與行政權之間的平衡需要有一定的把握,這對于檢察機關來說也是一個具有挑戰性意義的事情。
(二)適用《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4款時的考量
“不依法履行職責”條款設定的目的與初心必然是出于對公共環境以及生態的保護,對于前文提到的是否必須要等到“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行政機關才需要“履行法定職責”這一點從環境與生態保護的立法初心來看未必如此。因為環境的破壞與生態的破壞在更多時候是不容易一下就發現的,不是一種做了之后就立刻會發生的結果,并且一旦出現環境或者生態被破壞的結果,對于這種情況,如果按照侵害結果發生之后再去有所作為,那么對于環境及生態造成的侵害大多數都是不可逆的或者有更高的恢復成本,這對于環境的保護不是一種積極的方式。再者,“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早就已經深度認可,我們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應當是放在前列的,生態的修復是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其難度之高,成本之高,都是難以預料的,且能夠確定的是,環境的破壞對于全人類的發展都是絕無益處的,對于全體人類來說破壞掉生態環境帶來的不良后果都是無法預估的。由此可見,單純結果論來認定“不依法履行職責”不夠符合立法初心,也不符合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理念。
對于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職責的范圍,又需要進一步將其劃分為,監督層面和管理層面。行政機關的監督職責這里是指行政機關對于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等負有一定的監督職責,比如某一級政府對于當地的企業排污情況就負有一定的監督職責,監督是為了讓企業排污更加規范合理,企業排污的指標一旦超過規范的指標就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負擔,進而帶來的環境壓力是不可逆的,這一環節若是缺少行政機關的監督,企業本著逐利的心理必然會對生態環境進一步的消耗,以此換來一定的收益,殊不知,一時的收益對于整個生態環境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消耗,對一種不可再生資源的極大消耗。所以行政機關的監督職責是極其重要的存在,對于法律法規中規定了行政機關具體的監督范圍或者領域是必定要執行的,但是對于法律法規之外,比如各種地方規范里的內容又怎樣界定是否為行政機關必然要履行的法定監督職責?對于這一范圍的確定,應當考慮到其存在一定的公信力,對于相關的抽象行政行為一旦發布,必然會獲得群眾一定的信賴,如同行政機關制定的規則或者做出的承諾,行政機關需要對自己制定的規范負責,在合法的范圍之內,所承諾的內容也應當按照規定的內容真正落實。也即,對于行政機關是否真正的履行監督職責,不能僅僅考慮法律法規規定的內容,在適用時應當對其作出擴大解釋。否則行政機關在執行各種地方性規范文件按照名權責其所履職的范圍也是受限制的。行政機關的管理職責同樣也是對于行政相對人的管理,行政機關對于某一個體或者企業如其行為對生態環境產生了一定的損害,或者說企業應當配備相關的排污設備而其實際不具備,那么行政機關在日常檢查工作中就應當對其進行管理,要求企業或者是某一行業都要配備相關排污設施,例行日常檢查也是行政機關的一種管理職責。
“不依法履行職責”條款中的違法行使職權包括了幾種情況,行政機關對于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事項應當依法履行職責,但是現實情況中有許多樣態存在。如行政機關環境生態保護中有所作為,但是職責履行的程度并不夠,或者說在最初設定的期限之內并不足夠解決相關的問題,以至于最終并不能夠達到理想的效果,此時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理想效果,還需要考慮的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利現實情況中是否能夠真正地達到理想效果也即行政機關對于理想效果實現的現實可能性。其他的違法行使職權還包括如程序上或者實體法律依據上存在錯誤等,違法行使職權也包括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對于權力使用的越級等,如對生態環境具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不當的越級使用更高的權力去左右企業的排污等情況進而對生態環境造成不當影響與損害的,行政機關應當為其不依據相關法律規范履行職責而承擔相應責任。除此之外行政機關的不完全履行職責也屬于不依法履行職責,如現實中,某一企業的生產造成了環境污染,行政機關對其處以罰款加要求其對鎖造成的環境污染進行恢復,明明是兩種處罰,但是現實中的操作有許多僅僅對企業進行了罰款,形成了一種虎頭蛇尾的做事風格,最終對于真正需要修復的被污染環境進行了一種放任的姿態,那么行政機關這一處理行為就屬于不完全依法履行職責。現實中有許多行政機關只注重對企業的罰款,而不注重真正將生態環境保護落到實處,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易檢索到,較多的行政機關對于這一監督管理職責的履行都是不夠到位的,并沒有將“生態環境保護”的理念化為具體實踐。從而導致了現實中有許多企業在悄無聲息地慢慢吞噬著我們珍貴的良好生態環境,犧牲自然而獲得經濟上的收益,這里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作用正是其要發揮之處,但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便是檢察機關應當履行職責的重點了。行政機關的遲延履行也是一種典型的不依法履行職責的形態,但是這一遲延履行最終還需要綜合考量行政機關真正履行的現實可能性。
“不依法履行職責”條款中的不作為是行政機關明確的不履行法定職責,不作為的樣態同樣也會發生在檢查建議提出之前,即行政機關對于環境資源保護應當行使其職權進行監督管理時,行政機關選擇了消極的應對,甚至是不管不顧,或者視而不見,這種不作為也體現在現實中的“踢皮球”狀態,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將其應當處理的事項推諉至其他行政機關,或者對于已經產生的生態環境污染置之不理,都是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現實寫照。對于在檢察建議之后的行政機關不作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認定相對來說沒有提出檢察建議之前的這一階段那么被動,但是后一階段行政機關的現實操作的可能性此時要考量的比重應當更大。
四、結語
對于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的認定,“提出檢察建議”的前后階段中對于“不依法履行職責”的判斷,需要綜合多方面考量,并非簡單的“結果論”“行為論”就可能認定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這一制度的適用不應當僅僅解釋為字面意思,更加周全地認定需要綜合多種角度來考量,雖然目前相關法律規定并未做出很詳盡的指引,雖然實踐中的各種認定標準五花八門,但是基本上對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的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認定都是需要偏向于整體性考量的。
The Identification of “Not Performing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eng Yuanyuan Zhang Beibe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revised in 2017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and whether administrative organs perform their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is the focus of disputes in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in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at does not perform its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so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to be clear and integr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ging standard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ility, convenient operation, convenient judgment, convenient ident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termination of “not performing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can not on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from the “conduct theory” or “result theory”,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ailure to perform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