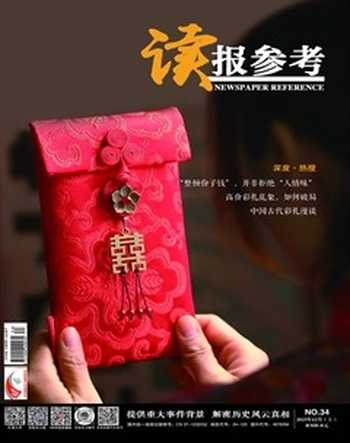國家數據局揭牌,把數據管起來
10月25日,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中設立的國家數據局正式揭牌。根據《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國家數據局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
數據局“招新”
雖然是剛剛正式揭牌,國家數據局的管理人員早已就位。
7月28日,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消息,任命劉烈宏為國家數據局首任局長。公開資料顯示,即將年滿55歲的劉烈宏是管理學博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他在信息通信領域擁有30多年工作經驗,2018年7月,自企業步入仕途,先后在中央網信辦、工信部任重要職務,2021年8月起執掌中國聯通,任董事長、黨組書記。此次履新國家數據局,是劉烈宏5年來的第4次職務調整。掌舵中國聯通期間,劉烈宏將“大數據”打造為中國聯通“主責主業”之一,而他在中央部委以及國有企業的履職經驗,也與國家數據局的職能密切相關。其后在10月11日,沈竹林被任命為國家數據局副局長。多年任職于國家發改委的他,長期關注數據領域,一直將數據看作經濟和戰略資源。
根據近期公布的《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4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招考簡章》,國家數據局已開始“招賢納士”。本輪國考中,國家數據局計劃招錄12人,要求基層最低工作年限為3年,崗位工作內容中的關鍵詞包括“數據治理和發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數據資源管理和開發利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等。
針對國家數據局的人才招聘,劉烈宏說,這次重點招錄既懂專業又懂行業的融合型人才。“圍繞數字中國建設、數字經濟發展,將招聘一些熟悉這類工作、具有良好專業背景、善于作規劃、有很強統籌協調能力、有工作經歷的公務員。”
基于這些人才,國家數據局未來的工作重點,劉烈宏同樣給出了明確方向。在接受央視專訪時,他表示:“接下? 來要加快推進國家數據局的運行,切實履行好我們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數字中國建設的職責。”
把數據管起來
數據常常被比作數字經濟時代的“石油”。早在2020年,中國就首次將其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寫入中央文件中,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
以數據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當今各國角力的重要領域,呈現出中、美、歐三極格局——根據網信辦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占 GDP比重提升至41.5%。
從黨的二十大,到去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又稱“數據二十條”),再到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都體現了中國對數據問題的重視。
但數據背后,蘊含著復雜的利益關系。比如,數據處理者與數據的內容主體之間、數據擁有者與數據生產者之間等,往往會涉及不同的利益。傳統的“所有權”式思路,已經對此種數字時代的產物“無能為力”,在全球范圍內也尚未形成成熟的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數據也可能涉及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利益——滴滴公司就曾因“存在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而被處人民幣80.26億元罰款。
事實上,全國許多省份或地市已成立專門負責數據管理工作的機構。據媒體報道,國內最早設立的大數據管理機構,是成立于2014年2月的廣東省大數據管理局。截至目前,在省級層面已有19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成立大數據管理局。
大數據管理局等專職機構的設立,表明各方充分認識到大數據的重要性。但同時,實際工作需要涉及大量跨部門協作,單憑基層發改委的力量,存在號召力不足的可能。
而在中央層面,長期以來,數據領域的管理體制是分散治理模式,由發改委、工信部、網信辦、國務院辦公廳、國安機關、公安機關等部門分工負責,難免會出現“九龍治水”的現象,導致監管效果有待改善。
多位專家學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都提到“統籌”的重要性,認為需要清除“數據孤島”和“數據煙囪”,打通數據壁壘,全國下“一盤棋”。
“我國是首個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的國家,數據要素化尚處起步探索階段,國際上亦無先例可循。”中國科學院院士梅宏說,“數據要素化在資產地位、權屬確權、流通交易、利益分配和安全隱私等方面存在諸多障礙。”
破除這些障礙,離不開國家數據局今后的推進。而當數據聚起來、動起來、用起來、活起來,一幅更新、更復雜,也更能代表未來趨勢的數字畫卷正徐徐展開。
(摘自《看天下》白嶄)